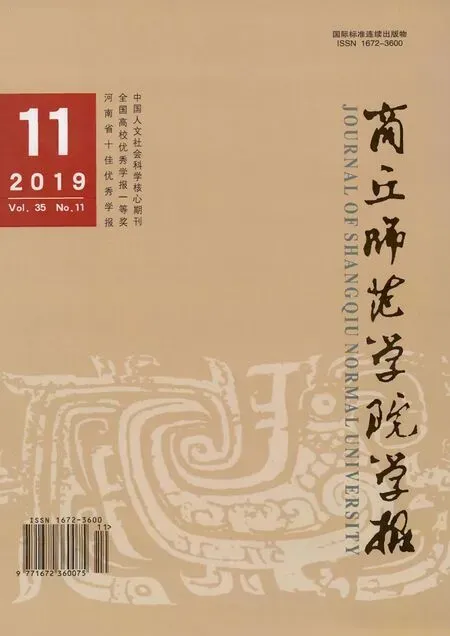伤怀与讥刺:《二子乘舟》中的亲亲之道新探
樊 智 宁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82)
《二子乘舟》是春秋时期在卫国被广泛传唱的民歌,记载于《诗经·国风·邶风》,亦是《邶风》的最末一篇。《二子乘舟》的篇幅较为简短,共分为两章,每章四句,诗文如下: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1]656-657
从字面上看,全诗描绘了诗作者送别“二子”远去的场景,其中“中心养养”与“不瑕有害”两句,使得诗作者依依不舍,心怀忧虑的情感跃然于纸上。
《诗经》作为儒家的“六经”之一,绝不能仅以文学作品的态度审视它的价值,解读它的内容。《诗经》中的诗文蕴含着超脱于文字所直接呈现在世人眼前的义理,其中的诗文往往关怀人们的日常伦理生活,《二子乘舟》亦不出其右。事实上,《二子乘舟》绝非简单的怀忧送别之诗,其诗文内容不仅影射了一段令后人唏嘘不已的历史,同时也包含着发人深省的家庭伦理意蕴。
一、同舟之祸:《二子乘舟》的悲剧始末
《二子乘舟》背后的历史真相不仅是围绕卫国储君之位的政治斗争,同时也是卫宣公家庭的悲剧,这一系列事件的始末记载于《史记·卫康叔世家》和《左传·桓公十六年》。卫宣公为太子时甚是爱慕自己的庶母夷姜,遂与夷姜有不正当的关系。卫宣公即位后立夷姜为夫人,生下了太子伋,并且让右公子作为太子之傅。卫宣公还向齐僖公求亲,齐僖公就将女儿宣姜许配给太子伋。但是,宣姜还未入室,卫宣公见她貌美,便自行纳取之。卫宣公与宣姜生下了两个孩子,即公子寿与公子朔,并且让左公子为公子寿和公子朔之傅。夷姜因失宠而自缢,卫宣公又改立宣姜为夫人。
卫宣公因为自己强夺了自己的儿媳,从而忌惮太子伋,夷姜死后便动了废长立幼的念头。宣姜在被立为夫人之后,便与公子朔共同构陷太子伋。卫宣公趁此机会亦向太子伋发难,令他到齐国去。卫宣公“与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2]1915。公子寿获知卫宣公的阴谋之后,在太子伋将行之时向其告密,劝阻太子伋去齐国。太子伋则言:“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1]3817遂毅然决然地前往齐国。公子寿见兄长危在旦夕,便在太子伋临行前将其灌醉,盗取他的白旄自行先乘舟前往齐国,在莘地遭遇卫宣公的埋伏,遇害身亡。待到太子伋酒醒,立即赶往莘地,见公子寿已然遇害,乃谓盗曰:“所当杀乃我也。”[2]1916遂也为盗所杀。
太子伋和公子寿遇害之后,卫宣公立公子朔为太子,次年即薨逝。公子朔即位为卫君,是为卫惠公。由于卫惠公参与了构陷太子伋,致使太子伋于公子寿死于非命,国人因此怨恨卫惠公。于是,在卫惠公即位后的第四年,卫国左公子洩和右公子职发动叛乱,将卫惠公驱逐出境,拥立太子伋的同母弟弟公子黔牟为新君。自此以后,卫国之地就兴起了《二子乘舟》之诗,纪念太子伋与公子寿两位异母同胞所经历的“同舟之祸”。
二、聚讼纷纭:《二子乘舟》的释义争论
结合《二子乘舟》的历史背景,自汉代以降的学者关于其所蕴含的义理就有不同的解释。个中的分歧,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中,便已初现端倪。
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齐诗》《鲁诗》和《韩诗》的注解是一致的,“三家诗”皆认为《二子乘舟》是一首伤怀之诗:
寿之母于朔谋,欲杀太子伋而立寿也,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沉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固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二子乘舟》之诗是也。[3]213
“三家诗”对《二子乘舟》的历史背景与《史记·卫康叔世家》和《左传·桓公十六年》相比,在细节上有一些差别。在义理方面,他们不仅仅认为《二子乘舟》是一首伤怀之诗,而且还认为此诗是太子伋的傅母所作。太子伋的傅母在太子伋乘舟将行之时,恐其为人所害,故而心生怜恤,伤怀而作此诗。
而作为古文经学的代表,《毛诗》则与“三家诗”的观点有所区别。《毛诗》在注解《二子乘舟》一诗时,认为《二子乘舟》在义理上的确是一首伤怀之诗,但并非太子伋傅母所作:
《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1]656
《毛诗》认为《二子乘舟》是卫人对太子伋与公子寿争相为死之事表达哀伤,故而作此诗以思念太子伋与公子寿。
《毛诗》与“三家诗”皆认为《二子乘舟》是伤怀之诗,但是在伤怀作诗的主体上产生了区别,这也就导致《二子乘舟》的义理产生了区别。按照《毛诗》的观点,《二子乘舟》为国人哀伤而思念太子伋于公子寿所作,这就表明此诗之义理所指向的是兄弟之情。“三家诗”认为《二子乘舟》是太子伋之傅母所作,这就意味着此诗之义理指向在于母子之情。
“三家诗”与《毛诗》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他们在“三家诗”和《毛诗》的基础上,对《二子乘舟》的义理有不同程度的发微。
清代学者王先谦、马瑞辰和魏源采纳“三家诗”之义,认为《二子乘舟》乃是太子伋之傅母所作。王先谦从《二子乘舟》背后的事件始末入手,认为“沉舟秘计,傅母知而不敢言……而寿有救伋之心,傅母必知之,故闵伋兼闵寿也”[3]214。在王先谦看来,《二子乘舟》不但是傅母怜恤太子伋之作,亦是她悯恤公子寿之作。马瑞辰则从《二子乘舟》的诗文入手,认为“首章‘中心养养’,二章‘不瑕有害’,皆二子未死以前恐其被害之词,非既死后追悼之词”[4]162。魏源在《诗古微》中将诗文分析与历史考据相结合,以《二子乘舟》叙事过程中所表达的情绪与相关历史文献进行对照,从而辨别其义理指向。他认为,“诗有‘乘舟’之文,则非待隘之役;曰‘泛泛其逝’,‘不瑕有害’;则非既死之词。诗作于事前,不能害诸水而后该谋害诸陆”[5]377-388,因此《二子乘舟》之诗乃太子伋傅母所作,这是断无可疑的,其义理指向亦当遵从“三家诗”之义。
孔颖达、欧阳修、苏辙和朱熹则采纳《毛诗》对《二子乘舟》义理的解释。孔颖达在其《毛诗正义》中就围绕《毛诗》中“二子争相为死”和“国人伤而思之”这两点作解释,其注疏曰:“二子争相为死,即首章二句是也。国人伤而思之,下二句是也。”[1]656孔颖达将《二子乘舟》的两个章节分别解释,首章“中心养养”是针对太子伋与公子寿相互为了保全对方而甘愿赴死,从而彼此心中感到忐忑不安;而二章“不瑕有害”则是国人对太子伋与公子寿“同舟之祸”的伤怀与惋惜。欧阳修在《诗本义》中则以司马迁《史记·卫康叔世家》所记载的历史文本为出发点,兼采《左传·桓公十六年》的相关内容,从而阐明《二子乘舟》乃“国人怜而哀其不幸,故诗人述其事以譬”[6]199。尽管欧阳修在探讨了太子伋与公子寿的具体言行之后,对二人颇有微词,认为他们的行为皆不合理,死亦不得其所,“二子”之行为实不可取。但总体而言,欧阳修还是支持《毛诗》之义。与欧阳修相似,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对此诗首章的注释中认为,此乃“国人伤其往而不反,泛泛然徒见其景。欲往救之而不可得,是以思之养养”[7]338。朱熹对《二子乘舟》之义理,亦作出“国人伤之,作是诗也”[8]41的判定。
此外,另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认为“三家诗”和《毛诗》在对《二子乘舟》的释义方面皆不得要领。在他们看来,《二子乘舟》实际上并非伤怀之诗,而是一首讥刺之诗,方玉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方玉润认为,《二子乘舟》实乃“讽卫伋寿以远行也”[9]151。太子伋拘泥小节,不通权变,一味地顺从父命,因而陷父亲于不义。公子寿亦不明孝道,与太子伋一样迂腐不化,最后他还与兄长同舟殉死,加重了父亲的罪愆。
当然,近代以来亦有陈子展重申《二子乘舟》乃太子伋傅母“闵伋、寿也”[10]130而作,但就其论证手段与阐发深度而言,并未超出古人的视阈。闻一多在《风诗类钞》中认为,此诗就其情感而言的确“似母念子之词”[11]530,但他的理解缺乏进一步的论证,未免显得过于片面。
综上所述,历史上各家的注疏对《二子乘舟》的义理解释各执一词,难以达成一致。但就其研究方法而言,亦有所片面。他们或是从诗文本身的内容出发,以训诂考据的方式作经学考证;或是从诗文背后的历史出发,以探究本末的方式作史学考证。诚然,尽管亦有魏源这样学者,兼采经学与史学二家之长,对《二子乘舟》所蕴含的义理作出阐释,然则魏源的注疏与诠释,最终还是囿于文字与词句上的训诂考据,最终还是走到了纯粹经学的道路。
三、外伤内刺:《二子乘舟》的义理再析
通过梳理历代学者对《二子乘舟》的义理阐发,能够发现的是,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上自汉代的“三家诗”和《毛诗》,下至唐、宋、清三代的《诗经》研究学者皆有所缺失。实际上,若要挖掘《二子乘舟》中的义理,探究孔子在其中的“大义”,需要通过经史合一的方式进行研究。
在对《二子乘舟》诗文本身的分析上,历代学者注疏考证已足够翔实,故而这里只略作分析,不加赘述。实际上,《二子乘舟》两章之诗,其核心在于“中心养养”与“不瑕有害”二句。所谓“中心”,即心中之意,“养养”者,即忧思之状也。所谓“不瑕”为疑虑之词,所疑虑者乃是“二子”此行将“有害”。显而易见,《二子乘舟》全诗所呈现出来的,是满怀着忧伤与不安的情绪。送别“二子”乘舟远去之人,所担忧的“有害”是什么?这是理解《二子乘舟》一诗的关键。其所担忧的“有害”,实际上并非太子伋与公子寿遇害这件事本身,而是他们此行遇害所导致的亲亲之道的崩溃。
质言之,《二子乘舟》乃是讥刺之诗,分别讥讽了卫宣公、太子伋与公子寿。卫宣公、太子伋与公子寿,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同舟之祸”这场悲剧中产生不同程度的“有害”,在父子之伦的层面上破坏了亲亲之道。
首当其冲的讥刺对象当属卫宣公。卫宣公在《诗经》中可谓被讥刺的常客,邶、鄘、卫三风中有大量的诗文明确地展现出对他的讥刺,其中《新台》一诗尤为重要。《新台》与《二子乘舟》同属于《邶风》,《新台》之诗的编撰顺序位于《二子乘舟》前一篇。不仅如此,这两首诗背后的历史亦密切相关。《新台》全诗共三章,每章四句。
新台有泚,河水弥弥。燕婉之求,蘧篨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篨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1]656
诗文通过“燕婉之求”与“蘧篨不鲜”“蘧篨不殄”和“得此戚施”作对比,在强烈的反差之下,表达了一种怨愤的控诉之情。所谓“燕婉”,是夫妇之间美好的生活的描绘,“蘧篨”与“戚施”皆是癞蛤蟆。诗中的女子本想嫁给一位如意郎君,不承想自己的丈夫却如癞蛤蟆一样丑陋无比。对《新台》一诗所蕴含的义理阐发,历代注疏均无异议。诗中的女子所暗喻的是宣姜,诗中的“蘧篨”与“戚施”则暗喻卫宣公,《新台》之诗则是讥刺卫宣公“筑台纳媳”之举。
孔子在整理《诗经》之时,不可能没有考虑到《新台》与《二子乘舟》之间的关联,两首诗所反映的内容,即《史记·卫康叔世家》和《左传·桓公十六年》所记载历史全貌。卫宣公先是忤逆人伦,强纳自己的儿媳。随后又违背礼制,立宣姜为夫人,这就破坏了夫妇之伦。在儒家看来,“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12]17。夫妇之伦位于父子之前,因此,孔子在编排《新台》与《二子乘舟》之时,不仅是依照时间顺序,还依照了人伦之序。卫宣公“筑台纳媳”破坏了夫妇之伦,又设计擅杀太子伋,进而又摧毁了父子之伦。《新台》讥刺了卫宣公“筑台纳媳”,随后的《二子乘舟》讥刺卫宣公擅杀太子,这样的解读不仅更符合孔子编排《诗经》的逻辑,也符合“同舟之祸”这段历史的全貌。由此可见,将《新台》与《二子乘舟》联系起来理解,不难发现在《二子乘舟》之诗中讥刺卫宣公的义理指向。
其次讥讽的对象则是太子伋。正是太子伋在明知出使齐国是父亲要除掉自己的圈套的情况下,不听劝阻,执意尊奉父亲的命令前去赴死,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换言之,《二子乘舟》所讥讽的,乃是太子伋的愚孝,使得卫宣公杀子之心付诸现实。司马迁在《史记·卫康叔世家》的文末,专门论述了卫宣公杀太子伋之事。
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2]1928
司马迁将太子伋与申生的遭遇作类比,认为太子伋与申生的过错是相同的,即唯恐忤逆父亲的意志而蒙上不孝的罪名,但实际上二人都陷父于不义。《春秋》对太子伋之见杀无明文记载,然则于申生之死则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公羊传》以“曷为直称晋侯以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1]4884一语进行解释。在《公羊传》看来,晋献公杀死了自己的世子,所以直呼称君,这是认为晋献公太过分。《谷梁传》的解释亦大体相同:“目晋侯,厈杀,恶晋侯也。”[1]5194“目晋侯”即直呼君名,“厈杀”即“斥杀”。《谷梁传》认为《春秋》此语乃罪责晋献公。由此可见,在《春秋》看来,国君擅杀世子乃是大恶。在春秋之时,国君的世子和同母弟是自身在血缘关系中贯行亲亲之道的两条纽带,即父子之伦与兄弟之伦。以父子之伦为例,如若国君擅杀世子,这就有悖于亲亲之道。而太子伋与申生的所作所为,使得他们的父亲杀子之意成为既定事实,这就将他们的父亲推到了破坏父子之伦、损毁亲亲之道的境地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春秋》之所以未记载太子伋之祸,仅书写申生受戮,其缘由在于《诗经》已然有《二子乘舟》之诗以刺其罪,不必再费笔墨复述之。而《诗经》并无诗文讥刺晋献公与申生之事,故而《春秋》大彰其恶。
其三,《二子乘舟》之诗还讥刺了公子寿。有学者认为,在“同舟之祸”这场悲剧的整个过程中,公子寿先劝谏太子伋不可落入陷阱,在得知太子伋去意已决之时,为保全其兄,争先赴死,最终也为盗所害。公子寿的行为不仅没有任何过错,其以死护兄的举动甚至彰显了悌道。此种观点看似合情合理,实则大谬不然。苏辙对公子寿替兄赴死之举的评价可谓鞭辟入里:
二子若避害而去之,于义非有瑕疵也。曷为不去哉?夫宣公将害伋,伋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而寿之死独何哉?无救于兄而重父之过。君子以为非义也。[7]338
苏辙认为,太子伋与公子寿若以逃避卫宣公的加害之由出逃,他们在道义上并非理亏。卫宣公欲加害太子伋之事明矣,太子伋掣肘于孝道不愿出逃,实是属于无奈之举,尚能理解。可是公子寿替兄赴死之举,并不能够挽救自己的兄长,甚至加重了父亲的罪过,这既不合于悌,也不合于孝。就悌道而言,公子寿在获悉卫宣公的阴谋后,前去告知太子伋真相,并对其进行了一番劝谏,这已经履行了自身的义务,实现了悌道。至于他替兄长赴死之举,则是过犹不及。就孝道而言,公子寿确信太子伋不违父命,坚决赴齐之时,当知太子伋必死无疑,卫宣公擅杀世子之恶亦不可规避。但公子寿却争先受戮,最终造成卫宣公杀害两位世子,罪加一等。公子寿此举,乃是违背孝道。由此可见,《二子乘舟》之诗并非同情和惋惜公子寿的悲壮举动,而是讥刺公子寿重父之过。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二子乘舟》这首诗表面上以母亲送别“二子”乘舟远去的场景表达忧虑哀伤之情,实际上讥刺了卫宣公授意杀子、太子伋陷父不义以及公子寿重父之过。《二子乘舟》所含义理之深,亦不似太子伋傅母所能作之,当是卫人假借太子伋傅母送别之语表达他们对亲亲之道将要崩坏的忧虑。春秋之世诸侯放恣,礼坏乐崩,卫国尤甚之。自卫宣公继位以来,荒淫无道,屡屡做出背弃人伦之举。卫宣公“筑台纳媳”,本就损毁了夫妇之伦,卫宣公、太子伋与公子寿的行为又进一步损毁了父子之伦。自此以后,卫国亲亲之道业已不存,其国祚亦不历三世,终为赤狄所灭。正如《二子乘舟》诗文中所言,母亲之所以“中心养养”与“不瑕有害”,是料知“二子”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卫人之所以“中心养养”与“不瑕有害”,是料知随着“二子”背影一同远去的,还有不再复返的礼乐文明。
四、亲亲之道:《二子乘舟》的伦理意蕴
伦理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来源于人的现实生活,这就意味着伦理思想必定又要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无论是何种学派的何部经典,无论其中的义理多么丰富和深刻,它也必须对人的现实生活有所关怀。将《二子乘舟》的义理置于人的现实生活的视域中,此诗揭示的便是关于亲亲之道的伦理意蕴。
《二子乘舟》所揭示亲亲之道的伦理意蕴,主要是关于父子之伦的层面。那么《二子乘舟》所讥刺卫宣公与两位公子的父子之伦,对于处理现代中国家庭关系问题有何损益?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
在儒家看来,正确的父子关系应当是父慈子孝,父母和子女都应当具有各自的德性。也就是说,要维系良好的家庭关系,儒家对父母和子女的德性都有所要求。毫无疑问,就卫宣公和太子伋的关系而言,卫宣公宠爱幼子,欲废长立幼,甚至不惜设伏杀死太子伋,这是违背其作为父亲所应当具有的德性的。那么需要讨论的是,太子伋在父亲失德的情况下,是否应当顺从父命。事实上,太子伋的行为并非儒家所倡导的孝。在儒家真正所倡导的父子关系,并非父母一方绝对凌驾于子女之上,子女也不必对父母之命毫无条件的顺从。
在《孔子家语》中,有一段“曾子耘瓜”的典故。曾子于田间耕瓜,误把瓜根耘断,其父曾皙大怒,遂持棍打晕了曾子。等到曾子复苏后,他询问曾皙是否因为动怒而身体不适,甚至一边抚琴一边颂歌,以表明自己身体无恙。孔子听闻此事之后严厉斥责了曾子:
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13]101
孔子以舜与其父瞽瞍之事告诫曾子。瞽瞍要使唤舜,舜总是在其身边;瞽瞍欲杀死舜,却怎么也找不着舜。瞽瞍轻轻地打舜,舜就在原地忍受;瞽瞍用大杖击打舜,舜便逃跑。如此一来,瞽瞍不会因丧失父亲的德性而获罪,舜也践行了孝道。然而曾子现在侍奉父亲则截然相反,他不惜自己的身体,执意承受父亲严厉的责打。如果曾皙失手杖毙了曾子,这实际上是陷父于不义,自己也违背了孝道。
回到《二子乘舟》之诗中,太子伋在获知卫宣公的阴谋之时,其最正确的行动应当是逃亡他国,而非拘泥于从父之命的小节。同样,公子寿亦应当协助太子伋并一同出奔,而非替太子伋赴死。太子伋与公子寿的愚孝行为,在伦理层面不仅将父亲杀子之意图便变为现实,坐实了卫宣公不父之罪,同时对于自身来说亦是被冠上不孝之名。
正所谓“亲爱利子谓之慈,反慈为嚣。子爱利亲谓之孝,反孝为孽”[14]303。儒家伦理中的父母与子女之关系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当父母不具备相应的德性,作为子女的一方绝不能任而听之,父母过度责罚子女之时亦不能委曲求全。父母也应当对子女采取尽量一视同仁的态度,不可有过分的偏爱。只有如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亲之道才能得以彰显。在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中,美好的生活是人民普遍的追求,中国人历来重视家庭生活,如何追求美好的家庭生活是重要的问题。《二子乘舟》一诗,以外在伤怀内含讥讽的方式,揭示了亲亲之道,这对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父子关系提供了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