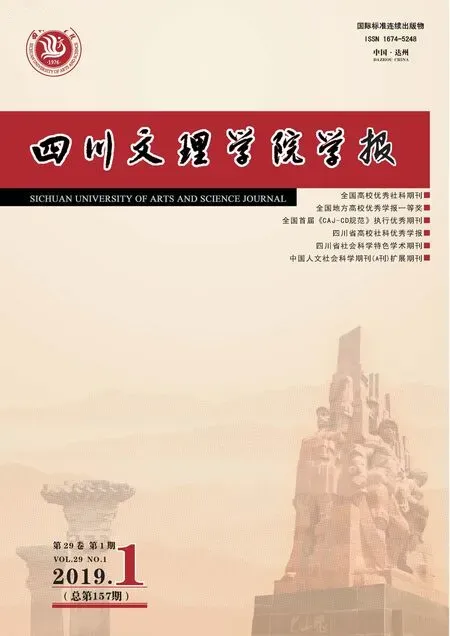汉赋文化意蕴特征与价值探析
冯英华
(1.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2.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文学院,新疆和田848000)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意味着,中国古代不同朝代都有各具特色的文学样式,如骚、赋、诗、词、曲等;也就是说,汉赋是汉代文学样式的典范之作,它以丰富的内容、鲜明的思想和独特的文化意蕴而受到后世读者或评论家的欢迎和喜爱。于是,汉赋作品蕴含着汉代的时代精神、文化价值和审美旨趣等不同内涵,使其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千百年来历久弥新”,[2]在这种意义上说,汉赋的魅力就是汉代文学的魅力。
一、汉赋文化意蕴特征
汉代文学魅力以汉赋作品为载体,其文化意蕴特征既具有儒家正统文化思想的光辉,还有汉代历史精神的丰富内涵。本文所谓“文化意蕴”指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现实性与道家文化之空灵缥缈审美性在汉赋作品中综合运用,产生诗化散文或散文化的诗,进而积淀成汉民族审美心理的组成部分。接着,汉赋文化意蕴特征主要表现为:文学现实性,汉赋作家用汉赋作品表达对国家统一、文化繁荣和社会稳定的理性思考;文学思想性,汉赋作家用汉赋作品抒发个人生命情感的不同体验,并构成社会、时代情绪的一部分部分;文学哲理性,汉赋作家用汉赋作品描写自然物的存在方式等。因此,汉赋作品中的现实性、思想性、哲理性形成文化意蕴特征体系,此体系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部分。
首先,文学现实性,汉赋作家用汉赋作品表达对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时代思想复杂内涵的理性思考,表现汉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与担当意识。此见于班固《西都赋》篇,“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旧德之名……故不能遍举也。”[3]114-115此对国家定都政治大事,进行理性思考、追问;文章借助于:西都宾和东都主人的辩论,汉帝国建都长安、洛阳之优劣比较,班固巧妙地表达对东都——洛阳的肯定、赞美之情,于是,“和帝大悦”。[3]79汉帝国定都不仅是最高统治者的事情,而且也关系到社会稳定、繁荣,还需要得到百姓的普遍认可、接受,这不仅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文化基础,而且也是专制下原始民主呈现的方式,源于汉代历史文化深处的汉赋以艺术或审美的形式予以表达。再如张衡《西京赋》与此情况类似,“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人,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与推移”。[3]143天子遵守自然规律,社会风谷习惯,顺天建制;设立都城,不仅是教化百姓的社会问题,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举措。此亦见于司马相如《畋猎》篇,载曰:“丞民乎农桑劝之以弗怠,使男女莫违,……醇洪鬯之德丰茂世之规,加劳三皇勗勤帝,不亦至乎?”[4]534-535于此处,司马相如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规谏帝王,劝农课桑 ,男女婚配,移风易俗,是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的基础,这也汉代社会君臣共同努力要实现的理想目标。汉赋作品表现出:汉代政治生活中伦理道德因素的重要性。有天地,成阴阳;有阴阳,别男女;有男女,成家庭;在家庭中,男女关系的中心表现为夫妇,五伦之中,夫妇为其首,这正如钱穆在《人生十论》中所说:“家的组织,有两个最重要的成分。首先第一是夫妇,没有夫妇怎么有家呢?所以中国人说,夫妇为五伦之始”,[5]这亦形成“家国同构”的文化现象。司马相如因汉赋创作而受到武帝喜欢,经杨得意推荐,改变命运;他也把汉赋作品当作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手段,他始终有着积极入世、关注现实、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因此,其汉赋作品“劝百风一,……曲终而奏雅”,[6]684司马相如开创汉赋参与政治生活之先河,此处汉赋文化意蕴特征是多样的,如政治、历史、社会、经济、伦理等,这亦是其崇尚阳刚之美表现,反映出汉赋文化价值判断与思想诉求,于是,汉赋文化意蕴的特征不仅是现实的,而且也是理想的,其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结合就赋予了汉赋作品持久的生命力,并进而为儒家思想经世致用、有稗于教化目标贡献出汉代智慧与力量。
其次,文学思想性,汉赋作家用汉赋作品抒发个人生命情感体验;接着,生活在汉代社会中的作家,把个人感情融入到社会情绪中,与社会情绪“异质同构”,共同建构汉赋文化意蕴特征的多维性。汉赋文化意蕴特征的多维性是汉代作家视野开阔、胸怀宽广、思维活跃的体现。如贾谊《鵩鸟赋》载:“三年,有鵩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7]788-789贾谊看到鵩鸟(猫头鹰)入室,感到不祥,恐惧灾祸将要来临,遂安慰自己,“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7]789-790“德人无累,知命不忧”。[7]795此处,人是自然人,鸟是社会鸟,人与鸟的精神、思想交流就可以置换为:灵魂与身体的对话;灵魂因身体羁绊而无法超越,身体因灵魂逃逸而空虚、无依,灵魂与身体分裂而产生痛苦。生命的本质即为痛苦,痛苦生命是由表象、意志构成的世界,表象、意志世界的本质是欲望;欲望是生命前进的动力,一个欲望满足后,下一个欲望就会接踵而至,往复无穷,生命的过程是一个又一个欲望完成的过程。生命有限,欲望无穷,有限之人与无限之欲望不断博弈,博弈必然带来痛苦,痛苦也是欲望的本质,痛苦的极端体验形式为死亡。人死亡是自然生命结束,但其文化生命可以永久存在。人存在的世界是有价值与意义的,我们在与他者——他性的关系中,确定——自我性,存在者不断以解蔽的方式言说、追求可以达到生命澄明境界的可能性和多样性,进而探索人类重返精神家园的现实性与超越性。又如班固《幽通赋》载,“惟天地之无穷兮,鲜生民之晦在”,[7]832“天地之无穷”与“生民”,一在天,一在地;一虚,一实,一高,一低;明显有着地上之人对自身生命存在本质的思考与追问,也有着“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建构努力。于是,不同的人(生民、作者、帝王、商人等)是汉赋文化意蕴特征体验的中心或重心,其体验可以分为:一般体验与极端体验,二者完美结合就能达到自我文化价值需要的实现。换言之,芸芸众生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形成乐生恶死的人生价值观。其实自然生命、社会生命与文化生命是交织、含混的状态,其生命历程从一个原点出发,经过循环、往复,再次回到原点。再次回到原点的生命与从原点出发的生命是不同的,其彰显出存在者不同存在的合理性。从生命的本质意义看,生与死是相对的,不仅只是自然生命,更有文化意蕴上的生命形式,其无目的而合目的,在生命的感性形式中积淀了理性的内容,形成其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意蕴特征。再如曹大家《东征赋》载,“历七邑而观览兮,遭巩县之多艰”[4]575“睹蒲城之丘墟兮”。[4]576汉赋作家经常以不同的方式走进社会、生活,感受底层百姓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进而触摸历史文化的脉搏,与百姓、时代、历史同呼吸、共命运。在汉代的社会生活中,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汉赋作家、作品关注的对象,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文明、文化的发展水平。“蒲城之丘墟”意味着曾经文明、文化的没落;同时,作者因遭到“巩县”人生旅程的艰难、艰辛和艰苦,体悟到人生存困境的多样性。她的汉赋作品文化意蕴之根源于历史、社会生活、民族精神的深厚土壤中,个人情感抒发因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而厚实、沉重,作家与她生活之时代精神、文化意蕴和审美风尚有机融为一体。
最后,文学哲理性,汉赋作家用汉赋作品描写自然物的存在方式。此在世界存在是人的存在,也是物的存在,更是人与物共同的存在。存在不仅表现文化意蕴特征,更传达出此在之存在价值与意义。如张衡《归田赋》载曰:“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頏,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7]888“归田”意味着对作者官场政治生活的厌倦,渴望回归自然;这不仅指自然界,也指精神的自由自在状态。文中自然之气清、原隰、王雎、鸧鹒等因作家描述、欣赏而充满灵性、灵气和灵动,自由自在之物与被束缚、限制之人形成对比,由此,张衡体悟到:人应该像物一样存在,与物一起思考,是多么重要。这不仅影响到陶渊明,而且宋人欧阳修还把自己的作品取名为《归田录》;明人瞿佑诗话又名曰《归田诗话》。此意味着,我们的身体需要回归自然,思想、精神亦需要回归自然。又如杨雄《长杨赋》,“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4]538目的在于:“纵禽兽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4]539即为了取乐,但此处却意味着,“是时农民不得收敛”,[4]539追逐快乐是人之本性,帝王寻欢逐乐方式或行为尤甚于常人,上述描写这些都是汉赋文化意蕴特征的现实性或残酷性;但作家深入思考的是:“我禽兽不知我亦获其王侯”,[4]552即社会之人以自然之物的性命,取得功名、富贵或荣耀。从本质上看,天地万物的性命是平等,这只是理想状态;社会、现实或历史中却处处以不同方式表明人优越于自然物,人或以智慧或以工具任意主宰或控制着自然物的存在形式,此谓之,人在物化的过程中,不断被遮蔽或“异化”,在不断“去蔽”或“反异化”的过程中,人之本性才能回归,回归到本真存在状态,这亦是对生命的热爱、敬畏。再如杨雄《甘泉赋》载曰:“荫西海与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蛟龙连蜷于东厓兮,白虎敦圉乎昆仑”,[4]448这里所表现自然之物,带有想象性,浪漫性,这些神奇、神秘之物,与天子息息相关,其文化意蕴特征为“人格的天(天志、天意)是依靠自然的天(阴阳、四时、五行)来呈现自己的”。[8]“天意”依靠自然来实现统治,也就是说,其超验性之威严来自“天意”,但需要在社会、政治中进行理性实践。此文化意蕴特征是先验性、超越性的。
于是,汉赋作家是汉代生活的参与者、时代精神的见证者与文化意蕴特征的思考者,他们把时代文学精神、生命情感体验、历史意识等以汉赋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积淀成中华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一部分。那么汉赋文化意蕴特征形成原因又是什么呢?
二、汉赋文化意蕴特征形成原因
汉赋文化意蕴特征形成原因主要为:内因和外因。“文体的变异,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9]具体而言,汉赋文化意蕴特征形成的“内在原因”指作家与其作品;“外在原因”指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有时候,“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
首先,汉赋作家及其作品是其文化意蕴特征形成的“内在原因”。汉赋作家是其文化意蕴特征的创造者,经典性汉赋作品也以无与伦比的魅力把作家留在文学史中;汉赋作家名家辈出,代有杰出之人才,如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班固、张衡、杨雄、王褒等人前后相继,不断努力,把汉赋创作推向顶峰。本于此,汉赋是源于汉代社会生活、历史文化、时代思想等的精神之花,其既有对先秦儒家正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补充,也有对道家文化的合理吸收。如“学而优则仕”[10]“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小之,故能为百谷王”。[11]汉赋作家作为汉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自觉承担起时代、国家、民族赋予的责任、使命,用汉赋记录文化生活的印记,表达对人生、人性的思考追问,在思考、追问中来实现超越。如司马相如《长门赋》载:“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金,为相如、文君取酒。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7]906此赋表明:汉赋是语言的艺术,在汉赋的语言世界里,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汉赋文化意蕴的魅力,而且还跳动着汉赋作家鲜活的个性;接着,司马相如《长门赋》以真情之语感动武帝,使备受冷落的阿娇又复得庞幸,不论此事真实与否,读者或批评家猎艳或好奇之文化心理得到满足。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7]906此赋表明:汉赋是语言的艺术,《长门赋》以真情之语感动武帝,使备受冷落的阿娇复得宠幸。再如司马迁虽以《史记》为后世赞赏,其实他《悲士不遇赋》也意味深长,书写在困境、厄运中一代知识分子对理想的执着、坚守。《汉书·艺文志》载曰:“司马迁赋8篇。”[12]43除汉赋作家创作个体外,汉赋文学作家创作群体也颇值得关注。《汉书·艺文志》收录“淮南王赋82篇,淮南王刘安群臣赋44篇”,[12]41“长沙王群臣赋3篇”;[12]44梁园也聚集了许多文学士人,如枚乘、邹阳等,他们之间相互唱和,留下诸多传世赋篇。汉赋作家个人或群体用毕生精力和心血追求国富民强的文化梦想,一代又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在守望人类文化家园中,文化生命得以延长,且官方及社会给予他们名声、地位,足以让他们青史留名。这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孔子便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他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浑厚关怀。”[13]这既是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精神的现实体现。在他们身上也寄托着作者的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如忧国忧民、兼济天下,这亦是汉赋作家人间现实情怀与理想浪漫追求的表现形式。因此。儒家文化执着于现实,佛家、道家文化具有超越性,儒家文化以人为本,执着于现实而苦难的人生、生活;佛家修身,佛家文化追求彼岸的浪漫、美好;道家养身,道家文化书写人间与天上的差异性,它们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追问人存在的本真状态,探寻什么样的人生是理想的、合理的。
其次,汉代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是汉赋文化意蕴特征形成的“外在原因”。有汉代国家,才有汉赋作家作品产生的文化土壤;汉帝国大一统带来政治上的凝聚力,文化上的向心力,且最高统治者提倡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汉赋应运而生,它强烈的国家统一意识、民族文化意蕴特征和审美旨趣,奏响汉代文化的最强音。此外,汉赋也可以为作家博取功名。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武帝有雄才大略,而颇尚儒术。即位后,丞相卫绾即请奏罢郡国所举贤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又以安车蒲轮征申公枚乘等;议立明堂,置五经博士。元光间亲策贤良,则董仲舒公、孙弘出焉。”[14]汉武帝时代诸多汉赋作家因此而获得施展文学才华的机会。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亦说:“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15]如果说武帝以武力缔造了政治上的汉帝国,那么,汉赋作家就以汉赋作品创造了文学理想王国,二者一明一暗,为后世留下民族文化精神高峰。本于此,开放、包容的汉赋作品蕴含着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再次,世界及文本是汉赋文化意蕴特征产生的土壤、载体,我们要关注其文化意蕴特征产生的文化、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等因素之作用,它是汉代文化、文学思想与审美等重要载体。每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都会产生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家及其作品,这些不同的作家或批评家分别以不同的方式阐释民族文化精髓的内涵,用他们敏感而多情的心灵感受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时代脉搏跳动的节律,他们在寻找自己梦想的同时融入时代气息与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特质,自觉或不自觉的以前一代的伟大作家为学习、模仿对象,同时用自己的言行及文本为后世作家及读者树立典范写作样式。
最后,“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相结合表现为:汉赋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继承”指汉赋文化意蕴特征对先秦文化、文学的学习、借鉴。先秦时期神话、诗歌、散文、寓言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层面为其提供思想资源,神话幻想与浪漫、诗歌节奏与韵律、散文语言自然与流畅、寓言犀利与深刻等皆是汉赋作家模仿的对象。楚地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人的作品直接影响汉赋创作。“发展”指汉赋作品不仅有先秦文学的外在形式,更有自己时代文化意蕴特征的内在精神。如从贾谊《鵩鸟赋》、枚乘《七发》到王褒《洞箫赋》等,对自然物与社会物的关注、思考,表现出汉赋作家求真务实的精神与审美风尚并重之情趣。此外,汉赋作家的作品,对于不同时代之评论家、读者既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其作品外在表现形式是相同的,内在文化意蕴特征阐释却是相异的。汉赋文化意蕴特征在阐释、相互阐释中不断丰富、完善。
从系统论角度看,作家、作品、读者与世界是一个完整系统不同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又相互启发,它们各自只有以合理的方式存在,才能发挥文化系统的作用,那么,汉赋文化意蕴特征的价值又有哪些呢?
三、汉赋文化意蕴特征的价值
汉赋文化意蕴特征“既是功利的,又是审美的、艺术的;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16]汉赋作家对汉代现实生活、时代精神、历史内涵等的书写及思考,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还是现实与理想的结合;现实与理想结合形成的文化意蕴特征价值表现为:汉赋作家用汉赋作品观察自然现象、思考社会生活、追问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汉赋文化意蕴特征价值上承先秦文学,下启魏、晋文学,具有“效果历史”性,它产生于历史文化中,又以自己的方式构成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积淀成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部分。
首先,汉赋作家用汉赋作品观察自然现象、思考社会生活、追问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如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6]684他指出司马相如汉赋作品中体现出理性批判精神,这亦是儒家正统文化所赋予知识分子的。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等含蓄委婉地提出,武帝要做传说中三皇五帝式贤明君主,于是,武帝幡然醒悟,改过不足,这亦是汉赋作家人间现实情怀的体现。对于汉赋作家而言,提升自身修养,才能成为民族崛起的脊梁。《孟子》载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17]于是,他们勤于修身、修心,齐家、齐国,治理好小家,才能胜任国家的治理,成为社会良知、正义的守护者。汉帝国强盛、民族发展和文化繁盛,关键在人才,为国家、社会选拔有用之才的帝王,如文帝、武帝等胸襟开阔,人格高洁,品质纯美,令后世文人羡慕不已。因此,汉赋文化意蕴价值就内化为知识分子创作的精神资源,他们以此进行观察自然、思考社会和追问人的存在,为的是既有助于汉代社会现实,也为后世树立为国为民的榜样。
其次,汉赋文化意蕴特征价值具有“效果历史”性,它产生于历史文化中,以自己的方式构成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汉赋作家及其作品,以善为起点,经过真的检验,到达美的境界;这既有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也没忽视审美旨趣追求。汉赋作家在寻梦过程中,融入中华民族文化意蕴的特质和汉代审美风尚。千百年后,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其作品中雄视百代文学的独特风采。
最后,从宏观的角度看,文化可以分为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但无论主流文化,还是非主流文化,其构成要素都离不开天、地、人、神等不同要素。人(汉赋作家)在地(条件与空间)下,以神(某种机遇)参悟天(道)的神秘性,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汉赋文化意蕴特征的价值是个体与群体价值观共同的体现,在传统中蕴含现代,如对现实的关心、对政治的热情、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文化的参与等,表明他们是汉赋文学的创作者,也是文化审美意蕴的实践者。拙作《明清话本小说中的清官形象研究》说:“人类学家指出,人类文化有大传统、小传统之分。大传统即是指一个社会的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主流文化,这是经过思想家、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家等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18]因此,大传统的主流文化主要指主流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创造的文化,这也是以显性方式存在的文化,它有着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性、引导性,它以时间性为基础,以道德性为内核,时间性提供文化意蕴活动的场域,道德性形成真理性标准,时间性支持道德性,道德性保证时间性,道德性与时间性结合就形成其超越时空的独特魅力。[19]
综上所述,“汉赋见证了我们民族童年时期天真浪漫的梦想,也目睹大汉帝国的显赫声威,它还将预见了我们民族的文学之花开得更灿烂。汉赋是无愧于时代、民族和国家的一代鸿文,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和魅力!”[20]汉赋文化意蕴的特征与价值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之精神资源,它的明天会更加辉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