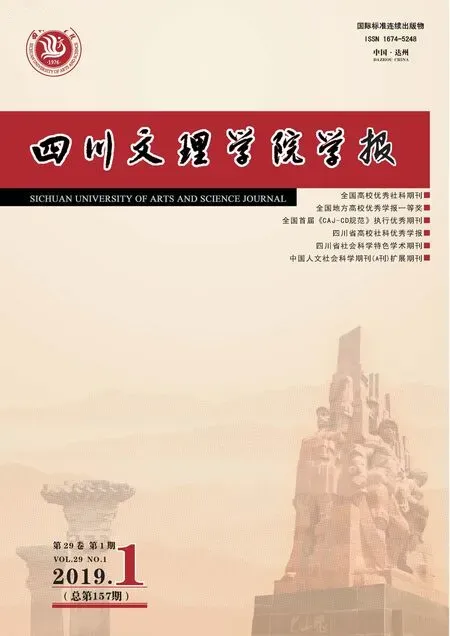川陕苏区时期经济政策与经济工作的特点分析
毕瑛涛
(中共达州市委党校,四川达州635000)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红色区域,川陕革命根据地其自身历史并不长,但其历史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红军有很多很大的作为影响深远,也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热点。本文拟讨论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经济政策方面的若干特点。
众所周知,川陕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时间只有两年多,事实上是短暂的。其任务无疑以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设为主。除此之外,川陕革命根据地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社会建设、医疗卫生、工会工作、妇女工作、共青团工作、少年儿童工作等等,经济工作也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令人颇感意外和兴趣的是,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苏区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构想和规定,跨越了时空,在今天研判起来,仍然具有强烈的时代价值,对当今时代的许多方面仍然能够引发人们一定的思考,这也是本文讨论的出发点。
一、经济政策定位明确
经济政策是经济建设的灵魂和核心,也是开展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前提。囿于历史时期的不同,执政者常常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确认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化的现象。众所周知,1942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当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阐明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同样,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实行武装斗争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其经济政策也必然具有强烈的时代印记。1933年8月1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川陕省苏维埃经济政策》,其中对自身经济政策作出了明确的定位:“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政策,应该建筑在严格的估计目前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的条件之上。一切经济的设施,应该无条件隶属于争取全国工农革命的民权独裁的基本任务之下。……苏维埃区域内一切经济的设施,应该根据工人阶级与农民联合的利益观点,根据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的观点来检阅。……这是正确的经济政策必要的前提”。[2]125
川陕苏区政府的这个经济政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一是提出和使用了“民权革命阶段”和“民权独裁”的概念。显然,这个概念的提出与使用,体现了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使用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思维惯性,它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就是推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革命。当然在194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成熟,将此表述并且固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以夺取政权为核心的政治斗争是唯一目的,一切工作必然必须围绕核心目标开展,川陕苏区的经济政策自然难以违背这一特点。二是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工人阶级与农民联合”“革命联盟”等概念,实际上表达的是经济政策中的领导权问题。土地革命战争也是战争,战争本身就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阶段,在这个特殊阶段中,实现完全化的市场经济或者商品经济,几乎没有可能性。因此,川陕苏区时期的经济政策必然必须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色彩,必然必须牢牢地把握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同样观察,在当前,执政党把握对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具有历史依据和历史经验支撑。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差异性是明显的。三是“根据工人阶级与农民联合的利益观点,根据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的观点来检阅”经济工作。这个观点,充分体现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体现了中共的执政者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阶段对人民群众利益的极大关注。
二、经济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职责明确
一般而言,经济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职责,自然会折射出执政者的经济政策理念,川陕苏区时期也不例外。1933年7月19日,红30军翻印了《川陕苏区苏维埃各部委员工作》,对“经济委员的工作”明确为:“(一)管理区苏的收入和支出,并计划集中经济。(二)所有收入款项一律交上级,按月向上级做收入和支付的报告,并将每月预算交上级审查,以便整个经济分配。(三)调查当地经济状况及来源及群众生活情形报上级。(四)实行苏维埃政府所规定统一累进税则,按本区情形实行征收。(五)办理工农银行兑换处”。[2]115《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指出:“苏维埃要集中经济,作有计划的运用,发展经济公社,并宣传群众合股来办合作社。”[2]53
从上述“规定”和文件中可以分析出几个特点。一是高度的计划经济。使用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只能根据所处的具体情况而定。鉴于川陕苏区时期处于高度军事化状态,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对于川陕苏区属于必然。川陕革命根据地辖区所处的川陕交界处广袤的农村,呈现高度自然经济状态的,本身生产力极为不发达,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只能是一种必然、被迫和无奈的选择。事实上没有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作为基础作为保障,红军和川陕苏区要追求军事斗争的胜利,是不可以想象的。二是十分注意关注群众生活状况。将“群众生活状况”作为经济委员的工作职责加以确认,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属性,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执政基础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虽然中共的“群众路线”是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但是在川陕苏区时期党和红军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可以看到端倪。三是以预算管理方法管理经济。现代的预算管理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1922年美国人麦西金在《预算控制》一书中从控制的角度,详细地介绍了预算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标志着现代预算管理理论的完全形成。应当说在川陕苏区时期就提出和使用预算管理的方法,无疑体现了当时中共和红军理念的前瞻性和时代性,体现了红军和川陕苏区执政者对先进生产关系理论的引入和实践,值得历史的肯定。
三、发展合作社运动
现代合作社本身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红军在川陕苏区时期大力引入和使用“合作社”生产方式,自然体现了执政者思想理念的前瞻和目光远大深邃。在川陕省《经济委员的工作》文件中的第6条明确规定:“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办理消费合作社、经济公社、生产合作社等事宜;奖励对外贸易,保护从白区来遵守苏维埃法令的商人。”[2]53在川陕省《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中明确提出:“发展合作社运动”,“党和苏维埃要用极大力量来推广合作社运动”,“加入合作社一定要农民自愿,反对强迫。要用实在的利益来引诱农民大批的加入合作社。应到处宣传合作社的好处”,“合作社要成为群众运动,群众自动到处成立各种各样的合作社(特别多多成立粮食盐布合作社),由群众自己推举经理,群众自己经营。……各县要大大的扩大合作社运动,要高山老林到处都有群众的合作社,……要依靠广大群众得到利益,自动热心来办,要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才能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2]333这些规定,一方面体现了执政者理念的先进,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功,对红军发展、根据地建设、苏区军事斗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同时,合作社本身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一种手段。在川陕苏区时期使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在今天看来,不能不佩服、不能不赞叹当年这些革命先辈的眼光和胆识。这些眼光、胆识对于当前时代中国社会推动改革的不断深化,无疑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四、重视税收工作与税种的建立健全
任何一个政权的存在,离不开相应的经济基础。川陕苏区时期的政权也同样如此。1933年夏,《川陕省苏维埃经济政策》中指出:“必须根据累进税的原则,制定简单的明显的税收制度。”[2]127在同年制定的《税务条例(草案)》中规定:“本局执行中央累进税率,……故命名为川陕省工农税务局”,“全省设总局一所;各县设分局一所;县所属之各场市,斟酌繁简,得设税务分局若干(如市镇交通繁盛,地域广阔,可增设分局)。各县所属之场市税务分所,直属该县税务分局;各县分局直属总局”。[2]205关于税目种类,“条例(草案)”规定:分为4类。甲类为特种税,包括白木耳、鸦片烟、屠宰三类;乙类为营业税;丙类为人口税,规定“纸烟、酒、旱烟、水烟、花粉、香水以及非工农必需品,皆得从值百抽五起,以至百分之十为止”,“盐、布疋、棉花、粮食、中西药材、耕牛、小猪、洋油、生发油等,皆得免税”。丁类为出口税,规定“粮食、布疋、棉花、中西药材、耕牛、小猪、盐等,皆得从值百抽二十起,以至值百抽五十为止。必要时,苏维埃政府得禁止出境”,“茶叶、锅、煤炭、木耳、木料、鸦片等皆得免税”。[2]205-206此外,还规定,“本局印制连三批单(存根二条,执照一条),数字印花(几分、几角、几元),纳税人必保存执照,丙执照上所贴之印花,以凭考核检验”,“非经本局指派负责人员,无论何人不得代征代收”,“凡税务机关所设之地,当地苏维埃政府机关得监督税务人员徇私舞弊”。[2]206
在上述各项规定中,可以剖析出几个特点。一是税务机关的设置对整个川陕苏区的全覆盖。川陕苏区的执政者们十分清楚,税务机关是一个政权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政权组织都离不开税务机关的支撑。税务机构的设立和存在,体现的是一个政权组织建设的稳固性与稳定性。[7]这种机构的设置必须是全覆盖无缝隙,必须是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和细枝末节。遵循这一客观规律,显示了川陕苏区红军和执政者的一种执政修养。二是税务种类基本齐全。川陕苏区执政者和红军对税务种类的设置设立,体现了对当时川陕苏区生产力状况的充分把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工农武装割据”区域,无一例外地都是远离中国生产力发达区域,都是总体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因此红色政权在设立设置税务种类时,只能依据所处的区域生产力状况来决定。川陕苏区政府曾经大力实行了戒烟禁烟运动。其实,仅仅是为了红军兵源的补充,也必须实行戒烟禁烟。据张国焘回忆:红军入川后“补充新的人力是我军一项极重要的工作,我军原来没有一个吸鸦片的,在意识上也反对吸烟,我们素来也拒绝任何一个烟瘾者进入我们的军队。但在此地却找不出一个不吸烟的壮丁来补充。虽有不少当地壮丁要求参加我军,但我们却难于接纳。一般战士认为在这里不能扩大红军,如果勉强把这些烟鬼引进来,会降低红军的素质”。[3]但是,川陕苏区政府又开征了鸦片税。可以说这是无奈之举,学术界为此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三是实行累进制。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举措,一般来说对解决社会财富分配均衡与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设置这个税种,体现了川陕苏区红军和执政者的前瞻性意识。当然,设置这个税种也有一定政治性思考。川陕省《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中明确提出:“统一累进税,是我们的阶级税收政策。”[2]334四是税务征收管理制度完备。这些相关的管理制度,尤其是对川陕苏区和根据地税务工作人员的监督制度,对今天中共的党风廉政建设具有明显的借鉴作用。
五、允许一定条件下的商业贸易和市场经济活动
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进程中,小农经济与小商品经济一直相安无事地发展进行着。在川陕苏区,红军和执政者继续顺应着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特征。1933年3月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印发了《经济政策(草案)》,其中指出:“苏维埃政府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保障苏维埃区域商业贸易”。[2]46同年7月,在川陕省苏维埃公布的《川陕省苏维埃经济政策》中明确规定“苏维埃政府应该保证商业的自由,不妨碍商品市场的关系,这是一般的规律”。关于商品的价格,苏维埃政府“只应当在极度需要的时期之内”,“规定最高价格”,“一有可能,便应该恢复商业的自由”。[2]126川陕省《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明确提出:“奖励开发各种工厂与企业,欢迎自由投资,苏区、白区各种资本可以自由经营。在严守苏维埃的法令之下可以允许商店工厂自由经营而且加以保护。”[2]334在《川陕苏维埃政府布告——苏区营业条例》的第一条明确规定:“苏维埃政府对于遵守苏维埃法令的中小商人,均准其商业上的自由,并予以苏维埃法律的保证。”[2]416
令人感兴趣的是,当年的川陕苏区政府一方面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又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商品贸易活动,这是一种事实上有些自相矛盾的举措。众所周知,商品经济虽然是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但是本质上还是市场经济性质的。自然经济以满足自我消费为生产目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以追求价值规律为本质,二者差异化明显。在一个执政区域内,实行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形态,本身就是一种特殊意义。当然可以肯定地讲,川陕苏区时期的商品经济其市场分额、比重、容量、交易量、价格尺度等等都是十分有限的和初级的。[8]然而这种貌似矛盾的格局,其本质属性反映的是一种务实的精神,体现的是一种求实的理念。须知道,在当年以激烈的军事化斗争为主的时代,在所治辖的区域内能够实现和开展一丝丝商品经济,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为此,川陕苏区时期为政者的这个群体,其理念、智慧、方式方法、手段等,无不令后人肃然起敬,并从其历史实践中获得了许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