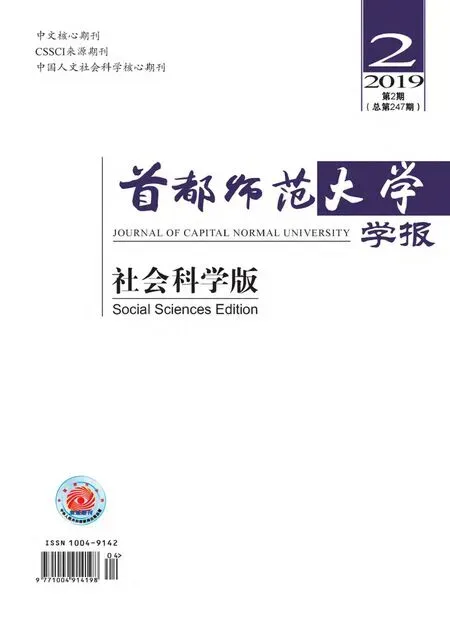杜勃罗留波夫:文学社会学批评的现实之维
王志耕
女作家巴纳耶娃在她的回忆录中曾回忆到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杂志决裂的情形,主要是因为屠格涅夫不满杂志发表了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其中记述了她与屠格涅夫的一段对话:
“我觉得奇怪,”屠格涅夫反驳道,“你怎么看不出杜勃罗留波夫有个大缺点,还把他跟别林斯基相比!别林斯基在对艺术性的理解上有一种天才,他对一切美的事物有一种天生的鉴别力,杜勃罗留波夫却处处表现出冷淡和偏颇!别林斯基用他的文章促进了人的美感,使人向往一切崇高的美!……我跟杜勃罗留波夫谈话的时候,甚至对他暗示过他有这个缺点,我相信他会注意到的。”
“屠格涅夫,你忘了现在并不是别林斯基那个时代。现在需要向读者说明社会问题,而且我完全不赞同你认为杜勃罗留波夫不懂诗歌这个意见;如果说他在文章中过于强调社会的道德方面,那末你自己也该承认这是必要的,因为这方面太薄弱,很不稳固,连我们这些代表人物都是如此,更不用说群众了。”[注][俄]巴纳耶娃:《巴纳耶娃回忆录》,蒋路、凌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这段话其实应当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那就是,时代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文学艺术的立场也应当相应地做出改变。这种改变在杜勃罗留波夫这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人民性理解的问题,二是如何让文学更切近地参与到现实社会的巨大变革之中去。而以往我们都是把别、车、杜相提并论,笼统地将其归于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批评,而忽略了其间的内在差异。澄清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在学理层面上更好地理解俄国文学社会学批评的学术真义。
一
别林斯基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论述过人民性问题的思想家。但别林斯基时代对于人民性的理解是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论争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他经常是把“人民性”(народный)和“民族性”(национальный)交叉在一起论述的,尽管他也对两者的差别做过区分。[注]参见[俄]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别林斯基选集》,第4卷,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365页:“‘民族的’(национальный)这个词,在意义上说来,比‘人民的’(народный)还要宽广些。‘人民的’通常指的是人民大众、国家的最低、最基本的阶层。‘民族的’指的是组成国家机体的全体人民,全体等级,包括从最低的到最高的在内。”俄文原文参见В. Белинский, Сочинени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Пушкина //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амах, т. 7,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5, с. 333.那时他更看重的是如何理解在俄罗斯民族意义上的人民性,其参照系是西欧的民族性。因此,他反对把“人民性”理解为对底层民众的抽象,而是主张民族性的超阶层性。也就是说,“人民性”包括在不同的阶层的生活方式之中,而不仅是指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身上才有人民性。但当时的某些斯拉夫主义者认为,只有那些描写了农夫、农妇、满脸胡子碴的商人和小市民,或者描写了谈话中夹杂着俄国俗词俚语的人物的作品,才算是有人民性。他指责当时的伪浪漫主义流派“喜欢用‘人民性’字样,主张不仅在长诗和戏剧中描写下层社会的正直人,并且甚至还描写小偷和骗子,它设想真正的民族性仅仅包藏在粗服和烟熏的茅舍里,描写以喝醉酒的仆人在一场斗殴中打破了鼻子,这才是真正的莎士比亚笔法”[注][俄]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别林斯基选集》,第4卷,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530页。。相反,一旦文学作品出现了描写现代文明生活的情节,就被说成是背离了俄罗斯的人民性:“许久以来在我们的头脑里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意见盘踞着,以为穿燕尾服的俄国男人或者穿紧身胸衣的俄国女人就已经不是俄国人,俄国精神只能求之于粗饭、草鞋、劣等酒和酸白菜。在这场合,甚至许多所谓有教养的人也不自觉地跟俄国平民老百姓采取同样的见解,那些人是喜欢把每一个从欧洲来的外国人都称为德国人的。这便是担心我们大家都将日耳曼化的无谓恐惧的根源!”[注][俄]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别林斯基选集》,第4卷,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页。别林斯基是在评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时说这番话的,是因为当时有人指责这部作品描写的人物带有西欧色彩,而在别林斯基看来这并不妨碍作品描写了真正的俄罗斯精神,更何况别林斯基的内心声音就是要俄国走向欧洲的现代文明。所以,他认为如果不是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俄国的军队还可能是一群乌合之众;跟别的民族接触就担心可能失去自身的民族性,这才是对民族性的“污蔑”[注][俄]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别林斯基选集》,第4卷,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527页。。
所以,别林斯基主张的人民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性”,是相对于开放和文明的欧洲而言的俄罗斯民族性。这一主张的意义在于,要让俄罗斯人民意识到,真正的民族性建构需要采取开放的态度,将俄罗斯传统精神与现代文明结合起来,俄国才会找到合适的出路。
但是,到了杜勃罗留波夫时代,即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俄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随着废除农奴制成为整个社会矛盾的焦点,当年面对欧洲的俄罗斯民族性问题被搁置了,而俄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成为新的焦点。杜勃罗留波夫的“人民性”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或者明确一点说,在杜勃罗留波夫这里,所谓“人民性”中的人民的底层意味被突出出来了,而其中的民族性意味被相对遮蔽。这也缘于杜勃罗留波夫的自觉的下层阶级立场。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的神甫家庭,这在俄国是比较典型的平民家庭,接受的教育也是在教会学校里完成的,而不是读贵族的专门学校。这也是他一直被称呼为“教会中学生”的原因,这个词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被视为没有教养的同义词,即使是《现代人》同仁圈子里的知识分子也这样称呼他和同样出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后来与屠格涅夫决裂也有同样的原因,后者的贵族身份和显赫的教育背景,使他对前者一直持居高临下的态度,虽然这也缘于当时的杜勃罗留波夫还年轻,1860年的时候他还只有24岁,但自觉的下层阶级意识,让他对屠格涅夫的贵族气派十分敏感,尽管他对后者的创作一直持肯定态度。
当年别林斯基在评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曾盛赞这部作品对人民性的表现,然而在杜勃罗留波夫这里,按照他的标准,普希金的“人民性”就不是完整的人民性了,尽管普希金比起18世纪那些诗人来已经对俄国的社会生活有了广泛的反映,但更多地仍然局限于对上层阶级的描写。比如,他创作了奥涅金这样的典型形象,这个形象固然是那个时代的反映,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奥涅金所在阶级的特征的出色描写,然而,这样的人物毕竟只是少数,或者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他不能代表“人民”。“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的水平,丢弃等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切质朴的感情,——这在普希金却是不够的。他的家谱学上的偏见,他的享乐主义的倾向,他在上世纪末法国逃亡者所教导下的基础教育,他的充满艺术的感受力、但和顽强的思想活动却格格不入的天性,——这一切都阻碍他去渗透俄国人民性的精神。不仅如此,——他还嫌恶那些从民间搬移到那个包围着普希金的人群里去的人民性的表现”[注][俄]杜勃罗留波夫:《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页。。
而杜勃罗留波夫强调的人民性则指的是那些生活在农奴制压迫之下的普通民众的意愿和精神。当然,杜勃罗留波夫这里谈的已不是对人民性的表现,而是引导和改造。也就是说,既要描写普通民众的愚昧的一面,也要揭示他们身上所潜藏的为改变自身命运的斗争的力量。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描写“平民”(простонародье),而不是贵族和有教养(образованный)阶层。因此,杜勃罗留波夫更看重民间文学,因为,民间文学是由底层社会所创造的,并真切地反映了底层人民的生活情状,“在我们的人民中,自古以来就保存着许多可以进行宏伟和有益活动的力量,保存着许多可以作独立而活跃的发展的萌芽。……民间诗歌长久以来都保持着它的自然而单纯的性质,对日常的痛苦和欢乐表示同情,本能地嫌恶光荣然而是无益的盛大武功和庄严的生活现象”[注][俄]杜勃罗留波夫:《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也就是说,在民间文学中,人民,或曰底层民众关心的是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而对于统治者的生活中的宏大叙事是一种否定和颠覆。
除了对民间文学的赞美,杜勃罗留波夫对于平民作家的创作也给予了格外关注。我们大家都熟悉他写的评论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冈察洛夫的文章,但很少有人去特别注意他写的评论柯尔卓夫(这一篇因为有中文译文而为更多国人所知)、舍甫琴柯、玛尔科·沃夫乔克、伊万·尼基金等平民作家的文章。在评论柯尔卓夫的文章中,尽管他一直强调他不是因为这位诗人出身低微而青睐诗人,而是因为诗人的卓越艺术才华。但实际上,他之所以关注这位诗人,除了其底层身份以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柯尔卓夫是一位歌谣诗人,而正是这种体裁决定了其诗中所描写的都是民间传说故事,表现的都是俄国民间的生活事件和朴素奔放的感情。另一位受到杜勃罗留波夫关注的是农奴出身的乌克兰诗人舍甫琴柯,当然,后者对底层人民生活的体验更为真切,这也让杜勃罗留波夫的评论更加充满赞誉之辞:“他完全是一个民间诗人,是那种在我们身边无法指认出来的民间诗人。……在舍甫琴柯这里,一切思考和同情都与人民生活的意义与制度完美契合。他出身于人民,生活在人民中间,不仅思想,而且他的整个生活状态都与人民密切相关、血肉相联。他曾经生活在有教养阶层的社会里,曾生活在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但长时期以来,他在这个社会上看到的只是令人厌恶和蔑视的粗俗、压迫、暴力、不公,然而,伴随着最初的道德和自由意识的曙光,他的灵魂对自己苦难的故乡的向往却越发强烈,这唤醒了他对故乡的叙事,让他反复唱起故乡的歌,思念起故乡的生活和大自然。”[注]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Кобзарь》 Тараса Шевченко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омах, т. 6, М.-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 142.
杜勃罗留波夫对平民作家的赞美,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描写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而是他要通过对这种底层性的推崇,来标明他的一种阶级意识和立场,即他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推翻这种充斥着暴力与不公的社会制度,解除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等级鸿沟。因此,在所有的平民作家中,杜勃罗留波夫更为欣赏乌克兰女作家玛尔科·沃夫乔克(此为笔名,原名玛丽亚·亚历山大罗芙娜·维林斯卡娅),原因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沃夫乔克描写了真实的“平民”(простонародье)生活,并且揭示了其中蕴藉的颠覆农奴制的力量。为此他写下了著名的长篇评论文章《俄罗斯平民的固有特征》一文,其中写道:“农奴制已近末日,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对此无可争议,它已行将就木。但在国家内部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事实不会随风而散、不留痕迹。即使它在法律上被取消两个世纪之后,它的某些地方性因素也会留存在人们的风习之中;是否有可能迅速重建由类似农奴制现象所导致的一切关系呢?否,农奴制还将长久地得到我们的反映——在书本中,在客厅的谈话中,在我们生活的整个体制之中。不仅仅上一代人的观念,就连正准备步入社会事务的一代人的观念,即使不是直接在农奴制的奴役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强大体制的影响。此前的一段时期内还不可能直截了当地来否定这些观念,因为作为这些观念的基础的农奴制仍然是受国家法律认可的。如今这个基础被否决了,被认为是与人权为敌的,它失去了法律的庇护,因此,由农奴制所孕育的观念与诉求将被置于过去属于它的地盘上接受审判。今天,文学的任务就是追究农奴制在社会生活中的残余,寻找到由它所孕育的种种观念的根源,将其彻底击溃。”[注]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Черты дл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русского простонародья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омах, т. 6, М.-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 223.而玛尔科·沃夫乔克的作品所展现的正是这样的典范,由于其作品的朴素而真实,使她成为清除农奴制残余的战场上的一个“艺术战士”。
二
与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较起来,杜勃罗留波夫具有更为激烈的社会变革欲望,因此也在其批评文章中表现出更为激进的现实主义立场。尽管别林斯基把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作家命名为以揭露现实为主导的“自然派”,但别林斯基是把这种对作品批判性的肯定融入到他对作品艺术性的分析之中,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因为一个激烈的批评家是不可能被尼古拉一世的专制暴政所容许的。到了相对开明的亚历山大二世时期,言论自由度提高。更重要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样的批评家,既带有底层社会的反抗性,又有自教会学校接受来的圣徒苦修精神,他们进行文学批评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对社会进行干预,所以文章表述的直接性大大增强。这种基本立场也导致了杜勃罗留波夫的批评带有更为明显的主观意向,即对现实性和批判性的肯定。
可以说,俄国文学的批判性意味,是由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们所揭示出来的。这不是说俄国文学没有否定性内容,而是指作家的写作更多受到俄国正教文化的制约,其基本价值取向是救赎,而非“审判”,因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精神是自我救赎,而不是拯救他人;尽管在俄国历史的现实叙事中存在着明显的帝国意识,但其文学叙事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东正教文化精神的影响。但在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们的眼中,文学对现实的忠实性描写,就是对俄国苦难现实的揭露与批判。这样的评价在别林斯基时代表现得并不明显,但到了杜勃罗留波夫这里,则他的批评文章总是把作品的主旨引向现实批判。
他的代表性批评文章《黑暗的王国》,看上去是为了澄清以往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的论争,杜勃罗留波夫提出要尊重作品的事实,而不是凭借自己的主观意愿来替代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内容。但实际上,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否定对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的斯拉夫立场的理想化解读,而要将作品的主旨引向现实批判的立场。
当时的斯拉夫派人士把奥斯特洛夫斯基视为“俄国美好的旧时代”的崇拜者,其剧作则是对俄国传统美德的正面描写,因此,他们在作品里看到的便是一个传统的卫道士,如果奥斯特洛夫斯基表现出一点否定性色彩,便被视为受到了“自然派”批评家的压力。斯拉夫派杂志《俄罗斯丛谈》曾发表评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文章称:“有的时候,他却缺乏决心和勇气,去实现他所思索过的东西:看样子,他是被那种为自然派倾向在他身上熏陶成功的、虚伪的羞耻以及卑怯的习惯所扰乱了。因此,他虽然常常开始构思什么崇高和阔大的东西,可是一想起那个自然派的尺度,他的构思就被吓跑了;他应当使他的欢乐的感想尽情奔放,可是他仿佛害怕高飞,因此他的形象总显出某种程度的不完全。”[注][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的王国》,《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63-264页。这是斯拉夫派政论家Т.菲利波夫发表在《俄罗斯丛谈》1856年第1期上评论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生活切勿随心所欲》的一篇文章中的引文,参见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омах, т. 5, М.-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2, с. 17, c. 564.对此杜勃罗留波夫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他看来,所谓理想性都是那些带有偏见的批评者强加给剧作家,而不是剧作本身所固有的。比如,受到斯拉夫派盛赞的剧作《各守本分》(直译为《不是自己的雪橇不要坐》),实际上主人公鲍罗德金的性格描写是不真实的,作为一个商人,其本性应当是唯利是图的,但在剧本中却被写成近乎完美无缺的个性,他忍耐、谦逊,最后还娶了富商鲁萨科夫的不名誉的女儿,“在整个剧本中,都表现出是一个遵循着古老的美德、高尚而善良的人,他的最后一个举动完全不符合鲍罗德金所代表的这一类人物的心灵状态。可是作者却要把尽其所能的善良品质都归到这个人物的身上,甚至把其中连鲍罗德金本人想必也会惊诧地否认的那些品质,也加到了他的身上”[注]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Темное царство//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омах, т. 5, М.-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2, с. 25.中文译文参见[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的王国》,《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76页。。显然,这样的剧作是杜勃罗留波夫所不欣赏的,他欣赏的是表现社会黑暗和民众苦难生活的题材,以及带有明显的被压迫者反抗色彩的作品。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评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两篇长篇文章中。
《黑暗的王国》一文主要是评价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的批判性内容,揭示其对现实俄国生活的揭露与否定。他断言:“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中,一切戏剧冲突和灾难,都是由于两个集团——老年的与青年的、富的和穷的、专横的和谦卑的之间冲突的结果。”[注][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的王国》,《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页。甚至,杜勃罗留波夫还以形象化的语言重构了“黑暗的王国”的景象,他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世界分成了由两种人组成的“黑暗的王国”,一种是“困顿衰疲的囚徒”,一种是“专横顽固、粗暴而蛮横的统治”的代表。通过这样的概括,杜勃罗留波夫成功地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归入了现实批判的创作类型。《黑暗的王国》这篇文章是针对1859年出版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两卷集所写,这个集子里收录的主要是剧作家的前期作品,里面较少反抗因素,所以,杜勃罗留波夫试图通过放大其中的“黑暗”性描写来强化作品的批判性效应。他就剧本中对底层民众悲哀处境的描写抒发了自己的愤慨:“在奥斯特洛夫斯基所描绘的黑暗王国里,那种外表的顺从,那种达到完全疯狂地步的、其中的个性被令人痛心地抹煞了的、迟钝的、集中起来的悲哀,是和奴性的狡猾、是和丑恶的欺骗、是和无耻的背信弃义交织在一起的。……在这个黑暗世界里,没有神圣,没有纯洁,也没有真理:统治着这个世界的是野蛮的、疯狂的、偏执的专横顽固,它把一切正直和公正的意识都从这个世界里驱逐出去了。……在这人类的尊严、个性的自由、对于爱情和幸福的信仰、正直劳动的神圣都被专横顽固粉碎成尘埃,都被赤裸裸地践踏的地方,这样的意识是不可能存在的。”[注][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的王国》,《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88页。杜勃罗留波夫强调作品所描写的“黑暗的王国”的黑暗性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激发民众的反抗意识,从而达到干预社会变革的目的,可惜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早期作品里很少出现有抗争意识的人物。
但这篇文章发表不久,剧作家就发表了他最重要的剧作之一《大雷雨》,而杜勃罗留波夫欣喜异常,立刻又写下另一篇长文《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称“我们找到我们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才能以及关于他的作品的意义的许多想法的新证据”[注][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68页。,而这种“才能”就是表现人民之中蕴藏的反抗性,这种反抗性的代表就是女主人公卡捷琳娜,这个性格“使我们呼吸到了一种新的生命”,它“在我们整个文学中迈步前进了一步”,因为此前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作中的人物,大多是逆来顺受的类型,如前所述,是“困顿衰疲的囚徒”,不仅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此前的整个俄国文学,也多是“善良的、令人尊敬的但却软弱而没有性格的人”[注][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97页。。如果是这样的话,俄国文学即使都表现出巨大的揭露性力量,但这能不能引发更广泛的抗争意识,却是一个未定的问题。而如果文学作品能够直接描写具有反抗色彩的人物,尤其是受压迫者的形象,则它的社会效应就会大大增强。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卡捷琳娜正是这样的人物,这种性格代表了“俄罗斯人的坚强性格”:“他是意志集中而坚决的,百折不回地坚信对(自然的)真实的敏感,对(新的理想)满怀着信仰,乐于自我牺牲(就是说,与其在他所反对的原则底下生活,他就宁使毁灭)。”[注][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01页。卡捷琳娜较之传统俄国文学前进了一步的主要之处在于,她不甘于屈服,而是保持着内在的自尊,始终不与压迫的力量妥协,当她的生存原则无法抵抗这强大的压迫力量的时候,她宁可自我毁灭。杜勃罗留波夫认为:“这就是无论什么场合都可以依赖的一种性格的(真正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生活在他们的发展中所达到的高峰,……因此他能够创造这种成为伟大的人民思想的代表者的人物,这种人物并不把(伟大的)思想挂在舌头上,也不放在头脑里,而是在敌众我寡的斗争中奋不顾身地坚持到底,直至毁灭,而又完全不计及自己有责任去作(崇高的)自我牺牲。”[注][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24页。杜勃罗留波夫在整个评论的过程中,总是力图把思想引到启发民众的抗争轨道上去,所以,他反复强调,与其在这种黑暗的王国里生存,不如像卡捷琳娜那样以死相争。虽然他不可能在那个时代公开呼吁人民起来拆毁这个黑暗的王国,但文章的结尾已经表达得相当明确了:“假使我们的读者,把我们的意见考虑之后,发现艺术家的确在《大雷雨》中号召俄国生活和俄国力量(采取坚决的行动。假使他们体会到这个行动的合法性和重要性),那时候不管我们的学者和文学裁判官怎么说,我们都会满意了。”[注][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页。
显然,杜勃罗留波夫把卡捷琳娜这个人物理想化了,卡捷琳娜的死并不能说明在她身上体现了“俄罗斯人的坚强性格”,或者说,起码没有体现出在抗争中毁灭的精神。另一位批评家阿·格里高利耶夫就认为杜勃罗留波夫是在用自己的理论来套《大雷雨》这部剧作[注]См. А.Григорьев, Парадоксы органической критики//Эстетика и критика,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80, с. 146.。而激进的批评家皮萨列夫在另一个层面上同样否定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评价。在他看来,在俄国的生活中只能产生两种人,一种是“侏儒”,一种是“永远的孩子”,“前者是积极作恶,后者是消极作恶;前者更多折磨别人,而较少内在痛苦,后者更多内在痛苦,而较少折磨别人。不过,一方面,侏儒完全不会享受宁静的幸福,而另一方面,永远的孩子则常常给别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只是他们并不是故意这样,而是出于令人感动的天真,或者就是因为十足的愚钝。侏儒会因为头脑的褊狭而痛苦,而永远的孩子则因为智力的冬眠以及由此导致的健康思想的匮乏而痛苦”[注]Д. И. Писарев, Мотивы русской драмы//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в 3 томах, т. 1, Л.: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1, с. 338, с. 350.。卡捷琳娜也不例外,她属于永远的孩子一类,没有自主的思考能力,因此也无法给俄国带来真正的光明。当然,皮萨列夫的立场也许更为激进了一些,他认为只有那些以实际行动给俄国带来变化的人才能给俄国带来真正的希望。然而事实上,即使在皮萨列夫时代,即农奴制已被正式废除之后的时期,俄国社会中也还没有产生明确的改革思路,民间的改革家们也仍然处在种种探索之中,那么当然,在提早若干年的杜勃罗留波夫时期,社会上就更少真正有行动能力的革命家。所以,杜勃罗留波夫的愿望是,只要受压迫者明白现行的社会秩序是不合理的,是一种对人的生命的压制,而宁可自我毁灭也不与之同流合污,则自由的曙光总有一天会真正到来。
三
然而,杜勃罗留波夫在他的时代是孤独的。19世纪中期的俄国,在国家变革的思路中,革命并不是主流社会的首选,更何况还有一大批艺术家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斯拉夫立场上,或者基于俄国传统的宗教文化精神,主张通过重建社会信任、重建个性美德、重新回归传统文化来解决俄国的问题。所以,杜勃罗留波夫呕心沥血写下了一篇篇充满激情和战斗精神的批评文章,然而却很少能从作家群中得到相应的回报。
我们看,从《黑暗的王国》到《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短短半年时间,这两篇文章的篇幅居然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有几百页之多,然而它从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那里得到的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为了这篇谈我的喜剧的有力文章,我衷心感谢您。”[注]А. Островский,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у (отрывок) август 1859//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2 томах, т. 11,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79, с. 113.这句话是留存到今天唯一一个奥斯特洛夫斯基对杜勃罗留波夫文章加以评价的证据,而奇怪的是,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量的书信中,在其他人有关当时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过两个人之间有过什么交往。而就是这句话也是写在一张草稿上,应当是一封信的草稿,但是否写完并寄给杜勃罗留波夫也未可知。[注]См. В. Лакшин, Об отношении Островского к Добролюбову//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 2, 1959, с. 193.有研究者认为,无论如何,这都证明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认可这位年轻批评家的意见的。然而,这种简单的回应相对于杜勃罗留波夫巨大的工作与付出而言,还是显得过于“吝啬”了。这其中的具体原因已无由推断,但总的来看,还是杜勃罗留波夫的批评锋芒过于激进了,以至于总体上倾向于“根基主义”的作家群体还无法与之形成整体认同。
这从杜勃罗留波夫与屠格涅夫的关系上也可见一斑。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对《前夜》的评价问题,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杂志分道扬镳,起因是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不顾屠格涅夫的反对,发表了杜勃罗留波夫的评论文章《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其实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把英沙罗夫理解成了一个“革命者”,并表示俄国也需要这样的革命者:“英沙罗夫这种自觉的全身心洋溢着解放祖国的伟大思想,并志愿对祖国发挥实际作用的人,是无法在当今俄国社会中得到发展和表现的。……难道所有英雄气概和务实作风必然会远离我们吗,假如不想在碌碌无为中消亡或徒劳地死去?”[注]Н. Добролюбов, Кагда же придет настоящий день?//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омах, т. 6, М.-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 138.同时文中也表示出,在俄国很快就会出现像英沙罗夫一样的英雄,即“真正的白天”就要到来:“到那时,文学中也会出现丰满的、刻画鲜明而生动的俄国的英沙罗夫形象。对此我们不必等待很久:在我们期盼它在生活中出现时所怀有的狂热而痛苦的焦虑,就是一种明证。对我们来说,这种形象是必要的,没有它,我们的全部生活就仿佛无关紧要,每一天都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而仅仅是第二天的一个前夜。但那一天终将到来!因为不管怎样,前夜距离随之而来的明天不远了:不过只有那么一夜之隔!……”[注]Н. Добролюбов, Кагда же придет настоящий день?//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омах, т. 6, М.-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 140.但这种理解却大大地背离了屠格涅夫本人的观念。至于到底为什么屠格涅夫对这篇文章大表不满,我们同样找不到可信的材料来说明[注]此前屠格涅夫与杜勃罗留波夫之间已有龃龉,屠认为后者有巨大才华,但与别林斯基比起来,却“处处表现出冷淡和偏颇”。参见巴纳耶娃:《巴纳耶娃回忆录》,蒋路、凌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07-315页。,但屠格涅夫毕竟要求涅克拉索夫拒绝这篇文章,他在给后者的信中写道:“我恳请你,亲爱的涅克拉索夫,不要刊登这篇文章:它除了让我不快没有别的,它偏执而刻薄——如果它被发表了,我将不知所措。请你尊重我的请求。”[注]И.Тургенев, Письмо к Н. А. Некрасову около 2 марта 1860//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в 30 томах, письма в 18 томах, т. 4, М.: Наука, 1987, с. 163.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屠格涅夫之所以对这篇文章不满,是因为他觉得文章贬低了他的艺术才华。[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道:“屠格涅夫把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视为对自己的侮辱:杜勃罗留波夫将他视为缺少那种把握小说主题的才华,缺少对事物的洞察力的作家。我对涅克拉索夫说,我看了文章,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这一类的话。……我对杜勃罗留波夫说,我没有看到其中有任何过错。”Н.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б отношениях Тургенева к Добролюбову и о разрыве дружбы между Тургеневым и Некрасовым//И. С. Тургенев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в 2 томах, т. 1,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3, с. 324.但在我们的论域中看来,屠格涅夫的不满还是源于杜勃罗留波夫无法理解英沙罗夫这一形象的复杂性,尤其是在他身上所蕴含的那种宗教意味,而一味地将其解读为一个革命者。
如前文所述,杜勃罗留波夫十分欣赏乌克兰女作家玛尔科·沃夫乔克,为此写了长篇评论文章《俄国平民的固有特征》,表达了他对底层书写的肯定性立场。然而,这篇文章却遭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否定,认为它为了表达个人的倾向而完全不顾作品的艺术性,因此,他同样写下长文《——波夫先生与艺术问题》,发表在自己办的杂志《时代》1861年第2期上,文中称:“在他的《俄国平民的固有特征》(《现代人》1860年第9期)一文中,在分析玛尔科·沃夫乔克的作品集时,——波夫先生几乎直截了当地声称他认为艺术性分文不值,并且声称,正因为如此,他无法理解艺术性的益处何在。在分析玛尔科·沃夫乔克的一部中篇小说时,——波夫先生坦率地承认,作者不是按艺术标准写这部小说的,但刚刚说了这些话,他马上又断定,作者通过这部小说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完全证明了在俄国平民之中存在着这种事实。实际上,这部小说不仅没有证明这种事实(非常重要的事实),反而处处引起大家疑问,原因就在于,由于作者缺乏艺术感觉,小说中那些用来证明作者主旨的人物,在作者笔下反而失去了任何俄国意味,读者更倾向于把他们称为苏格兰人、意大利人、北美人,而不是俄国平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够证明在俄国平民之中存在着这种事实,如果这些人物本身就不像俄国平民的话?可是——波夫先生根本不顾这一点;只要表现出思想和目的就好,哪怕破绽百出也无妨;这样一来那还要艺术性干什么?说到底,那还写小说干什么呢?不如简明扼要地写出在俄国平民中存在的这个事实——如此如此——又简单,又明确,又实在!‘还要讲什么故事!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注]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Г-н —бов и вопрос об искусстве//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т. 18, Л.: Наука, 1978, с. 80.尽管杜勃罗留波夫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严厉的批评,但在他年轻的25岁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卷集出版写下了他最后一部长篇论文《逆来顺受的人》。在这篇文章中,杜勃罗留波夫故意用大量的篇幅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描写,以说明他其实并不是要否定“美学的批评”,只不过,在他们那个时代,对俄国文学的艺术性的要求不能提到首位,很多人都是在杂志的催促中写作的,他甚至举例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为了定期交稿而匆忙赶写来说明这一点;但并不能因为作品在艺术方面的粗糙而放弃对它的关注,因为,我们需要发现艺术作品的思想,即使作家在艺术的“技术”方面乏善可陈,但只要一部作品在某一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就值得批评家大书特书。从杜勃罗留波夫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出他对于批评的实质的理解,那就是,作品艺术性的缺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社会意义,批评的任务就是把这种社会意义揭示出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改造社会的作用。
许多人都提到杜勃罗留波夫提出的“现实的批评”(реальная критика)概念。按照他本人的表述来看,是应当尊重作家的创作的“现实”,而不是把文学作品当作政论文来看。他在《黑暗的王国》一文中分析了俄国批评界对奥斯特洛夫斯基众说纷纭的评价,“其原因就在于,大家都竭力要他作为某一种信条的代表者,因此,当他不忠于这种信条时,就惩罚他,反过来,在拥护它们时,那就赞扬他”[注][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的王国》,《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页。。也就是说,批评家们不是批评奥斯特洛夫斯基,而是借着这种批评来验证自己的“信条”。因此,“为了做得更好起见——就得使用目的在于批评他的作品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的现实的批评,来对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注][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的王国》,《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页。。就此,杜勃罗留波夫提出了“现实的批评”的原则,首先是不以预定的标准来衡量作家:“我们并不向剧作家提出什么纲领,也并不想替他制订什么先决的规则,叫他应当按照这些规则来构思,来完成他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样的批评方法,对一个才能已经为大家所公认,公众对于他的敬爱已经根深蒂固,同时又在文学中占有一定成分的意义的作家,是非常无礼的。”[注][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的王国》,《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267页。其次,就是不把批评者自己的思想强加给作品中的人物,即“不允许强要剧作家接受别人的思想”,“对于现实的批评,这儿,首先着重的是事实:作者描写了一个传染着古老偏见的善良而又并不愚蠢的人。批评家应当去研究,这样的人物是不是可能的,是不是真实的。如果看出它是忠实于现实的,那末批评家就进而用自己的看法,来思考他所以产生的原因等等。假使在被研究的作者的作品中,已经指出了这些原因,批评家就应该利用它们,同时应该感谢作者;假使没有,也不要用匕首直指他的咽喉,对他说,为什么他胆敢描写这样的人物,而并不解释这个人物生存的原因?”[注][俄]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的王国》,《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68-269页。
总之,杜勃罗留波夫是要说明,应当区分艺术作品与理论思考的叙事方式,尊重艺术家的创作事实,是对这个事实做出评判,而不是用自己的思想替代文本事实。然而实际上,杜勃罗留波夫的“现实的批评”的实质,恰恰是要求批评者自己必须站在一个明确的立场上来面对所谓的文本“现实”,并以自己的主观价值标准来评判文本对象。实际上,这也是所有批评的正当阐释权力,只不过在杜勃罗留波夫那个时代,尽管他的立场已经足够激进,然而也还需要一个文本的限定性来为自己的批评获得合法性而努力。当然,在他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比起别林斯基来,他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社会改造的热情,总是更为鲜明地要把一部作品引入符合于个人价值立场的框架里来,从而使文学的批评变成了社会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