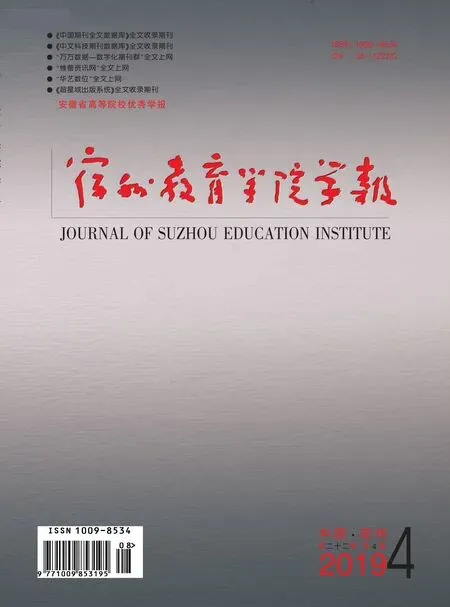析《文心雕龙·原道》之“文”
赵维宁
(武汉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2)
《原道》是刘勰《文心雕龙》的第一篇,位居“文之枢纽”部分之首。这一篇重要的开篇之作论述了“文”的本原问题,表现了刘勰文论最根本的观点和主张,是其他篇目的理论基础,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核心。
《原道》一篇中,共出现 20 个“文”字。关于“文”字的训释材料有许多,如《周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1]《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2]《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3]《原道》篇第一句第一字便是“文”:“文之为德也大矣”,可见“文”是统领全篇乃至全书的主题。这全篇第一个“文”字,具有极高的概括性。
《文心雕龙》是一本论文的理论著作,而《原道》位居首篇,因此,厘清《原道》篇中的各个“文”字的含义,对梳理《文心雕龙》中刘勰所构建的文论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道之文”
“道之文”是《原道》篇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全篇以“道之文”为开头,后以“道之文”为结尾,并认为文之所以具有教化等功能,“乃道之文也”,可见刘勰的“道之文”这一概念兼具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
全篇开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这一句中,刘勰指出,“文”是与天地并生的,以此来显示“文”的重要性。“何哉? ”刘勰接下来解释了这个定义的缘由,并引出了“道之文”:
此处的 “道之文”,包含了天地之间的自然现象,如:日月的光辉所代表的天文现象,山河的交错所代表的地理现象。那么这里的“道”,应为自然,即古人认知中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里的“文”,便是一个宏观的概念。
而后,刘勰从微观的角度,论及了“人”的“文”:
“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天地人三才”出自《周易·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1]将人与天、地的地位等同,那么“人”的“文”也与天文、地理一样,是顺应自然而产生的。刘勰也以此理论强调了《文心雕龙》一书论文的重要性。接着他讲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里谈的是“人”的“文”的产生由来,由“心”产生“言”,由“言”形成“文”。《礼记·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3]可见,人的“心”也是顺应天地而产生的,而“文”产生的根源在于“心”,所以“文”的最原始的来源乃是自然,这就是“自然之道”。
接着刘勰又从人以外的其他世间万物的 “文”来论证:“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虎豹等动物和草木等植物都有美丽的纹饰彩绘,刘勰认为这些花纹“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将动植的“文”的根源也归于自然,与人的“文”同属“道之文”的范畴。
除了视觉上的 “文”,刘勰认为听觉上也存在“文”,如山林、泉石之声,能使人产生美妙的感受的,都可称之为“文”。刘勰对于文章中听觉和谐的追求,也可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中得到印证。“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这里,刘勰将“章”与“文”两个概念并列等同。《说文解字》:“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2]可见“章”之本义与声音、音乐有关。
总之,这里的“文”,是指自然界中万物与生俱来的、令人感到愉悦的色彩或声音,是无意识而为之的“文”。而“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中的“文”,则强调了“有心”,乃是有意识而为之的“文”了。由此刘勰也引出了后文的“人之文”。
传统的地理水纹记号主要以地图图例为主,不能满足我国水利建设的需要。世界各地的地理水纹记号大同小异、种类繁多,我国的现代地理水纹记号虽然与之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差异。地理水纹记号覆盖面比较广,内容比较丰富,种类比较繁多,而针对水利的水纹记号又具有不规范、不全面等特点,不利于我国水利现代化的建设。
刘勰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阐释了“道之文”,认为“文”包含了视觉与听觉的感受,并将世间万物无意识所产生的“文”与人心所生的有意识的“文”的根源都归结于自然,解释了“文”的原始来源。
二、“人之文”
刘勰由“有心之器”而生的“文”,引出了“人文”的概念。“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刘勰将人类有意识的“文”的根源由宏观的“自然”具体到了“太极”之上。而《易》象、庖牺、仲尼等例,乃是人们对太极有意识的阐发而形成的典籍篇章,是“人文”的具体体现,此处的“文”,相当于《情采》篇中的“情文”:“五性发而为辞章”,则应有篇章、文章之意。
“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解道:“《周易音义》曰:文言,文饰卦下之言也。正义引庄氏曰: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皆文饰以为文言。案此二说与彦和意正同。”[4]可见,这两句当中的“文”,含有文饰之意。那么这一句,刘勰强调的是语言的文采,即人类有意识的对语言进行的雕琢,“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语言具有文采,是符合天地自然的规律要求的。然而下文中所举例的“河图”“洛书”,却带有明显的神话迷信色彩,刘勰将其归为“神理而已”,则似乎并不是在谈论“人文”的范畴了。可以说,刘勰过分强调了“自然神理”对于人所创作的“文”的作用,“表现了刘勰在其所论的问题上,存在着唯物与唯心的矛盾。”[5]这体现了刘勰思想观念上的局限性。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仓颉模仿鸟兽形迹创造了文字,代替了原始的结绳记事,于是人类用以记事的手段变得更清晰、具体。相较于用原始的方法记事的《三坟》,有了文字以后的唐、虞时代的文章,就得以传承,且文意更为丰富,这里刘勰强调的是文字对于文章表情达意的功用。
接着,刘勰谈到“逮及商周,文胜其质”,提到了“文”与“质”的关系。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也曾谈论“文质”的关系:“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6]虽然孔子谈论的是人格方面的问题,但可见“文质”应该“彬彬”,即文采和质朴应当配合适当,这才符合传统儒家观念。但刘勰此处似乎对商周时期文章“文胜其质”持褒扬态度,称其“英华日新”,然而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刘勰对“文”与“质”的关系是这样论述的:
“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可见,刘勰的“文质观”也是与孔子一致,认为应当“文质彬彬”。那么《原道》篇中所谈及的商周时期“文胜其质”,则更多侧重于“文”的发展过程。即到了商周时期,人们对文采的重视度提高,使得文采胜过了质朴,因而刘勰对这种情况十分赞赏。
在论述“人之文”,即人们有意识创作的典籍篇章时,刘勰笔下的“文”的含义就更偏向具体的“文章的文采”、“文字”等。刘勰肯定了文字的发明对于人类文章的写作、保存及流传的作用,对于文章之中文采的作用,他也是十分肯定的,虽在《情采》篇中强调“文质彬彬”,但对于商周时期“文胜其质”的现象,刘勰也是明显持褒扬态度的。
三、“圣之文”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在论述完“人之文”后,刘勰又将“文”的范围具体到了“圣之文”,即先贤圣人所作之文。
刘勰认为圣人所作之文,“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这句话出自《周易·贲卦》: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以‘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
这里提到的“天文”、“人文”中的“文”字该作何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中写道:
“在《文心雕龙》的不同篇章中,‘文’具有不同的含义:一是指文字、文学、文章、文采;二是指学术、文化、文明;三是指一切事物的形状、色彩、纹理、声韵、节奏等。[5]”
那么此处的“人文”,则与“人文之元,肇自太极”的“文”有着细微的差别:后者应指人所创作的文章,而前者则包含了社会文化、风俗文明等,不仅仅是文章的含义。至于“天文”,则可解为自然界万物的形态规律等。
“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里的“文”则可理解为“圣之文”,即圣人所作的典籍篇章。这个“文”既和“人之文”有关,属于人所作文章;又与“道之文”有关,因为“圣之文”由“道”而成,又反过来说明了“道”。黄侃认为这里的“道”:“即万物之情,人伦之传,无小无大,靡不并包。”[4]这个“道”包含了“天地人三才”之道,与“道之文”的“道”含义一致。
于是,刘勰指出了文章的教化功用:“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这里的“辞”乃引用《周易·系辞上》:“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1]可见在《周易》的原文中,“辞”是与“卦”相对应的,仅指对卦象的说明文字,而刘勰《原道》篇中将其含义扩大为了文辞、文章,应与上文的“文”含义一致,即圣人所作的“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的典籍文章。为什么文章能有这样“鼓天下之动”的功效,则是文章归根结底是“道之文”的缘故。这便使得“道之文”除了自然属性之外,兼具了更为重要的、能够影响人的社会属性。
结 语
《原道》篇中,刘勰认为“文”是与天地并生的,宇宙万物有“文”,人也有“文”,这里面包含了“文”与“道”的关系。随后,刘勰追溯了“人文”的产生与发展,论及“文”的教化之功用,归根于孔子的典籍,最终体现了其“宗经”思想。
由《原道》篇的行文脉络来看,刘勰主要以“道之文”“人之文”“圣之文”为线索,逐层阐释。“道之文”的部分中,刘勰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将世间万物无意识所产生的 “文” 与人心所生的有意识的“文”的根源都归结于自然,解释了“文”的原始来源。“人之文”的部分,刘勰笔下的“文”就由宇宙万物的宏观概念转而偏向具体的 “文章的文采”“文字”等,肯定了文采在文章中的积极作用。“圣之文”的部分,刘勰将“文”的范围具体到了先贤圣人所作之文,即《文心雕龙》核心所宗之“经”,而将圣人的经典又追本溯源到了“道之文”,同时也点明了“道之文”所兼具的自然、社会双重属性,实现了文章的首尾呼应,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理论系统。
《原道》篇中的“文”丰富多样,不同含义的“文”,都在书中其他篇目有所体现,《原道》篇所居“文之枢纽”之首,具有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
——“原道”传统与刘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