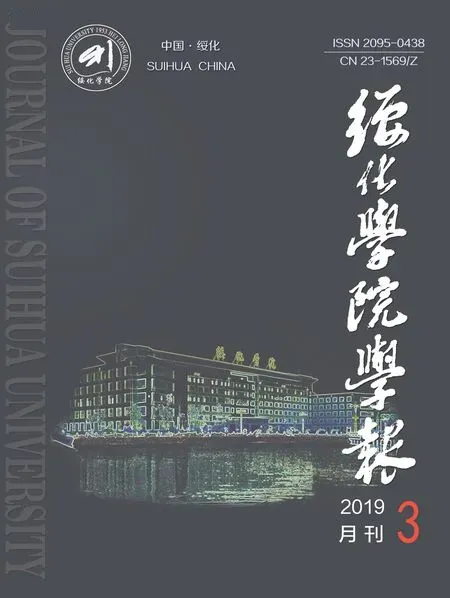小说到电影
——从《妻妾成群》到《大红灯笼高高挂》
李雅萍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大连 116000)
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传播媒介的日益信息化,人们对于消遣娱乐的审美需求越来越高,由此催生了视觉传播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文学文本与电影艺术的大融合。“电影和文学是可以优势互补的,在艺术殿堂里,它们交相辉映,可以绽放出更灿烂的华彩。就文学而言,它永远是其他艺术的老师;就电影而言,它尊重文学,热爱文学,并不断借助对优秀文学作品的改编以保护和提升电影的文化品位,促进电影健康发展。”[1]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便是改编自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该片上映之后以势不可挡的姿势斩获了多项国际大奖。趁此东风,苏童和文学文本《妻妾成群》也被更为广泛的人群所熟知。由此,文学和电影取得了双赢的效果。小说《妻妾成群》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以女学生颂莲嫁入陈家大院作为开端,在“妻妾成群”的模式下,见证和参与了高墙之内女人们的勾心斗角,最终在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压迫下走向崩溃。张艺谋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保留了文本的核心情节,但是由于文本和电影的艺术形式、传播媒介、作者和导演的审美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影片对小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编。正是这些全新的改编使得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从文本中抽离出来,具备了自身的独特生命力。
一、影像叙事——强烈的色彩对比
“小说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而电影基本是一种视觉的艺术。电影既然不再以语言为唯一的和基本的元素,它也就必然要抛弃掉那些只有语言才能描述的特殊内容,而代之以电影所能提供的无穷尽的空间变化。”[2]在电影无穷尽的空间变化中,色彩可谓是最原始的表现方式。它是一种隐形叙述,也是一种独特的表意方法。色彩的运用直接展现了导演的创作理念,影响着电影语言的讲述。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致力于展现色彩的视觉冲击力的张艺谋,通过对比强烈的画面色彩营造了可谓唯美的电影艺术。
如果用三种颜色来形容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那么具有视觉膨胀感的红白两色和视觉收缩感的黑色无疑可以概括这部影片。在张艺谋执导的诸多电影中,红色是当之无愧的“主题色彩”,如《红高粱》中迎风飞舞的红高粱、《菊豆》中的红染布等。《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色也不胜枚举,迎亲的红色花轿、红色的窗花、为数众多的红灯笼、梅姗的红旗袍。然而在影片中,本是寓意着热烈和喜庆的红色却是与沉闷、阴暗的黑色交互出现的。黑底红字的大标题;灿红色灯笼照耀下的黑色瓦片;四太太怀孕时满院子的红色长明灯,在假怀孕的事情被揭发后,红灯笼熄灭的同时还被罩上了黑色的布袋;一身红衣的四太太站在院子里,与一片漆黑的院落再次形成视觉的冲击。点灯、灭灯,红黑两色交替出现,高墙之内女人们的生命就在这一黑一红中悄悄流逝。红色在这部影片中像一种特定的符号,从细节处昭示着封建家庭对女性的摧残。而黑色就是这部影片的基调,从整体上以惨淡阴暗的黑色来讲述深院女人们的悲惨命运。在影片的初始,颂莲刚来到陈家,是伴随着一片暖红的夕阳余光,院子里落满了阳光的剪影。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场景几乎都为黑色所笼罩,阴暗的院子似乎连阳光都无法穿透。不仅仅是黑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白色作为丧色,同样预示着一种凄惨和阴冷。初入陈府的颂莲穿着白色的学生装,以一身的孤傲和清高挤到被黑色笼罩的密不透风的陈家大院;封灯以后颂莲木然地围着白色披肩站在高处,这时的白色则代表了一种落寞和凄惨。影片的最后,漆黑的陈家大院里落了一地的白雪,雁儿和梅姗都在这白茫茫的大雪中离开人世。白色的大地上留下了凌乱的黑色印记,一如雁儿双膝前的黑色灰烬,一如梅姗被抬去死人屋留下的行行黑色脚印。黑白两色的相互交缠,黑红两色的交替出现,在这种冷暖色调的强烈对比中影片逐渐走向了高潮。
色彩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因素,通过其自身的特性来传达微妙的情绪和感受。《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红黑白三色的交替运用不仅提高了电影的观感,也作为电影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了电影的审美性和艺术魅力。热烈奔放的红色,阴森可怖的黑色,逼仄凄凉的白色,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给观众留下不可磨灭的视觉印象。同时,在营造氛围、推动故事的发展、暗示人物命运等方面,三色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审美取向——人物形象的差异
电影和文学由于传播媒介的区别,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大为不同。文学语言概括性强,通过叙事、议论、通感和共鸣来引发读者的审美情趣和阅读兴趣,意在文字的断层和空白中引起读者的无限想象。相对而言,电影则更为直接具体,电影展现给观众的是声音和画面组合起来的意境,人物形象更为生动鲜活。因为电影和小说的审美取向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妨将这两种艺术形式视为独立的部分,互相关联又有所不同。通过对文学和电影中女主人公颂莲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在外形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从而形成了同一姓名却不同形象的两个颂莲。
小说一开始,苏童就交代了白衣黑裙的女学生——颂莲的形象:“那一年颂莲留着齐耳的短发,用一条天蓝色的缎带箍住,她的脸是圆圆的,不施脂粉,但显得有些苍白……颂莲的身影单薄纤细,散发出纸人一样呆板的气息。”[3]娇小单薄的江南姑娘就在苏童的笔下鲜活起来。而电影中的颂莲却是另外一副形象。电影一开场,观众看到的是一个鹅蛋脸、健康干练、胸前来回摆动着两条又粗又亮麻花辫的颂莲,是一个活脱脱的北方女性形象。人物形象从南到北的区别也是源于空间背景的南北转换。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在苏州,这里是苏童的故乡,也是他的心灵归宿;电影的场景却发生在北方的乔家大院,这与导演张艺谋的喜好有关。身为北方人的张艺谋更为喜欢北方的大气与粗犷,从温润潮湿的江南庭院到高墙耸立的北方宅院,女主人公的选择也自然由瘦弱娇小的南方女性转换为高大丰满的北方女性。
除了外形的诸多区别,两个颂莲在性格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书中的颂莲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她的身上被赋予了天真率性的品行。与陈老爷的初次见面,她孩子气地要求陈老爷与之在西餐社见面。这种青春气息和新奇的样子是封建陈旧的陈家大院所不具备的,颂莲也因此得到了陈老爷的宠爱。然而在电影中,颂莲的青春气息被完全泯灭了。她刚进入陈家大院,就给态度恶劣的丫鬟雁儿一个下马威,还命令宋妈给她锤脚。颂莲完全没有了知识女性的敏感与多思,在大宅门里女人相互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环境中,她也逐渐失去了人性,成为封建秩序的受害者和实施者。颂莲在欲望和现实中游走,在欲望和现实中煎熬,良知被残酷黑暗的现实一步步吞噬,最终在没有春天、没有希望的宅院里枯萎。
小说《妻妾成群》用幽远凄婉的笔调、意味深长的语言、入木三分的心理描写,塑造了一个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江南姑娘——颂莲在封建制度的禁锢下徒劳无望挣扎的叛逆女性形象,实为美丽的悲哀;电影则通过视听效果的辅助,塑造了一个干练倔强的北方姑娘在被男权制度规训后主动加入其中的可悲女性形象,实为可怜的奴从。
三、民俗元素——光影声色的狂欢
传统民俗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文化瑰宝,无论是服饰、行为方式、礼仪等各方面都留下了或深或浅的民俗烙印。民俗以其涵盖的历史、区域、民族等大量的文化因素,成为电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张艺谋的电影中有着诸多显而易见的传统文化因素,通过借助具有中国独特含义的文化符号形成其电影新颖的的艺术格调,这也是他创造电影神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红灯笼是一个显著的民俗元素和视觉符号。灯笼串联起了女主角颂莲的生活轨迹,从点灯到灭灯再到封灯,几个阶段的发展有力地展现了颂莲从初入府时的备受宠爱到和陈老爷产生隔阂直至假怀孕的事情被揭发后彻底失宠的命运。在封闭阴冷的高墙大院内,无论是红灯闪耀、熠熠生辉的良辰还是乌云惨淡、风雪交加的夜晚,灯笼都作为一种载体,是荣华富贵、恩宠权利的象征。颂莲的新婚之夜,灰暗的陈家大院变成了一片灯笼的红海,院落里十盏寓意着十全十美的灯笼、屋子里随处可见的灯笼都闪耀着红色的光芒。颂莲的脸在红灯笼映衬下散发着醉人的魅力。不仅仅是太太,就连丫鬟雁儿也渴望能有朝一日坦坦荡荡地点亮红灯笼,享受至高的荣华。影片在一次次点灯、灭灯的过程中,封建制度的欺人、害人、杀人的惨剧也在一次次的上演。影片通过对这种仪式的反复演绎,揭示了封建制度的丑陋本质,同时也对于人的本质和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入思考。
除了红灯笼外,京剧也是这部影片中一个显著的民俗元素。三太太梅姗是一个京剧演员,与她相关的诸多内容都离不开京剧元素。京剧的服装、道具、京剧的唱段,乃至三太太的屋子里都挂满了京剧脸谱。梅姗高兴的时候唱,不高兴的时候也唱。陈老爷宠幸四太太,独居闺房的梅姗一身红色戏服,寂寞地站在屋顶上唱;陈老爷来到三院,在老爷高声地喝彩声中,梅姗欢快的京剧唱段便袅袅地在院落里回荡。同时张艺谋还选用京剧唱段来烘托影片的氛围,别出心裁地以京剧作为影片的背景音乐开场。作曲家恰到好处地运用京剧的打击乐,锣鼓敲击的强弱和速度都随着人物的动作进行调整,演员的内心情感和面部表情都在这锣鼓声中进行细致的演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氛围也就在这密集的鼓声中流淌。
《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影片能够横扫众多国际大奖,尤其受到西方观众的喜爱,在一定程度上与电影中的民俗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象征着喜庆的红灯笼还是婉转动听的京剧唱段、华丽的京剧服饰都形成了一种视觉奇观,满足了西方观众对于东方文化的视野期待。张艺谋以此举推动了本土电影向国际市场的新征程,在商业考虑上也符合张艺谋电影一直以来的国际化路线。
结语
张艺谋导演曾说:“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4]随着大众审美需求多样化,文学和电影艺术已经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在影视改编的过程中,由于小说和电影在传播媒介上的巨大差异也使得两者必然存在诸多的不同。“名著的影视改编,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的再创造过程。因此,忠实于原著和创造性是对立统一的。改编实际上就是用影视思维对原作来一次再创造。”[5]因此我们要以公正客观的眼光去看待改编作品、看待《大红灯笼高高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