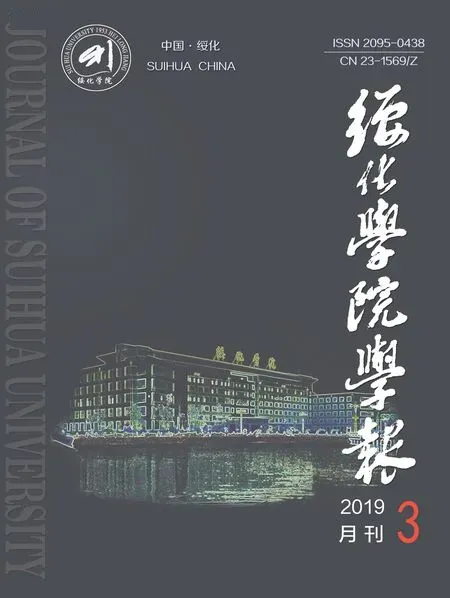《跋张文忠公帖》讹误辨析两则
王伟丽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12)
延祐二年科举为元代立国之后第一次科举考试,史称延祐首科,此科进士题名录不存于世。四库本王礼《麟原文集》中收录《跋张文忠公帖》,此中所列此科进士名单一直是元代延祐首科研究和元代进士辑考的重要依据。
王礼得见此帖,为其作跋,其中提及:
某尝求我朝科目得人之盛,无如延祐首榜。圣继神传累朝,参错中外。闻望之重如张起岩、郭孝基;文章之懿如马祖常、许有壬、欧阳玄、黄溍;政事之美如汪泽民、杨景行、千文传辈,不可枚举。[1](P439)
跋中所举进士除千文传和汪泽民二者,其余张起岩等人经诸学者多方查证皆第延祐首科无误。元朝科举进士名录多亡佚不存,自清末大家钱大昕至现代学者沈仁国,学界始终在努力构建元代进士名单,然而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非短时间内所能穷尽,且元代进士碑几经毁坏,现世所存文献资料真伪难辨,所以元进士辑考不免有遗漏错讹之处。这直接导致了元代科举进士群体研究缺乏明确史料支撑,进而影响元代科举制度的具体考察,基于元代科举之上的诸多研究亦不能得到充分展开。
一、“千文传”之误
干文传(1276—1353),字寿道,号仁里,平江人。延祐二年(1315)登进士第。《跋张文忠公帖》中为“千文传”者实为干文传。故宫博物院现藏干文传亲笔《跋朱熹<城南倡和诗卷>》,落款“吴郡干文传”,由此可见四库本“千文传”为误。
元代王礼“著作甚富,不求闻于时,故所传绝少”[2](P920),又因元明易代之际,文多散逸。《麟原文集》四库全书抄本以清代扬州马家藏书为底本。马氏尤富藏书,清代大儒全祖望在《丛书楼记》中称赞马氏其书精核,更无伪本。《麟原文集》是马家呈献朝廷珍本,献书之前必经百般思量,非精品不敢进呈。且因四库传抄书目庞大,抄写过程中难免出现纰漏,之所以出现“千文传”,很大程度上当为馆臣抄写出错。这种基于字形相近传抄出错的情况在四库全书中屡见不鲜,四库中干文传的姓氏“干”就有“千”“于”两种的讹变。“千文传”出现在《麟原文集》,“于文传”的错讹出现之处更多。如:
《延祐四明志》中有“延祐庚申同知于文传”。[3](P560)
《珊瑚木难》中《啸堂集古录序》落款“吴郡于文传题”。[4](P246)
《明一统志》载“于文传,同知昌国州事”,“至元年知州于文传募好義者建”。[5](P1085)
《御定孝经衍義》载“于文传”登延祐二年乙科,在昌国“长于治”。[6](P278)
干文传姓氏出错的情况不仅出现在四库全书收录书目中,其他版本也不免出现类似错讹。清影元抄本《金华黄先生文集》 载干文传时写道:“姓于氏,干之得姓始于春秋时宋大夫犨……”同是此书的元刻本《金华黄先生文集》记载同段文字时却为“姓于氏,于之得姓源于春秋时宋大夫犨。”犨姓干,《左传》中有宋大夫干犨御吕封人华豹的记载,《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也记载干氏为左传宋大夫干犨之后。由此可见,干文传姓氏的错误早在元刻本《金华黄先生文集》中就已经出现,清影元抄本更是在版本辗转的过程中出现“于”“干”自相牴牾的荒唐局面。
其实“干”作为姓氏错乱的情况早已有之。《搜神记》作者干宝曾被误作“于宝”,且古人早就发现了这个错误并予以纠正。如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就记载了杨万里谈及于宝时,一吏以韵书纠正说应为干宝。[7](P53)由四库抄本《麟原文集》等书中干文传姓氏的混乱,可见古籍抄录时“形近而误”所引发古代文学研究的困扰。
由干文传和干宝姓氏的错乱,可以窥见古籍数字化的数据录入时“形近而误”的弊端。古籍数字化依据强大的技术支撑,极大地推进了古籍保护的历史进程,它依靠强大的数据库基础,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和利用。
二、汪泽民之误
《元史》中有明确记载汪泽民“延祐初,以《春秋》中乡贡,上礼部,下第,授宁国路儒学正。五年,遂登进士第。”[8](P4252)《类编历举三场文选》存有王泽民延祐元年(1314)甲寅乡试和延祐四年(1317)丁巳乡试程文。由此可推知道《元史》记载无误。王礼跋中把其列入延祐二年进士实为错误之举。既为误举,必然存在误举的历史原因或现实基础:
(一)元代“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予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元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予山长、学正,受省札,后举不为例”[8](P2027),汪泽民“延祐初,以《春秋》中乡贡,上礼部,下第。”[8](P4252)汪氏被授予宁国路儒学正,正符合此项规定。文人士子因科考落第却被误载进士及第的情况在元代时有发生。林弼,字元凯,元至正七年(1347)中江浙乡试,王廉《中顺大夫知登州府事梅雪林公墓志铭》记林弼为“丁亥领江浙乡荐,登戊子(至正八年)进士第”[9](P202)。
王廉和林弼一起出使西域长达十月之久,于情于理,他的记载也是较为正确和令人信服的。可事实不然,林弼曾经在《林登州集》卷八《送实达道之官兴化序》一文中明确说明自己“至正戊子,予试艺于京师……是年,原德成进士,予下第南归,适达道来监漳州参司……”[9](P71)由此可知,林弼确实是参加了戊子年的科考,但会试下第了,王廉误记其进士及第。交游颇密的朋友尚且会记错,汪泽民被错载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中国科举辞典》载:“乡贡进士:贡举礼部试应举者名……元时对乡试中试并贡于礼部参加会试者的泛称。有时也作会试落第举人的雅称。”[10](P21)所以元朝所谓的进士身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廷试进士。
元朝经常出现称呼乡贡进士为进士的情况,可见元时人并不严格区分乡贡进士和进士。元人习惯称呼中乡试举人为“乡贡进士”,“乡贡进士”脱为“进士”之说的情况在元代司空见惯。《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所安遗集》载其作者元人陈泰为延祐二年进士,实际上在《所安遗集》中陈泰本人的诗《将离京师别李朝端陈伯奎二同年》一诗已经写到其“陈生射策未三十,笔箭如峰不破的”“纷纷鸾鹄好羽翼,莫笑垂翅南飞鸿”,“不破的”“垂翅南飞鸿”皆表明陈泰下第的事实,且《嘉靖赣州府志》卷七《秩官志》也记载陈泰以乡贡进士的身份入仕,人龙南县尹。故陈泰为延祐二年进士实际上是“乡贡进士”讹变为“进士”之说。
清代学者在编纂整理地方志时已经发现这个情况的存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十八史略》的解题关于其著者元代曾先之有这样一段描述:
先之字从野,庐陵人,自称曰前进士,而《江西通志·选举》中不载其名。盖前明之制,会试中试称进士,乡试中试者称举人,皆得铨选授官。自唐宋至元,则贡于乡者皆称进士。试礼部中选,始谓之登第。不中选者,次举,仍由本贯取解。南宋之季,始以三举不中选者一体径试于礼部,谓之免解进士。先之所谓进士,盖乡举而试不入选者,故志乘无名也。[11](P454)
曾先之自称“前进士”,可见元时人并不严格区分乡贡进士和进士在名称的差异,而且这个习惯,自唐宋至元一直有之。所以汪泽民虽然延祐二年会试下第,但因为其乡试中举,在当时亦可被称为延祐二年“进士”。基于“进士”和“乡贡进士”在称谓上的指向不明,可说是误载汪泽民的原因之一。
(三)历史对于成功及第者倾注的热情,较于落第失败者甚多。史料中关于科考者落第的稀少记载可见端倪。元人辛文房博采历史,于元成宗大德甲辰(1304)年成书《唐才子传》,保存了唐代诗人大量的生平资料,对其科举经历的记叙更为详备,但是对于这些才子落第的情况却很少提及。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此书作为传记体裁作品的程度,以致于有学者评价“此书的主要价值与其说在提供诗人传记史料方面,倒不如说是在唐诗的品评方面。”[12](P261)如书中在提及唐代文人才子的落第经历时,只是简略概述或略过不提。如:
綦毋潜:字孝通,荆南人。开元十四年严迪榜进士及第。授宜寿尉,迁右拾遗,入集贤院待制,复授校书,终著作郎。与李端同时。[13](P416)
钱起:及就试粉闱,诗题乃《湘灵鼓瑟》,起辍就,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主文李暐深嘉美,击节吟味久之,曰:“是必有神助之耳。”遂擢置高第。[13](P425)
姚合:陕州人,宰相崇之曾孙也。以诗闻。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贡举,有夙好,因拔泥涂,郑解榜及第。[13](P425)
《唐才子传》精减文人士子的落第经历,并非是其考察不周,更多地是辛文房等著作者受元代对于落第考生的整体态度影响而有意隐晦。传统落第考生或许要面对亲族、乡邻的议论,甚至是嘲讽非难。为维护汪泽民政事之美和隐逸文人的完美形象,选择忽略汪泽民下第的事实,对其人物形象进行美化装饰也不无可能。
(四)王礼生于延祐元年(1314)年,元统初进士,历元明之乱。刘定之《麟原文集》序中写道“托耕凿以栖迹于运去物改之余,依曲糵以逃名于头童齿豁之际。其文奇气硉矹胸臆,以未裸将周京故也。”[11](P1460)他以王礼“裸将周京”讽喻弃元投明的刘基。王礼入元以后隐居,“明兴不仕,聘为考官,亦不就。”[11](P1460)可见他对于明朝政权是采取不合作的敌对态度。
对元王朝的留恋和对明王朝的抵触,促使王礼追忆元朝先烈。汪泽民以其政事之美和忠贞不二的美名跃然进入王礼观照的视野。王礼曾选辑同时人诗为《天地间集》,“案谢翱尝录宋遗民诗为《天地间集》,以袭其名,盖阴以自寓。”[11](P1460)王礼效仿宋遗民诗人,辑集元朝遗民作品,寄寓自己对元廷的追思。汪泽民作为王礼的道德标杆和政治榜样,出于美化人物形象忽略汪泽民的落第,可以说是汪泽民被王礼误载的主观原因。
《跋张文忠公帖》是学者辑录元代首科进士不可忽略的重要史料,它对于元延祐二年进士名单和科举效用研究都有一定意义。元延祐二年进士名单的重构亟待解决,但由于进士题名录的亡佚和种种条件限制,元代进士辑考工作存在一定难度,这就需要学界在面对类似《跋张文忠公帖》这类文献资料时小心对待。这不仅有利于原本恢复,更有利于元代进士个体文人风貌的考察和进士群体研究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