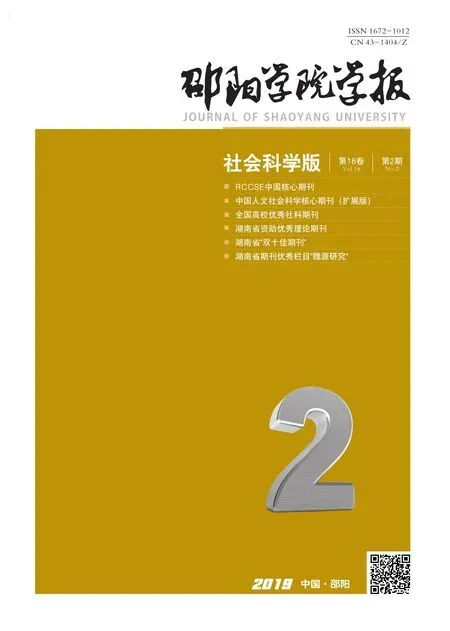《克拉丽莎》中的新女性个人主义述行
张 琳
(邵阳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继首部书信体小说《帕梅拉》后,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接连创作了第二部力作《克拉丽莎,又名一位年轻女士的生平》(Clarissa,orTheHistoryofaYoungLady)(1747—1748)。该小说以财产争夺、私奔和性暴力为主线,讲述了纯洁美丽的淑女克拉丽莎为反抗家庭包办婚姻,求助于声称爱她的贵族青年拉夫雷斯,却不幸落入圈套,被强奸失去贞操,最终伤心逝去的悲剧故事。
《克拉丽莎》具有上百万单词篇幅,卷帙浩繁,规模宏大,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狄德罗曾说,如果只允许保有寥寥几本书,他“会把理查逊的作品和摩西、荷马、欧里庇得斯以及索福克里斯的不朽经典一起留在身边”[1]166;约翰逊博士认为“就其所表现的对于人类内心的了解而言”,《克拉丽莎》“堪称天下第一书”[2]249。目前,符号学家、解构主义者、话语研究派等各类文学研究专家已经从小说悲剧根源、情节设置、叙述视角及技巧、小说与中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兴起等方面对小说进行了研究,但少有学者关注小说所反映的新女性个人主义特质。
克拉丽莎作为“新个人主义中所有自由和正面的因素,特别是与清教主义密切相关的精神独立立场的英勇代表”,是在反抗多种敌对势力——包括同样“与清教主义密切相关的经济个人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1]177本文将基于文学述行理论,对克拉丽莎的新个人主义与其他人物的经济个人主义进行对比,旨在揭示以言如何行事,即小说如何述行克拉丽莎这样一个在精神与道德上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
一、真善美的新女性形象
理查逊在撰写《帕梅拉》第二部时曾阐发对于妇女命运的思考,因此后于帕梅拉来到世间的克拉丽莎天然具备了她的创造者的经验和智慧,既保留了“经济个人”的特质,又展现了真善美的新女性形象,她的特质与社会规约相符,她的形象是通过语言来“实施”的。
《克拉丽莎》故事本身预设了“经济个人主义”这一18世纪英国社会规约,即强调关注个人、以个人利益为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这种经济个人主义包括对金钱、簿记和契约的重视。在小说中,克拉丽莎对每事每物都认真掂量、仔细权衡。她是协助母亲掌钥匙的持家人,在家庭财产方面,对于祖父遗赠给她的地产项目,她每年都亲自过目收益账目。此外,她考虑问题时,条理分明,深得核算的要义。比如,在向女友说明自己对拉夫雷斯的态度时,她把对后者的感受和看法条分缕析地陈列出来。在遗嘱中,她详细列出个人财务细目表并一一说明对这些大大小小物品的处置方式。“文学话语的述行性是在文学规则制约下产生的”[3]8,克拉丽莎的言行符合“经济个人主义”规约。
此外,克拉丽莎还展现了“真善美”的新女性形象。伊安·瓦特(Ian Watt)曾指出:“《克拉丽莎》以其松散性迫使读者转向革命性的认识:自然、真理、‘真实’本身是以自我概念而存在,具有强烈的主观性。”[2]6克拉丽莎的“真实自我”尤为体现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不同于帕梅拉将婚姻视为自己的全部,克拉丽莎对婚姻不存幻想。她表示“全心地愿意独身”,因为女人一旦结婚,“就被毁弃或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就要“放弃自己的名字,以标志成为他的绝对附属财产”,还得“让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4]139。在“婚姻即交易”的18世纪英国,克拉丽莎的语言具有革命性,她的独身宣言实施了“独立自主”这一自我塑造行为。
克拉丽莎容貌美丽,知书达理,品行出众,善解人意。此外,克拉丽莎也深受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她追求自由,肯定个人价值。她的价值观与当时通行的社会法则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同于自私自利的拉夫雷斯,她坚信良知和真理的存在。在生活的各种矛盾和价值冲突中,她像清教徒一样不断地进行道德衡量,反复探究以期获得真理。
美中不足的是,作为新于帕梅拉时代的女性,克拉丽莎却仍残留着旧时代的道德观念,把贞操视为生命般珍贵,这一贞洁规约也决定了她最后的悲剧结局。但是,尽管生活在狭小闭塞的封建家庭并遭遇了遇人不淑的命运,克拉丽莎始终怀揣着美好的理想,终其一生坚持着对真善美和自由的追求。
二、追求自由爱情的精神
在18世纪英国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经由“启蒙运动”渗透至宗教、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英国社会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均高举自由旗帜,提倡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在这一规约的影响下,克拉丽莎追求自由,并将其视为“作为英国臣民的与生俱来的权利”[4]92。
克拉丽莎非常坚定地要求自主选择爱情。她坚持选择爱人应是“发自真心,为了自己”[4]198。因此,在面对父母安排的对象——有着优渥条件却形容猥琐的索尔米斯时,克拉丽莎以否定语词“不”,实施拒绝这一行为。关于婚姻,她有自己的看法,“婚姻是友谊的最高形式:美满的婚姻给我们甘苦与共的伴侣,将忧愁减半,让幸福加倍”[4]653。她的语词述行了作家理查逊对于女性婚姻的道德关怀,即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应该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来判断对方的人品和道德水准。
与拉夫雷斯的相处中,克拉丽莎渴望自由,追求自由。在全家逼婚的境遇下,克拉丽莎选择与拉夫雷斯出逃,吸引她的是“自由承诺”:拉夫雷斯庄严许诺将把她“从牢狱中解救出来,使她重享自由意志”;他将“绝对服从”她的意志,使她“成为自己的时间和行动的‘主人’”[4]349。拉夫雷斯深谙克拉丽莎的艰难,“自由承诺”既实施了给予希望这一行动,又引发了成功带离克拉丽莎这一言后行为。而“自由承诺”本身也预设了克拉丽莎的悲剧命运,因为克拉丽莎渴望自由,却没有自由的权利,只能依附另一男权者来抵抗眼前的婚约安排,而依附他人往往是靠不住的。
此外,克拉丽莎的新个人主义,在与拉夫雷斯的对比下,体现得更为明显。拉夫雷斯处理世事符合“产权关系”的社会规约。他精通用钱来打通道路,例如事先收买哈娄家的仆人,在克拉丽莎犹豫之际,及时制造骚动,成功带离克拉丽莎。他将克拉丽莎视为自己“所购买的最昂贵的一份财产”[4]595,于是他理直气壮地拦截、偷阅并篡改克拉丽莎和安娜的通信,因为“财产是可以争夺和控制”的。在强暴克拉丽莎后,他炮制假婚姻时提出的“婚约”非常务实,充满了具体而切实可行的经济条款,表明他对这一套驾轻就熟。这位对交易规则了如指掌的“复杂的市场动物”以控制与征服他人为乐,行事宗旨为“自我中心”。
克拉丽莎强调主体自我的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在强暴事件后,克拉丽莎以一连串否定词“不”来实施否定、反抗和抵制行为。她说:“曾经如你(拉夫雷斯)那样以卑劣手段待我的男人,永远别想娶我为妻。……我决不、决不原谅你。”“我有自己的意识,我从心底鄙视你。”克拉丽莎对拉夫雷斯的抵制并非装腔作势,而是出于内心认定的是非原则,她宣称,“……我思想中的原则,无疑是被第一位仁慈的种植者(指神)植入的,它们迫使我……一言一行无不遵循”[4]736。基于清教徒对神的虔诚,以及忠贞不二的规约,克拉丽莎最终决定以死亡来结束这一切。有评论者认为,克拉丽莎的言与行体现了“以自我为中心”,她的“自我关怀(self-regard)内在于每个言说着的‘我’的行动中”[1]177。她对个人的感情、倾向和愿望的表达实现了她自我审视、自我监督以及追求自由的精神述行。
三、反抗专制的男权规约
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曾指出:“在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男人是绝对的主体,而女人只是作为男人的对立面和附属体存在,是男人的客体和他者。”[5]5在18世纪英国父系社会的文化中,女性作为“第二性”存在,表现为“没有品性、没有她自己的声音”。此外,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中、上阶级人将婚姻视为交易,将家族内的女儿视为“促进家族财产增值的手段”。在以上社会规约的制约下,克拉丽莎受到了来自父权和男权的双重压迫。她的新女性个人主义形象也通过与老小詹姆斯的经济个人主义特质对比而得以成功述行。
首先克拉丽莎受到了来自父权的压迫。老詹姆斯通过语言实施“压迫”这一行为,以确保父亲的绝对权威。当克拉丽莎拒绝嫁给条件优渥的索尔米斯,此举将影响家族利益时,老詹姆斯恼羞成怒,一再打断克拉丽莎的话,并说到“我的意志不容违背!——我没有孩子——不肯服从的就不是我的孩子!”此外,他还亲自出马下最后通牒,通知克拉丽莎必须“照我的旨意改换姓氏(指出嫁)”[4]188。老詹姆斯属于锱铢计较的商人阶层,在他看来,钱和产权关系是第一位的,是目的和根本。
其次克拉丽莎受到了兄长小詹姆斯的男权压迫。小詹姆斯是哈娄家族的长子,在18世纪的英国,长子占据特殊的地位,是家族财富的惟一继承者和人格代表。此外,哈娄家族的男性们有个共同心愿,即把财产集中到小詹姆斯名下,从而为家族争取一个“爵士”名号。因此,出于嫉恨祖父遗赠克拉丽莎地产(因为随着克拉丽莎出嫁,这份地产就将成为嫁妆而转为他人的财产),小詹姆斯先是与拉夫雷斯决斗,随后又极力促成克拉丽莎与求婚条件更为优渥的索尔米斯的婚姻,丝毫未曾考虑克拉丽莎的感受。对他来说,自由和权利只是一己的自由和权利,其他人不过是自己的工具。他人的意志若是与自己的意愿冲突,就无自由可言,只是应被制服的对象。
在面对压迫时,克拉丽莎的语言反抗既具有革命性,又存在局限性。她的革命性体现在她从根本上对“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世界观提出质疑。她指出:“依我看,世界是个大家庭,或原来曾经是这样。那么这种左右着我们的狭隘自私态度又是什么呢?岂不就是因尚记得的关系而反对被忘却的亲人?”[4]596她的语言实施了控诉与怀疑行为。她对老小詹姆斯的担忧和恐惧,来自于对主宰现实世界的“现金关系”的痛切感受。此外,关于逼婚,她敢于出逃;关于受辱,她敢于以死亡的形式来结束,这一切体现了她的强烈自主意识,也是理查逊第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帕梅拉所没能做到的。
然而,克拉丽莎的反抗也存在局限性。首先,面对经济至上的父亲,克拉丽莎自愿把祖父遗嘱中留给自己的地产对其进行让渡,并声明不愿意与之对簿公堂;其次,面对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小詹姆斯,克拉丽莎在出逃后仍愿意原谅,盼望与之和好,重新回归家庭;最后,面对试图以强暴来控制自己的拉夫雷斯,克拉丽莎以“圣洁之死”来证明自己的非功利性,她的理想个人主义也最终转化为对个人的否定和超越。
四、结语
约翰·普瑞斯通曾指出:“真正的写作过程,文本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它不是对叙述行为的描述。小说中的语言就是行动。”[6]91在《克拉丽莎》中,文本话语“述行性地”建构了故事,也建构了克拉丽莎这一新女性个人主义的形象。在与拉夫雷斯,老小詹姆斯的经济个人主义的对比中,克拉丽莎对于自由和真善美的追求,以及以死亡来进行的超越和反抗,体现了理查逊对妇女婚姻问题的道德关怀,以及新女性的现代自我和现代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