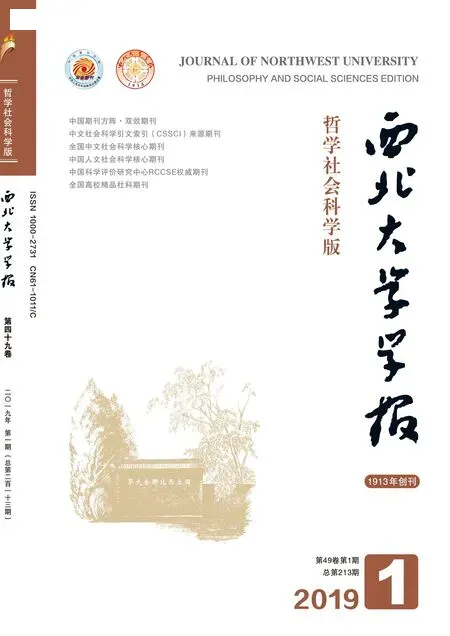“每一个词语都是一扇大门”
——论王富仁的语言观及其鲁迅研究中的应用
谭桂林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经谈到过自己的一个苦恼,这就是做教授和做作家的选择。做教授需要理智,做创作需要激情,这是两种矢向相反的心力。一般说来,做教授和做作家还是可以兼而得之的,民国时期这种例子很多,今天的作家重回高校似乎也是一个时尚。但鲁迅却为此选择而苦恼,是因为他的内心与智慧上,这两种力量都非常强大,强大到非得把对方压倒不可的地步,所以,鲁迅后来终究去了上海做了一个自由作家。这两种心力的强大给鲁迅带来的影响就是,无论他写作还是问学,都会有一个强大的自我意志渗透浸润其中,形成精神上的自我徽章,无人能够重复。王富仁的学术研究是从鲁迅研究起步的,虽然他没有像鲁迅那样产生这种选择上的烦恼,而且一生走的还是学院派的学术之路,但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这两种不同的精神与心力的活动,也曾经贯穿他的一生。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发表的小说曾经被《小说选刊》选载,他在中年时代出版了自己的散文诗集《呓语集》,前前后后也曾写过不少怀人叙事的散文。这些作品无论主题和表达都堪称上乘,只是多年来这些创作的价值和意义一直被王富仁的学术成就的光芒所遮蔽,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笔者在此想要讨论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需要具备驾驭语言的能力,文学研究则需要对文学语言的鉴赏的能力,所以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这两种心力活动的交集,很自然地引发了王富仁对语言的自觉关注与重视。就像他的鲁迅与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以其思想的深刻与问题意识的突出而深受研究者赞赏一样,王富仁的学术与创作中所呈现出的鲜明浓郁的语言意识和言语特点,也是我们应该予以关注的一笔精神遗产。
一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以其思想的深刻以及对鲁迅作品主题发掘的时代意义而著称,但是他接近鲁迅却是首先被鲁迅作品的语言所吸引。他曾经这样回忆过自己阅读鲁迅时的最初印象:“现在回想起来, 从初中一直到大学, 始终没有放掉的, 就是鲁迅。为什么喜欢他? 他好在哪儿? 我不知道。但一翻开鲁迅作品, 他实在让我入迷, 尤其是它那个语言。那种魅力, 在别人的作品中是没法获得的。鲁迅的杂文好像很简单, 但是你一接触它的语言, 就觉得跟别人不一样。它唤起你心里的一种东西, 你的心里确实是有感受的。不仅仅是你知道它好, 而且是你感到它好。我喜欢它那种语言以及它传达的东西。那种东西我觉得是说不出来的。比如说, 我也喜欢朱自清的散文, 它的好处我能说出好多来, 给学生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 但我从朱自清的散文中感受不到从鲁迅杂文中感受到的那种东西。所以, 鲁迅杂文我一直读下来, 始终没有放弃。‘文革’结束后, 涉及到我要做下边的学问, 考了研究生, 因为我喜欢鲁迅小说。”[1]这段话有三层意思是很明白的,一层意思是,王富仁认为鲁迅的语言魅力是独一无二的,在别的作家那里是感受不到的;第二层意思是鲁迅的语言是有力量的,它能唤起你心里的一种东西,激起你的感受;第三层意思是鲁迅语言的妙处在于你喜欢它,觉得它好,但这种好好在哪里,为什么好,你未必能够说出来。当然,这种说法是王富仁在接受访谈时所作的一种多少有点夸张的描述,强调的是自己在最初接近鲁迅作品时那种震撼性的阅读感觉,并非真的指谓鲁迅的语言魅力不可道也不能道。其实,当他后来从事鲁迅作品的学术研究,面对鲁迅的语言特色不能不道时,他对鲁迅小说语言之分析是十分深入细致而且是独具慧眼的。
王富仁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研究其中心观点乃是鲁迅小说是现代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他在80年代关于鲁迅的方方面面的研究,不管是小说主题、人物、情节、情调的渲染、气氛的铺设、色彩的敷染,还是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等等,其最终指向都是这一“镜子”说,语言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王富仁对鲁迅小说语言现象的观察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就是对鲁迅小说人物的言说方式包括语气、语式、语调、语词的细致分析。王富仁认为,鲁迅从反映中国思想革命的要求出发,他着重塑造了两种类型的人物,一种是堕落的上流社会。在鲁迅的思想启蒙格局中,像赵太爷、赵七爷、鲁四老爷这类肉食者是没有前途的,他们既不是思想启蒙的对象,更不是思想启蒙的动力,他们乃是思想启蒙运动的阻碍力量。所以,对于这种人,“在表面堂皇的言语和行动的隙缝中窥探他们内心的卑劣欲望则是鲁迅塑造这类人物的主要艺术手段。在这里,语言和行动的描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言语一般较少,言少而重,没有感情的温度,透体的冷酷,多纯理性的判断,无内在感情的真实表达,多命令句,判断句,少祈使句,疑问句,感叹句,反映着他们做为主人的专断与自信”[2](P35);王富仁特别以《祝福》中的鲁四老爷为例,分析了鲁迅在塑造这类封建礼教的“吃人者”所运用的语言功能。“在全部《祝福》中,鲁迅只给鲁四老爷这个人物设置了六句话的人物语言,共57个字,有两句只有两个字,一个四字句,最长的也只有20个字。但这几句话都处于读者能够集中关注的地方。第一次是在祥林嫂死后:(略)试想,在傍晚的宁静时刻,在‘我’用力辨听着内室嘁嘁喳喳的小声谈话而谈话乍止,‘我’仍用力倾听,等待下面的话声时,突然传出了鲁四老爷的高声诅咒,对‘我’这个小心翼翼地,怀着不安心情注视着有无意外变故发生的人,该是多么响亮、清晰得有些震耳的声音啊!这也有效地在读者的耳目中突出了这句话。而在这句话里,包藏着鲁四老爷那心灵的极端冷酷,这是对人的生命丧失的全然漠视,是对一个被他所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吃掉的弱小者进行的鞭尸行为。少而酷,短而重,如冰谷上突起突落的一阵旋风,起时让人惊而不觉,落后方感寒意透骨。全句二十个字,被分隔成三节,二三节间是一个较大的停顿,如粒粒铅丸,坠落心田。”[3](P319)
另一种人是下层社会的不幸人们,如祥林嫂、闰土、爱姑,等等。这些人是思想启蒙的对象,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鲁迅写这类人物时往往写出他们言语方式上的木讷,言语态度上的沉默。其实,底层群众虽然少受教育,对文字的运用能力很弱,但是由于民间生存方式的接近自然以及民间日常生活的丰富、民间人物情感交流方式的清新,民间言说方式往往成为古代社会民族语言发展的一种动力。鲁迅不是不清楚这一点,在关于艺术起源的观点上,鲁迅就表示过赞同劳动产生艺术的态度,自称杭棛派,后来在关于大众语的讨论中,鲁迅以民众语言的生动有力表达过明确的意见。但在自己的小说人物塑造上,为什么把劳动者都塑造成语言的木讷者。对此,王富仁有深刻的分析,他从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大局设计着眼,指出“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禁欲主义、抑情主义的长期统治,使劳动人民思想情感的表现长期受到摧残,这在他们的精神发展中造成了异常严重的损失。中国文字的繁难,劳动人民没有文化的落后状态,也使他们的语言表现力受到极大限制,而语言是思想的外壳,劣于语言表现即难于进行正常的心理思维活动。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只有鲁迅才能如此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劳动人民那寡言少语背后所隐藏着的深沉悲剧性,而这又经常被人们误认为是人民群众的高贵品德而错误地加以歌颂。人民应该有自我表现的权利,应该有自我表现的能力,这是鲁迅严峻地向我们提出的问题”[3](P344)。这一分析从具体的言语方式上升到了文化剥夺与精神治理的社会政治高度,这无疑是对鲁迅创作意图的知己之言,也是对鲁迅小说人物言说方式设计构架的高度评价。
对于鲁迅小说的叙述语言,王富仁也这样描述过自己的阅读感觉:“鲁迅的小说语言有种滞涩感,一般句式较长,读来会使人觉得气力难接,而在长句式中又夹入极短句式,在长句式过程中储足的气力在突然遇到短句式时又会发生回噎,两种句式之间的转换没有固定的规律,使语言的整体像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流着的泥石流,重拙而不畅快,起伏突兀而不平顺,在情绪感染上造成了强烈的沉郁感受。”[2](P48)这种特点当然与鲁迅的表达习惯相关,但王富仁认为,鲁迅是最典型的五四人物,他的语言的凝练与含蓄更主要的原因还应是体现着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维特征。他说:“《呐喊》和《彷徨》语言的凝练和含蓄,与它们整体的凝练和含蓄出于同一本源。语言是外部的思维,思维是内部的语言,语言的特征反映着思维的特征。思维空间的无限扩大,是伴随着我国闭关锁国状态的打破,伴随着接受全人类思想精神的成果和二十世纪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造成的思想精神成果的可能性而产生的中国现代社会意识的代表着的重要思维特征。思维空间的广阔性带来了艺术联想的丰富性,艺术联想的丰富性带来了从有限中发现无限,从一点中看到全面的可能性。鲁迅的语言特征最充分地体现了现代中国人所应有的这种思维特征。紧紧抓住具有极丰富内涵的细节和极具表现力的特点,以可以唤起丰富联想的精炼语言和传神性能极强的词汇,简洁地画出事物和人物的神态,为读者留下多方面联想的可能性和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补充大量次要特征的余地,是鲁迅小说语言之能够达到高度凝练和含蓄的主要原因。具有多义性象征意义的语言的运用,最突出地体现了《呐喊》《彷徨》语言的这种特征。”[2](P50)同时,王富仁也充分注意到,鲁迅语言总体上的含蓄与凝练风格,同样体现着鲁迅从事思想启蒙的文化改革的策略。“我们还不难发现,鲁迅小说语言的凝练和含蓄,与鲁迅着眼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状况的表现还有更直接的联系。它决定了鲁迅不注重政治、经济细节的精细描绘,而更注重人物精神面貌的再现。中国古典文学以形写神,重在传神的传统,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得到了鲁迅的发展、运用。”[2](P50)
确实,古代小说以形写神,重在传神,这是中国小说从评书发展过来的一种书写传统。但是,古代评书重在叙事,而现代小说重在描写,小说作者在语言上的特色才充分地体现出来。在这方面,鲁迅曾说他写起小说来,靠的是读了几十本外国小说。王富仁在考察鲁迅的语言特色时,也特别注意到了鲁迅对外国文学经验的吸取,“鲁迅曾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它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同样的话也用语称赞巴尔扎克,他说:‘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3](P338)。以语气、声音、对话来写人物精神,来凸显作者的写作意图,这是西方小说的特点,王富仁在他的鲁迅语言研究中,突出鲁迅对这一西方经验的吸取与化用,一方面是这些特点确实能够贴切地说明鲁迅小说思想革命主题的表达策略,一方面也是为了说明鲁迅小说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彻底性与整体性:鲁迅始终保持着对封建性文化的警惕性,即使在艺术形式上,鲁迅所用的也是从异质文化渊源中吸取的经验。
二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联名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章,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这一命题的影响、意义在当代学术史上已有公论,在此不赘。这里要提出的是,这一命题把中国新文学出现的时间上限推到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这就有意无意地抹除了五四新文学革命作为中国新文学源头的意义。当学界都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的革命性与颠覆性而欢呼时,最早意识到这一命题对五四新文学革命意义的抹除并且公开表示他的忧虑与反对意见的,正是作者们的好友王富仁。到了80年代末期,由于寻根文学的兴起抱怨五四文学革命斩断了民族文学的根,再加上海峡对岸的新儒家文化思潮乘机重返大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祭的时期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批判乃至谩骂的声浪可谓甚嚣尘上。在这种思想文化的大环境中,只有少数学术界的精英分子挺身而出,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评功叫好。王富仁也是这少数的学术精英之一,他发表的长文《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当时阐述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价值和局限最为系统与深刻的论文。可以说,从开始研究鲁迅起一直到他离世,王富仁都是五四新文化、五四新文学的坚定而有力的捍卫者。这种捍卫的姿态,在理论上当然主要是围绕思想革命、现代性转型等中心词来体现,但语言变革上的意义发掘也是王富仁的思考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值得学术界予以重视。
关于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性质,当事人自己已经有不同的说法。胡适是语言形式革命论的始作俑者,而周作人则认为第一步是形式革命,第二步是思想革命,而第二步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后来对于五四新文学革命的评价几乎主要是循着这两条思路展开。王富仁是坚定的思想革命论者,他对于鲁迅的伟大意义的发掘,对于创造社的青春文化的评析,后来对于左翼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论述,都是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来进行的。甚至到了新世纪,当他提出“新国学”的命题,当他参与“汉语新文学”概念的讨论时,他不得不面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白话文的革新成绩时,他仍然认为:“严格说来, 受到白话文革新直接影响的是‘宣传’, 而不是‘文学’。‘新文学’ 也是在白话文革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只有白话文革新还不足以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命。‘宣传’ 是对一种语言形式的直接运用, 而‘文学’ 则是对一种语言形式的创造性运用。没有文学家个人的创造, 任何一种语言形式本身都不可能自成文学。这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 文学革命的关系中也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都是白话文的自觉倡导者和运用者, 他们都能够写出一手明白晓畅的白话文, 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革命却是通过鲁迅、周作人特别是鲁迅的文学创作成其事端的。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 胡适、陈独秀、钱玄同是其‘先驱’; 在‘五四’ 文学革命中, 鲁迅、周作人是其‘主将’。二者相辅相成, 但却不是同样一件事情, 用‘文白之争’ 只能说明‘五四’ 新文化运动, 却不能完全说明‘五四’ 文学革命。”[4]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王富仁虽然认为仅仅只有白话文运动还不足以说明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性质,但他以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从白话文的社会功能上充分肯定了这一运动对现代中国人的现代生活的形成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心虽然在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也首先必须在思想革命的成果上予以体现,但恰恰是在思想革命的进程中,旧的思想传统、旧的文化因子最容易发生复辟,也最容易以借尸还魂的方式卷土重来,也就是说思想革命的成果最容易坍塌,也最容易变形。倒是语言形式的革命成果迅速扩展开去,不仅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固化下来成了五四新文学革命运动的主要标志。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中,王富仁指出:“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因素中,最有力、最不可逆转的稳定性的因素却恰恰是这个白话文运动所确立的语言文字的改革。虽然后来屡有白话与文言之争的余波,但它却像一堵牢不可摧的高墙一样堵住了重返古代文言的道路。我认为,它所具有的潜在能量我们至今还是难以估量的,至少人们还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些普遍的事实:它使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和青年再也不可能首先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获得自己最初的思维习惯和审美意识,它使文言成了他们有类于外国语言的第二语言系统,并且永远与之保持着或显或隐的距离感,永远具有一种非自我的那种异己感,它使古代典籍中的东西都必须纳入到他们首先在白话文的诗文中形成的思维习惯、审美意识甚至思想观念的基础上来理解,接纳和运用,并同时进行取舍,甚至它的难度本身也疏离了现代中国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在生存竞争日趋艰难与激烈的现当代和未来的中国社会上,它逼使传统文化必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取得自己的立足地,而不是依靠人们对它自身的敬畏心,即使如此,它再也不可能维持在古代社会那样的绝对统治地位,它将被日益丰富着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未来的文化、外国文化所冲淡。”[5](P67)在这段话中,“第二语言系统”“异己感”“逼使”等概念的运用,从语言功能的角度上充分说明了白话文运动所取得的成效,也充分表现了王富仁建立在现代人的现代生活基础上对白话语言使用的自信力与自豪感。
当然,这种语言的自信力和自豪感的基础,除了对现代人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充分信任,也包括王富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的一种独特的认知。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告诉我们的是:中国人要重新学说话,重新学听话。重新学习和建立中国的语言”[6](P215)。这里的“说话”与胡适当年在探讨国语文学时所提出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样说就这样说”的观念有所不同,胡适的意见还是“我手写我口”这一主张的白话阐释,强调的是手口言文的一致性,而王富仁所谓“重新学说话,重新学听话”,不仅指的是手口如一,更重要的是强调作者的心口如一。他说:“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剧在于:学一辈子话,说一辈子话,但替别人说话说得头头是道,但自己的话却说得糊糊涂涂。”“替古人说,替外国人说,替未来人说,替在高位的说,替在低位的人说,但到应该替自己说话时,却说不明白了。大家都看不起鲁迅,因为鲁迅为自己说话说得明白。”[6](P246)为了说明所谓“怎样学说话”的含义,王富仁还举了一个例子:“假若有人问我: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应从哪里开始?我将这样回答:首先思考这样几个问题:我是谁?我是怎样的?我现在需要什么?我怎样才能得到它?对这样一些问题,每个人的回答将是不同的。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的回答也将是不同的。但只要这样不断地问下去,切切实实地问下去。中国将不知不觉间便会走向现代化。但千万不可这样问: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他现在需要什么?他怎样才能得到它?”[6](P257)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言文是封建统治者管理和驯化知识分子的工具,知识分子通过文言文的掌握获得一种做奴隶的资格,而统治者则通过科举、八股、制式等方式,代圣贤立言、文以载道等观念,将知识分子圈养、训练和提拔成家臣与奴隶。而白话文则是自己的日常语言,也是自己的生命体征之一,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语言观来看,就是自己生命的栖居之地。所以,归根结蒂,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开辟了一条说自己的话的通道,提供了一种说自己话的工具。五四新文学革命之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弃用文言文,学做白话文,其实就是“重新学说话,重新学听话”的开始。用这一观点来论证五四白话文运动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成果,较之纯粹地比较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优劣长短,空乏地去讲语言文字之进化的道理,无疑更加痛切有力。
三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王富仁在学术之余,将自己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思绪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下来,出版了他的散文诗集《呓语集》。这是当代文学史上一部其非凡价值尚未被发掘被认识的作品,里面包含着作者对思想、文化、语言、历史、习俗、生命等等的富有智慧的思考。在这本集子里,作者曾说:“如果说人生有一百道大门,前九十九道你都可以在古代人留下的钥匙中找出一把合适的来将它打开,而最后一道门,则必须要用你自制的钥匙来打开。这最后一道大门才是你的智慧之门。前九十九道只是你的知识之门。”[6](P215)这本《呓语集》没有引经据典,没有注释,也没有中心主题,没有逻辑线索,只有一个个从作者脑海里蹦出的断想,一道道从作者心灵之弦上弹出的情调。所以,这本《呓语集》与王富仁其他的著作完全不同,它就是作者为读者更是为自己开启的一道智慧之门。集子中对语言问题时有精彩灼见,非常明显的是,王富仁不是语言学家,他也无意于对语言问题进行纯粹的理论性思考,他的语言见解完全是现实文化生活的有感而发,与他自己的学术活动息息相关,所以从这些语言见解中,可以看到王富仁是怎样观察自己的生命与语言之间的碰撞遇合,也可以看到语言问题的思考是怎样引领着他的学术路径的发展。
归纳起来,王富仁在《呓语集》中表达出来的语言观念有如下两点最值得我们关注。首先,王富仁认为语言是有质变的。在传统的语言学理论中,语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种共识,但语言学者们往往只承认在一个民族语言的历史中存在着语言量和表达方式的变化,不认为一个民族语言体系会发生质的变化。王富仁在《呓语集》中明确地对这种语言发展观提出质疑:“一个民族的语言会不会发生质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你要承认一个民族的文化有质变,你就必须承认一个民族的语言有质变;你要不承认一个民族的文化有质变,你就不能承认一个民族的语言有质变。”王富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坚定的拥趸者,他坚信五四新文化是一种与封建旧文化传统完全不同质的文化体系,当然地他也就是民族语言有质变的观念信奉者。对民族语言的质变方式或路径,王富仁也有自己的独到体验,他指出:“语言的变化不仅表现在新词的产生,新的语法形式的出现和旧词的消亡,旧的语法形式的改变上,更表现在旧词意义和色彩的变化和旧的语法形式功能的变迁上。”譬如说,“‘褒义词’向‘反义词’的变化是语言的一种质的变化”[6](P215)。当然,在学术问题上,王富仁能够固执己见,但他对于不同的观念一向持有宽容的心态,虽然坚定地捍卫自己的观点,但也绝不抹杀对手坚持自己观念的权利。只是在真理的阐释与坚持方面,王富仁最为器重的学术品格是真诚。这一态度,在他对语言的思考中也得到鲜明的体现。他说:“文化上的保守派必然是语言上的保守派;文化上的革新派必然也是语言上的革新派;否则,他的保守和革新就是假的。继承传统的意义是:继续沿用传统的基本语言概念系统。发扬传统的意义是:在传统的基本语言概念系统的基础上继续丰富它。假若连传统的基本概念系统也抛弃了而又说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传统,那么,文化间的传承关系就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了。到那时,连马克思也可以被说成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了。”[6](P216)传统文化的基本语言概念系统是文言文,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要做传统文化的保守者,就应该做文言文的保守者,说的是白话,写的是白话文,却说自己是文化的保守者,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这种保守的态度就是假的,反之也一样。所以,这里说的是语言,其实批判矛头指向的是百余年来那些形形色色的假传统与假革新,也就是鲁迅当年所痛恶的“做戏的虚无党”与“吃教者”。
其次,王富仁十分重视语词自身的创造性功能。20世纪90年代,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中国批评界流行起来。解构主义理论以颠覆语词的延展意义为己任,在人类文明发展到知识膨胀信息爆炸的时代,语言本身与真理的距离越来越远,解构主义对语词繁殖给人类思想带来的遮蔽与扭曲的解放与颠倒,也确实激动着无数学术界的年轻与叛逆的心灵。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由于教条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思维方式泛滥,不仅语词一直遮蔽和压抑着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存在,而且语词本身也常常出现异化,无论内涵与外延都在冠冕堂皇地走向它原初意义的对立面。从解放思想、恢复语词的本真这一意义上,王富仁对解构主义的这种思想功能与效果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对语言的思考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解构主义观念的影响。譬如他认为,“有重复的语言没有重复的思想。任何一次的重复都使语言获得新的含义。对它的解读只能是对它自身含义的解读,与它原有的意义毫无关系”[6](P253)。 解构主义重视语词的创造性解剖,王富仁也认为,“每一个词语都是一扇大门。推开它,里面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不推它,它是一堵墙,挡住你的视线。有的人一生都站在门外叫喊,没有推开过任何一扇大门,他们的语言是词典里的语言——这扇大门的门窗,而不是门里的世界”[6](P257)。这些思考的意思与解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一致的,强调的都是解释主体的重要意义。但是,西方解构主义的弊端也十分显著,它把自己的精力集聚在语词本身,只注意语词本身的运动,而对语词相关的其他人类精神活动与文化创造则有视无睹,这种语言上的解构态度走到极端,就最终把理论本身变成了语言与智力的游戏。所以,王富仁在语言功能的思考中也对解构主义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他不同意解构主义只在句子内部的对立与联系的格局中研究问题,他指出:“一个大句子的意义主要不是由它内部的各个词语及其关系构成的,而是与其他很多大句子的联系和区别中产生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分析这个大句子的内部结构而在它的整体存在中便能感知它的意义。文学作品也是这样。文学作品是在诸多文学作品的联系和区别中获得自己的整个意义的,而不是由它的内部诸种联系和对立单独构成的。”[6](P76)“句子是人类语言的最小单位,有小句子和大句子,但没有单词。所有的单词都是在一个句子中获得自己的意义的,它是被高度的简化了的一个小句子。‘爸爸’是‘他是我的爸爸’的简化,‘祖国’是‘这是我的祖国’的简化。作者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用的都是句子而不是单词和短语。一次性的把握一个句子。文学研究是句法研究而不是词法研究。句法研究是外部研究而不是内部研究。形式逻辑的局限性在于它只解决语言内部的自身组织,而不是在语言与语言的外部对立或联系中确定。”[6](P77)这些论断的意思显然是,文学作品的解读,文学问题的研究,必须要在语词与外部社会与文化的对立与联系中进行,才能真正得到文学精神的真髓,才能找到解决或回答文学问题的方法。所以,针对90年代批评界解构主义的泛滥,王富仁语重心长地提出了警告:“语言中的每一个词都像一个魔棒,它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形象。有些时候,整个民族,整个人类,都会掉到一个语言的陷阱里,不论它怎样挣扎,都没法从这个陷阱中爬上来。人类爬出自己的语言陷阱的方法是:造一个新词或给予一个旧词以一种全新的用法。但要小心,这个新词也可能成为一个新的陷阱。”[6](P258)
也许正是这些语言学的思考,王富仁在新世纪中提出“新国学”概念,整体性地定位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的时候,他开始主动地从语言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譬如,他在谈到“新国学”命题的语言表达方式时说:“在我们现在的语言论中, 语言文字只是思想感情的交流工具,是文化的载体。似乎我们的思想感情可以用民族语言进行表达,也可以用外国语言进行表达;我们的文化可以装在这艘民族语言的船上,也可以装在那艘外国语言的船上。但在章太炎这里, 却把民族语言提高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的重要地位上。‘古字至少而后代草乳为九千, 唐宋以来, 字至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 如伽、去、僧塔等字, 皆因域外语言声音而造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 转造一字, 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于是始作《文始》, 分部为编, 则攀乳浸多之理自见亦使人知中夏语言, 不可贸然变革。’也就是说中国的语言文字, 是一个由最初极少的古字逐渐草乳衍生而成的彼此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每一个字词都与其他的字词有着特殊的关联,并形成自己繁多而又相对独立的意蕴与意味,中国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思想、感情、情绪和意味,是它种语言所无法完整地进行表达的, 而它种民族语言所能表达的,中国语言文字也是无法完整地进行表达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语言体系,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将中华民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首先就表现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立性上。实际上,直至现在,我们所感到的中国文化的危机,仍然主要是中国语言文字的危机, 假若中国人不把自己民族的语言当作自己的母语,假若中国知识分子劣于用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优于用外民族的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危机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的到来;假若中国人只能使用外民族的语言文字,而不再使用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解体。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首先孕育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之中。”[注]参见王富仁:《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第1辑,2005年4月。
王富仁曾有感于鲁迅研究界对鲁迅哲学思想的盲视,他从时间、空间和人的关系上广泛而整体地阐析了鲁迅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指出:“西方知识分子的时空观仍然主要是在人对周围世界(自然、社会、人)的相对客观的考察中建立起来的, 即使像弗洛伊德、柏格森、海德格尔、萨特这样一些非理性主义者、直觉主义者、存在主义者, 仍然是立于‘世界人’的立场上对人类的时空观念进行的探讨。他们是以‘人’有统一的本质、统一的时空观念为前提的, 各自的差异只是切入点的不同,而不是因为人与人的不同。这不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时空观念的建构基础, 更不是鲁迅时空观念的建构基础。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及其鲁迅的时空观不是在‘世界人’的基点上建立起来的, 而是在‘民族人’的基点上建立起来的。不是在人与人都有相同的时空感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而是在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承认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时空感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前者讲的是我们人类应有什么样的时空观念, 后者讲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应有什么样的时空观念。这二者是不完全相同的。前者更重普遍性, 后者更重独立性。”[7]王富仁的这个论断当然有诸多原因的分析,譬如近代中国人的空间意识首先就是被民族的挨打的耻辱所唤醒的,等等,其中有一条论据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王富仁细致深入地比较和分析了中国人的时间、空间与人的关系在语言中的习惯表达。他说:“在中国的语言中, 没有像西方语言中的那种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的明确划分, 因而中国古代人的‘现在’的观念是极不明确的, 特别是在文化发展中更是如此。对于他们, ‘现在’ 是什么? ‘现在’只是说话时的那一刹那, 是在过去和未来这整个连线中点上的一个随时就可抹去的点。是随时就可以消失的东西, 它像一条水流的前点, 时时出现时时消失, 对我们没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种特点甚至一直影响到我们当代的文化。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标题:‘孔子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象征’。这在中国的语言中是常例, 是屡见不鲜的表达方式, 但在西方语言中, 这种语言形式则是极少出现的, 因为这句话中的‘是’必须有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的区分, 在一般的情况下, 三者必居其一, 也只居其一。”[7]
无论是“新国学”的命题的提出,还是鲁迅的时间意识、空间意识等哲学思想体系的阐发,王富仁的目的都在说明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都是在自己的文化本源基础上(这个本源既包括思维方式,也包括民族母语的表达方式)断裂,而不是在外国文化本源上的断裂。所以这种断裂不是颠覆,而是创新;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应时代要求的一种文化发展趋势。“就这个意义而言, 说鲁迅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发生的是断裂性的变化并没有根本性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把这种‘断裂’视为一种不合理的文化现象, 视为对中国文化独立性的戕害。实际上, 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这跳跃性的‘断裂’过程中实现的。没有这种断裂性的变化, 就没有文化的发展。这种‘断裂’, 在我们中国现代文化中就叫做‘革命’。但是, 这种‘断裂’只是一种新的文化产生过程中的现象, 中国文化迄今为止也不是、也不可能是仅仅由鲁迅一个人的思想构成的, 甚至也不仅仅是由‘五四’以后产生的新文化构成的。我们的图书馆里不仅仅有鲁迅的书, 也不仅仅有‘五四’ 以后出版的书;我们课堂里讲授的不仅仅是鲁迅的小说和杂文, 不仅仅是‘五四’以后的白话文作品, 我们的城市里不仅仅有现代的建筑物,我们的农村里不仅仅有‘五四’以后形成的新风俗, 我们的政治结构不是按照鲁迅的设计建构起来的, 我们的经济家不是按照鲁迅的思想进行经营的。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极其庞大、极其复杂的文化结构体。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就是鲁迅在这样一个极其庞大、极其复杂的文化结构中与其他各种文化成分所构成的共时性的关系。就这个文化的整体是没有断裂的。中国文化至今还是中国文化, 而没有变成美国文化或俄国文化。正像太阳天天发生着内部物质的裂变而太阳还是太阳一样。在这里, 我们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文化的超越性特征。文化, 就其产生, 有其特定的现实需要, 但它一经产生, 就具有了超越性。语言文字本身就是具有超越性的, 语言文字作品超越了时间上的瞬间性和空间上的。”[8]
不管是恶意还是善意,在社会上总有一种这样的声音,批评鲁迅的语言过于尖刻,鲁迅的文化批判言词过于激烈。也许正是对语言功能效用的观察,对语言自身力量的局限性的反思,使得王富仁一有机会就要为鲁迅的所谓言辞激烈而辩护。他说:“时值今日,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还把鲁迅对儒家文化的批判视为过激的批判。实际上, 这些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与法家专制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儒家文化对一般社会群众和社会改革者的‘过激’行为。慈禧太后对维新派的镇压, 清王朝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镇压, 张勋、袁世凯对民主革命的反攻倒算, 段祺瑞执政府对徒手请愿学生的枪杀, 1927 年国民党政权对共产党人及无辜青年的屠杀, 都是比鲁迅的‘过激’言词‘过激’千万倍的行为。所有这一切在中国都是受到儒家文化价值观念的保护的。即使林纾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攻击,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站在政治立场上对‘胡风反革命集团’ ‘右派分子’的批判, 都带有实际的吃人性质为什么偏偏觉得鲁迅对儒法合流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反倒是‘过激’的呢? 在中国现代社会上, 儒家的政治观念和思想观念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政治力量和思想力量。鲁迅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反映着中国社会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中国知识分子社会意识的加强, 是在‘人’的基点上重建中国文化的需要。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所以,王富仁对鲁迅的语言做了高度的评价:“我觉得, 鲁迅的话语是有力量的, 因为他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誓言, 就是一种行动。他在支撑着一个世界, 他同时在爱, 也是在憎。我觉得中国的鲁迅研究遇到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严重的危机。中国现代文化的绅士化的发展、才子化的发展、流氓化的发展, 已经达到了从中国文化诞生以来从来没有达到的最高点, 这就使中国的鲁迅研究遇到了从鲁迅诞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既来自于外部, 也应该来自于我们内部, 所以说我们不要埋怨外部世界, 中国鲁迅研究者自身也应该反思自己。通过自我反思, 把处在这样最困难时候的鲁迅研究坚持下去。中华民族需要鲁迅, 不能没有鲁迅。也就是说, 中华民族不能光有一些绅士、光有一些才子、光有一些流氓, 让他们占领我们的世界, 鲁迅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