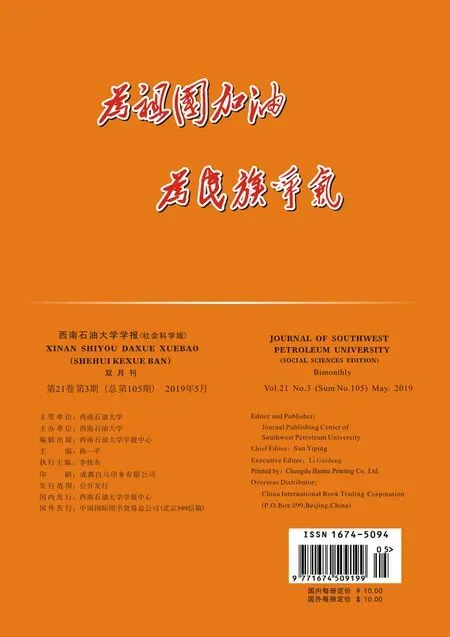试论《昌黎先生集考异》创作的理学目的
赵 聃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引 言
朱熹所作《昌黎先生集考异》(下称《韩文考异》)之所以受到后来学者的重视,不仅仅在于其成熟的校勘学方法及以文学方法来校勘的价值,还在于朱熹在校勘韩文时所蕴涵的深刻的理学目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其所校勘,乃以求史实,而主要更在发挥义理。然则校勘虽小业,于义理经术史学文章靡不有其相关互涉之处。”[1]因此,很有必要对朱熹创作《韩文考异》的理学目的进行讨论,从而有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韩愈思想对朱熹理学思想体系形成产生的影响。
朱熹在《韩文考异》中多借批评韩愈的儒家经学思想来阐释自己的理学思想。朱熹在《韩文考异》卷十中,辩证地评析了二程与王安石对于韩愈思想的评价。朱熹引方氏《附录》所载程子对于韩愈的评价:“程子曰: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之言,虽不能无病,然自孟子以来,能知此者,独愈而已。”[2]627朱熹认为,二程对于韩愈是自孟子之后唯一能够知“道”之人的评价是择其大要来说的。同时,二程亦认识到了韩愈所作之《原道》亦存在不足。王安石通过作诗对韩愈进行了评价,其诗曰:“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未俗,可怜无补费精神。”[2]627关于王安石对韩愈的评价,朱熹认为:“其为予夺,乃有大不同者。”对于二程与王安石对于韩愈的评价,朱熹则“折其衷而论之”,对韩愈思想做出了一个总体的评价。他说:
窃谓程子之意,固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为无理。盖韩公于道,知其用之周于万事,而未知其体之具于吾之一心。知其可行于天下,而未知其本之当先于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详于外而略于内,其志常极于远大而其行未必能谨于细微。虽知文与道有内外浅深之殊,而终未能审其缓急重轻之序,以决取舍。虽知汲汲以行道济时、抑邪与正为事,而或未免杂乎贪位慕禄之私,此其见于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讥者矣。[2]627
朱熹对于韩愈思想的批评是围绕着“道”的理解而展开的。朱熹认为韩愈不明“道”之体用,不知“道”先于吾之一身;虽知文道深浅不同,但最终不能明其缓急之序,因此在文中表现出了对于高位利禄的贪慕。与此同时,朱熹在对《与孟尚书》一文校勘时,不仅谈到了韩愈思想的不足,亦进一步借此阐释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他说:
盖韩公之学见于《原道》者,虽有以识夫大用之流行,而于本然之全体,则疑其有所未睹,且于日用之间,亦未见其有以存养省察而体之于身也。是以虽其所以自任者不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至其好乐之私,则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于流俗。所与游者,不过一时之文士,其于僧道,则亦仅得毛于畅、观、灵、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内外所立所资,不越乎此,亦何所据以为息邪距诐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无复平日饮博过从之乐,方且郁郁不能自遣,而卒然见夫瘴海之滨,异端之学乃有能以义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之人。与之语,虽不尽解,亦岂不足以荡涤情累,而暂空其滞碍之怀乎?然则凡此称誉之言,自不必讳,而于公所谓不求其福、不畏其祸,不学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虽然,使公于此能因彼稊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诸身,以尽圣贤之蕴,则所谓以理自胜,不为外物侵乱者,将无复羡于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余地矣。岂不伟哉![2]494
根据上文与朱熹思想的相关材料,可以将朱熹在校勘韩文时对韩愈思想的批评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①束景南先生认为:“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朱熹把韩愈的不识‘道’归结为五点:(1)讲大道的日用流行,而不讲大道的本然之体;(2)讲向外的发用施为,而不讲向内的一心修养;(3)讲文字语言工夫,而不讲涵养省察工夫;(4)讲治国平天下,而不讲致知格物;(5)讲性善,而不讲气禀。”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43页。,分别是:批评韩愈不懂“践履玩味”;批评韩愈不讲道之体,只“说得用”;批评韩愈“举说《大学》,而不说‘致知在格物’”;批评韩愈“论性不论气”;批评韩愈“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批评韩愈不重“存养省察”。朱熹在校勘韩文时,不仅从这六个方面批评了韩愈思想的不足,而且借批评之机阐释了自己的理学思想,这也正是朱熹之所以花费大量时间来校勘韩文的深层的理学原因。
1 批评韩愈不懂“践履玩味”
朱熹对于韩愈不懂“践履玩味”较为全面地批评是在回答门人的问题时,据《朱子语类》载:
又问:“与康节如何?”曰:“子云何敢望康节?康节见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见得大纲,有七八分见识。如《原道》中说得仁义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践履玩味,故见得不精微细密。伊川谓其学华者,只谓爱作文章。如作诗说许多闲言语,皆是华也。看得来退之胜似子云。”[3]4245
朱熹认为,虽然韩愈《原道》一文说到了“仁义道德”,但是于他自身却不去“践履玩味”,因此韩愈对于“仁义道德”的理解也是不精微细密的,在实践工夫上是不够的。“践履”即践行,侧重于行。“‘践’以用身,重在行与能。”“通过践履来使之即为我真有。”[4]441-442“玩味”,即体味,“涵养”的意思。朱熹认为韩愈虽然在《原道》说到了仁义道德,但只“有七八分识”的原因,就在于缺少“践履玩味”。朱熹不仅批评了韩愈的不懂“践履玩味”,而且要求人们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来践行、体味“仁义道德”。他在《答吴晦叔》一书中说到:
盖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在,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学于大学,则其洒扫应对之间、礼乐射御之际,所以涵养践履之者略已小成矣。[5]1914
朱熹认为在教育上应该从小教孝、悌、诚、敬,长大教育《诗》《书》《礼》《乐》,让人们在学习中不断地从一事一物之间去理解体味践行义理。可见,朱熹在承认韩愈《原道》中对于仁义道德说法的同时,亦批评韩愈不去“践履玩味”,即韩愈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去践行自己所说的仁义道德,因此就不能更好地去体味其中的精微细密之处。
2 批评韩愈不讲道之体,只“说得用”
在朱熹看来,“道者,古今共由之理”[3]397是“天地万物最高的终极之理”。朱熹引程子之言,认为:“程子言之矣。‘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皆与道为体’。‘与道为体’,此句极好。”[3]1353可见,“道者,体也”。韩愈在《原道》将“仁义道德”解释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6]1朱子门人蒋明之对此提出了疑问,据《朱子语类》载:
蒋明之问:“《原道》起头四句恐说得差,且如‘博爱之谓仁’,爱如何便是尽得仁?”曰:“只为他说得用,又遗了体。”[3]4256
朱熹认为韩愈将仁解释为博爱只是说的仁之用,即博爱只是仁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而不是仁的本体。在朱熹看来,“仁义礼智,性之大目,皆是形成上者,岂可分也。”[3]246可见,仁是形而上的。并且“‘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3]249。“‘体仁足以长人’,以仁为体,而温厚慈爱之理由此发出也。”[3]250朱熹认为仁的本体是仁,而“博爱”只不过是仁的一个表现,是用。朱熹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当“蒋兄因问:‘博爱之谓仁’四句如何”时,朱熹才认为韩愈“说得却差,仁义两句皆将用做体看。事之合宜者为义,仁者爱之理。若曰‘博爱’,曰‘行而宜之’,则皆用矣”[3]4257。另外,朱熹亦批评了韩愈“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的说法,当门人问朱熹韩愈这个问题时,他认为:“此是说行底,非是说道体。”[3]4256可见,朱熹认为韩愈此处所说之“道”是“道”之表现,而没有涉及到“道体”。因此,朱熹对于韩愈《原道》起头四句的批评,更多是指韩愈“讲大道的日用流行,而不讲大道的本然之体”[7]1043。即韩愈从道的表现着手,只讲道的外在表现,而对于这一表现之下的“道体”则没有涉及。这也体现了朱熹与韩愈二人对于仁的不同看法。
3 批评韩愈“举《大学》,却不说‘致知在格物’”
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其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学章句》,而朱熹在对《大学》的解释中最重要的就是增补《大学》第五章的文字,即《格物致知补传》。朱熹认为,“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从而依据“程子之意以补之”,原文如下: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8]20
朱熹认为《大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格物致知。虽然韩愈在作《原道》时引用了《大学》第一章“古之欲明明德于天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6]3,并对其进行了阐释,但他并没有提到《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思想。其实,韩愈要说明的与《大学》中“三纲八目”的“格物”“致知”无关,并且韩愈在此引用《大学》是为了说明“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的道理,因此《原道》一文中不涉及格物致知之说也是可以理解的。朱熹在此之所以批评韩愈,认为他在“《原道》中举《大学》,却不说‘致知在格物’一句”[3]4257,其目的在于阐释自己的格物致知思想,以及提高《大学》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从而为确立“四书”学系统服务。其实,朱熹对于《大学》的推崇未尝没有受到韩愈的影响,但他却在《大学章句序》一文中直接不提韩愈,而认为二程是上接孟氏之传的人物。他说: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8]14
另外,韩愈“不探其端,而聚语其次”,从而也不免流于“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之病矣”[9]。对此,朱熹的学生陈淳也认为:“韩公学无源头处。如《原道》一篇铺叙许多节目,亦可谓自见得道之大用流行于天下底分晓,但不知其体本具于吾身,故于反身内省处殊无细密工夫。”[10]可见,朱熹对于韩愈的批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亦是其不懂道之体,本质上二者思想的焦点在于是否认为天理是宇宙本体的道德本体论思想。
4 批评韩愈“论性不论气”
韩愈在《原性》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品”说,他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义,曰礼,曰信,曰智。......”[6]47对于韩愈提出的“三品”说,朱熹既有批评,也有肯定。他在《朱子语类》回答门人“退之《原性》‘三品’之说是否”的问题时说:
退之说性,只将仁、义、礼、智来说,便是识见高处,如论“三品”亦是。但以某观,人之性岂独三品,须有百千万品,退之所论却少了一“气”字。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此皆前所未发。如夫子言“性相近”,若无“习相远”一句,便说不行。如“人生而静”,静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带着气质言了,但未尝明说著“气”字。惟周子《太极图》却有气质底意思,程子之论,又自《太极图》中见出来也。[3]4258
朱熹认为韩愈从仁、义、礼、智出发来讨论性是很有见地的,这是因为“仁义礼智,乃未发之性,所谓诚”[3]243,也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岂可分也”[3]246。朱熹认为仁、义、礼、智是未发之性,是性的重要表现。从这一点上看,朱熹亦承认了韩愈在“三品”说中对于仁、义、礼、智重视的合理性。但是,朱熹紧接着又对韩愈将性分为上中下三品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按照韩愈的分法人之性不仅仅只有三品,而是可以分为千万品。对此,朱熹进一步认为韩愈之所以将性分三品,其原因在于韩愈论性少了一个“气”字。在朱熹看来,“仁、义、礼、智”是理,他说“理则为仁、义、礼、智”[3]115,“性,本体也。……且性之为体,正以仁义礼智之未发而言,不但为视听作用之本而已也”[5]3584。可见,在这里仁、义、礼、智就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而韩愈所说的“三品”则是性的三个表现,不具有本体论的含义。朱熹认为“性即理”,性是世界的本原,是无迹的。他说:
人之所以为人,其理则天地之理,其气则天地之气。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3]252
正因为“性”是无迹的,所以朱熹在论性时,必兼气而言。他说:“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掛搭处。气则为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3]115“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3]114“有是理,便有是气。”[3]114“理未尝离乎气。”[3]115而韩氏言性不言气,因此朱熹认为“退之所论却少了一‘气’字”。另外,朱熹认为:“盖天之生物,其理固无差别。但人物所禀形气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异耳。若所谓仁,则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别为一物而与性并行也,然性人心至灵,故能全此四德而发为四端,物则气偏驳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5]2767-2768这样看来,“理固无差别”,韩愈所说之“三品”亦只是由于人物所禀之形气不同而产生的不同表现,这样性就不只三品,而有“百千万品”了。这也正是朱熹批评韩愈性“三品”,提出“须如此兼性与气说,方尽此论”[3]1888的根本原因。
5 批评韩愈“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
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朱熹认为韩愈“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2]494,而文字言语相对于道而言则是第二义的。对于这一问题,他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进一步做了解释。据《朱子语类》载:
至问:“孟子谓‘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韩文公推尊孟氏辟杨、墨之功,以为‘不在禹下’。而《读墨》一篇却谓‘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韩文公第一义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于道’,他本只是学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于道尔。把这个做第二义,似此样处甚多。[3]4259
在这里,朱子门人指出,“韩文公推尊孟氏辟杨、墨之功,以为‘不在禹下’”,那么韩愈肯定是认同孟子“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观点,而韩愈在《读墨》一文中却认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这二者显然是矛盾的。对此矛盾产生的原因,朱熹的回答是:“韩文公第一义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认为在作文与“穷究道理”二者的选择上,韩愈将作文放在第一义的位置上,而把穷理放在了第二义的位置上,因此为了“文字言语之工”,会忽略甚至不在乎道理是否正确。韩愈的这一作法,在朱熹看来显然是不可取的。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朱熹虽不如周敦颐等人那样重道轻文,提倡“文以载道”①周敦颐认为:“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用,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通书·文辞》,《朱子全书·通书注》第13册,第121页。)也不像二程那样认为“作文害道”②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之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8,《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39页。),但他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3]4314,“文皆是从道中流出”[3]4298的文道合一的观念。虽然朱熹非常重视文在其思想体系中的作用,认为“不学文,则事事做不得”[3]374,并且“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5]3734,但是朱熹认为文不能贯道。他在对李汉所作《韩文序》的批评时说:
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来有病。”陈曰:“‘文者,贯道之器。’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说皆是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3]4298
李汉乃韩愈弟子,又是他的女婿,虽然韩愈本人并没有说过“文者贯道之器”之类的话,但是在《与孟尚书书》的写作中却因文而废道。虽然朱熹对文很重视,但是却决不会因文而废道。所以,朱熹才批评韩愈“第一义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从而提出了自己文与道合的文道观。
6 批评韩愈不重“存养省察”
朱熹在《韩文考异》中对《与孟尚书》一文校勘时说:“且于日用之间,亦示见其以存养省察而体之于身也。”[2]494另外,朱熹亦在回答门人的提问中,提到了这一点。据《朱子语类》载:
先生考订韩文公《与大颠书》,尧卿问曰:“观其《与孟简书》,是当时已有议论,而与之分解,不审有崇信之意否?”曰:“真个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贬从那潮州去,无聊后,被它说转了。”义刚曰:“韩公虽有心学问,但于利禄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于外面皮壳子上都见得,安排位次是恁地。于《原道》中所谓‘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为宫室,为城郭’等,皆说得好,只是不曾向里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细密做工夫。只从粗处去,不见得原头来处。如一港水,他只见得是水,却不见那源头来处是如何。把那道别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于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议论风采,亦有可观,却不是从里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诗,饮酒博戏为事。[3]4259
朱熹批评了韩愈在日常生活中,不注重“存养省察”与不从自身修养上下工夫。“存养省察”是朱熹道德修养论中的重要内容。“存养”,“即收敛此心。”[4]250据《朱子语类》载:“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不须枉费工夫,钻纸上语。待存养得此中昭明洞达,自觉无许多窒碍。恁时方取文字来看,则自然在意味,道理自然透彻,遇事时自然迎刃而解,皆无许多病痛。”[3]3644可知,朱熹认为在道德修养之时,必须把无有不差的本心存养起来,收敛其身心,从而才会不失本心。因此,要“操之而存,则只此便是本体,不待别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于义理而不妄动”[5]2189。“省察”,即反省检察。朱熹强调通过省察“求其寂然”,他说:“今乃欲于此顷刻之存遽加察识,以求其寂然者。”[5]2189
另外,朱熹认为“涵养愈熟,则省察愈精矣”,涵养对于省察有促进作用。不仅如此,朱熹亦认为“涵养”“省察”没有先后,二者可以相互帮助。他说:
有涵养者固要省察,不曾涵养者亦当省察。不可道我无涵养工夫,后已发处更不管他。若于发处能点检,亦可知得是与不是。今言涵养,则曰不先知理义底涵养不得。言省察,则曰无涵养,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檐阁。......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3]2405-2406
朱熹亦认为,不论是已发时或是未发时,都要无时不省察、无时不涵养。他说:“已发时亦要存养,未发时亦要省察,如是则已发日用细下工夫,善加体会。”所以朱熹在《韩文考异》中对《与孟尚书》一文校勘时说:“且于日用之间,亦未见其有以存养省察而体之于身也。”[2]494因为“须是平日有涵养之功,临事方能识得”[5]1899。
7 结 语
综上,朱熹之所以选择给韩文作考异,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借对韩文思想的批评,来阐发宣扬自己的理气论、体用论、文道观以及修养方法等理学思想。正如束景南先生所说:“朱熹在党锢中选择韩愈文集作考异的目的又不仅仅是为考订一书,他还有借韩愈这个大文豪来巧妙宣扬‘道学’的深意。贯穿在《考异》中对韩愈批评的一面,便渗透了他的道学‘伪气’。”[7]1042因此,在对《韩文考异》进行研究时,要跳出《韩文考异》一书校勘学的表象,以便去研究朱熹之所以选择韩文来进行校勘的深层次的理学目的。
——“原道”传统与刘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