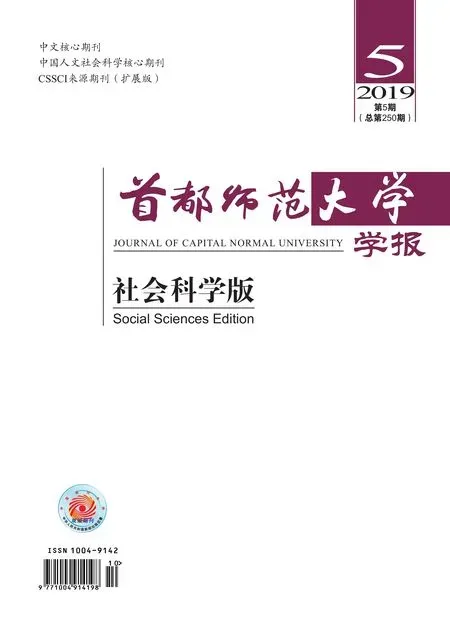生态帝国主义在澳大利亚:以灌溉农牧业的发展为重点(1830-1860)
乔 瑜
引 言
“生态帝国主义”是由克罗斯比在《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1)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中提出的。他将生态与帝国这两个重要的概念连接在一起,这种连接蕴含着对殖民主义的生态解释:克罗斯比认为,欧洲移民能够在全球的温带地区立足,不仅是因为军事、经济、文化和制度优势,其背后还有持久、系统且不对等的生物交换佐助。生物交换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诸多温带殖民地从生态学上适宜欧洲人生存,也帮助欧洲人在以上地区迅速获取人口数量优势,欧洲人最终将这些地区改造成为“新欧洲”(neo-Europe)。
克罗斯比提出的这一命题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与书写,也极大地启发了澳大利亚的环境史研究,尤其是农业环境史研究。澳大利亚的学者意识到,他们的研究目的不仅仅在于为世界环境史的研究版图增添了一个新的地域,作为“新欧洲”的有机组成部分,澳大利亚近代以来的经历与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浪潮密切相关。他们研究的意义还在于拓宽全球视野,揭示跨洋的生态与多元文化互动。澳大利亚学者在这个框架下进行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个案研究。在《生态帝国主义》初次出版近十年后,汤姆·格里菲斯和利比·罗宾将部分成果收入论文集《生态与帝国:拓殖者社会的环境史》(2)Tom Griffith and Libby Robin ed., Ecology and Empi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ettler Societi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7.有关这一问题,亦可参见包茂红:《澳大利亚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这些研究从个案出发考察生态因素是如何在帝国边缘的殖民进程中发挥效应的。但是克罗斯比的这一框架在澳大利亚的适用亦有局限:第一,克罗斯比本人曾在书中指出,澳大利亚等地因其独特的内陆环境和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生物系统并未能彻底被改造。但是克罗斯比重点解释了生态与帝国在殖民地的互动,并没有对“新欧洲”的生态限度,即在“新欧洲”的“非欧”环境中建立欧式农业、畜牧业所遭遇的困境和阻碍有充分考量。第二,克罗斯比强调“新欧洲”的建立依靠的是欧洲人携带的生态资产,实际上澳大利亚的边疆推进更仰仗土著居民传统的资源管理技艺所维护的“非欧”环境。克罗斯比对土著居民的特殊农耕实践的存在,以及殖民进程中土著居民主动的生态适应也未给予特别的重视。
从上个世纪末以来,在英帝国环境史的滋养下,大洋洲的环境史研究被置于帝国与全球视野之中,这类研究是对克罗斯比具有整体视野的全球环境史的新推进。詹姆斯·贝缇提出“环境焦虑”解释帝国扩张进程中殖民地的陌生环境、短时间内的资源短缺和生态危机是如何催生殖民者的生态忧虑和朴素的资源保护行为的,随后他又与其他研究者提出“生态文化网络”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帝国扩张引发的生物、生态经验交换及其环境影响。(3)James Beattie, Edward Melillo and Emily O'Gorman, eds., Eco-cultural Networks and the British Empire: New Views 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詹姆斯·贝缇等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帝国的生态限度之疑。这些研究也开始关注帝国网络所及之处非欧洲族裔的传统生态经验。这些理论上的突破启发了本文对于澳大利亚境内生态帝国主义的思考。
灌溉农业是全面分析欧洲在澳大利亚生态扩张的极好个案。首先,灌溉农业并非单一物种抑或病菌的生态“入侵”,它是欧洲人企图在全新环境条件下进行欧式农耕所创造的一种生态复合体,包含了物种交流、生态实践和社会经济诉求等多个层面的生态扩张;其次,澳大利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对灌溉农业设置了极大障碍,土著居民对于土地的诉求亦是灌溉农业推行的现实阻力,所以它自身也应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变动处于动态的变化和调整中。因此分析澳大利亚灌溉农业的发展史不仅可以呈现殖民扩张的生态层面,还将清晰展示这一过程中具体而复杂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纠葛,不同种族间的生态矛盾,以及土著居民在强大环境压力下的生态调节。本文将以灌溉农牧业的发展为中心,呈现欧洲人试图在澳大利亚建立“新欧洲”的过程及其对土著社会的冲击、土著社会的生态反馈,并进一步分析影响这一历史进程的动力。
一、灌溉农牧业发展的生态起点——土著居民的环境管理
土著的环境管理客观上为欧洲人到来后的灌溉农牧开垦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改造了澳大利亚大陆的景观,是新移民所仰仗的生态遗产。如果没有土著居民千万年以来的环境管理,欧洲人开辟“新欧洲”的进程将更加艰巨与缓慢。
土著居民不是现代农学意义上的农夫,不对土壤进行耕作,不圈养动物。火是土著管理和经营土地的工具。在欧洲人1788年到达澳洲时,生活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大约有25-30多万人,分处于500多个部落,遍布在大陆各地。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尽相同,大多数生活在东南部的海滨、河岸、林地,少部分居住在中部的沙漠以及西部北部沿海。(4)比尔·甘觅奇:《地球上最大的庄园:土著人如何塑造澳大利亚》,段满福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土著居民是采集狩(渔)猎者。在一年中的多数时间里,土著人在各自的部落领地内以几个家族为小群体生活或者迁移。在欧洲到来之前,澳洲的土地已经被土著经营了成千上万年。土著人通过长时间内使用火控制丛林猎物,提高土壤肥力。经常的烧荒使枯枝落叶化为肥料促进野草的生长,新生的小草嫩芽不仅是土著居民的绿色蔬菜,烧荒后草地的生长也更适合动物的栖居,它会吸引袋鼠、小沙袋鼠和其他动物,这些正是土著捕猎的目标。经常的小规模烧荒不仅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更高,也避免燃料日积月累引发毁灭性的大火灾。(5)比尔·甘觅奇:《地球上最大的庄园:土著人如何塑造澳大利亚》,第39页。
土著居民长期持续的烧荒也改变了澳大利亚的自然景观,制造和维护了以桉树为主要树种的疏林,以常年生深根草类为主的地表植被覆盖。这种景观成为欧洲人进行农牧开垦的生态基础,大量被烧荒平整过的疏林草地的存在更是为后来的灌溉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澳大利亚东南部相对湿润的地区,土著最初生活的土地上覆盖有木麻黄属的各种常绿乔木、本土柏树、松树、桉树以及热带雨林物种。乔治湖等处土壤沉积中的谷物孢粉学分析显示:湖区最剧烈的植被改变发生在13万年以前,草地和桉树开始在湖区占据主导地位,土壤层中碳的猛增表明火的使用一定程度降低了树林的多样性。(6)比尔·甘觅奇:《地球上最大的庄园:土著人如何塑造澳大利亚》,第61页。也就是说,在土著持续用火的情况下,木麻黄树、松树和柏树都没有办法和耐火的桉树竞争。经土著改造而成的树林呈现出在山坡平原比较稀疏、沿河地带比较密集的特点。土著居民又通过常规的用火防止桉树过分密集的再生长。疏林下部是丰厚的海绵状土壤,被深根的草皮覆盖。山坡的土层较浅,树少,为浅根草皮覆盖。如果没有长期持久的火烧,澳大利亚会有更多的灌木林,而不是疏林,这无疑极大的降低了欧洲人进行农业开垦的难度。更重要的是,土著居民长期持续的烧荒改变了澳大利亚的自然景观,为澳洲大陆制造了一个条件优厚的人工草场。
二、灌溉农牧业的生态扩张及其限度
灌溉这种农业管理方式是由欧洲人带到澳大利亚的。从英国人登陆澳大利亚大陆开始,伴随着舰队而来不仅有罪犯,军人和平民,还有大量各类动植物。其中重要的植物成株和种子有英国草籽、柑橘(citrus)、柠檬、葡萄藤、无花果、苹果、梨等。(7)Australia Bureau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Commodity Statistical Bulletin,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89, p.10.它们主要来自于英国和欧洲大陆,是英国人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所必须的生态资料。这些物种在英国温润的气候和比较适合的土壤环境中得到充分的生长。但它们在澳大利亚的生长则面临着多重挑战,其中之一就是澳大利亚的干旱气候。因此,在澳大利亚的畜牧业繁荣之前,殖民者已经开始通过灌溉进行小规模蔬菜、果物的培育,服务于日常生活,这些不多的灌溉地面积大概在5-6英亩之间。(8)W.Howiit, Land,Labour and Gold: or, Two Years in Victorian with Visits to Sydney and Van Diemen’s Land,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1855, pp.146-147.
19世纪2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迎来了“羊毛繁荣”。畜牧业最先发展的地区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河谷地和沿海湿地山坡。随着畜牧业进一步向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带深入,降水量递减而蒸发量递增,如果要提高畜牧业产量,就必须在少雨期进行灌溉。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劳顿谷(Lyden Valley)和瓦库尔谷(Vakel Valley)等地殖民者开始经营灌溉牧场。1822年亚历山大·瑞德(Alexander Reid)在克莱德河(Clyde River)附近开辟了面积约为1400英亩的灌溉牧场。1837年底瑞德出售牧场时,所登广告着重的标出牧场亮点在于拥有从克莱德河引水进行灌溉种植的英格兰牧草。麦克·芬腾(Mike Fenton)曾经在印度服役28年,退役后被授予了迪文特河(Derwent River)的支流沿岸1970英亩土地,麦克·芬腾是第一个将灌溉和水车结合起来使用的人。(9)L.L.Robson,“Michael Fenton,”in Australia Dictionary of Biography,Vol.1, 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68, p.31.他雇人开凿出了一条水道,利用河流下游水进行灌溉。(10)C.L.Watson, “Irrigation,” in J. Russell and R.F. Isbell eds., Australian Soils: the Human Impact,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sland, 1986, pp.334-56.此后托马斯·帕里莫尔(Thomas Parramore)在维特莫(Wetmore)(3062英亩),山缪·霍顿(Samuel Horton)在桑末科特(Somercote)(1045英亩)都陆续开始了灌溉牧场的经营。在这一阶段,由于不少牧场主为牧场租借人(Squatter)(11)牧场租借人一词源于英国历史上对要求占地定居农村者的蔑称。在澳大利亚,该词失去原来的本意,而是指代19世纪非法占用超过定居限制的王家土地的放牧人。牧羊人的非法占有开始于19世纪初,牧场占有者的占地行动客观上促进了澳大利亚羊毛产业的发展和牧场占有者这一社会阶层的力量壮大。,租赁土地和放牧的活动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他们可以在干旱的情况变得严重之前出售土地或者搬迁到气候环境相对优越的地方去,所以对于灌溉的投入也是相对有限的,并没有建设大型的灌溉工程。另一方面,要进行更高要求的灌溉农业仅仅依靠牧场主的经济条件也没有办法完成。所以租地牧场主更多的依赖自然条件的优越,选择靠近河流的地段开展畜牧作业和少量种植。
灌溉农业的规模在19世纪中期的拓荒运动中进一步扩大。淘金热后,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滞留矿工成为新农民,他们身体强壮而且有志于从事农业生产。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两地陆续颁布《选地法》,平民可以用较低价格购得牧场租借人所占土地。由此,大量农民陆续来到古尔本(Goulburn)河谷,北部平原(North Plain)和吉普士兰(Gippsland)等地区,加入到了开辟良田、建设家园的拓荒运动中。(12)P. J. Hallows and D. G. Thompson, The History of Irrigation in Australia, Mildura: ANCID, First Mildura Irrigation Trust, 1995, p.18为了避免出现大地主借机囤地的现象,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的法律限制了个人选地的上限为320英亩,此后略有调整但是幅度不大。这样的规定在使大部分自由劳动力能够比较容易获得土地的同时减弱了农场主个人抵御危机的能力。320英亩的农场规模只能适用于比较肥沃的土地和资源条件,这种限制使得轮耕无法进行下去,这对于维多利亚州北部平原等较为干旱的气候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一旦遇到极端干旱的气候情况,农场主自然就无法承受旱灾的袭击。如果要在较小规模的土地条件下生存下去,必就保证中小农场的农业用水,进行更加集约化的生产。农场主开始寻求合作扩大蓄水规模,殖民地政府也开始介入。在维多利亚殖民地本杰明·诺德(Benjamin Node)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大西北水渠灌溉计划”,希望将维多利亚古尔本河的水向西引,浇灌广阔的北部平原。该计划的执行也标志着灌溉农业由私人事业成为殖民地的公共事业。(13)P. J. Hallows and D. G. Thompson, The History of Irrigation in Australia, Mildura: ANCID, First Mildura Irrigation Trust, 1995, p.32.截止到1860年,维多利亚与新南威尔士约有3000公顷土地被灌溉。(14)A.S. Kenyon, “Irrigation in the Early Days,” Journal of Agriculture Victoria (JAV), 1912, pp.658-661.
灌溉农牧场引发了急剧的景观变迁:土壤夯实、水流加速进而压缩水源。在土地被开垦之前,澳大利亚东南沿海的土壤松软,水可以渗入而不流走,因此较少的雨水就可以维持较多的植物生长。在牧场取代疏林后,土壤质地发生变化,牛羊的踩踏让土壤变得紧实,上层土更容易被吹走,小山更容易滑落,进而导致水沟干涸、泥沙阻塞。而流入溪流和河流的水也使得整个地表水流变快。急速流动的水冲刷着水沟,河床被冲刷得很深。墨累—达令流域是澳大利亚最大水源地,这里曾经遍布季节性的小水塘。但是为了发展灌溉牧场和灌溉农业种植,这些季节性的蓄水地都被排干。后来人们还从沼泽引水,农牧场附近的沼泽也被排干。1860年代,墨累—达令流域的一半水源已经消失。水坝和灌溉系统代替了这里的一切,这些变化也使得干旱情况更加严重。
作为生态扩张的灌溉农业自身也面临着水土不服。灌溉牧场引发了部分地区的土壤盐碱化和土壤肥力退化。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朗顿(Loddon)和维库(Wakool)山谷等地,土壤表面原本的盐碱化程度就很高,部分地区地下水位很接近地表。自然力持续不断的冲击使地下盐水安全地保持了地表以下的动态平衡。19世纪50年代后,随着灌溉的开展,水位不断上升,盐分析出地表,盐碱开始渗漏。殖民者用冬眠的葡萄藤、果树代替当地的常绿植被,继而大范围的牧草漫灌更加剧了这种不平衡。19世纪60年代后期,盐碱化导致克朗(Kerang)灌溉区和巴尔河区(Barr River)的生产力下降了三分之一。(15)Ann Young,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Australia since 1788,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51-63.此后农民通过开挖排水渠、平整土地、改长宽畦为短窄畦等方法进行治理,土壤的盐碱化得到了稍许控制,但仍时有反复。
而从长久来看,澳大利亚内陆地区土壤与干旱的气候也成为灌溉农业推行的持续阻力。在主要从事果园种植的米多拉(Mildura)殖民地,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夏季的缺水,这不仅会影响作物的栽培,水流的下降甚至断流还会影响水上运输。殖民地不得不减少果树的种植面积。牧草漫灌持续加剧了盐分失衡和盐碱渗漏。遭遇严重旱灾的情况下,灌溉区无水可用,土地退化,甚至又重新变成荒野,新农民落难而逃。实际上,殖民地的农民很少有足够的资金储备,两三年的歉收就足以让他们破产。农民破产后自然无力偿还购地贷款,只有选择逃避或出售土地。在这些地区“新欧洲”从未能够建立起来。
三、灌溉农牧业扩张造成的土著社会生态危机及其应对
欧洲人畜牧、农耕灌溉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是获得草场、田地和河流。在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土著居民逐水草而居。为了尽快占领土地,租地牧场主使用了军事暴力驱赶土著居民,签订欺骗性的土地合同截断土著们对土地和水资源的自由使用。更多时候殖民者会在与土著居民未达成任何谈判协议的情况下占领澳大利亚土地。1830年代,墨累河南部白人与土著直接因由土地与水资源争夺发生数十次争端,土著大部分时候只能以偷袭或者偷盗白人所畜牲口的方式来反击。朗斯戴尔(Lonsdale)当地甚至于成立了本地警察队(Native Police Force)来维护白人牧场主的利益,对土著进行严厉打击。而在很多地方,白人牧场主则以“私刑”的方式给土著的反击以惩罚。1844年麦考瑞河沿岸的平贾拉(Pinjarra),牧场主斯特灵(Stirling)下令袭击偷盗牧羊的土著人部落,结果土著死亡30人。(16)The Age, Melbourne, January 13, 1881, p.3.
因此,欧洲人灌溉农牧经济的发展是以驱赶和迫害土著居民为前提,以土著社会的经济生活遭受破坏为代价的。渔猎曾经是东南部土著居民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他们通常会沿河流布下捕鱼陷阱。每一个陷阱都由3、4个横跨河流的石墙组成,每个石墙都有枝条或是灌木做的入口,这样鱼可以在陷阱内部自由的活动。土著居民被赶出河流及其附近区域后基本丧失了这一重要的食物来源。(17)Simon Ryan, The Cartographic Eye: Scopic Regimes in Journals of Australian Exploration, Sydney: St. Lucia , 1998, p.196.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殖民者对牧场面积的要求继续扩大,土著居民被要求一次次搬迁。土著居民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被强行改变也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生活。在欧洲人殖民之前,澳洲大陆存在大量有袋哺乳动物,这也是土著的肉食来源之一。环境的变化,白人故意的捕杀让大量有袋哺乳动物在短时间内迅速灭亡,取而代之的是欧洲大陆来的狗、牛、羊。畜牧业的推进更是加速了这个过程。除此之外,人工草的种植几乎摧毁了土著赖以为生的薯类植物。(18)比尔·甘觅奇:《地球上最大的庄园:土著人如何塑造澳大利亚》,第96页。
但是不同于生态帝国主义所描绘的“无声”消失的土著居民,澳大利亚土著以进入白人农牧场工作的方式来应对生态危机,在生存空间持续压缩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习得全新的生态语言,放弃迁徙游牧转而进行现代农学意义上的农田耕作,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来获取生态资源,尽管这样的应对很多时候是无力的,但是这种“软”对抗行为提供了不同于典型“新欧洲”所发生的生态帝国主义的另一种版本。
在遭遇过最暴乱的短兵相接后数年,一些土著居民就被迫或自愿进入殖民者开设的牧场、农场工作。(19)Ann Curthoys, Race and Ethnicity:A Study of the Response of British Colonists to Aborigines,Chinese and non-British Europeans in NSW, 1856-1881, Phd thesis, Sydney: Macquarie University, 1973, p.56.土著劳工对于殖民者来说是非常好的劳力,他们对丛林环境很熟悉,能够轻易在山林中找到食物,并且愿意进入到白人殖民者不愿意去的边远地区。对于土著居民来说,在丧失了大量土地后,部落已经不具备进行传统迁徙狩猎采集的客观条件,进入白人的牧场工作,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和传统土地的联系。而那些没有进入白人农场工作的部落成员,就被迫迁居到分散在新兴农牧业中心的边缘地区。由于游猎生活所依赖的生态链条被打断,加之内陆自然环境的限制,这部分土著居民逐渐发展起农牧生产且渐剧规模。他们清空了土地上的植被,进行土地开垦和庄稼种植,主要种植麦子和牧草。(20)Diane Barwick, “Coranderrk and Cumeroogunga,” in S.Epstein and D.Penny eds., Opportunity and Response: Case Stud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47.除了满足基本的粮食需求外,土著居民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并拥有“财产”。在克拉瓦拉(Killawarra)土著居民建立起了三个较大型的农场,占地均在20公顷左右。(21)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P Register of Reserve Folio, 20, Canberra: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Press, 1996, p.60.农场有牧羊200-300只,种植烟草、西红柿和玉米,其中部分用于销售。(22)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P Register of Reserve Folio, 20, p.61.有的农场主还拥有马匹和二轮马车,甚至还有自己的船只。这部分土著居民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原来的迁徙游猎,转而依赖定居农耕。(23)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P Register of Reserve Folio, 20, p.65.很多土著部落的家庭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劳动分工格局:妇女、儿童、老人和部分的成年男子留守在家庭内部从事家务劳动、农牧作业,维持原有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另一部分成年男性则出外在白人农场或者牧场做工,获取一定的现金收入,这部分收入也构成了这些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
但是灌溉的推行使得土著劳工和白人农、牧场主之间的雇佣关系越来越不稳定。在1850年代拓荒运动的推进过程中,为了满足激增人口的土地需求,殖民地开始执行“近距离定居”计划,推广集约化的小农家庭经济,灌溉农耕的规模继续扩大。随着灌溉农业的推进,畜牧业逐渐被转移到了北部,南部以及东部新兴农业带的边缘。小型农场取代了之前蔓延的农牧站。东南部沿海粗放式的伐木业和畜牧用地转而变成了依靠灌溉的密集型农业用地,主要用于小麦和少量牧草种植。这些农场对于土著劳力的需求远远低于之前的白人牧场主。并且随着种植带的推进,还有大量土著被驱赶出了已经有效开垦的土地,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也被破坏,不得不生活在因灌溉农耕而繁荣起来的城镇边缘,逐渐陷入贫困。(24)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P Register of Reserve Folio, 20, p.73.
在这种情况下,土著开始用多种方式向白人殖民者索要土地。很多时候土著居民会邀请一位白人警官或者教士,向殖民政府传达他们的愿望。这些警官和牧师通常与土著居民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在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和公信力,往往也对土著居民抱有同情的情绪。(25)Charles Rowley, The Destruction of Aboriginal Societ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430.1865年,一位部落首领巴拉克(Balurk)向牧师马卢加(Maloga)表达了这样的请求:“我们希望有充分的土地用于耕种,蓄养牲口,用几年时间慢慢能够维持家庭的开支,用我们的产业支持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求的是一种补偿,因为所有原本在部落界内的土地都已经被政府和白人殖民者夺走。”(26)Diane Barwick, “Coranderrk and Cumeroogunga,” in S. Epstein and D. Penny eds., Opportunity and Response: Case Stud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47-49.牧师使用了基督教的语言和欧洲人的产权概念来描述土著居民的请愿,请求政府“为我们在这片广阔的国土上保有小片土地,因为拥有土地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力”。(27)Charles Rowley, The Destruction of Aboriginal Societ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78.少部分土著居民对于土地的正当需求获得了白人殖民者的短暂许可。但是对于大部分土著部落来说,他们并没有能够在他们已经“占据”的土地上将土地所有权合法化。(28)Charles Rowley, The Destruction of Aboriginal Societ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40.土著居民的牧地和农地基本位于白人殖民城市的边缘地带和农场交界处的无人占领区,面积狭小,流动性也很大。土地随时面临被白人掠夺的危险,土著居民渴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增加土地产出改善生活。因此土著居民想尽办法最大限度地榨取土壤养分。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是小规模环境破坏的制造者,也是环境影响的承担者,而后这种“破坏”亦成为殖民者推行科学农业的理由。但是客观上他们对于土地和水资源的要求成为白人殖民者必须面对的生态与文化制约。
四、推动灌溉农牧业扩张的主要动因
首先,灌溉农牧业的扩张受制于生态环境的驱动。英国人的殖民正式拉开了澳大利亚物种引进的序幕。但是在没有人工干涉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的本土环境很多时候并不适合这些物种的生长。换言之,在澳大利亚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下,新物种的引进必然会导致灌溉的发生。英国属于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凉爽湿润。澳大利亚全国面积中约有四成位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六成属于温带,降水量从北、东、南三面沿海往内陆递减,植物带也相应由沿海森林向大陆中心逐渐进入草原、荒漠带。澳大利亚大部分国土位于南纬30°左右,强大的高压中心从西向东掠过国境,给澳大利亚带来连续不断的晴朗天气。东部边缘隆起的山地,减少了海洋对内陆的影响,广大地区地势低平,很难形成地形雨。澳大利亚降雨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年季变化大,年内则呈现季节性的分配不均。(29)W. P. Gange and S. J. Hutchinson, Water in Australia, Melbourne, Canberra: Cheshire, 1967, pp.16-31.因此要在澳大利亚境内种植英格兰牧草、蔬菜、果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保证适时并且合理的浇灌量。
灌溉牧场所引发的物种替代进一步推动了灌溉系统的规模扩大。养羊业兴起后澳大利亚原有草种逐渐被英国草种所代替。澳大利亚当地常年生的深根草种适应于澳大利亚干旱和湿润的气候循环,以及有袋动物的吃食和软蹄的踩踏习惯。山坡和平地上的深根草都是成块状分布的。它们的块状分布可以在干旱季节里保护植物的根部。植被在气候恶劣的年份保住自己占据的地盘,然后在好年份中充分的生长。有袋动物也不是有攻击性的食客。他们小口啃食植物底部,而将种子穗留给鹦鹉和麻雀,这样保留下来的草根在雨季就可以再次生长,种子也在所到之处生根发芽。而羊群坚硬的蹄子会让土壤变得坚实。它们对食物是选择性的,只吃它们喜欢吃的草。并且它们吃掉整个植物,包括底部的叶子和穗子。在食物短缺的时候,它们就会吃掉草丛下面的保护根。很快深根的草类就被过度的啃食了,它们的种子没有机会得到繁殖,也无法在坚实的土壤中生长。(30)Division of National Mapping, Soil and land Use. Volume 1, Atlas of Australian Resource, Third Series,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80, p.56.在许多地区,本地多年生的可食性草类竞争不过其它的物种,尤其是殖民者引进的一年生英国草种。英国的草种很快就占据了山坡和土壤变得越来越坚实的平原。这些一年生草类在夏季少雨季对水的需求更大,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灌溉面积。(31)William Howitt, Land ,Labour and Gold, Kilmore: Lowden Publishing, 1972, p.76.另外,《选地法》所规定的320亩的人均占地上线人为制造的生态瓶颈,也推动了灌溉农业的生产规模扩大。
其次,殖民地经济也助力了灌溉农业的扩张。从19世纪中期开始,澳大利亚主要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经济全面繁荣。首先是“畜牧业时代”全面开启。当时英国的纺织业发展迅速,澳大利亚的羊毛也因此供不应求。从1820年到1850年,澳大利亚出口到英国的羊毛从970万磅增加到7420万磅,约占英国羊毛进口数额的一半。(32)Alan Barnard, The Australian Wool Market, 1840-1900, Victor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218.在灌溉条件下葡萄、橘子的培育获得了成功。(33)C. J. Lloyd, Either Drought or Plenty: Water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in New South Wales, Parramatta: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1988, pp.164-166.葡萄酒的酿造也由此兴起,19世纪30代初勃艮第葡萄酒的总产量达到9万升,并开始供应出口。悉尼、墨尔本等城市中设立了销售机构和金融机构来组织羊毛和其它殖民地产品的出口以便利资本和消费品的输入。伴随着澳大利亚的羊毛牧场和葡萄酒酒庄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也受制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宰制。澳大利亚的灌溉规模在本国农业更深卷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张。(34)E. Dunsdorfs, The Australia Wheat-Growing Industry 1788-1948,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78-89.
最后,澳大利亚独特的种族主义生态文化也影响了灌溉农牧业的扩张。在欧洲人看来只有在土地上发展定居农业、建造城镇的居住者才具有土地所有权,无人居住或是居住者没有采用“有效”开发方式进行利用的土地就是荒地(terra nullius),他人可以自由获取。所以最初殖民者将夺取土著土地视为理所当然。而现在土著对土地的开垦和利用已经“提升”。土著居民土地产权观念的变化显然引起了白人社会的警觉。在对当地的一份调查报告中,白人殖民者认为土著居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悄然发生变化——诞生了一种原始与现代并存的混合性概念。随着农牧定居生活的日益普遍,土著已经认可土地作为个人私有财产的概念,承认并接受土地的自由买卖。尽管没有土著居民对这种概念进行详细的解释,但是很明显居民普遍认为“最高神明”赋予了他们拥有土地的权力,这正是马卢加在请愿中所说的“拥有土地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力”。土著居民在每一个申请和要求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情绪,通常的表达是“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拥有土地”。(35)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P Register of Reserve Folio, 20, Canberra: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Press, 1996, p.45.土著要求土地的运动对白人的土地所有权构成了威胁。
为了能够理所当然的占领土地,驱赶土著,殖民者针对土著居民的生产生活,生态实践展开评述:其一,从古代开始直到殖民时代,土著不科学的用火使得澳大利亚丧失了热带雨林,澳大利亚土著的狩猎导致了大型动物的灭绝,即对土著烧荒引发的森林景观退化的判定。(36)O.C.Stewart, “The Forgotten Side of Ethnogeography,” Method and Perspective in Anthropology, Papers in Honor of Wilson D. Wall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54; A.R. King, Influence of Colonisation on the Forests and the Prevalence of Bushfires in Australia, Canberra: CSIRO, 1963.其二,殖民时代以来土著居民不科学的耕作对土壤产生了巨大的破坏,给澳大利亚的环境带来了伤害。英国殖民者认为土著在所圈土地上的耕作引起了澳大利亚土壤养分的流失。(37)R. Gatty, “Colony in Transition,” Pacific Affairs, Vol.26, No.2, 1953, p.127.第三,澳大利亚干旱的气候成为阻止土著居民更好的在这片大陆定居的障碍。在殖民者看来,澳大利亚具备成为一个伟大和丰产大陆的潜质,但是由于土著的低劣和无能,澳大利亚将会有停滞和倒退的危险。因此殖民者提出,要优化澳大利亚需要两个转变:第一,大量的白人移民;第二,在干旱缺水的澳大利亚可以依靠灌溉农业来完成澳大利亚的复兴。(38)参见拙作:《澳大利亚灌溉叙事的演变及原因》,《世界历史》,2018年第6期。
澳大利亚的干旱环境和土著生态调节所伸张的环境权力实际上构成了欧洲人不得不应对的生态与文化限度,引发了白人殖民者的生态焦虑。灌溉农业被认为是化解这种焦虑的最好方式。在拓荒时代,灌溉农业引导的乡村建设以集约化的小农生产和优美的景观为特征,被认作是对工业革命前欧洲田园牧歌生活的复兴,灌溉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史上开始拥有特殊的地位。它帮助殖民者实现了长久以来的梦想,把这块棕色土壤变成绿色,让沙漠开花繁荣。盐碱化问题的初步控制和农牧生产的持续繁荣使澳大利亚整个社会对于灌溉的信心进一步巩固,对于农业科学技术的信心陡增。此时正是英帝国灌溉工程技术和土壤科学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农业开始使用肥料,牲畜的品质得到了巨大的提高,更多的作物品种被选种和培养,整个农业产量都得到了提高。最终,帝国农业成为世界农业的榜样。
五、结论
土著居民长期以来的环境管理改变了澳大利亚的生态景观,也在客观上助力了灌溉农业的起步与发展,是生态帝国主义在澳大利亚发端的起点。而作为一种生态复合体的灌溉农业,从其进入澳大利亚起就与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裹挟纠缠:澳大利亚与欧洲迥异的气候、土壤条件决定了在澳大利亚进行欧式的农业种植和大规模畜牧业就必须进行人工干预。而淘金热后骤增的人口压力则进一步推动了灌溉农业的扩张。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种族主义导向的生态文化中,灌溉农业被描述成最具生态优越性的农垦方式,不仅先进于土著居民的“刀耕火种”,还迎合了欧洲人的田园梦想。
而灌溉农业在澳大利亚的扩张不仅直接改造了土著居民环境管理所塑造的景观,也彻底改变了土著居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轨迹。灌溉农业的扩张过程中田园牧歌从来都只是愿景,从本质上说灌溉农业的生态扩张直接服务于英帝国的资本扩张,因此也难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冲击。灌溉农业扩张之处,田野成为工厂,水成为资本,灌溉农业在内陆地区引发的包括土壤盐碱化在内的生态退化更是将绿色的乌托邦中残存的美学属性摧残殆尽。尽管移民们也认识到,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各样植物可能非常不适合在澳大利亚的环境中生长,但是他们更相信作物产出可以通过改良品种来提高,土壤出现的问题可以用更加科学的耕作方法和手段来解决。各殖民地政府和农场主个人对于技术可以提高生产力愈发深信不疑。这种信念更使得人们对于灌溉农牧业出现的问题不以为然。
上个世纪60年代,殖民时代开辟的内陆农牧场几乎都放弃灌溉作业转而依靠旱作农业。盐碱化导致的生态危机在时隔百年后终结了灌溉农业的生态扩张,灌溉农业的边界全面退回沿海地区。气候与土壤条件就是灌溉农业在澳大利亚扩张的生态限度。尽管在殖民进程开启后短短的数十年间,伴随着源源不断的欧洲移民进入,澳大利亚已经成为全球最“白”的国度,欧洲人的生态旅行箱(39)这是克罗斯比在《生态帝国主义》中提出的概念,生态旅行箱指的是欧洲人所携带的来自旧大陆的杂草、病菌等等生态工具,生态旅行箱帮助了欧洲人在新大陆的殖民扩张。也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澳大利亚的环境,但是从生态环境的改造和利用角度来说,澳大利亚的灌溉区从来都没有成为“新欧洲”。欧洲人在澳大利亚的生态扩张并不意味着土著居民历史的终结。从殖民时代开始,土著居民不仅习得了新的生态技能,甚至还掌握了全新的生态权力语言。他们需要土地用于农业耕作,作为对传统经济资源流失的一种补偿。他们对土地的要求一方面来自于直接的生存之需,另一方面则是把土地作为经济支持,进而成为加入资本主义乡村经济的基础。最终,灌溉农牧业的扩张将土著居民推向了无尽的荒漠,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生态牢笼面前他们的抵抗和澳大利亚土地的申诉一样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