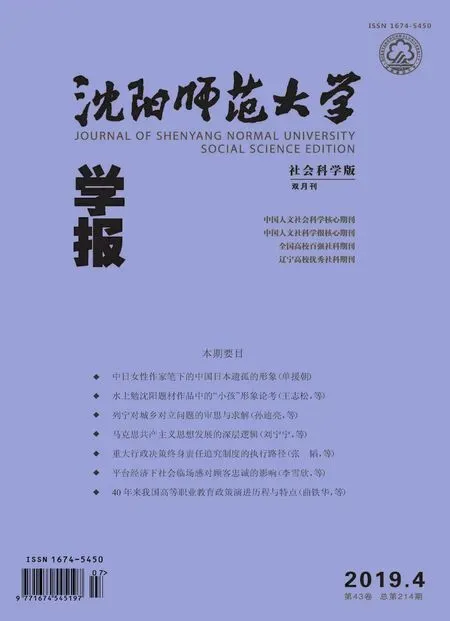“非遗”保护理念下满族刺绣技艺传承与创新
唐保平
(沈阳师范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我们能了解到的满族刺绣艺术从刺绣的创作发生与服务对象来看,一方面来自宫廷,另一方面来自民间。清代宫廷刺绣随着王朝的覆灭也走进了尘封的历史,我们欣赏宫廷刺绣艺术主要来自博物馆保存的刺绣文物;满族民间刺绣艺术伴随大众生活需求在满族人口集聚地区世代相传保留下来。从满族风格独特的刺绣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其蕴含的鲜明民族精神与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满族民间刺绣保存着农耕时期特有的创作思维方式与造型特点,题材内容博大,想象力丰富,针法独特,绣工精美,不仅装饰与美化生活也充分反映出满族人的道德观念、审美习俗和理想追求。然而,满族民间刺绣艺术在近代遭遇大众审美观念的改变与现代机器工业生产的冲击,刺绣艺术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
一、“非遗”概念与相应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非遗”概念的由来。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提出要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代相传以各地区民族集聚地为主要存在场所,在人们适应自然与周围环境互动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不断得到创新,它促进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并形成维系群体关系的文化认同与历史使命感。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
“非遗”保护,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形式的确认、立档、研究、宣传、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弘扬等[2]。回顾我国“非遗”传承与发展事业走过的历程,从认识“非遗”到立法,从筛选保护内容、保护措施、保护试点、成果推广等,整体保护工作是系统与循序渐进有法可依的过程,从宏观到具体以点带面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从发展时间看,我国于2004年8月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第一次提出要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到2010年,我国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到2015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
二、满族民间刺绣手工艺的发展现状与“非遗”理念下的手工艺保护
(一)满族刺绣手工艺的历史面貌与当代发展
传统手工刺绣艺术是中国孕育在各民族生活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手工艺,刺绣艺术由于其材料特征、审美表达、工艺特点成为以民间妇女为主要创作者的手工艺门类。满族民间刺绣是满族集聚地的先民从最初的“钉线补绣”最原始的服饰修饰方法发展到体现不同针法、色彩、造型,不同寓意内涵的刺绣作品,从“无意识”的实用向有目的的审美装饰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满族民间刺绣在发展过程中借鉴汉族与其他民族刺绣技艺并结合满族人生活特点创作出具有满族特色的刺绣艺术。
满族刺绣工艺在过去是满族女性在出嫁前必修的技艺,她们通过纤细的钢针、彩色丝线绣出内心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刺绣作品包括:枕顶纹、香囊、荷包、围裙、肚兜、鞋垫、鞋面等,在东北地区具有广泛的普及性,它表现出鲜明的满族民间特征,并用特色的“图案设计”作为主要创作风格展开。满族民间刺绣在日常生活中的装饰主导地位与作用在近代发生微妙变化并逐渐加剧。伴随近代工业技术发展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推进,新材料、时尚流行、抽象美学在改变大众的审美取向,刺绣手工艺被高效率的工业流水线生产取代,机器生产逐渐取代传统手工艺生产,刺绣手工艺日渐萎缩。如今,满族民间刺绣较少的份额保留在满族集聚地,现集中分布在辽宁锦州、兴城、阜新、抚顺、岫岩、丹东,吉林通化等地区。然而,满族刺绣艺术以承载的深厚历史与文化积淀在当代设计文化发展中愈发引人注目,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了“中国故事”文化展示现场,“盛世龙”浮雕刺绣作品技惊四座。满族刺绣艺术对当代审美设计与文化传播等领域不断激起波澜,受到业内设计师的关注与大众的喜爱。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满族民间刺绣艺术在社会发展新阶段生态环境再次得到社会关注,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产生更广泛更深远影响。
(二)“非遗”理念下的满族刺绣手工艺保护
1.关注传承人群的生存境遇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关键在于对传承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依附于个体、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的“活态”文化[3]。传统手工艺技艺由于活态传承与口传心授的特点,录像、录音、文字记载也不能充分体现传统手工技艺的完整面貌,传统手工艺一旦后继乏人,传承人高龄化突出手工艺的传承便面临断层的困境[4]。从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开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世界申遗、立法,从对传统民族文化物的保护到对传承人保护的转变,表现出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特征、文化影响的清晰认知。依据“非遗”法规对传承人传统手工艺自然情况进行调查、认定与登记注册,以利于对传承人有针对性与有效的保护,如关注传承人的生活情况、工作境遇等。辽宁锦州满族刺绣第五代传承人夏丽云,其作品枕顶《独占鳌头》与壁画《十相自在》获得葫芦岛国际文化节服绣艺术精品奖,2005年7月受到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的接见,充分体现政府对民族刺绣艺术发扬光大的期望与对传承人生存状态的关怀。
满族传统手工刺绣艺术发展要与不同时代社会生产背景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在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阶段,妇女有民众认同的时间去进行刺绣手工艺生产与创作。时代发展,当代女性的社会职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业文明取代了更多的手工劳作,大众审美观念与快节奏生活需求使传统手工刺绣创作模式发展空间变得更加狭窄。当代满族刺绣传承人每天也要忙碌家庭生活为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奔波,无暇从事刺绣手工艺创作。传承人当代表现的生存境遇具有普遍性,个人或某一地区刺绣传统手工艺的成绩还不能代表整体满族刺绣艺术的发展,这需要政府、社区、相关文化机构共同努力与研究长久保护和扶持发展之路。
2.传统手工艺的师承范式在学校教育中的全新体现
学校教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更多体现了工业化的教育思想,高等设计教育体现出精英式教育模式。我国现代高校设计教育以稳定的教学师资、环境、制度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成功证明为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主流文化设计人才。2015年6月,为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当代实践水平和传承能力,进一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文化部启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培训计划”试点工作[5]。并确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20余所院校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培训计划”研修培训试点院校。
(1)打破传统技艺传承的理论局限。满族刺绣传统手工艺行业是当代设计发展中表现民族地域特色的一个特殊的群体,“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与技能教育以师承为主导,手工艺产品经营沿袭传统模式,传承人普遍表现出文化水平与美术设计能力局限,在经营产品的设计理念、加工工艺等方面受到旧有模式的束缚。刺绣传承人群在地域高校研修研习培训过程中,耳濡目染感受现代高等艺术教育的气息,从理论广博涉猎与刺绣技艺现代工艺视野的审视,使传承人从设计与现代生活的观念上有了新的理解,理解了城市生活对美感作品的需求特点,认识自身艺术特色,对满族刺绣艺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坚守有了自信。
(2)立体化教学模式促进传承人设计思维的改变。设计思维体现创作者在作品创作中对作品审美构想与受众审美观念相统一的整体思考。传承人设计思维的开发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内容表现形式跟上时代发展的核心问题,与保护传承人就是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承接的关系。“非遗”传承人也在不断探索不同发展途径,把“非遗”技艺、产品融合到现代生活中,融合到市场进程中,这一过程是体现在最初的作品设计上,是艰难的转变过程,也是“非遗”现代传承后继乏人与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怎样衔接传承人群文化水平不高、美术设计能力表现不均衡的问题,在地域高校承办文化部、教育部国家“非遗”研修研习培项目的过程中,各地区院校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相关学者指导与各地院校培训经验交流的过程里,达到培训师资组成、培训内容理论与设计指导相结合、校内培训与校外考察相结合,形成视觉、听觉、思考与实践多感官联动的立体化教学模式。刺绣传承人在当代审美设计理论与美术基本功素养提高瓶颈问题,在高校美术与设计学院的研修研习培训中将得到有益启迪与相应程度提高。
(3)传承人设计审美认识与实践在培训中得到较好的实现。传承人刺绣作品的审美表现力体现在把握时尚设计构思与实践工艺过程中,审美认识、审美感、审美表现力依据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时代背景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这样,满族刺绣传承人在研修研习培训中通过设计理论学习、设计实践来深入认识当代大众审美发生的原因、特点,结合自身满族刺绣技艺特色,创作出能够深受当代人喜爱的作品。这种对审美需求的判断需要实践指导教师针对学员领会的不同进行引导,在作品设计过程中出现的理论认识、美术基础问题也要进行相应的引导。满族刺绣传承人培训以地域民族刺绣特色传承与发展为基础,在理论讲授、作业实践中,强化地域特色观念,借鉴其他地区刺绣艺术特色,把本地区刺绣艺术独有的风貌展示出来。学员不仅要了解宫廷满绣艺术的发生、发展,也要了解民间其他形式刺绣艺术的表现方式,把满族刺绣与当代设计风尚及实用品有机结合是指导教师与传承人共同思考的问题,满族刺绣艺术作品能够成为当代消费满意的消费品,要满足以上条件。满绣传承人群不仅要表达自身的审美愿望,传承满绣针法技艺,更要把满绣艺术与当代大众时尚审美理念有机结合,使满绣技艺得到发扬,同时也能更好地服务社会需求[6]。
(4)地域高校“非遗”培训拓宽传承人群的概念与范围。传承人在大学校园中与设计专业大学生有了紧密接触,大学生青春朝气在现代设计构思上的突发奇想引起传承人的兴趣,传承人笃实执守业精于勤的精神也感染现代大学生。传承人群在培训中有机会走进大学讲堂,为大学生讲授刺绣工艺经典案例。这一过程是双向收获与提高的过程,传承人要把自己多年刺绣造型与针法绝活展示给大家,一方面是交流,另一方面是自身在短短讲授中对刺绣技艺又有了新的认识与提高。大学生与教师在接触满族刺绣手工艺的过程中也更深刻认识与了解满族刺绣技艺的精髓,在未来设计与传统文化传播中更具有针对性,一些优秀的大学生也可能成为刺绣传统手工艺的爱好者或潜在的传承人。
3.满族刺绣技艺与生产实践性保护
对满族刺绣传承人群生存境况的了解,仅仅解决了认知问题;地域高校传承人群培训工作具有阶段性与灵活性,满族刺绣技艺传承还需要在日常实践中得到真正体现。传统民间满族刺绣手工艺以妇女为技艺传承与生产的主要实践者,手工艺创作以满足日常生活装饰的需要,年轻女性掌握刺绣技艺也是体现自身审美素养与生活技能的标准。在工业技术发生与成为社会生产主导力量以前,刺绣、纺织、缝制服装是妇女日常主要生产实践活动。伴随近代工业技术与经济的发展,手工刺绣生产逐渐被机器刺绣取代,大众审美情趣也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发生着变化,满族刺绣手工艺原有生产模式已经不能再适应现代大众生活的需要。现代生活中,从个体刺绣手工艺传人创作作品到集体公司经营,设计理念、经营资金、公司运营管理等多方面都要跟进社会发展脉搏才能走出自己发展的特色之路,这需要政府的扶持与保护。“非遗”文化生产性保护指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7]。“非遗”传承人结合自身实践与社会资源,可以创办满族刺绣培训机构;参加文创博览会融合“文化+旅游”发展方式,设计创作满族刺绣文化旅游产品;传承人与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培养年轻大学生接触与接受满族刺绣文化设计创作符合时代需要的刺绣作品等形式。
满族刺绣艺术生产实践性发展动力,一方面来自传承人对传统手工刺绣艺术在当今社会发展艺术魅力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来自“非遗”保护概念下社会各界对满族刺绣生产实践性支持。正在实践与成功的例子有:锦州满族刺绣国家级传承人夏丽云积极探索满族刺绣艺术生产性保护模式,从家庭作坊到刺绣培训公司创办,先后得到街道、政府相关部门扶持逐步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带动大批下岗女工与农村妇女就业;辽宁省工艺美术大师兴城第四批非物质遗产传承人董宁创办泰美民俗文化有限公司;沈阳家传第四代传人杨晓桐创建晓桐绣春秋满绣坊、盛京满绣文化研究所,从事满族刺绣创作与学员培训工作等。
三、满族刺绣技艺传承发展在历史新阶段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一)对“非遗”保护观念与发展形式的认同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对静态物的保护到对“非遗”传承人保护的转变,我们感受到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所表现的活态传承历史价值与人文价值的深刻认识。时代发展,当代年轻人对传统手工艺不了解,更多的群众对刺绣手工艺不熟悉,对满族刺绣手工艺的保护不能采取博物馆式保护,满族刺绣传承人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脉络相统一的活态传承才是传统手工艺当代有效发展之路。在“非遗”地域高校研修研习培训实践中,一些专家、学者对新形势传统手工艺传承提出不同观点和问题,比如:高校设计专业作为传统手工艺活态传承的新形势,对“非遗”传承要“原汁原味”,还是要融入现代生活?对“非遗”传承人开设美术基础课程会不会造成对传统文化的背离?是让“非遗”传承人做高校教师的学生,还是聘请传承人大师来讲课?是抢救保护“非遗”,还是经营开发“非遗”?是民间传承“非遗”,还是学院传承“非遗”?另外,还涉及“非遗”进校园与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形式和“非遗”保护侧重点等问题。“非遗”保护中呈现的认识与方法等问题,要在“非遗”保护工作不断深入开展中变得清晰,这需要专家、学者要首先理清,也要让每一位学员与潜在“非遗”传承人理清,这样才能更益于刺绣传统手工艺在现代文化发展环境中有效传承与发展。
(二)“非遗”保护的针对性与持续发展
在“非遗”保护的过程中,相关学者建议基础教育美术教材增设编写传统手工艺内容,基础教育阶段对民族文化传播具有较好的普及性,但美术课时比例相对较少,很多有兴趣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社会培训机构学习传统文化。美术教师不是“非遗”传承人,传统手工文化普及教育结合“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活动,让学生身临其境接触传统手工艺,传承人演示传统手工技艺更有说服力与真实感,但“非遗”传承人进校园的活态传承存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非遗”普及后期跟进表现出不稳定性。传承人开办的刺绣传统手工艺作坊承担刺绣创作与普及性培训,对基础教育学校传统手工文化教育是有效的补充。高校承办的国家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工作对满族刺绣传承人手工艺设计发展的时代感领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由于时间紧凑辐射面广,在刺绣手工艺地域传承针对性、刺绣技法提高、后续培训时间连贯性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高校工艺设计专业对刺绣传统手工艺课程设置与人才配置等问题探索还需要加强,使满族刺绣传统手工艺文化在社会普及与审美设计提高方面得到持续发展而不流于形式。
四、结语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满族先民逐渐发展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文化,其中,满族刺绣手工艺术是其杰出的代表。当今,一方面由于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使曾经令满族人所骄傲的民族文化走到了消失的边缘;另一方面,近代工业技术发展与大众审美观念、生活需求的变化,传统满族刺绣手工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设计与生产实践的影响日趋萎靡。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倡议,我国政府与社会各界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高度重视,抓紧与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工作。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各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优秀的满族刺绣手工艺术在“非遗”保护工作的进程中,生存环境不断得到改善,满族刺绣手工艺逐渐被更多的人关注与接受。在“非遗”保护中,各地政府对刺绣传承人生活境遇的关注,对刺绣传承不同形式的投入,使满族刺绣传承再次焕发新的生机。地域高校承办的满族刺绣传承人群培训对满族刺绣艺术传承人审美能力、设计创作、交流传播等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整体培训活动也得到社会各界与媒体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传承过程中,仍然面临来自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的认知、保护与发展方向、保护方法与手段等诸多问题,而“非遗”保护观念的社会认同与不断发展,满族刺绣传统手工艺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与时俱进,不断繁荣与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