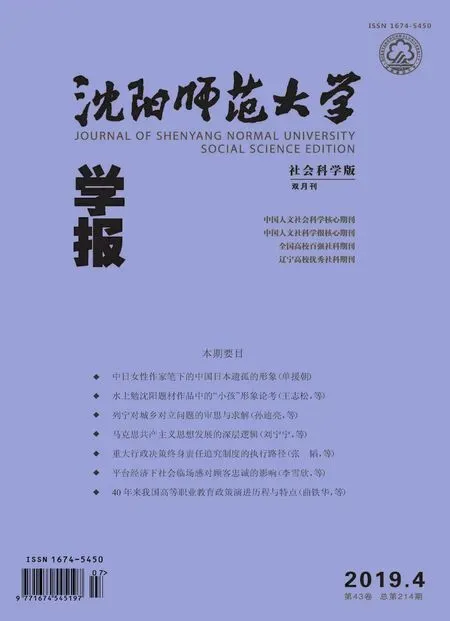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理论的生成轨迹
徐明玉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沈阳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作为理论资源诞生于英国。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戏剧性变革——“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事件”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促使爱德华·汤普森等知识分子与英国共产党决裂,伴随决裂出现的还有英国牛津大学新左翼俱乐部的创建及新左翼杂志的创刊。结合英国的社会现实,新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进行批判和修正,逐步确立了以“文化”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这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滥觞。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创办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建制化的文化研究作为专门的学科踏上了历史舞台。文化研究始于却不止于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都在开展基于本土文化的研究。
英国文化研究始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它从批判经济政治决定论开始关注社会中的文化问题,尤其是文化的政治权力问题。从最初为非精英的工人阶级争取权力,到对黑人群体、青年亚文化群体、女性群体、同性恋等不同族群和边缘性群体的持续关注,都呈现出霍尔领军的文化研究对文化政治权力的关注。霍尔关注不同身份的主体在社会中的“位置”(霍尔语),主体位置即主体身份。从主体到身份再到文化身份是霍尔将身份问题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身份还是认同:问题缘起及国内研究现状
(一)概念引入,界定模糊
1986年林彦群在《南洋问题》上发表《战后新、马华人“文化认同”问题》,首次探究华人在海外的文化身份问题。这是关于身份问题的实践性研究,并未上升到理论高度。文中明确指出,“至于什么是‘认同’,目前尚未有公认的定义”[1]。较早把“文化认同”理论推介到国内的学者应属陶东风,1998年他以《全球化、文化认同与后殖民批评》为题,介绍后殖民语境下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多元文化主义、文化认同以及差异政治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人文与社科界的热门话题”[2]。在这篇文章中,陶东风更多的是在谈及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问题。他认为“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该文并未对“文化认同”进行界定。1999年,王宁尝试界定“文化身份”。“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身份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迹的文化本质特征”[3]。显而易见,该文把“文化身份”与“身份认同”等同起来。
随后,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借鉴西方文化理论,借鉴霍尔对身份的阐释作为理论资源。2004年,陶家俊发表《身份认同导论》和《同一与差异:从现代到后现代身份认同》两篇文章。前者强调了“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及其同西方文化研究的关系。“身份认同(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特别青睐。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这个词总爱追问:我(现代人)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4]后者强调了“身份认同”理论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发展历程,从启蒙时代的以同一为主导的西方现代知识话语,到以差异为话语中心的后现代身份理论。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在文中明确身份认同的概念,不仅如此,在《同一与差异:从现代到后现代身份认同》正文的第一段,作者借用了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文化身份”的表述替代他在标题中呈现的关键词“身份认同”,但是,在接下来并没有对二者关系进行论述[5]。2006年,周宪给国内学者勾勒了文化认同(文化身份)研究的概况:“从经典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到拉康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认同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认同问题作为焦点问题被突显出来”,“其中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霍尔的认同理论特别有影响”[6]。至此,文化认同/文化身份问题才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霍尔的重要性也被凸显。但“身份”和“认同”,“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界定及界限仍不清晰。
(二)概念梳理,内涵不清
通过前期研究的积累,国内学者逐渐意识到身份/认同、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问题的模糊性,并尝试从不同角度厘清、规范这些概念。首次对身份和认同进行区分的学者是阎嘉。继其之后陆续有学者开始关注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的区别(陶家俊、邹威华、罗如春、贺玉高等)。2006年,在《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中,阎嘉关注了英文identity与中文的对应问题。其中提及了“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区别,英文identity在汉语语境中译法有多种:“‘认同’‘身份’‘身份认同’‘同一’‘同一性’等”[7],其实身份和认同不太一样。除去identity在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用法不谈,阎嘉认为在文化研究中要区分不同语境分别使用“身份”和“认同”这两个概念:“其一是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identity可作为‘身份’”;其二是当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可作为‘认同’”[7]。
2000年以后,国内学界经由引入霍尔的理论,发展成为对霍尔及其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截至2019年,国内对于霍尔文化理论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共有三本专著和一本文集。三本专著分别是武桂杰的《霍尔与文化研究》(2009)、邹威华的《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2014)和甄红菊的《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2018);一本论文集《理解斯图亚特·霍尔》(2016)由张亮、李媛媛编译,该文集收录了国外学者撰写的研究霍尔的十余篇论文。在众多成果中,对于霍尔文化身份论述的引用率极高,但对文化身份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的文章却极为少见。笔者尝试从这个方面进行梳理,希望能够有助于厘清身份及其相关概念的内涵。
二、霍尔身份问题研究的关键词:身份和文化身份
霍尔到底赋予identity什么样的文化逻辑和文化内涵,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
霍尔对identity和culturalidentity为主题进行论述的文章集中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这10年间。1989年霍尔发表文章Ethnicity:Identity and Difference首次深入阐释了identity的内涵。霍尔指出这个词在传统意义上的逻辑就是指“真实的自我”;它的“话语中包含稳定的主体概念”;“它告诉我从何而来”;它是“那个能反思的自我”;它具有“连续性”;它“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呈现自我”[8]。显而易见,霍尔阐释了一般意义上的“身份”,身份是判断一个人是谁,是什么样的人的依据。身份是一个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标记,是个体区别于他人的差异性标志和象征。在社会学中,“‘身份’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出拉丁语statum(拉丁语stare的过去分词形式,意思是站立),即地位。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广义上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9]。可见,霍尔正通过identity为我们呈现一个社会学意义上判断自我、反思自我的依据,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霍尔的identity就是“身份”。当然,霍尔阐释身份的目的不是介绍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相反,他意在与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进行决裂。他解构连续的“身份”,建构“未完成”的身份,以此消解传统的社会身份。当霍尔使用“身份”这个词的单数形式时,他多指“个体身份”(individual identity)。
相较于个体身份,霍尔更关注集体身份。在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中,霍尔以自传的形式从自己的非裔黑人和移民身份入手,解构英国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10]。霍尔使用“文化身份”指代“集体身份”,包括“民族身份”和“种族身份”(ethnic identity)。种族(race)是一个有歧视含义的词汇,霍尔认为狭隘的通过肤色、身体等遗传和生物性特征区分人群的种族身份之所以根深蒂固是“西方”政治体系构建的结果。比如,霍尔是“黑人”这个种族身份是他来到英国之后才意识到的,在此之前他认为自己只是个“棕色的人”。与种族身份对应的是民族身份,民族与国家匹配,是“想象的共同体”,它关系到文化和宗教的纯粹性,强调原初居民的纯洁性,如在英国社会中并非所有的白种人都被认为是英国人。霍尔通过阐释媒介对非裔加勒比黑人身份的构建和表征来说明种族身份的政治性,消解种族身份的内核;通过阐释东方与西方的非地理性差异来说明民族身份是西方欧洲中心主义通过陌生化、妖魔化、差异化这些物理特征把其他人群构建成“他者”,从而凸显自己的高级性,合法化自己的霸权地位的结果。至于“认同”,霍尔则在文中使用了另一个英文词汇 identification。霍尔认为identification(认同)是一个过程,它是我们“再次概念化身份的过程”(reconceptualize identity)[10]。认同是心理学上的概念。文章中霍尔讲述自己来到英国之后对黑人、移民身份的觉醒和反思,这就是霍尔自我“认同”(identification)的过程。在霍尔论述身份的文章中基本都会涉及认同,虽然涉及的篇幅不会很长,但每每提及都是在提醒读者,这个来自于精神分析的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人们对个体、群体身份的一个虚幻的认知。霍尔认为,“认同是一种政治,认同是一套表征体系引导下的意义构建方式”[10]。霍尔提醒读者思考:“什么样的人才是英国人?通过什么样的表征方式英国人会获得认同,会把自己定义为具有英国身份的人?”[10]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身份(l’identité)、认同(identification)、身份政治(la politique de l’identité)、身份危机(crise de l’identité),这一系列的高频词在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视野中占据着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理论领域的激烈争论”[11]。从这一表述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身份问题(包括身份、认同、身份政治等)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也能看出身份和认同是文化研究中两个相联系又不同(中英文表述都有差异),但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只是在霍尔的理论中更侧重身份),不能混淆。
三、霍尔“文化身份”理论的发生轨迹和逻辑
(一)文化身份理论发生的前提:社会阶级的解构和个人主体的召回
文化身份反映群体性主体的生活样态,身份是主体的身份。想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身份,首先霍尔要做的就是还主体自由,接下来再唤醒自由主体内在的反抗意识。霍尔为主体争取自由是从解构主体的社会阶级身份开始。
在《意识形态问题:不做保证的马克思主义》(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中,霍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阶级问题进行了详细阐释和评价。霍尔把重点放在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和阐释上,因为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政治和策略问题”[12]。在承认意识形态对主体建构的同时,霍尔更关注对主体反抗意识的挖掘。霍尔认为,意识形态不仅是思想体系(systemofthought)而且是一切与实践相关的思维和思考模式(让人们产生行动力的那种思维模式)。意识形态既包括实践的也包括理论的知识体系,它赋予人们理解社会的能力,它是一种分类模式和话语体系,我们能够以此来感受我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客观的位置(objective positioning)。
借助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修正,霍尔意在强调个人主体已经加入历史进程。阿尔都塞关注的是意识形态的内化过程,即在意识形态话语里对主体的训唤过程,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对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通过对主体的训唤阿尔都塞把个体概念引入了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不再是一个整体性结构概念,而是由个体参与的社会实践。但霍尔认为,如果意识形态的功能是为了按照体制需求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那么如何解释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斗争呢?这就拆解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base/superstructure)的必然联系。转而用主体训唤和主体定位来探讨意识形态的主体化问题。
如果说阿尔都塞进行的是“破”的工作,那么霍尔接下来就在进行“立”的工作。霍尔在接下来试图阐释为什么会出现扭曲的意识形态以及虚假的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为什么人们在虚假的意识形态下生存却不自知?霍尔认为,通过重读马克思发现意识并没正确和错误之分。意识形态不能直接导致错误意识。人们生活在关系当中,这种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出来。这些话语通过显化和隐藏一些关系来实现对主体的定位。相反,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或称经济关系则并不能保证单一、固定和不变的概念化意识形态的过程。
除此之外,霍尔还借助拉克劳以及葛兰西来拆解阶级决定论以及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一对应的关系。拉克劳把意识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同语言和话语之间的关系作以类比。逻辑是意义的链条,受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在意义系统内部还是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这些意义链条都不能被永久地固化下来”[12]。因此,也没有特定阶级的特定意识形态。某一特定概念的意义只是在特定语境下历史集团进行政治表征的方式而已。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就是把一些概念的某些意义同公众的常识性意识解构开来,然后把它替换成政治话语的其他逻辑。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的争斗就是位置之战(war ofposition)。换言之,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是把某个概念意义的解构和建构同特定的政治位置和政治权力相结合的过程。所谓的常识(common sense),就是意识形态斗争争夺的战地,而常识的主体化过程就不可能缺少作为个体的人,至此个体就被召回到文化研究的视野之内,而且占据了霍尔今后研究的中心地位。
(二)文化身份理论的立足点:身份问题的回归及去中心化的个体身份
霍尔从新左派的身份出发,尝试把传统左派对阶级问题过度关注转移到对不同身份的个体和族群的关注上来,提醒人们思考身份构建的方法与目的。霍尔以他的个人成长经历为切入点,对身份问题进行阐释。第一篇涉及身份(identity)的文章是霍尔在1987年发表的《最小的自我》(Minimal Selves)。文中谈到霍尔在英国身份的尴尬引发了他对身份问题的思考。文中提出了“身份”(identity)问题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成为霍尔后期身份问题研究的关键词。文章开篇就表明霍尔“要在后现代语境下,从一个移民和不同于‘英国人’的角度,思考自己身份的意义”[13]。霍尔指出,身份由“历史叙事和文化叙事建构”,这就消解了身份具有稳定性的假象;“身份在心理、文化和政治上都具有不稳定性”,霍尔尤其强调集体身份是“想象的共同体”,是文化表征和意义构建的结果[13]。
接下来霍尔在《虚幻、身份和政治》(Fantasy,Identity,Politics)中,阐释了身份不稳定的根源——身份意义的滑动。虽然霍尔认为身份的意义一直在漂浮,“身份永远在滑动”,但“这个滑动不是无限制的”[14]。他把历史比作公交车,身份就是乘客,“无论你想去哪,你都要先上车”[14]。也就是说,人不是脱离历史而存在的,特定的历史条件赋予个体特定的身份位置。但这个位置只是暂时的,车在行驶,位置就永远在改变;历史在演进,身份的意义就永远在滑动。
同年,他发表了第一篇以身份为主题的文章《族性:身份和差异》(Ethnicity:Identity and Difference),从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和主体观、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对传统身份问题的逻辑进行了“去中心化”的尝试,霍尔在这篇文章中提到身份是通过“差异构建”的“未完成”的身份[8]。这种漂浮、滑动的身份对霍尔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意味着身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处于开放和漂浮的状态,等待被连接,等待被接合。只有在这种开放的状态下,新的社会关系才能被生产,新的文化形态才能被创造,新的政治空间才能被打开。
(三)文化身份理论的关切点:去本质主义的文化身份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消解
霍尔对于个体身份的解构只是他身份理论构建的第一步,是他尝试拆解总体性身份的基石。霍尔以个体身份的不稳定性和碎片化为前提,阐释集体身份——无论是种族身份、民族身份抑或其他族群身份——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由历史和传统赋予的具有总体性和同一性的特征,而是被言说和表征的幻象,是接合的政治。
如果说霍尔在之前的文章中是在纠正人们对身份的看法,明晰身份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文章中,霍尔努力呈现的是身份(尤其是文化身份)构建的方法。在这个阶段霍尔关注的是加勒比黑人的种族身份构建和其中的文化政治问题。1989年,霍尔发表了另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文化身份和电影表征》(Cultural Identity and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遗憾的是该文章的重要性在学界很少提及,而《文化身份和族裔散居》(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确是国内学者争相引用的文章。实际上,《文化身份和族裔散居》是在《文化身份和电影表征》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大多修改之处是为了明确语义)后发表的。霍尔关于文化身份及表征的主要论述都出现在该文中。霍尔在这两篇文章中都谈到了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主要观点包括:1.文化身份是集体性身份;2.传统的观点认为文化身份是共享的文化和共享的历史中稳定的、连续的、统一的共享身份;3.霍尔在自己去“中心化了的身份”的基础上,认为文化身份是“去本质主义的”“延异的”“断裂的”,看似“存在”却永远在“形成之中”[15]。在《文化身份和电影表征》这篇文章中,霍尔借用法农反殖民主义的理论,透过第三类电影(泛指第三世界电影工作者制作的反帝、反殖民与种族歧视、反压迫等主题的电影)“加勒比海电影”的视角探讨“黑人身份”(集体/种族身份)建构和表征的复杂性。这篇文章是在明确文化身份确切地说是种族身份内涵的基础上,重点阐释加勒比黑人身份的文化表征路径。对于“成问题的加勒比身份”的探讨还出现在霍尔的《加勒比海身份的协商》(Negotiating Caribbean Identities)一文中。非裔加勒比海黑人是霍尔探讨种族问题的出发点,他接下来深入思考了族群问题。霍尔提醒人们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人们都需要做好迎接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以及不同群体混杂生活的准备。霍尔在《新族性》(New Ethnicities)、《新旧身份,新旧族性》(Old and New Identities&Old,New Ethnicities)中,重点论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身份和权力及政治之间的关系。在这两篇文章中霍尔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种族、民族及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社会型构问题,文章中多次提及身份的政治及身份问题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此外,霍尔还探讨了身份的“空间性”问题——身份的缺席和在场,以此进一步探讨历史进程中的集体身份通过“他者”的构建过程。
霍尔对文化身份的思考包含以上文章中出现的种族身份(流散族群、加勒比海黑人群体)问题,也包含接下来文章中出现的民族身份问题。《文化身份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全文共40页左右,霍尔在文中明确说明“我在这里探讨的文化身份主要是民族身份问题(当然同时可能涉及其他身份)”[16]。霍尔从现代社会的身份危机入手,谈到启蒙主体和社会学主体的解构以及后现代主体的生成。霍尔谈到同一主体内部存在多重身份,各种身份相互矛盾。霍尔认为,“单一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总是尝试通过文化表征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和归属感。在后现代的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身份一定会被侵蚀”,“民族的身份必将衰败,最终被混杂的身份所代替”,“身份的政治正在向差异的政治所转变”[17]。最终,西方(the West)和其他世界(the Rest)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霍尔通过对文化身份的去本质化,通过对西方二元对立文化身份观(西方和他者)的批判,“对文化身份及表征主体展开一种对话,一种探查”[17],来消解西方文化身份自我标榜的真实性、权威性和可靠性。
(四)文化身份的归宿:混杂身份的形成与单一文化身份的幻灭
霍尔认为,实际上传统的阶级冲突已经不复存在,各个族群之间的社会分野也不再明显,不同群体都应该为自己谋求一定的政治空间,这个空间无所谓边缘或中心只要能为自己发声就好。霍尔认为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应该警惕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单一民族国家必将走向消亡。
霍尔在《导言:谁需要文化身份?》(Introduction:Who Needs Identity)中,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探讨主体和主体性问题。文中谈到了主体、身体和身份之间的关系,霍尔通过拉康镜像理论想象的认同出发,通过福柯的权力、训唤消解个体主体,通过朱迪斯·巴特勒解构性别主体,最终从源头上消解身份赖以生存的“容器”[18]。试问连主体都不复存在了,“身份”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连个体都不存在了,集体的文化身份又从何而来?
霍尔通过文章多次强调,未来是不纯净的,是混杂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形态。《历史中的主体:族裔散居身份的形成》(Subjects in History:Making Diasporic Identities)是根据霍尔在美国发表的演讲整理成文。文中着重强调了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它是构建身份的场域,是构建社会性主体的场域,也是政治斗争的场域。霍尔提醒大家警惕身份、种族、差异甚至是少数族裔所带来的本质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立场。而在《多重身份世界中的政治归属》(Political Belonging in a World of Multiple Identities)一文中,霍尔从理论和经验两个角度谈到了身份的多重性问题,再次强调我们需要摒弃对于“单一民族国家”(nation-sate)的忠诚和幻想,甚至要摒弃对于统一社群的幻想,我们应该尝试建立一个在种族、民族、宗教、性别之间的对话模式,构建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