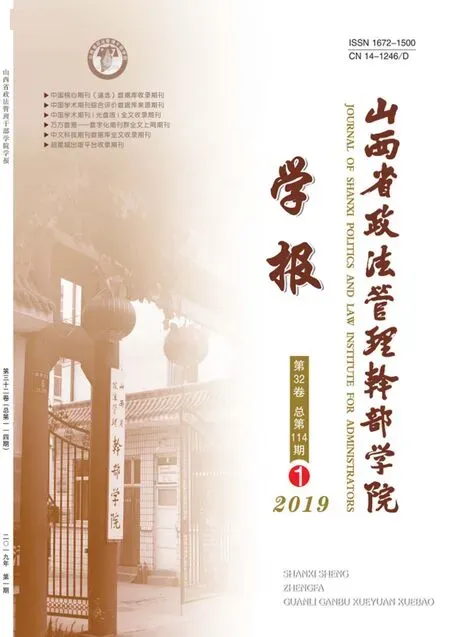国际法渊源一般法律原则的功能定位
鞠 徽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63)
国际法的渊源是指国际法作为有效规范之所以形成的方式或程序。《国际法院规约》(以下简称《规约》)第三十八条规定:“法院对于陈述各项争端,应以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1)不论普遍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2)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被接受为法律者。(3)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4)在第五十九条规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二、前项规定不妨碍法院经当事国同意本“公允及善良”原则裁判案件之权。”一般认为,上述条款是国际法渊源的权威宣示。一般法律原则在《规约》中被视为与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并列的国际法依据,并且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作为法官裁判国际争端案件的依据也曾多次被援引和适用。但对于一般法律原则,仍存在较多模糊点。首先,在一般法律原则的来源性质问题上,其是来源于自然国际法还是实在国际法?其次,是在一般法律原则的地位问题上,其是国际法三大渊源之一还是仅仅为次要渊源?再者,是关于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习惯的界限问题,两者在法律与实践层面的相似点使得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笔者认为,上述三个问题实质上反映了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法渊源理论层面与国际司法实践层面所存在的定位不清晰问题。明晰上述三个问题,有助于推动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司法机构中的适用与发展。
一、一般法律原则来源的性质
在对一般法律原则的来源进行界定之前,我们有必要明晰什么是自然法,什么是实在法。
自然法最早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当时的“主权在民”“直接民主制度”,以及十七十八世纪时启蒙思想家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民主权、共和等观念都带有浓浓的自然法色彩。关于自然法,西塞罗认为其“是万世存在的,发生于成文法未制定、国家未成立之前”。[1]实在法的概念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臻完善,其制定依据是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与人们的经验事实,具有可变性,是一种“公共的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对于法律而言,自然法注重“实然”,实在法更加注重“应然”。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不得不说,相较于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存在着概念的模糊与范畴的不确定等特点。比如如何从成文的法律文件中找寻一般法律原则,法律原则具备怎样的条件才可称之为是国际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一般法律原则的界定范畴在哪等问题。也正是这种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部分学者将一般法律原则混同于自然国际法。这种观点抹杀了一般法律原则与人的理性、意识等自然法的区别。
自然法作为对自然理性等抽象价值体系的概括,凌驾于实在法,并在某些方面指导实在法的发展。如前所说,如果认为一般法律原则源于自然国际法,则相应地推导出一般法律原则是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存在,进而在《规约》第三十八条中,就会出现一般法律原则凌驾并指导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其功能等同于国际强行法的矛盾现象,这与当前国际法理论实践不符。
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是对各国国内法律体系所共有的法律原则的概括总结,是各国国内法律原则这一实在法的最大公约数。因此我们说一般法律原则源于实在国际法,而非自然国际法。
二、一般法律原则的功能定位
随着国际实践的发展以及国际法理论的完善,国际法学界逐渐将一般法律原则纳入国际法渊源之列。但对于一般法律原则究竟是如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一般为主要渊源还是区别于两者之外为次要渊源的地位问题存在争论。
有学者认为“国际法院只是在没有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规则可供适用的情况下,才会求助于这几项规定,与国际条约相比,他们只能是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起辅助性的作用。”[2]鲍威林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其认为一般法律原则是一种具有重要系统作用的渊源,但是是一种“次要”的渊源。[3]詹宁斯、瓦茨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在该问题上主张,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渊源,而不是“辅助方法”之一,这样做的目的是“授权法院在可以适用于国家之间关系的范围内适用国内法理的一般原则”。[4]
不得不承认,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法院的适用较国际条约、国际习惯确实为数不多,这也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一般法律原则属于次要渊源的理由之一。实际上,这种“为数不多”仅仅是相较于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而言,国际法院实践中存在大量直接运用一般法律原则的案例。例如,在1928年德国诉波兰的“霍茹夫工厂案”中,国际常设法院在确定不法行为所造成损害赔偿责任的过程中所依据的就是恢复原状原则。在1962年“隆端寺案”中,国际法院在驳回泰国地图存在错误的主张时,适用的是“默认、排除和禁止反言”等原则。再者如不得滥用权利和诚信原则在1930年上萨瓦及节克斯自由区案的运用,国际法优于国内法原则在1930年对希保少数民族“社团”问题的咨询意见中的运用等。这些案例都表明国际法院在实践中都是将一般法律原则作为主要渊源来适用的,这是毫无争议的。
“从内容上看,一般法律原则体现了国际法秩序的基本因素,例如禁止翻悔、接受审判权、禁止滥用法律等,所以尽管这些原则无具体的对象,但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5]换言之,一般法律原则的法律拘束力不仅仅来源于其是从各国国内法共有法律原则抽象概括而来,还是因为各国对这种原则的承认使其获得国际法上的效力,从而成为国际法规范。从业已确认的国际法辅助渊源来看,首先,国际法院的判决案例虽然仅仅针对个案而言,但就特定案件得出的结论,对以后类似案件的审理以及相关领域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建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具体体现在国际法院对个案的判决意见以及在审理过程中某个或者某些法官针对案件其中的一方面所进行的精辟的阐述。但是这种指导意义并没有法律拘束力,即并不构成国际强行法。同样,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在国际法院实践中引用的意义“在于作为法律的证据,而不是作为产生法律的因素”,它也不属于国际强行法的范畴,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如此比较,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司法判例和权威公法学家学说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也是不能将一般法律原则纳入“辅助渊源”之列的强有力原因。
在承认一般法律原则是国际法主要渊源之一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般法律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所起的是辅助性作用。一般法律原则在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的很少适用主要是因为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已经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方面的法律需求,但这并不代表一般法律原则失去了用武之地。国际条约规定了两国或多国之间权利义务的分配问题并由此成为争端解决的依据,国际习惯是各国在国际实践中逐渐“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可以说,这两项渊源涵盖了国际法上大多数国家的行为模式。但是国际实践是复杂的发展的,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国家之间纠纷处理的解决措施,此时就需要由从各国国内法律体系共有的法律原则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一般法律原则发挥作用。国际法院在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两者中未寻求到判决依据时,才会诉诸一般法律原则进行案件的处理。可以说,一般法律原则是为了弥补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的“法律罅隙”。简而言之,与国际条约、国际习惯的地位一样,一般法律原则同样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之一,而非次要渊源。
三、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习惯的界限
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习惯在实践层面以及法律层面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使得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
(一)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习惯的相似点
首先,在法律层面。通例是在各国实践的基础上而成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习惯,其成立必须具备心理要素,即被接受为法律。通例的产生表明该实践已经被大多数国家所践行,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性。但这种认可仅停留在各国零散的、不具有普遍说服力的实践层面,尚未具备可适用于所有国家实践的效力。当各个国家在现实中多次将通例运用于实践,并且将通例的行为规则认为是国际关系所必需的,相约接受通例的拘束,即产生“法律确信”,通例便具有法律拘束力,由此形成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来源于各国国内法律体系所共有的原则,在一般法律原则尚未形成时,这些“共有的原则”便已存在,零星地散落于国内法规范之中,并且具有拘束一国国内行为规范的效力。“各国法律体系是各国意志的体现,各国的承认可以说包含在各国的法律体系之中,而似乎是无需各国另做承认的表示。”国际习惯与一般法律原则在形成过程中,如果仅仅停留在国家实践层面,则不具备国际法上的法律效力,无法产生国际法层面的法律拘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只能约束国家内部行为或是狭窄范围内国家间的关系,无法成为国际法上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依据。当其上升到法律层面,被国际社会所认可,才能具备国际法上的法律效力,从而成为国际法渊源的组成部分。
其次,在实践层面。国际习惯立足于国际实践,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该国家实践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时间发展阶段。关于该时间的长短目前尚无具体的规定,基于国际社会实践的复杂性,当然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普适的规则来约束。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践行越频繁,则通例形成的时间便越短。二是该国家实践必须被一定数量的国家在国家行为中所实践。与前者时间条件类似,没有也不可能有同样的规则来确定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数量点。三是该国家实践必须在国家行为中保持同一性。如果国家的实践行为前后不一致,则很难成为通例。一般法律原则,从文本理论成为实践依据需要国际实践的认可,即国际法院的确认。在1962年“隆端寺案”中,国际法院在驳回泰国主张地图存在错误的主张时,使用的便是“禁止翻供”原则。这些原则在某些国家之间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援引,各国国内法律体系中所共有的原则,在尚未得到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时,“沉睡”在各国国内法体系之中,只有被国际法院等国际实践所“唤醒”,其才有可能成为一般法律原则。作为国际法渊源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在形成过程中都需要实践的确认。同时,也只有立足于各国的实践,才能在实践中体现并协调各国的共同意识。
(二)一般法律原则与国际习惯的区别
其一,实践立足点不同。总体而言,各国的法律或多或少存在精神主旨相同或相近的法律规定,在此种法律规定的指导下,各国的法律实践理应一致。但国际习惯之“通例”形成于国际法层面,立足于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国际实践;而一般法律原则概括产生于各国国内法律体系所共有的原则,其立足点在各国国内,是各国国内范围的相对独立的、各自为政的实践原则。对一般法律原则来说,各国共有的法律原则是立足于国内法的实践,其调整范围也只局限在国家内部。这与国际习惯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其二、法律来源不同。一般法律原则是将各国国内法共同的法律原则所确认的法律,法律来源为国内法。国际习惯产生过程中,要使通例获得法律效力,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是出现心理因素——“法律确信”。通例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通例,“法律确信”是国际法层面的产物。在1927年的“荷花号案”(法国诉土耳其)中,虽然船旗国管辖原则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反复实践,并形成了通例,但在本案中,该通例因并未获得法律确信,故国际法院在处理本案时便不能援引船旗国管辖原则。国际习惯成立的条件——法律确信,必须在国际法层面进行确认才能使国际习惯获得法律效力,一国国内或者少数国家的确认不能使其产生法律效力。而各国国内法法律体系所共有的法律原则在国内法范围中当然的具有法律效力,并受制于国家权力体系,无需其他国家乃至国际法院的确认。
其三,其依据是否为成文规则不同。国际习惯的实质在于各国的实践,是各国在实践中反复的、叠加的渐进状态,因此为展现其形成机制必须借助或寻求于司法判例、权威公法学家学说等加以确认,由此才可展现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渐进过程。一般法律原则是具有相同或相近主旨的各国国内法的共同原则的高度概括,其依据来源于各国国内法成文规范。
四、结语
学界对于国际法渊源中的一般法律原则的争论体现出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法实践运用中的困境,这种困境来源于一般法律原则在理论层面某些概念、原理的模糊性。通过梳理、分析,明确一般法律原则来源于实在国际法,并且是国际法主要渊源之一,同时明确其与国际习惯的界限,这有利于弥补无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存在时的法律空白,以期更好地在国际司法实践中适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