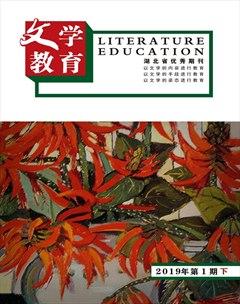《封锁》的叙事艺术难度探究
内容摘要:《封锁》以高超的叙事技巧在不到八千字的篇幅中完整呈现了吕吴二人在封锁的电车上的爱情故事,并在这故事中注入丰富的人性内涵。小说题材的复杂性与篇幅的超短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现代中国小说的艺术难度:限定时空结构中复杂爱情故事的叙事可能性及其有效性。本文从《封锁》叙事的可能性即叙事手段和叙事的有效性即叙事结果两个角度来探究《封锁》的叙事艺术,意在发掘其叙事艺术难度所在。
关键词:《封锁》 短篇小说 叙事
一.叙事的可能性
张爱玲的《封锁》发生在一九四三年八月,描述的是旧上海的某一天,电车被封锁的短暂一刻所发生的爱情故事,正是这个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封锁》的独特叙述方式,即以空间叙事代替时间叙事。恩格斯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1]但在小说叙述领域,向来是重时间,轻空间。大多数小说的叙事都是按照时间发展为线索的,但张爱玲的《封锁》却采用了空间叙事,用空间叙事代替时间叙事。
小说叙事存在一个时间维度,也存在一个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就是线性连贯,即情节的历时性,空间维度就是同时并置,即情节的共时性。张爱玲的《封锁》采用的就是从“线性连贯”里抽出一个“同时并存”,而这个“同时并存”就是吕宗桢、吴翠远爱情故事发生的主体时空环境。小说开始说“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2]接下来就是“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而在故事高潮结尾处也有与此相互呼应的描写,“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时间与空间。”这一前一后切断了时间与空间的电车就是从线性连贯里抽出来的一个弱化了时间概念的独立空间。而在这个空间里的叙事则弱化了情节的历时性,强调情节的共时性,即用空间叙事取代时间叙事,用空间存在强化短时间内完整爱情故事发生的可能性。
张爱玲具体是怎么采用空间叙事的呢?她把着眼点放在了电车内和电车外两个相互分割的世界,用对这两个世界相互交换的场景描写,推动剧情发展。电车里的人都很安静,仿佛被一种巨大的力量给压住了,而电车外则是一个乞丐和一个胆子较大的乞丐的叫喊声,以空间视角的推移来表现封锁时时间的推进。然后视野再回到电车内,有乘客下车,有一对长得像兄妹的夫妻的对话,再才是主角上场。这段时间里的世界仿佛不是随着时间在走,而是随着作者的描写、经过空间的转换推移在走。完成任何一个叙事作品,都应该包含两个步骤,即确定事件和赋予事件秩序。确定事件就是理出要描写的中心对象,赋予秩序就是怎么让对象行进发展,所以,赋予秩序就是一个怎么安排叙事的问题。《封锁》的主体情节采用空间叙事,它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并置叙事。小说的结构是短小的,可它的内容却是丰富而真实的,这样的叙事效果正是得益于对叙事时间的弱化。封锁那段时间本身很短,它的故事容量有限,如果按照时间叙事就会压挤内容显得节奏紧迫,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吴吕之间爱情发生的可能性,可是当作者选择空间叙事的时候这种紧迫感就会消失,事实存在会被放大进而强化爱情发生的真实性。所以,张爱玲用空间叙事取代时间叙事,从而消解了时间之短与爱情故事之完整之间的矛盾,使得《封锁》叙事成为可能。
二.叙事的有效性
文学叙事在更大程度上是心灵叙事,而不是直接的现实性叙事。一篇小说要达到它叙事的有效性,不仅要运用各种叙事策略把作者心中那个文学事实建构出来,使读者对作者建构的这个文学事实达到大致统一的感受和认知,更要在这个从现实剥离出来的文学事实中注入丰富的思想和内涵,使得故事本身有其深度,力求达到一种以情动人或是以某种思想激起读者的深思和共鳴的效果,这样的叙事才是有效的文学叙事。对《封锁》来说,其最大的难度在于限定时空结构中复杂爱情故事的叙事有效性,让读者读完确信事件是真实地发生了且不免为之欷歔,而当胡兰成第一次在《天地》杂志第二期上读到张爱玲的小说《封锁》——惊为天人,足以证明张爱玲完成了《封锁》叙事的难题。
张爱玲的《封锁》向我们展现的是非常态时空的人性,这时的非常态时空造成了一个人性大逃亡的机会,即做常态时空里不会做的事情,因为非常态时空是短暂的,这种短暂给人一种安全感,即当时空回归正常,人就可以把现实当做退路,随着时空回归正常,人也变回伪饰的人,或者说社会的人。正如牛顿说“我可以计算天体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性是深不见底的深渊”,人在觉得自己可以放弃或是短暂逃离束缚的时候会做出一些“有违常规”甚至是疯狂的事情。吕宗桢并不是一个洒脱大胆的人,他即使不愿意穿着西服戴着眼镜提着公文包去偏僻的小巷子买几个菠菜包,可他还是不情愿地照着妻子的话做,可见他是一个有点懦弱且向现实低头的人。所以如果不是封锁造成的非常态时空,吕吴的爱情就不会发生。罗·勃朗宁说“爱情、希望、恐惧和信仰构成了人性,它们是人性的标志和特征。”吕宗桢对妻子不满,吴翠远对家人和现实不满,所以他们想要寻求摆脱这不满的出路,对他们来说,彼此就是对方的希望。可是生存的压力和现实的阻力使得他们恐惧且不得不放弃。用吴翠远的话来说就是真人和好人之间的挣扎。真人是赤裸表达自己的人,好人是屈于现实而妥协退让过日子的人。而张爱玲的小说是很少涉及信仰这个东西,因为她总是冷眼、悲观看俗气又功利的世界,对于信仰这种较为理想化的东西她避之不谈。所以,《封锁》就是一部赤裸裸揭示人性的小说。
吕宗桢的婚姻生活索然无味使得他有了想结第二次婚的冲动,这何尝不是人性的贪婪;而他之所以和吴翠远调情这中间还得感谢他的侄子无意中的推波助澜,这何尝不是一种功利;他觉得自己穿得体面不想去小巷子买菠菜包子,这何尝不是一种虚荣。总之,吕宗桢是一个饱满俗气的人。吴翠远相对来说要更单纯一些,但是她也是潜意识抱着借吕宗桢去反击她所讨厌的周围的人目的去附和吕宗桢的调情。总之,他们俩都一样,都是对现实不满渴望那么一点改变和反击的人。但是他们最终失败了,归根到底这也是人性软弱的一种体现。人往往会为了生存而委屈求全,隐藏掉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努力把自己打磨成可以在社会中行动而不碰壁圆滑的人,很少有人是为了生命而生活,大多数是为了生活而生活,这也就是吴翠远所谓真人比好人可爱的原因。总之,《封锁》是人性欲望的一个短暂释放的故事,他向我们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东西,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这本真中褪不去的世俗的侵染。俗世中的人总在真实的欲望和对现实的妥协中不断挣扎,这就是生存的束缚与困境,这就是无法摆脱的痛苦的根源。总而言之,《封锁》叙事的有效性在于短小篇幅所包藏的丰富人性内涵,正是人性本身的复杂容量成全了她短小篇幅事实的有效性。
《封锁》是一部合情合理、深入人性的杰作。它借吕吴二人在封闭时空里的爱情故事来揭示现实对人性的束缚、生活对爱情的谋杀,以及世俗人生的困境,使得小说在不到八千字的叙述里呈现出丰富的人性内涵,这是张爱玲叙事上的成功,同时也真正确定了短篇小说叙事艺术的有效性:丰富又复杂的人性使得读者在有限的字里行间能够去理解和接受无限的生命可能。
注 释
[1]恩格斯:《反社林论》[M],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I:34页.
[2]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148.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封锁[A].张爱玲集[C].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2.杨春.叙事时间策略和叙事时间维度-张爱玲的时间叙事[A]学术探索 2015-02-15
3.罗勋章.小说真实性的判断标准[A]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15
4.刘川鄂.《封锁》: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杰作.合肥师范学院院报[A]2012-01-2
0
5.(奥)弗洛伊德著,郑希付译.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A]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05-01
6.尹鴻.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A]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04-25
7.[德]叔本华,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A]商务印书馆,2007年
8.[法]让·雅说·卢梭,何兆武译:《论科学与艺术》,[A]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年
9.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A]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王飞.小说的真实性的深层探究[A]作家.2009-09-28
11.格非.小说叙事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王百玲.论张爱玲小说的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5
13.李伯勇.当“小说难度”成为一个问题[J]小说评论.2008-01-20
(作者介绍:何田田,中南民族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