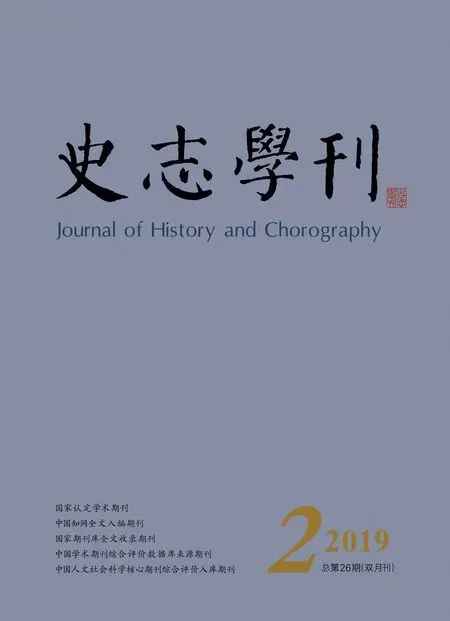历代《芮城县志》篇目及内容的比较分析
赵永强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太原030012)
“国有史,郡有志”,编修地方志就是对地方历史的书写过程,反映着当时人们的时代观念和价值认识。通过对地方志书进行长时段的历史比较和分析,可以使人们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地方的历史和文化,了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继承和创新。芮城县在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州县中,属于典型的“非著名”一般县。无论古今,从地理位置、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等多个维度来看,这里都属于国家的中部、中等发展程度。因此,选取这样的一个非典型县作为分析对象,具有一般性的代表意义。
一、历代《芮城县志》的编修概况及卷帙规模
和全国绝大多数县份一样,《芮城县志》首纂始于明代。迄至2017年,共计编纂10次,平均约50至60年编修一次,分别是:
首纂于明永乐十九年至正统六年间(1421—1441),由佚名编。志佚[1]各版《芮城县志》未记载,祁明编著.刘纬毅,武承审定的《山西方志要揽》(1997年内部印刷)第153页有录.李裕民辑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古方志辑佚》第503页辑录“风俗”“形胜”两条.。仅在《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中有著录,成化《山西通志》(卷二)有引。
第二次纂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由知县白世卿主持、刘良臣主纂。刘为本县举人出身,曾任平凉府通判。志佚,仅在清乾隆《芮城县志》“芮城旧志历修姓氏”中著录。但自明代隆庆版《芮城县志》开始,历代编修者都以刘良臣主纂为本县修志之发端。
第六次纂于清咸丰九年(1859),由知县丁树勋对乾隆二十九年(1764)《芮城县志》进行了增补,其卷序、篇目等都没有变动,仅在卷后对相关题目进行了增加(因此,未列入下表)。志书的时间下限整体延后。
其余第三至五次、第七至十次编修,分别为明隆庆、清康熙和乾隆,清光绪、民国及1993年、2017年出版的《芮城县志》。各志基本情况见下表:
从现存上述各代各朝《芮城县志》的卷帙规模上看,旧方志与当代新方志的体量、记载内容的全面性上都不可比拟。在各版旧志中,民国《芮城县志》的卷数和字数都是最多的,但也不过16卷、20到30余万字。1994年版《芮城县志》[1]芮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秦出版社,1994.除大事记外,共36卷150万字;2016版《芮城县志》[2]芮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2016.则有46卷445万字。这首先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差距,但也与旧志、新志的功能定位有关。旧志的功能定位,首先在于资治和教化,存史的功能并不能得到很大重视。而新方志首先被定位为“一方之全史”,地方志书被定义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3]2006年5月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资料性文献”的定义是对地方志“存史、资治、教化”作用“存史”功能的突出强调。
旧志的规模大小,也是当时当地经济发展情形的间接体现。隆庆、光绪版的县志,在现存6种旧志中字数和卷目都是最小的,而隆庆、光绪年间,芮城人口减少是历史上最剧烈的时期。各版《芮城县志》记载:成化八年,芮城共计5354户68768人,隆庆五年迅速减少到1306户19278人,是芮城县有记载以来人口最少的时期;光绪三年,芮城人口共26404户126191人,随后的三年大灾,人口迅速降到光绪六年的13483户56034人[1]芮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芮城县志(上册).中华书局,2016.(P339)。而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两版新志,是处于我们当代的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新时代所编修的不用赘述。
二、各版志书篇目设置、内容上的继承关系
顾颉刚在《中国地方志综录·序》[2]朱士嘉撰.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引述的一般方志记事要目为:地理——沿革、疆域、面积、分野;政治——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经济——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社会——风俗、方言、寺观、祥异;文献——人物、艺文、金石、古迹。各《芮城县志》旧志篇目的设置,对上述目录的范围并没有溢出和超越,各旧志之间的相互传承十分明显。
康熙版县志对隆庆版县志的继承最为直接和密切。两志均十分简略,仅仅分设4卷,卷题也完全一致。各卷下分目中,康熙版有增无减。乾隆版县志更加细化,增加到16卷,但对康熙县志的所设篇目并无削减,艺文由1卷扩充至4卷。至于上表中未列出的咸丰版县志,与乾隆版县志篇目则完全一致。光绪版县志卷数重新变为4卷,卷目要素也照例继承和沿袭前述各志。到了民国,社会丕变,县志《例言》虽然强调“旧志所载,上起成周,下逮光绪六年,此次悉为重修,应因者因,应革者革,门类次第视前多有不同”[3]民国十二年重修.2016年芮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扬州广陵书社影印出版.,但大体上仍不脱旧志窠臼,尤其是更多地继承了康熙版《芮城县志》的体例。
即使是作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两版《芮城县志》,对旧时代的县志,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以新旧志的篇目设置比较来看:旧志中的“疆域”内容,在新志中演化成为建置、自然环境、乡镇村居、环境保护等内容;旧志中的“政教”内容,扩充为城乡建设、人口、政权、军事、教育、司法、文物、民情风俗以及自然灾害、地方名产等内容。旧志中的“选举”内容,往往被分解到新志中的“人物”“职官年表”部分;“灾祥”的内容,在新志“大事记”和“自然灾害”“军事”等内容中都有体现。至于“人物”“艺文”从来都是各朝各地志书中的主体内容,以为二者“实有关人心世道”;在今天的新方志中,也都受到特别的重视,尤其是“人物”部分,最为修志者、读志者关切和重视。除了志书的这些主体内容的继承外,旧志中在志书卷首一般都有“图”的内容,排列境域、县治、衙署、学校、坛庙等绘图,而新编县志中则以地图、照片等代之。这也是各志之间明显的承继关系。
正是因为各朝各代的志书之间、新时期与旧时代的新旧志之间有这种前后相因、不绝如缕的继承关系[4]周立业.也谈新编地方志对旧志的继承和创新.史志学刊,2015,(3).,才形成了一个地区、一个县的地方历史叙述的相对完整性。在新编《芮城县志》的过程中,资料最为完整和丰富的部分不外乎疆域、建置、人口、赋役、风俗、灾荒、人物、艺文这些部类的内容。正是因为各个时期县志篇目、内容的相对稳定,才有利于地方历史叙述的系统和完整。这种地方历史叙述的系统性,反过来又促进了地方志书作为资料性文献的权威性、实用性。
三、各版志书在篇目尤其是内容上的变革、创新
考察各版《芮城县志》之间的不同,首先最大的当然体现在新旧志之间。无论是在各个方面,两者都差别太大。由于认识水平和篇幅所限,笔者不能识大,在此仅仅谈几点小而具体的见解:
(1)旧志中的一些内容为时代所淘汰,不再出现。如“疆域”中的“星野”,“人物”中的烈女、仙异等内容。至于田赋、荐辟、封荫等封建内容,在今天的志书中,自然也没有痕迹了。随着社会新兴事物的产生,旧的内容被新兴事物所替代。乾隆县志中有“铺递”的内容,新修志书中的“邮政”内容,某种程度上就是铺递、驿站制度的延续,但却是完全不同的记述对象,新者兴、旧者废。
(2)经济业态的大量记述,是新志与旧志在篇目和内容上的最大区别。但民国版《芮城县志》虽然仍为旧志形态,但已经出现了“生业略”的篇目设置,这一点十分引人注视,体现了民国时期新旧志之间的过渡属性。编纂者言“芮僻邑也,民皆终岁勤苦,不敢少休,虽城镇繁华之区,游手好闲者亦无几人。然仰事俯蓄多称不给,抑又何也?吾尝适田野、游工肆,见其所经营大率沿数百年前故智,未尝少变,岂非山河障隔、风气闭塞闻见少而改良难欤?迩来倡兴实业,文明蔚起,为农工商者,其亦于各生业亟为加意,土瘠民贫之说,当不为观风者再述焉。作生业略”[1](民国)芮城县志(卷五).中华书局,2016.。至于具体记述内容,虽然只有不足千字的内容,但已经述及农业、桑蚕、工业、商号、妇女纺织、骡马转运、商号商业等内容,成为新方志中“经济业态”的雏形,实在算得上志书体例、内容的巨大创新。
(3)氏族、方言的内容,从民国县志开始有记述,体现了县志地方性、基层性特点的凸显;而新方志中,县志地方性特色越加突出,地方文化、生活风俗、方言、姓氏、谚谣等成为不可缺少的记述内容。应当说,旧志虽然也重视地方内容的记述,但由于立意、定位在为统治者治民理政提供服务,更多关注于上层建筑领域,因此对于方言俚语、土风民俗一般并不多着笔墨。氏族虽有关注,但一般都记录在名宦、乡贤等内容中,并不关注普通民众的姓氏、源流。风俗也有记载,但不会涉及衣食住行、岁时节令、婚丧喜庆等具体化的内容,代之以“魏地狭隘,其民机巧”“其俗刚强,人民朴陋俭啬”“其民大抵犷悍”等概括性的语汇。
“氏族略”是民国《芮城县志》的一大亮点。编纂者将芮城县三个区主要村庄凡5户以上的姓氏,其祖籍源流、迁入迁出、官绩科名、各姓户数,都进行了详细记录[2](民国)芮城县志(卷四).中华书局,2016.。如卷首《例言》所述,“旧志本无氏族。今特创此体,重本源也。”这既是对地方志书木本水源传统的继承,又是民国肇建、民主思想的体现,尤其是把主体民众的家族源流记载进县志里,必然极大地提高了志书的地方资料作用,吸引更多的人读志、用志,可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因为历史上无论是《史记》一类的本纪、年表谱系,还是唐代以后兴起的氏族之学,所记录的都是帝王诸侯、名门望族的“木本水源”,和一般百姓并没有多大关系。在1994、2016版的新志中,“全县部分姓氏源流表”的资料基本上源出于此。
民国县志中,对方言还没有专门设立子目,而是放在卷14的“业载”中。“业载”类似于杂记,共包括仙异、方言、志余三个子目。作者叙述“在昔若仙释神异、今若方言之类,虽怪与俚,皆一邑所有事,不妨汇而志之。虽曰无关切要,亦足为考古证今之一助尔”[1](民国)芮城县志(卷十四)之业载.中华书局,2016.。由此可知,作者虽然认识到方言的地方性,有所重视,但还将其视作与“仙异”一样的鄙俗之物,并列而论。志书品类的萌芽与僵尸并存,融为一炉,这或许是民国志书中的特有吧!
(4)新旧志篇目设置、记述内容的不同,体现了指导观念的不同。康熙、乾隆、咸丰、光绪、民国各版县志中,都设有“祥异”的专门目录,其内容以地震、灾荒等灾难性事物为主体,也还有粮食丰收、天降祥瑞的欢乐气氛。这体现了古人敬天畏人、天人互动的整体观念,但“敬天”观念不止是恐惧和小心行政的成分,还有感恩的成分在内;另外,民国县志中把兵祸、匪事也记入“祥异考”,更是有“儆人”的用意了——“旧志兵事附于兵防,今改附祥异,以见荒灾相同,不可一日忽也”[2](民国)芮城县志.例言.。反观新志,将“自然灾害”的题目一般都置于“自然环境”的卷下,便难以体现人与自然互动的先进理念,也起不到读志、用志的警示作用——实际上,许多的自然灾害并非自然,而是人类的盲目活动所导致。又如“艺文”的选录,旧志一般特别注意选取“真切恳挚之文,多有关于人心世道,搜考往事,振起顽懦,当必有藉”[3](民国)芮城县志(卷十五)艺文录·上.,但一般新志选取艺文,其价值取向明显不同于以往。
对明隆庆年间以来出版的各种《芮城县志》的比较分析,有助于加强对地方志在地方历史记录中重要作用的深度理解。如上所述,(1)由于地方志持之以恒的编修传统,以及中国地方志书比较成熟完善的体例传统,形成了各代志书之间前后相因的继承关系,也便有了各个地域比较系统一致的地方记忆、地方历史。这种地方历史的一致性认同,是形成整个中华民族历史认同的基础;地方志在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2)地方志从来便具有资治、教化的重要功能,新志的“存史”功能更加得到重视。由于地方志的这些实际功能,使它具有“实学”特点,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因此,在地方志的发展史上,一直随时代的变化而变革、创新。今后,如何适应新时代、新事物的要求而开展地方志理论、实践的变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题。(3)民国时期,无论是在地方志书的篇目设置、记述内容,还是对地方志书的指导思想、功能定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是新旧地方志之间的重要过渡时期。目前,对民国时期地方志编纂实践和地方志成果的研究还有所不足,应加强对民国时期地方志书版本和地方志编修实践的研究。
——以山东省部分史志机构的旧志整理成果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