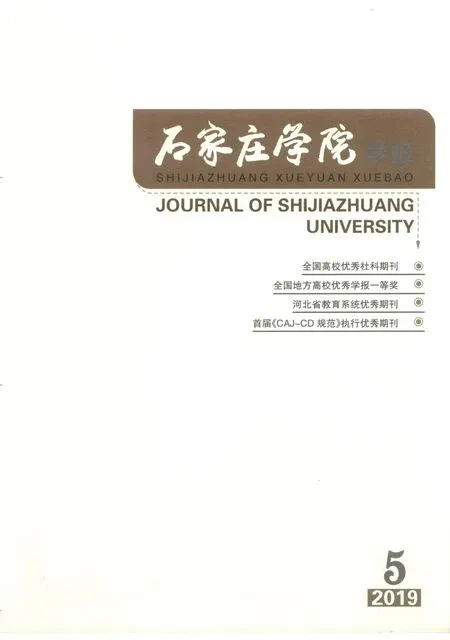论丁韪良“礼赞中国”的个人精神因素
——基于丁韪良在华旅居自由和执教尊荣
黄 涛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是美国基督新教长老会传教士。字冠西,号惪三。1850年来华,1916年在北京病逝,“在华生活时间长达66年之久”[1]1。他集传教士、教育家、翻译家、著作家和外交家于一身,是当年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堪称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脱离不了他的西方血统的基督文明至上论,但相较于在晚清孱弱国势下的一片诋毁中华文明的靡音,丁韪良却对中国经典、中国宗教、中国政制和中国未来带着宽容、理解、客观的态度加以阐释和介绍,其中,他的“礼赞中国”系列正义之语是近代中国在遭遇西方世界近乎千篇一律诋毁中华文明的客观世界中一种思想进步潮流的典型反映,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之后的“万山丛中一点红”。细究丁韪良“礼赞中国”的根源,不外乎政治、传教、文化交流、自身发展等因素的单向或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就个人因素而论,“仓廪实而知礼节”或许是最好的理论阐释。在文化传承的意义上讲,“仓廪实而知礼节”就是个体之人的生存和发展。“礼赞中国”的基础性的人文精神需求,在于人身安全和生活自由以及相关而来的人格尊重和人尽其才。丁韪良以美国传教士身份进入处在不平等国际地位下的近代中国,无疑面临着人身安全的危机,也面临着异质文化的无情冲突,但所幸的是,他逐渐成了某种意义上中国化的西方传教士。这种生存状况使得他的发展超越了单纯的传教文化范畴,进入了更宽广的中西文化的砥砺事业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观察家,并以执教和管理近代中国最为有名的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而享誉世界。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0多年,虽未加入中国国籍,就这个年数足以让人惊叹,而且离世后夫妇同葬北京墓园,更是一曲无声胜有声的中国赞歌。所有这些非一般西方人极难获得的国民礼遇,无疑成为丁韪良“礼赞中国”的最个性化的一种必然结果。即便在所谓世界一体化的今天,这样的殊荣也是不多见的。因此,考察丁韪良在华旅居自由和执教尊荣的两大生活篇章,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礼赞中国”的真心实意和寄托其上的福音使命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和谐的文明意义。
一、丁韪良“礼赞中国”的起源和基本内容
丁韪良“礼赞中国”不是一句闲言碎语的巷头街议,也非明确书写出来的横幅标语,而是蕴涵于他的思想深处和学术著作中的真诚信仰,如同他所笃信的福音理想一样。无声胜有声,无字胜有字,这才是丁韪良对他生活60多年的第二故乡中国的深沉爱护和永久眷念。丁韪良从一名赴华传教士转向中国近代教育领域,最终成为一位资深教育家和著名汉学家,实现了根本意义上的人生转变。除了精通中文以及翻译有关基督教、自然科学、国际法方面的书籍向中国人传布之外,丁韪良还笔耕不辍,撰写有《花甲忆记》《北京被围目击记》《中国人对抗世界》《中国古世公法论略》《汉学菁华》《中国觉醒》等著作。由于丁韪良的汉学研究领域庞杂,缺乏自成体系的学术框架,难以界定学术源流,似乎与著作等身的美誉无缘。据不完全统计,丁韪良一生出版中文著作、中译著作42部,英文著述8部,在各种报纸杂志上至少发表了153篇文章。他的英文著作中有3部主要作品现已译成中文,它们可以被视为一个系列的三部曲:1896年出版的《花甲忆记》(The Cycle of Cathay)主要是对他在华期间前46年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和所结识的各类人物以及亲身感受中国社会外部生活,包括他执掌京师同文馆的回忆;1901年出版的《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是他对于中国人的内在精神生活、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内涵以及中国教育定位,如科举考试、国子监、翰林院和京师大学堂等问题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1907年出版的《中国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则是对上述两部书的补充,它在回顾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时,着重描述了作者所亲身经历的1902至1907年间清政府推行的新政和改革,并试图解释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以及表达对中国光明未来的极大期盼。丁韪良认为,只要宪政和改革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中国社会注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的强盛和融入国际社会的那一天也就必将能够到来。[2]3这三部曲贯穿着一种积极的政治变革思想,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的衍变过程。1868年10月,同文馆教习丁韪良以“中国通”的身份出席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东方学会,并以《中国与西方的现状及未来关系》为题发表演说。这篇演讲稿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为题,发表在1869年1月出版的《新英格兰人》上。他把清朝同治新政称之为“大智识运动”,在意义上等同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1880年略作修改后,他将这篇文章收入《翰林集》第一编。20年以后,尤其在亲身经历戊戌维新时期社会变革以后,丁韪良对《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文再作修订,又以《中国的觉醒》为题,置于其《汉学菁华》一书的“序篇”。1901年,当西方列强仍沉浸在瓜分和灭亡中国的喧嚣中时,他却依据当时中国社会改革的新趋势,大胆地提出了更为惊人的预言:“20世纪前几十年将看到新中国的崛起,它注定要在世界大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难道还会有什么疑问吗?”1906年,丁韪良将《中国觉醒》作为他的新著之书名。[3]
细捋蕴涵在《花甲记忆》《汉学菁华》《中国觉醒》三部汉学作品中的有关“礼赞中国”的精言名句,就能更形象而生动地展露丁韪良“礼赞中国”的真情实意和真知灼见。丁韪良“礼赞中国”的系列文化观念,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的沟通意义,而且也有助于中西关系正常化和多元文明互补共赢的新发展。
第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丁韪良在华旅居的半个多世纪里,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各地,加上他勤勉钻研,博览群书,因而对中国的地理面貌和环境优劣有着一般外国人不常有的体验和感受。本着实事求是和某种眷念的情感,他对得天独厚的中国地理环境有着简明而重点的描述,其中包含着中国学研究的内在逻辑性和思想深邃的历史见解,堪称晚清末期西方来华汉学家中屈指可数的中国地理知识的权威。在1907年出版的《中国觉醒》一书中,丁韪良潜意识地按照中国传统以汉族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来划分晚清中国的行政地理全貌,将之分成五大地区,即十八行省、东北、新疆、蒙古和西藏,并采纳了1905年中国内地绘的一份关于当时中国十八行省的面积和人口统计图,总计国土面积1 532 420平方英里,有407 331 000人。丁韪良眼中的中国最初的形象是富饶的土地、大自然丰富的产物和勤劳的中国人民。“可以断言,在太阳所照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区能够享有支持一个富足而繁荣的民族所必需的这么多的优越条件。”[2]3从积极意义上讲,丁韪良对于晚清中国十八行省和满蒙新藏等地区的简述具有很强的地理可靠性和较熟识的文化底蕴,是一位外国人眼中的粗线条型的中国地理面貌,就像一部蒙太奇的脸谱画,真切而又梦幻,朦胧而又魂牵。
第二,普惠他邦的古代文明。丁韪良认为中华民族并不缺乏原创性,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有很多影响全世界的发现或发明,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是名列前茅的,“也许很难显示中国人具有出众的创新才能,但是像他们那么聪明和注重实际的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可避免地会积累大量的技艺和科学基础知识。他们并不缺乏原创性。但西方人在历史的发端与他们初次相遇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显然是土生土长的。甚至在今天,西方旅行家也会对他所看到的一些中国人所特有的方法感到吃惊。正是这些独特的东西构成了中国人的物质文明”[4]3。除在技艺和科学领域里的物质文明之外,中国人还创造了内涵深厚的精神文明,在哲学、文学、宗教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文化成就。“作为一个历史跟埃及同样悠久,而因异邦征服造成其连续性被打乱的时间却要短得多的民族,中国人曾经有许多有价值的发现,这一事实本身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令人感到奇怪的倒是居然没有人肯花一点精力来指出远东古代文明对于西方人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在很多情况下,西方人所受到的这类影响都可以得到证明。即使在另外一些证据还不是非常充分的情况下,根据排序而得出的推论也对中国人有利。传播文明的渠道也许并不容易查明,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传播早在有历史记载之前就已经存在,正如大海的潮起潮落享有一个共同的脉搏,以及遥远的海岸线之间有暗流相牵。”[4]3在公认的世界文明古国中,迄今仍有中华民族5 000年连绵不绝的文明,既延续了中国人优良的生活理念和方式,也更新着新的生活元素和创造着新的生活奇迹,为人类社会的繁荣、幸福和安宁继续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热衷和平的进步使命。丁韪良认为,如果把闭关政策看成是中国不开化的民族劣根性的一个标志,那么近代中国史就是一部走向开放进步、走向更加和平的文明进行曲。可惜的是这支进行曲充满了悲壮的民族色彩,因为它是在战争硝烟中来消弭战争的一系列战歌,“这个庞大帝国对于其他国家无节制交往的开放并不是来自其内部的一个逐渐的演变过程——它是远东保守力量跟西方进步力量之间一系列碰撞的结果”,“这些碰撞每一次都演绎为战争,并滋生出扑朔迷离而又转瞬即逝的文献”,“在过去七十年中,中华帝国至少有五次跟外国列强发生了冲突,而且每一次,它的政策都会经历一些多少有点广泛的修正。……中华帝国是一个戏剧舞台,这里上演着一部可以分为五幕的悲剧。该戏剧的名称为‘中国的开放’”[2]121-122。在这五幕侵华战争的背后,是晚清恪守的最低和平界限。中国人的和平特性,世有公论,正如一代“文化怪杰”的晚清学者辜鸿铭所指出的:“今天的中国人仍然过着孩童般的生活、心灵的生活。……但他却有着一种思想和理性的力量,使得中国人成功地解决了社会生活、政府以及文明中许多复杂而困难的问题。我敢断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欧洲民族,都未能取得像中国人这样辉煌的成绩,他们不仅将亚洲大陆上的大部分人口置于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之下,而且维护了它的和平。”[5]34
第四,前赴后继的变革精神。在丁韪良的心目中,中国人是那么勇于革新、努力向上,“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要求驱逐满人和瓜分中国。凡是了解1900年所发生故事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即满人应该得到这样的下场。……我之所以公开放弃这一说法,是因为看到了清政府倡导改革精神这一富有希望的变化。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要比迎来一个新王朝或在波兰的分裂政策下更容易获得和平的进步”[2]210。对改革精神和改革现实的崇重,竟然让这位美国传教士可以忽视自近代以来满清政府对西方诸国“肇事”的各种灾难,显然是一种渴慕世界同步的文明的人性光辉。尽管晚清的各项改革事业成效甚微,但一种前赴后继的改革精神令人鼓舞,让丁韪良感到了中国将会在改革洪流中能争取到一个辉煌的未来,而这无疑是他“礼赞中国”的政治信心,“所有的改革都归结于新式的教育,而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开展了教育改革。在铁路、电报和报纸的支持下,教师们将会驱散边远地区的死气沉沉,并且给所有的村民带来一个比他们的乡村更为开阔的视野,比他们的锅碗瓢盆更高一层的思想境界。在完美科学和真正宗教的激励下,只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人民就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据一个主要的位置”[2]211。
第五,睡狮惊寤的大同世界。丁韪良深谙中国文化精髓,坚信中国这头近代酣睡的雄狮即将惊寤醒来,所带来的不是灾难,而是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排外精神是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正常思维,绝非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他甚至认为庚子之变后的中国人排外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要求取得国家间平等和人权平等,“在四个相隔甚远的省份里,人们受共同的仇恨所驱使,并出于同一个目的,把愤怒相当公平地发泄在来自四个不同民族和所有职业的人身上。如果说他们有共同目的的话,那么它就是要迫使外国列强重新调整不平等条约中的关系”[2]184。这种深入骨髓的思想见解,并非个案,美国著名女作家、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在《我的中国世界》中也有类似的认识:中国整个民族和每个人都具有强烈的自豪感,他们不喜欢以强凌弱。中国人的这种特性,加上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的傲慢态度以及有意无意的白人优越感,都在中国人心头激起了满腔怒火。愤怒的火焰已经燃烧了一个多世纪,而白种人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6]52丁韪良对于中国大同世界理想充满了敬意,并看重美中友好关系的未来,“谨将此书①指丁韪良著《花甲忆记》,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献给我的孙辈和全体美国人民,希望它能使大家关注一个伟大民族的未来,美中之间的关系将来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紧密和重要”[7]题献词。
简言之,蕴涵在三部汉学作品《花甲记忆》《汉学菁华》《中国觉醒》中的丁韪良“礼赞中国”的系列褒扬之语,其内容十分丰富,论证十分深入,影响十分巨大,对中国人的激励作用是持久性的。丁韪良“礼赞中国”的真知灼见和慈善之德,充分体现了他的东西通情和文明共享的世界主义立场。建立在世俗文化研究和福音神职任务相得益彰的基础上,丁韪良“礼赞中国”的系列文化内容,有助于中国人民获得更多的外部知识,开阔视野,逐渐养成与世界各种文化相连接的主动性,同时也有助于外国人在“西化”和“现代化”中国问题上达于某种程度上的趋同,尊重中国文明进化的历史规律和变革进步内容,使互不信任和排外的文化冲突化为同舟共济的文明共享,为构建人类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协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讲,丁韪良是中国人民的诤友,也是中国进步事业的同道者。他的“礼赞中国”,或许也将他自己包括在内。
二、丁韪良旅居中国的自由康顺
年仅23岁的丁韪良在1850年踏进中国土地,直至1916年病逝在北京,长达66年的在华生活已然将他在诸多方面、不同程度地中国化了。传教生涯的微不足道、执教生涯的风云人物、潜心著述的晚年风采,都使这位美国侨民旅居华夏的生活相当康顺,并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获得在华游历、考察、研究和工作的极大自由。这种极其难得的自由和康顺造就了一代社会活动家和汉学家,丁韪良的“礼赞中国”也就有了足够多的心理优势,一幅美好的中国图景就是他着墨的研究对象。他在《中国觉醒》的第一部分讲述“帝国全貌”,是通过亲身游历和书籍考察,对晚清中国所辖十八行省和边缘地区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归纳,藉此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虽有挂一漏万和浮光掠影之嫌,但其中不乏有意思的段落,既表达出作者对于中国诸如绍兴这样小城镇的喜爱,也反映出了他对上海和北京这样大都市的流连忘返。丁韪良虽然出生在美国,但大半辈子都定居在北京,并在北京去世,和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北京完全可以称作他的第二故乡。因此,举例他在中国一些地区的旅居经历,将有助于理解在那种自由康顺的生活里,丁韪良对中国的赞誉并非一时意气,而是在久经考验下、深思熟虑后的必然结果。
作为一名基督新教传教士,丁韪良赴华的使命是前往开埠不久的宁波传教。宁波是美国长老会在华活动主要据点,1844年6月20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首先到达这里传教,到1845年5月已有7名长老会成员,并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基督教新教教会宁波长老会。在丁韪良抵达宁波之前,除了麦嘉缔外,该会还有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袆理哲、娄理华、柯理、克陛存、露密士、卦德明、怀特、歌德和兰金等人。[8]129-158初来乍到的丁韪良受到了克陛存教士的接待,并在工作住所里得到中国仆人的伺候。几天后,丁韪良的宁波话学习进展从一个使人厌倦的任务变成了令人兴奋的消遣。他的妻子成为他学汉语的伙伴,开始一直走在他的前头。她成功地学会了当地方言,并且挤出时间劝说几位本地的妇女皈依了基督教。由于宁波话只有口语,无法用文字表达,而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语音的音值很不确定,这就促使丁韪良用无所不包的罗马字母来加以表述。虽然丁韪良的创造和推广汉语拉丁化拼音体系的努力并未得到美国长老会传道部的支持,但他依旧充满希望,他不认为自己的这一努力有什么过错,到1902年他仍然感到需要一种书面的拉丁化体系作为沟通中介,为大众“从中国的精神枷锁中逃离提供一条生路”,并且希望京师大学堂能试验这一新体系。[9]19当然,丁韪良的汉语拉丁化活动也表明其早期传教的重点在于用宣传福音的方法做下层中国人的工作,他和其他传教士推广“洋字编音”,主观上显然是为了让中国各地说不同方言的不识字者尽快接受基督教,但同时他们的活动也刺激了20世纪初在中国语言领域的改革,拉丁化体系最终成为民国时期到解放后诸汉语拼音方案的滥觞。[1]42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拼音系统的推广很不容易,它最终局限在宁波一隅,但对年轻的丁韪良而言,这项学习汉语的发明却是一种荣耀,至少是一种能够长期在华生活的自信和自勉。事实上,丁韪良也特别看重这种成就,并且潜心学习中文,所取得的成绩能让一般来华传教士感到惊奇,这更为他日后加入中美外交谈判和执教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奠定了语言运用和文化理解上的坚实基础。“在这一时期,我开始用文言或古文来进行写作,并且完成了《天道溯源》①《天道溯源》是一部有关基督教证据的论著。这本在中国和日本流传甚广并多次再版的中文书。我相信,在文人学士中,有许多人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才皈依基督教的。荣耀属于上帝!”[7]31从总体上说,丁韪良在宁波城里一住6年,依靠勤勉和语言天赋,他的宁波土话和中国官话均已炉火纯青。曾在宁波任职并熟识丁韪良的赫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1855年1月30日:今天我的老师批评了这里各个英国人的汉语,他认为丁韪良是最好的——无论是说官话还是说土话都行。他对密妥士先生的官话似乎并不怎么欣赏。至于玛高温大夫,他似乎是最差的。”[10]142无疑,学习官话的成功为丁韪良日后北上充当美国公使的翻译和进入清政府上层官场提供了机缘,后来他把在宁波的这些年描述为他一生“最有成就”的岁月。[11]67
在宁波的旅居生活中,丁韪良的在华传教也初见成效,这对年轻的他产生了很强烈的所谓上帝事业的归属感,也使他的中国式生活更加稳定,并加深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丁韪良能够在城市教堂里主持晚祷会,一个有200个座位的小礼拜堂里经常是座无虚席,其中大多数人是工匠和手艺人,他们干了一天活以后,来听他讲述基督教那些引人入胜的寓言。而在大礼拜堂里,听众大部分是受过教育的文人,其中有些是老师和其他传教使团的本地传道人。由于勤勉的努力,丁韪良在宁波传教成果也是很好的,皈依上帝的人数和中国教徒的再生产能力都让他感到不辱使命。他这样回忆说:“我们的房子总是对外人开放的,有时候在我们的客厅里聚集着来自五个行省的陌生人。我们的住宅周围还有衙门和官员的住宅,许多官员都来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而他们的夫人们也跟我的妻子互相来往。……我的官话老师后来成了基督徒,并且在把福音书传播到华北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教我们说宁波话的鲁老师也从我们这儿学会了信奉基督教,并且成了一位传道人。他贤惠漂亮的妻子最先跟他一起成为基督的信徒,后来他的妹妹也这么做了,最后是他母亲,这位过去曾经强烈反对他改变信仰的虔诚的佛教徒,也入了基督教。……大约同一时期皈依基督教的还有谢先生和贾先生。前者是我雇来印刷汉语拼音文字的工人,后者是他的朋友,他俩对基督教都很虔诚,试图尽自己的能力过一种圣洁的生活,并且通过参加宗教仪式的实践来增进德行。……这位贾先生受到洗礼后,被我派去负责学校的工作,他在教书的同时,还认真地研读基督教神学著作,他后来成为,并且至今仍然是一大批本地传教士中的佼佼者,拥有高度的‘仁慈、坚忍和精明’,这三种品质被杨格非教士誉为传教士成功的三要素。”[7]39-40
1860年,决意北上的丁韪良对他首途赴华传教的驻地宁波充满着留恋之情,这种情怀又因他赴京为更大的理想努力而加强,因为他离开宁波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访了。他写道,“在那里,我度过了朝气蓬勃的十年光阴,那是一生中最容易感受新鲜事物的十年,也是一生中学习外语的黄金季节”[7]137,“宁波,我在这里找到了毕生的友谊,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中国知识,也写出了一些我最好的作品。我再也没能回到这个城市”[7]139。而且在宁波期间,因为传教和研究中国文化的需要,丁韪良结识了一批中外友人,增添了异国生活的安全感和学习乐趣。这些知心的中外朋友,主要包括中国士绅张鲁生、长老会宁波传教站的先驱者和创建人麦嘉缔医生、英国传教士阿尔德茜小姐、设计砖石结构的宁波教堂的克陛存、在中国重逢的童年好友古尔特夫人、兰金牧师和他的太太、祎理哲牧师、英国圣公会的陆锡主教、郭保德和高富、慕稼谷和慕雅德、美国浸礼会的高德、外科医生玛高温和罗尔梯、倪维思夫妻等。丁韪良特别感激比上述诸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物,即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 和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两位英国人。赫德由一位初出茅庐的翻译人员发展成为著名的政治家,被称为“伟大的总税务司”。戴德生是新教的罗耀拉,他领导了许多人并对他们具有绝对的权威,他建立并管理的内地会的做法在传教事业里开创了一个新纪元。[7]139-144无可讳言,以上在宁波结识的诸多中外人士,不仅是丁韪良在华传教事业的同道人和精神力量,更是潜力巨大的人脉资源,成为沟通传教和美中关系走向的人为力量。丁韪良在传教实绩上微不足道,却因文化修养和语言天赋而成为传教士翻译官,进而登峰而成为一位披阅中西文化的传教士教育家,难以背离上述珍贵的人际关系和深厚友谊的助力作用。
在华60多年的旅居生活中,丁韪良曾游历了中国广大地区,但最让他心存眷恋的地方就是上海,“在那儿住了一年以后,我怀着深厚的感情把它视作我在东方的第二故乡”,在《中国觉醒》一书中,他满含深情地写道,“上海位于中国一条大动脉入海口的广阔平原之上,它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的一个重要场所。中国城的低矮城墙后面仍然隐藏着破旧的贫民窟,但是在北城门外有一大片地方被称作‘公共租界’,那里有一座被称作‘模范租界’的城市如出淤泥而不染的美丽莲花般拔地而起”,“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开始超越广东,它要比任何其他口岸都更多地向中国人展示着西方令人惊叹的技艺、知识和进取心”,“在公共租界内实行的是法制,并非像中国其他地方那样是靠地方官员的人治,这里一切都讲究自由和公正”,“上海有各种等级的学校,有些归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管辖,另一些则归属于传教使团。属于美国圣公会的圣约翰大学和美国监理公会的中西书院,在继承原来由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传教团所长期担负的教育事业上是出类拔萃的优胜者。此外,外国人和中国人的报纸——后者在这个作为避风港的城市里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在别处是无法想象的——还有广学会和其他外国人和中国人的翻译机构,在蒸汽印刷机的帮助下出版了成千上万种图书,汇合成一股中国人已不可能在漠然处之的力量”[2]22-25。可见,上海素有的地理优势和人文气息,让这位远海而来的传教士深深迷恋,并进而升华到与身共存的人文境界,实属难能可贵的异国情怀。
与对上海的情感相比,丁韪良对北京的感情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北京看作他的家,“北京并不缺乏粗野而又光彩照人的景色,就生活便利程度而言,这个著名的京师还比不上西方世界的一个乡村。它大致与费城处在同一纬度上,只不过这里更为干燥、炎热和寒冷。这里的气候如此上乘,以致虽然没有一套公共卫生系统,但北京人的死亡率仍然低得惊人。我第一次进入北京的城门是在1859年,1863年我开始定居于此。这里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像我的家,我很可能会在这里结束自己的朝圣之旅”[2]34-35。尽管丁韪良首次进京正值大清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受失败,但并不能持久支配丁韪良对北京的贬抑之感,因为他事实上在北京生活了40多年,真的把它当作家了,特别是他在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执教生涯,最终让他越来越感受到了北京的生活如家的温暖和安定。1863年6月,丁韪良来到北京拜会新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既进呈刚刚译成的《万国公法》,又陪同公使和卫三畏博士游览了美国公使馆避暑胜地的三山庵前面的那座高耸山峰,得以再次领略北京风貌。在他看来,“北京居于两座呈抛物线形状的山脉的焦点上。一座山脉与蒙古高原擦肩而过,向东延伸至渤海湾;另一座则从西北高原向南延伸大约四百英里,到达黄河沿岸。除了在北京种植的一些小树林外,这些山脉多草而乏树,它们层峦叠嶂,就像绿色海洋上翻滚的波涛。至于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山峰的高度,有一些山峰可能高达四五千英尺”[7]151。京师附近最美丽的山谷被选来兴建佛寺,而丁韪良的住家就选在其间的宝珠洞,“这些庙宇都非常美观。兴建它们的和尚在选择归隐之处的时候都有很高雅的情趣。不断地向上攀登,眼前越来越开阔,直到到达八大处中最高的宝珠洞为止。……登临其上,一切都豁然开朗了,可以远眺远处群山环绕的巨大平原。偌大的北京城及其闪闪发光的宫殿是最引人注目的。南边的南苑,西北方向富丽奢华的颐和园与万寿山是慈禧太后还政于光绪之后的住所。光绪皇帝必须每隔五天拜见太后一次,还得给她磕头。最后,两条蜿蜒流淌的小河与一片水光潋滟的湖泊构成了这优美壮观的全景”[7]152。随着在京生活日久,丁韪良对北京的名胜古迹和现代景观都有了自己的独特感知和深厚感情。其中,北京风景中最让丁韪良感慨万千的建筑,就是长城,“长城这个名称十分贴切,实际上它仅仅环绕着蒙古高原,绵延其周边大约一千五百五十英里。长城成为防御中原良好的屏障。它随着山峦的起伏而蜿蜒不绝,十分壮观。想想看,它从沙漠直达海边,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壮举!”由于长城历史悠久和迄今巍然而立,令人遐想而感慨古今,丁韪良同样抚今追昔:“要研究埃及的历史,就应该登上金字塔的顶端。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就没有比长城顶点更适合于放眼远眺了。在烟云似的上古与我们生活的这个多事之秋中间,长城矗立着,它支配着全部不断变幻的历史舞台。尽管它十分巨大,成为地球表面一道独特的地理风景,但是对我们来说,它的重要之处在于它的历史而非规模。一些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当代,但正是在这个独特的地方我们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回想过去,远眺未来,把自己关于中国全部历史的一点肤浅印象介绍给读者。”[7]171-172简言之,丁韪良在北京的旅居生活是非常惬意的,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将他与北京结成了生死不渝的情感,以至于他们夫妇都在北京病逝,并安葬在北京墓园,堪称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三、丁韪良在华执教的尊荣惬意
在19世纪中国国门徐徐开启的岁月里,美国传教士作为当时最有文化素养的学者雅士能够在中国教育舞台上人尽其才,也是凤毛麟角。丁韪良以其勤勉精神,深谙中西共性和差异,在文明传教和文化研究方面堪称精英人才,因而恰逢其时地获得在近代中国著名的两大学府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执教尊荣,既是必然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又是他在华生活的最惬意的人生经历。而这种惬意和尊荣所产生的心理优势,无疑也潜在地成为丁韪良“礼赞中国”的最基础的个性因素,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发展趋势。在获得这种执教尊荣的同时,丁韪良也为近代中国西方化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或许是一位传教士教育家所不期而遇的社会进步之举,“对中国的西方化的研究不能忽视丁韪良,他是十九世纪晚期在中国的著名外国人之一。……他是近代中国国家教育之父。……他也扮演了向中国介绍国际法的领先者的角色,他还通过他的教学与出版物……在中国这块仍然熟记着儒家学说及其他古代书籍的土地上,传播了许多西学知识”[12]6-8。从人生进程的角度上看,丁韪良在华的主要工作是在国际法、简单科学、近代教育以及早期汉学这些领域进行的,所幸的是,“丁韪良漫长的为中国基督教化及西方化所作的努力,赢得了专家权威们的高度评价,并使中国人像美国人那样对他非常感激。他是一位毋庸置疑的到中国的伟大的新教传教士,并极大地促进了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他在他的职位上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并且比其他个体的传教士们更好地达到了目的。他成功地帮助中国成为更意识到周围的世界,并且通过近代教育,使中国朝着有利于西方化的方向发展”[12]217-232。
当然,丁韪良能够顺利走上近代中国的最高学府讲坛,离不开他在中美关系构建上的建功立业,尽管这种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在宁波传教已近8年的丁韪良,因为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作为西儒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美国对华事务择取中获得遴选。丁韪良自此获得了为上帝服务的国家意识上的政治机遇,成为美中再续条约的所谓谈判过程中的一位中文翻译。这项任务在如今世界格局中似乎不值一提,但在100多年前各国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具有“中国通”的素养和中文语言能力的传教士乃是西方国家的国宝级精英人物。因为有了他们,西方有了与晚清中国沟通的桥梁,甚或某些翻译成果是自觉地有利于西方列强的。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准备北上攻打天津和北京之际,美国派遣来华的全权公使列卫廉也随之北上,成为丁韪良参与美国使团的良机:“听到美国全权公使列卫廉将要北上的消息后,我觉得加入此行可以看到许多大事,也许还可以为传教事业开辟新的领域。好几年前我就掌握了中国的官话,会话水平通过我和中国官员的频繁接触得以提高。美国领事裨辣理卫廉(Charles William Bradley)正好没有雇用翻译,便请我做他的翻译,同时处理一些临时事务。由于我拒绝接受薪金,他便竭力为我在美国使团里谋到了一份差使。在他和卫三畏博士的推荐下,我对使团中文秘书一职的申请获得成功。他特派羚羊号汽船给我带来这一消息,并载我来到上海,列卫廉先生聘我为中国官话的翻译。”[7]98-99在美中《天津条约》签署后等待清廷批准和换约的间隙,丁韪良回到了宁波继续传教活动。不曾想到的是,他从此与美中关系结缘了。1859年初美国新任的驻华大使华若翰及其秘书卫三畏博士来到宁波,邀请丁韪良陪同北上并担任原来的职位,同时属于美国传教会的艾奇逊也加入其间,担任翻译助理。中美《天津条约》在天津换约成功,意味着华若翰的使命完成,但却没有终止丁韪良在华生活,反而将他的传教使命和中国北方文化相连接,“我们背向京师离开时的心情,可能和我们进入城门时一样高兴。我又怎能想像到我还将在那个守旧的堡垒里面再过上31年繁忙而欢乐的生活呢?我离开了它,没有被它的虚华所迷惑。我必须努力寻找它所蕴藏的伟大和壮美,而乍眼看来,它在各方面都显得腐朽肮脏”[7]134,“北上之行使我关注大清国的北部,并觉得应该去那儿服务。这个念头促使我决定离开宁波,这一个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你缺点很多,但我爱你始终不渝’的城市”[7]137。
事实证明,丁韪良参与中美《天津条约》谈判和签署,不仅确保了美国在华既得利益,也因宗教宽容条款而使传教特权得到新的保护。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中,丁韪良不自觉地成长为一位声名显赫的在华传教士,加上他的聪颖勤勉以及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里的成果,不久就成为中外条约制度的和局维系中的一个难得的人才。翻译《万国公法》及其他在总理衙门刊刻推广,成为丁韪良在清政府官场上抛头露面的重要筹码,成为架设在中美关系沟通桥梁和晚清中国教育变革桥头堡上的一个指向标。1862年,回美休假两年的丁韪良返回中国,希望能到北京去传教。在上海滞留期间,他花了一段时间翻译惠灵顿的《万国公法》。“最早介绍近代国际法到中国的,是美国传教医生伯驾,他是受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委托,翻译滑达尔的《国际法》一书中的几段,供林则徐参考的。滑达尔是瑞士国际法学者,所写之书是1758年出版。丁韪良认为此书已过时,因此选用了惠灵顿所著的《万国公法》。该书1836年出版,在当时算是最新和最通用的国际法蓝本。惠灵顿从1815年起到1827年是美国著名的律师,后来被派赴欧洲出任外交官有20年之久,1847年回到美国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被认为是国际法权威。”[13]191-192丁韪良得到了时任美国首任驻北京公使蒲安臣的多次鼓励和向清廷推荐使用的保证,加上总税务司赫德的支持,使得这部书的翻译得以进行下去。1863年6月,抵达京师后的丁韪良遇到了卫三畏博士,并在离京城12英里的西山见到了美国公使蒲安臣。从个人声誉而言,翻译《万国公法》和呈送清廷采纳是丁韪良登陆美中关系舞台的一种政治资本,“我认为这部作品可以对我自己的事业,以及中英这两个帝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其实,局势对这种书的需求早已引起我的注意”[7]150。历史已经证明,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校定的《星轺指掌》以及稍后的《公法便览》《公法会通》《陆地战例新选》这5部国际法译著,基本上将西方最新、最有代表性的国际法著作介绍到中国,这些译著涵盖了国家主权、外交、战争、海洋、公民权利等国际法的主要内容。从总体上看,这些国际法译著填补了晚清国际法及外交学著作的空白,许多内容对当时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特别是在派遣驻外使臣、处理外交事务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先进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开放也产生了积极影响。[14]当然,这些国际法译著毕竟是以西方外交制度为模版,其应用于清朝外交需要一个国情结合的问题,在当时弱肉强食和晚清颓势的背景下,西方国际法并不能公平对待中国。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的一段话堪称点睛之笔:“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苟欲望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15]314从这个意义上讲,丁韪良翻译美国学者惠灵顿的国际法著作而来的《万国公法》更具有重大的政治外交意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国际法的‘作者身份’在这里显得相当关键,因为西方列强争夺的焦点之一,就是谁的国家更有资格代表普世价值”[16]160。美国因这部国际法在总理衙门推行而获得了较其他列强在华更多的文化优势,“西方文明在东方获得进展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惠灵顿先生这部著作被支那政府采用,作为其官员在国际法领域的教科书使用。这本书是在1864年朝廷的赞助下翻译成中文的。这项译事系由美国公使蒲安臣提议、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译,并得到总理大臣恭亲王委派的支那学者的协助,此书是献给蒲安臣的。支那政府在与西方列强驻北京的使节办理外交交涉时已经引用和依赖这部著作了”[16]183。
1863年秋,丁韪良终于在京师找到了合适居住的地方。那儿临近总理衙门,在内城的东南角,其空间足以开办学校和小礼拜堂。房子的地板是用砖铺成的,后用木质地板更换,包括两间厢房。这样的居住环境是非常有利于丁韪良进京完成他的使命的,“我移居北京期间最重要的使命是准备在北京建立一所学堂来培养传教士、医生和工程师。我提交给美国北长老会教会秘书娄理瑞博士的一份关于开办学校的草案,但除了在一份报纸《中外纪事》上刊登了这份草案外,没有进行任何实际行动。我把这份报纸递给赫德先生,没有恳求他一个字。令我惊喜的是,他竟然答应从政府的资金中每年拨出一千五百两白银以供办学使用。第一年我花去了九百两,第二年花去了六百两,第三年只用了五百两,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很难从士绅家庭招收子弟入学,我不得不限制自己活动的规模。此项几乎流产的工作带来的最大收获是在格物学方面准备了一份教材”[7]160。1865年,是丁韪良在华活动的重要转折期,是年3月,他经由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推荐,就任京师同文馆第3任英文教习。这项任务开启了他从传教向执教转变的人生跨越。1967年10月,他以翻译《万国公法》的声名应邀为同文馆英语翻译教习,讲授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丁韪良在欣然接受这种聘任之前不得不把传教事宜托付给别人,并于1868年暂回美国进修以便为新的岗位作好准备。1868年6月,丁韪良进入耶鲁大学,在校长吴尔玺的直接指导下进修国际法。在美国进修期间,他曾接到赫德催促他尽早返华的来信,因为清政府对同文馆的工作不甚满意,甚至有可能解散它。在回信中,丁韪良却表达出信心满满的前景:即使同文馆被关闭,也是可以使之重开的,或者说,即使削弱到了尽头,它的全部价值依然丝毫未损。[7]1641869年9月,丁韪良进修和休假结束后,立即回到北京,首先拜访了赫德,得到了两条令他惊喜的消息:一是同文馆依然存在,一是赫德决定让他担任同文馆的总教习。从某种程度上讲,丁韪良受聘同文馆总教习,或许因他是力挽狂澜的教育奇才,颇有临危受命的意味。“同治六年(1866年)正月,(曾著《瀛环志略》的福建巡抚)徐继畬担任同文馆总管大臣。他时刻没忘让大清国尽快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着手对同文馆的教学进行改革。有两件事奠定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基础,一是确定了同文馆办学方针:兼容并包,智周无外。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滥觞,这一胸怀博大的方针可以看作老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先声。第二是聘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把这所单纯培养外国翻译人才的学馆演变成以学习外语为主,兼习多门现代科技知识的综合性学校。同时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丁韪良的《万国公法》也成为学生必读的教材”[17]52,“同治八年(1869年),心力交瘁的75岁的徐继畬怀着黯然心情再次回到山西老家。他走了,总教习丁韪良继续留下来,这位说着带有宁波口音的汉语,并成为大清国三品官员的传教士,在同文馆的教学中贯穿了西方科学知识和教育思想,为大清国的教育步入现代化做了一系列开拓性的工作”[17]54。1869年11月26日,丁韪良在总理衙门几位大臣和美国代办卫三畏博士的陪同下,到同文馆就任总教习一职。在就职典礼仪式上,大约有40名学生,分班由曾出使欧洲的斌椿提调率领,向总教习行额手礼致敬。学生们身穿长袍,头戴饰有流苏的礼貌,场面甚是壮观。丁韪良用汉语发表了就职演说。总教习的职务大抵相当于后来大学的教务长,权力很大,其职责主要是教务管理,如课程表的制定与实施,对教习的监督与稽查,各项定期考试的执行;统筹编译教材、图书事宜,如译书章程的拟定,印书处的筹办,译成图书的鉴定等。因此学校主要的教务活动都由丁韪良全面负责和指导,所以他自称是同文馆的“保姆”。[18]在随后20余年的任职时期里,丁韪良不仅感同身受地意识到同文馆创建的时代意义,而且孜孜不倦地将同文馆的教育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高度,所取得的成就进一步使得他声名远播,以致在中国著名的戊戌变法期间得以升职为首屈一指的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教育家。
甲午战败揭开了维新派自上而下的清廷政治变革,在1898年春肇起的戊戌变法中,教育改革是重中之重,其中创办京师大学堂是令人振奋的一项举措。孙家鼎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校长,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工资与他在同文馆时期一样,每月500两银子,折合当时美元375元。此外,清政府把丁韪良的官衔从三品晋升为二品顶戴。1899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丁韪良被选定为西学总教习,应该说是丁韪良长期以来在宣传“实学”或“新学”方面对中国上层以及士大夫的影响所致,也是他自己出于使中国皈依的使命而主观努力的结果。[1]294然而,京师大学堂命运多舛,戊戌政变和义和团运动使之步履维艰。1900年6月,北京城里已是义和团的天下,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丁韪良只得回到美国暂避一年。1901年9月返回北京的丁韪良,仍被清政府聘为大学堂总教习,而管学大臣张百熙被慈禧任命为校长。张百熙对外国传教士控制国立大学早已不满,认为这些传教士并不是什么学有专长的专家,京师大学堂理应完全由中国人自办。于是他以学校经费困难为由,在1902年2月26日解聘了所有外国教习,包括总教习丁韪良,只发给他们18个月的工资,“惟现在大学堂开办需时,各洋教习闲住一月,即需月修金。大学堂经费无多,不能不设法樽节。是以将各西教习不论去留,目前一概辞退”[19]113。显然,在管理和执教京师大学堂的几年里,丁韪良对中国教育试图加以更有力度的西方化变革,但未能所愿。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首批招收的学生在两三百之间,都是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功名的秀才、举人和进士。大学创办初期,朝野上下一致拥护。但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后,风向就变了。两年后,大学堂在义和拳的动乱中被迫关闭。大学堂的一位教授、一位助教和一位学生分别在动乱中丧生。……这座专门培养精英的大学堂与那个必将把学校推广到大清国每一个城乡的复杂国民教育体制之间相去甚远。实际上,旧制度下的高官贵爵们仍对这种新式教育侧目而视。就像对待铁路那样,他们将它视为一种危险的尝试和祸根。”[2]160-161尽管如此,在京师大学堂的管理和执教生活依然成为丁韪良在华生活惬意的重要内容。值得提出的是,丁韪良在同文馆20余年的总管和先后担任英文、国际法、富国策、格致等教习的经验,使他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近代教育家,荣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或许并非匹配他的才干。1898年9月24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帝国大学——美国人丁韪良博士被任命为校长》的文章或许才是实意。从历史进程来看,丁韪良实际上成为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当然,现在很少有人提到他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但是,是他在京师同文馆中引入了西方的教育体系,是他担任了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西学总教习,于情于理他都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20]
尽管被京师大学堂解聘,并不意味着丁韪良在华惬意生活的中断。当时正处在清末新政初期的改革用人之际。庚子之变之后,慈禧太后回銮京师,继续执掌苟延残喘的满清王朝,不得不推行1902年开始的清末新政。湖广总督张之洞是这场绵延数年的清廷改革的政府要员和地方大员之一,他以湖广总督的身份着力在两湖推行变法。丁韪良在1902年接受邀请,赴武汉帮助张之洞推行他的教育变革运动。丁韪良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三年,回顾往昔,他认为这段在华度过的日子是他在远东生活半个多世纪以来最有趣的一段时光。除了教授张之洞的官员们《万国公法》知识之外,丁韪良还给他们讲授地理和历史,这两门课程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相互协同的。在此期间,一部论述国家间交往的书和一部达德利·菲尔德的《国际法》的汉译本就是那些讲座留下的成果,但是湖广仕学院并没有真正办起来。原因是丁韪良抵达武昌的一个月之内,张之洞总督就被调到了南京,去填补因他那位著名同事刘坤一去世而空缺的位置。在南京几乎待满了一年之后,张之洞又被召到了北京,在那里他又度过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将来目的地究竟在哪里的一年时光。张之洞从北京回来之后,身体已经垮了,他把剩下的那一点儿精力全都用在了为日俄战争这一不测事件而作的军事准备上了。这样,那个有待成立的大学一直停留在纸面上。实际上它是流产了,始终没有出现和存在过。尽管如此,丁韪良对这三年在武汉的生活还是感到满意的,“说句公道话,我对于张之洞总督的礼貌周全和薪酬发放的准时感激不尽。每个月一次给我的薪金信封上总是称我为湖广仕学院总教习,尽管实际上我可以被称作‘虚无乡大学’总教习。在有一点上,他甚至超越了我们订立的合同,即让我免费住进了一个有十个房间和一个花园的两层楼别墅。这个别墅坐落在大江的岸边,对面就是风景如画的汉阳山峦,在城里我挑不出一个比这里更好的地点。我在这里可以享受最纯净的空气,并且能够免受那些狭窄而肮脏的街道的困扰。毫无疑问,正是因为有这些非同寻常的优点,使得我能够保持身体健康,尽管这里地处内地,纬度高达三十度三十分,所以天气炎热,俗称火炉”[2]173-175。
总之,在华生活60多个春秋的丁韪良,在福音传教和近代中国教育舞台上可谓游刃有余、尊荣惬意,在个人发展上获得了很大成就感和满足感,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佳绩。“作为一个传教士,丁韪良在晚清中国最有影响的工作却与宣教布道并没有直接关系,尽管他的身份依然是一个宣教布道者。但他所宣、所教并非基督福音,而是西方近代自然科技知识;他的目的也已不是基督教化中国,而是‘文明化’或者近代化中国。更有甚者,在离开江南地区、尤其是浙江的传教工作之后,他在北京的主要工作不仅充满了世俗色彩,而且也与宗教信仰多有矛盾冲突——他所从事的,是一个自然科技知识教育者和翻译者的工作。有意思的是,我们从丁韪良的回忆录中,并看不出多少理雅各那种身份认同上的困窘以及由此而生的困扰痛苦。丁韪良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文化信仰方面因为跨文化、跨宗教的对话交流而滋生的困扰,他在宣教布道使命与作为一个西席总教习的世俗身份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或者剧烈的内在冲突。”[21]192可见,在华世俗教育的过程使丁韪良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并显示出了他对中国前景的乐观精神。他在华执教获得的尊荣和惬意,使他在从事翻译、教育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放弃了其赴华之时以“属灵派”传教方式来传播基督教的神圣使命,而成就了他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他乡异客的卓越丰碑,“丁韪良在中国66年中,一直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改变人们的思想,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正如他晚年文章中所阐述的,对他来说‘科学是箭的两翼,而宗教则是靶心’。但最终,他所传播的福音的目的并未达到,因西方科学而接受福音者寥寥无几。然而他主持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编写传播西方科学的书籍和期刊等活动,却为中国引入新文化、新科学作出了贡献”[22]70。如此的人生嘉誉和平安有福的生活过程,加强了丁韪良“知恩图报”的教育有成和汉学精进,“礼赞中国”之心油然而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丁韪良确实具有超越一般西方人甚或一些中国人自己的优长或慧眼。他能从中国近代文明的悲曲中看到潜在奋发的动能,也看到了基督教文化使者的真正使命是和平共处而非取代或同化。这是他的社会进步主义和世界主义理念规制下的中国观,尽管其中不乏溢美之词。丁韪良对中国觉醒或崛起的政治敏锐性和文化洞察力是非常人所能比的远见,这正是他“礼赞中国”的最深层次的心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