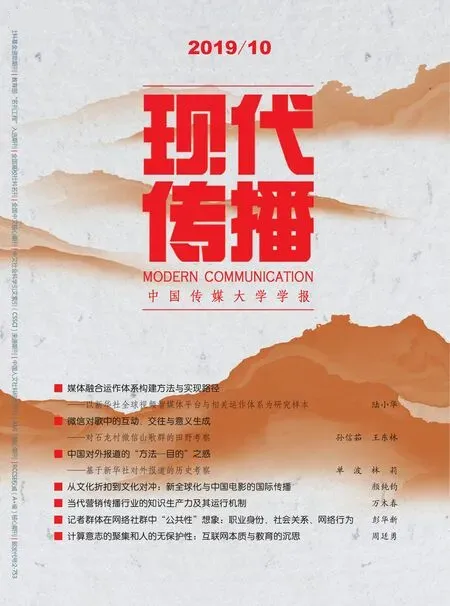记者群体在网络社群中“公共性”想象:职业身份、社会关系、网络行为*
■ 彭华新
记者作为一种职业,其主要职能是运用社会公器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信息,带有强烈的公共性特征。但是,记者以个人名义在微信群、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网络社群中的信息发布、意见表达,一方面是对非职业媒介平台的运用,属于非职业行为;另一方面又受到职业经验、职业伦理的影响和规范,在交流和互动中体现出了公共性的身份认同和专业特征。这种介乎职业与非职业的模糊地界,为记者在网络社群中的职业身份、社会关系和行为特征提出了“公共性”与否的思考。
一、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
(一)文献综述
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社交媒体的时代背景下,传媒公共性都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潘忠党从中国传媒改革的历史探讨中引申出了公共性问题,认为传媒公共性是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实践逻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传媒服务的对象必须是公众;第二,传媒作为公众的平台必须开放,其话语必须公开;第三,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必须公正。①李良荣认为公共性是传媒在具体的现实场景中的实践逻辑,公共性实践是在社会变迁、政策变迁和媒介变迁背景下对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参与。②通过梳理发现,类似的传媒公共性文献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传媒业”的公共性实践原理,聚焦于传媒机构、传媒市场等宏观领域的概念。而朱清河讨论了“传媒人”(新闻从业者)的公共性问题,“新闻从业者所进行的新闻传播实践是以全体公民为对象、为全社会提供接触和分享新闻(公共物品)的机会、设立专业的传播机构(公共领域)来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职业具有显著的公共性。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即具有非人格化”③。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在中国兴起后,公共性问题回归到媒体中的公民参与或社会行动上。王蔚研究了微博平台中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身份和表达,观察到了一些新的媒介现象,比如介于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的中间地带——知识分子话语。同时,她还观察到了微博诞生以来学界对公共性问题的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同微博建构公共性的积极作用,认为微博具有“去中心化”特征,在这种观点中,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波兹曼的“文化向技术投降”论断成为其理论支撑;另一种观点反对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指出微博建构公共领域的有限性,庞勒的乌合之众和桑斯坦的群体极化成为这一观点的理论支撑。④袁光锋以情感社会学为基础,讨论了公共舆论中“同情”与“公共性”的关系,认为在互联网社会中,“许多类型的‘情感’都是公共性自我构成和公众进行公共实践的重要方式”⑤。郑燕指出微博作为展现意见的最佳场域,弥补了传统媒体的被动、非交互性和难接近性,也发现了微博中话语权被少数精英控制,易导致群体极化、网络欺凌等一系列问题。⑥在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公共性比较上,Seungahn Nah的研究值得关注,他以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为框架,检验了非营利组织通过地方报纸和互联网分别获得的公共性认同程度。⑦
公共传播的相关理论对本文的“公共性”是否有启发意义?这是需要进一步在文献中发掘的。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梳理发现,“公共传播”并不是一个“显概念”,也没有共识性概念,甚至“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美国传播学界基本上很少再用公共传播这个词汇”⑧。即使在后来的发展中受到社交媒体影响,公共传播的研究也与公共关系、政治传播等概念含糊不清,比如,Koenen研究政治传播中的媒体公共性,其目的是发掘政治的可预见性。⑨但是,胡百精以公共性视角分析的公共传播的两种潜质对本文有一定的启发价值,这两种潜质包括功能层面的“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对话,旨在促进认同、整合与合作”和价值层面的“多元主体基于公共性的价值和规范展开协商,以增益互惠和公共之善”⑩。这两个层面的思考路径对本文考察记者群体在网络社群中的对话、协商等行为有一定的价值。
此外,记者群体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中英文文献,大部分成果围绕新闻室(news room)的生产流程,讨论记者群体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工具变迁、身份转型、伦理挑战。但是,与前期研究成果不同,本文脱离传统的新闻生产理论背景来探讨记者群体参与公共事件和表达公共意见的行为。与此相关的已有文献中,研究国外记者的网络参与行为及其公共性的较多,比如Terje研究了埃塞俄比亚的散居犹太人网络社群,通过对社群中新闻发布者和编辑者自认为的新闻理想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考察,回答了社群成员是记者还是社会活动家的问题。
(二)研究问题
本文作者深入观察了记者群体参与的各类微信群(职业群、跑步群、选题群等)、微信朋友圈、微博,对他们的情感交流、信息分享、意见表达等文本进行了比较。微信群中的记者们除了进行“联盟”式的资源分享之外,还会针对某些社会事件展开争论,而且争论双方均声称自己代表“公共利益”。然而,在长期的观察中,本文作者发现了记者群体在“公共”之外的另一层运作逻辑,一些案例显示,“公”与“私”是网络社群互动中的一对复杂而隐性的关系。本文遴选了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1.江西J县在殡葬改革中出现的“抢棺”事件引起了某记者微信群的广泛讨论,讨论时间持续将近一个月,并有记者不断地往群内添加最新视频和证据,引起新一轮的评论。为什么S市记者对一起异地突发事件如此关注?通过观察发现,其中一名记者的家乡为J县,其父母正在为保护祖坟与当地官方抗争。2.微信群中记者对XX医院发生的医疗事故进行传播和评论,意见明显倾向于患者(代表公共利益?)。通过观察发现,参与评论最多的一名记者的妻子曾经在该医院经历了类似医疗事故。3.全国各地出现灭杀流浪狗事件以及相关政策出台后,记者在微信群中也开始分析讨论这一政策的伦理基础和在本地的适应性,观察发现,一些反对该政策的记者大部分为养狗人士。4.一家海鲜超市进驻某小区,业主大规模抗议,认为养殖海鲜的盐水腐蚀建筑物,一些记者参与报道,并将报道的内容与观点转移到微信群,让同行参与讨论,其中一名记者公开支持业主,但该记者被发现为该小区业主。这起事件在微信群里的讨论前后持续将近两个月。
对这些经验材料的观察引发的仅仅是感性层面的思考,通过抽象化过程,可以发现底下隐藏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也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1.网络社群中的记者是“公共人”的身份吗?作为职业媒体人的记者,承载了党和人民的“喉舌”、公共利益代言人等多重公共身份,但是以个人身份出现在网络社群中的记者还有这层公共“外衣”吗?
2.网络社群中记者的社会关系能否体现公共性?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将有什么社会后果?这些涉及到公共资源的私人利用、职业化公关与记者的利益分配和情感交流等问题。
3.网络社群中的记者行为在主观和客观上能否体现公共性?他们私底下是否真的如同在专业报道中宣称的那样“维护公共利益”?记者在网络社群中表面上维护的利益是否是理性的“公共利益”?
二、职业身份:媒体人与“网民”的冲突
(一)当代记者的社会身份类别
在中国的新闻生产框架中,记者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暗含着记者的两重公共身份,第一是宣传和解读政策的人,可称为时政宣传者,第二是表达人民心声的人,可称为公众代言人。前者与权力接近,在身份上类似于半官方人士;后者与知识接近,作为一种专业人士,更接近于知识分子。与此不同的是,记者群体在新闻生产中也存在非公共身份,为了适应新闻机构商业化运作的需要,记者以半商业人士身份出现也成为常态,如产业新闻、经济新闻的宣传功能往往裹挟了商业诉求,甚至某些机构的舆论监督功能也服务于商业诉求,试图通过负面报道胁迫被监督对象加大广告投入,这种身份与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均无关联。陆晔、潘忠党提出的“政治宣传体制、新闻专业理念和商业传媒体制”话语场域契合了“二公一私”三种身份,在两种公共身份中,作为专业人士的记者与作为宣传者的记者存在区别,“在‘专业模式’下,新闻从业者首先被认为具有独立的专业人格……在‘宣传模式’下,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角色得不到这种尊重,‘专业化’仅限于形式、手段和技能上的创造及提高,而不包括在内容上——包括选题、思想、新闻框架(news frames)的选择——的独立判断的权力”。陈阳也提出了中国记者的“宣传者、参与者、营利者、观察者”四种身份。具体到我国记者类型中,“跑线记者”有更多的机会充当宣传者,并在“对行政权力的维护上达成共识”,而深度型的调查记者更类似于公众代言人身份,他们“依赖公共立场对专业知识拥有解释权”。
(二)公共身份在网络社群中的延续:介乎媒体人与“网民”之间
脱离新闻生产流程框架,网络社群中的记者不受职业伦理的约束,但他们是否会在网络使用中延续自身的宣传立场和专业技能?在“跑线记者”的材料分析中发现,宣传类(政策解读、政府形象宣传等)网络文本很少出现在记者的职业微信群中,但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中却可以经常见到。综合对7名电视记者和5名报社记者的网络访谈的内容,发现了几种心理:1.不同网络社群的目标受众不同,职业微信群成员均为记者,不存在宣传必要性,而微信朋友圈、微博中则有各种社会人士,自认为一些政策确实需要广而告之。2.转发宣传类网络文本是为了与政府部门公关人员(通讯员)维持工作关系,公关人员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中均可见到转发内容。3.一些宣传类文本是记者的采编成果,记者通过网络二次传播来树立自己的名望。4.一些资深的“跑线记者”希望通过宣传类网络文本向亲友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即与某些政府部门的特殊关系。从这几点心理特征来看,网络社群中的记者群体是介于宣传者与普通网民之间的一种特殊人群,他们选择宣传场所(不同的社群),携带不同的宣传目的,是公共身份在网络中的一种延伸。
网络社群中的记者群体是否在实践专业主义的延伸?记者以非官方身份进行的自媒体使用或网络社群参与,使人们不得不反思他们是否是记者的另一种采访方式,还是记者出于职业惯性的日常生活内容。从记者微信群中可见,他们运用以往采编经验和个人经历分析网络事件,但不同于在职业生涯中形成的中立、理性等专业立场,他们带有的个人主观色彩更浓,客观性不足。传统媒体的采编活动是一种集体话语方式,而记者们在网络社群中采用的是个人话语,是作为“网民”身份出现的表达个体,记者的讨论也并非规范化的新闻生产流程,而是汇聚在一起的意见生产场域,这种意见生产有可能通过新闻倾向性原则来反作用于规范化的新闻生产流程,也有可能直接通过微博等开放式的网络社群来影响公众的观点。
(三)网络社群中的记者身份与“公共领域”实践者
讨论网络社群中记者的公共身份问题,公共领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概念。在哈贝马斯的理解中,“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这个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和“政府权力领域”(sphere of public authority)的一种相互关系。
在某些话题中,本文研究的网络社群显现了公共领域中的两种相互关系。在规范化的新闻生产流程中,记者作为公共性传播主体,不可能与公共权力机关处于抗衡状态,但是在私下的网络社群互动中,记者却以个人名义将私底下的不满情绪直接表达出来。在涉及到公共政策的案例中,批判性或对抗性语言较多。例如江西J县“抢棺”事件,类似的语言包括“丧尽天良可以说,换我敢拼命的”“知道现在很多基层官员的三观了吧”“不是有侮辱尸体罪么”“越土鳖越觉得别人习俗土鳖,越容不得传统和民俗”。但是,我们并不能凭借这些只言片语就简单地将记者的微信群、朋友圈定性为公共领域,更不能将记者身份判断为公共领域的实践者,原因有二:第一,由于微信群或微信朋友圈的半封闭状态(仅为熟悉的人所见),这类似于一种私底下的情绪表达,而非公开的意见表达,也就是说,这种抗衡手段是不为公共权力所知的,更不能实现相互沟通的效果;第二,从一些案例中可以发现,大部分记者的批判性或对抗性表达,是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而非以公共利益为诉求,“当记者们在新闻政策和管制规定中遭遇不公,微信群会出现较为集中的批评声音,直接针对制定政策或执行管制规定的管理者,这种对抗可以形成共鸣,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底层记者随时都可能遭遇‘恶政’”。因此,这种对公共政策的批评仍然介于“私人领域”与“政府权力领域”之间,而非二者的相互关系。
三、社会关系:对“公关参与者”的两种态度
(一)“亲密性专制”的社会驯化
“公关参与者”(public relations practitioners)与记者具有天然的特殊关系,其影响力渗透到记者的专业行为、日常生活、社会活动等方面,能够体现记者社会关系的公共性特征。因此,本文以“记者与公关参与者”的关系作为切入口,来分析记者的社会关系复杂性。
公关参与者与新闻事件无直接关系,但作为第三方参与调和、斡旋,并从中获利,如政府通讯员(为政府部门获得较好的形象,从而个人得到升职机会)、企业公关人士(为企业进行形象宣传或产品推广,从而个人获取经济利益)。在这种关系中,“跑线记者”与公关参与者的联系比一般记者更为紧密,在长期的接触中建立的私人关系也更为亲密,比如公关参与者给予记者独家采访权,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宴请、旅游等机会)。但是,这种氛围为记者的信息获取和话语自主权设定了更多的限制,亲密关系也更便于公关参与者对记者们进行“友善提醒”,甚至在采访中以“陪同”“保护”的名义进行监视。这种关系类似于桑内特提出的“亲密性专制”,即权力中心通过诱惑,而非强迫,来管理各种行动和习惯,其后果是“公共秩序被一种认为个人情感产生了社会意义的观念所消灭了”。在长期的亲密性互动中,一部分记者对公关参与者的工作产生了认同,甚至对此进行了公共利益的想象,认为公关参与者作为官方代表,是公共利益的方向,这种理念也体现在记者的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中。2019年3月,成都某中学食堂被曝使用发霉食材,当官方消息在网络中受到质疑之时,有记者在微信朋友圈和微信群中同时发言:
虽然说出我了解的情况可能会让群友们不高兴。但我确实被目前展示的证据说服了。1.为什么没有检测细菌总数?事实是,部分样品检测了的。但细菌培养时间是36小时以上,无机物检测结果先出来。由于有要求,检查结果出来多少就发布多少,就造成了这个后果。2.有没有查封仓库我不了解,但家长确实是在仓库门关闭的情况下强行破门进入的。3.微博网上的图片是压缩过的,我看过原图,毛肚、冻肉上的黑点,确实是红曲米。肉夹馍上的白斑,确实是冰霜。
虽然我们无法判断记者在网络社群中发布这段文字的主观意图及其真实性,但可以明晰地知道,记者与公关参与者立场(一般为官方代言人或通讯员)是一致的,冒着舆论“风险”发布这样的文字也可以证明记者与公关参与者关系的亲近。
(二)“专业性对抗”的利益分歧
记者群体并非总是以一个整体出现,这种亲密性关系也并不能得到所有记者的认同。2016年11月,深圳洪湖公园荷花池被当地水务集团改造成污水处理场,跑线记者发表了题为《污水处理厂建在洪湖公园内?听深圳水务集团怎么说》的报道后,在微信朋友圈和职业微信群中解释了水务集团的规划,但是这些解释性信息遭到了部分调查记者的批评,具体言论包括“无耻记者,通篇写水务集团的各种理论”“不采访居民,也不采访专家,自己也不研究,简直给这职业抹黑”“跑线跑成了水务局的人,也是够了”“做新闻必须自己成专家,否则就会被蒙蔽”。其中,“跑线跑成了水务局的人”这句话就证明了部分记者对“跑线记者”与公关参与者的亲密关系的不满,因为亲密关系掩蔽了传媒公共性的实践,而使这种社会公器“私化”为某个权力部门的工具。
公关参与者作为一种亲密性关系,为记者们生产新闻半成品,在找选题、写稿、摄影等方面协助记者。但是,我们也无法掩饰二者在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等方面表现出的强烈冲突,在这方面,国外的理论倾向比我们更为明显。“当人们把公关参与者看成是与记者无差别的群体时,记者们却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专业性比自己低。”除了身份认同带来的歧视,专业主义与新闻伦理的分歧更是二者出现裂痕的主因,“记者对公关从业人员作为倡导者的角色持负面看法,认为他们有隐瞒议程、隐瞒信息和损害新闻伦理的嫌疑”。而且,记者们还不断抱怨公关参与者对他们造成的职业威胁。“当公共关系作为一门专业在许多领域都开始增长之时,记者们正面临着工作时间增加、工资下降、地位下降、工作满意度下降和职业倦怠的困境。”虽然中文文献较少探索二者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我们却在网络社群的对话中观察到了不少案例。2018年10月,一篇题为《记者监督权力,谁来监督记者》的文章在记者朋友圈中转发,提出了记者的一系列问题,指责记者权力过大,而且“好战”“强势”“唯恐天下不乱”,“个别缺乏职业操守的记者甚至可以借助舆情,绑架基层政府和部门,更遑论威慑、威胁普通公职人员和普通群众了”。这篇文章获得一定的影响力之后,记者们很快在微信群中宣称找到了作者的职业背景——该市某街道办宣传科工作人员。随后,记者们在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中发起“反攻”,声称该作者已在微信朋友圈发表道歉信,并有记者将道歉信截图发至微信群中。即便如此,记者们仍然不依不饶,认为这种道歉“阴阳怪气”,并在微信群中继续攻讦,对话内容摘抄如下:
记者L:这人(指该文作者)我打过几次交道,平时就乐呵呵的,真是看不出来。自己舆情压力大,吐槽一下可以理解。不过不去反思根本原因,反而迁怒于服务对象。
记者B:这么搞(指道歉的态度不真诚)反而显得他是备受媒体从业人员压力,迫不得已才撤的。
记者Z:他应该是自以为是媒体人了,其实不然。
记者L:我感觉他是在讥讽。哪次记者调查不找街道?撕拉硬拽回街道办会所一坐,山珍海味上来,接着称兄道弟那套就来了,临走死活要给你意思一下,要不是看在宣传口的面子上,早给他们录下来,要说部分记者腐败,也是街道带的。
记者M:老大你这说的太真实了。
记者B:给钱就是宣传科的人给的啊。
记者G:你的意思是大家就是一丘之貉,别装清高了?
从这些对话中可以发现,记者并未依照网络文章从“权力过大”这层逻辑进行反思,其逻辑出发点是指责公关参与人(宣传口)的“合谋”。实际上,“权力过大”是一个公共性议题,即媒体与公众和公共利益的关系,是市民社会对权力的影响,而“合谋”则是一种私利性议题,即记者与公关参与者的个体利益问题。这一案例至少可以说明,无论记者与公关参与者处于亲密性关系还是对抗性关系,我们都很难从中找到“公共性”走向,即使在网络社群中,个体利益或群体利益仍然是主要的行为驱动力。
四、网络行为:公共性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操作
(一)行为动机:为人还是为己?
与记者的正常采编工作不同,他们在网络社群中的话语是一种日常生活行为,是以私人名义开展的非规约性的传播行为,判断这种行为是否具有公共性原则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动机是为公还是为私,或者说为人还是为己。“对哈贝马斯而言,公共性原则作为一种普遍性‘共识’,成为国家机构本身的组织原则,它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国家公共权力行使的正当性或合法性。公共性与私人性是不同的,在私人领域中,价值可以多元化,任何信仰、偏好也可以各行其是,不需要形成共识。”我们可以将公共性原则看成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行为准则,从这个维度来看,是否服务于公共利益是“公”与“私”的界限。本文所采用的案例均为记者在网络社群中讨论激烈,并且话题延续时间较长的新闻事件。经过对话题发起原因的分析,发现其中隐藏了一层“私人”关系,即上文“研究问题”中所述的“与己有关”,所有话题的引发,均与网络社群中的“私人”有直接的关系,网络社群中不同成员的诉求与价值观是多元的,无法形成普遍性“共识”,甚至辩论与争端随时发生。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本文作者对“海鲜超市进驻小区”事件进行了参与式观察,记录了这起事件在记者微信群中的起因、进展和收尾。为什么引用这一案例,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这起事件在记者微信群中相较其他事件持续时间更长,从2018年6月底到8月中旬,事件发酵将近两个月时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二,这起事件属于典型的公共事件,与市民生活直接相关,记者们在微信群中的观点也比较鲜明,具有研究的典型意义。
1.起因。一家品牌海鲜超市进驻某小区,业主向媒体投诉海鲜超市造成卫生问题。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海鲜超市随后整改。但业主们继续向媒体投诉,理由是海鲜超市的盐水腐蚀楼层结构,试图将海鲜超市遣出小区。记者认为理由过于牵强,不具有新闻价值和社会意义。有记者在微信群中直接表明立场:
记者L:媒体关注后业主越来越得意,越闹越离谱,都上升到腐蚀楼层结构了,我就有一点无语。拜托,养殖海产的水虽然有一定盐碱性,但是现代化钢筋混凝土结构,楼板渗漏那点海水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你以为是硫酸吗?
2.进展。从措辞中可以发现,记者L的态度比较理性(以盐碱性、混凝土结构进行对比分析),具备媒体应有的客观性,但也具有一定的情绪性和倾向性(越来越得意、拜托、硫酸等词明显具有感情色彩)。这一立场在微信群中出现之后,获得了大多数记者的拥护,部分言论记录如下:
记者S:家门口医院不能开,保障房不能建,现在超市也不让开,花几百万买房干啥?
记者Y:手机基站、变压站都不能(在小区旁边)建,那别用电别用手机了。
记者L:记得去年有个报料吗?后海的反对修建安居房,说影响社区档次,人员复杂,哈哈,都公开不要脸了。
实际上这些言论中隐含了“公共利益”的指向,多数人(比如小区业主与超市、医院、建筑方等相比,属于相对的多数人)的利益不一定代表公共利益,而仅仅是一个集群的利益,整个社会由无数的集群组合而成。但是,这些言论却遭到了记者N等人的公开反驳,从而导致记者之间展开关于“公共利益”的争论:
记者N:我们业主一直是在合法合理维权,你有种到现场来看看!别在群里口若悬河。
记者F:就事论事,如果确实因(海鲜)超市导致漏水,该处理还是要处理,但扯其他的就有点远了。
记者N:海水的PH值最高就是8.5,你知道这小区的PH值吗?12!
记者N:你的这一段(指记者L最开始表明的立场),我已经截图了!不道歉,业主就去找你,看着办!
记者L:不道歉,谢谢。
随着记者之间的意见冲突越来越激烈,有记者开始质问记者N在群里发言的动机:
记者C:你在这个群里是记者还是业主?是记者欢迎讨论,是业主TM滚蛋,业主了不起啊。
记者H:你张嘴闭嘴我们业主,你是那里的业主吧?
记者群中针对此事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微信群中发言属不属于公共言论。记者N质疑记者L在微信群中表态的合法性,但大部分记者则认为微信群对话属于日常生活言论:
记者D:L哥(记者L)的言论怎么了?是发在电视上还是发在报纸上,让您龙颜大怒?讨论讨论关你什么事?
记者们提出了微信群这一网络社群的公共性问题,并与电视、报纸进行了比较。
3.收尾。大部分记者开始质疑记者N的记者身份,认为他在微信群中鼓动记者参与这起事件的动机并非维护公共安全,而是维护自己(业主)的利益。也有人开始劝说记者N:
记者X:你也是做过某报首席的人,怎么就这么不冷静?他说他的,不对的地方你就和他私下讨论。在群里吓唬人干啥?动不动就找领导?领导还管着我们日常说话。
大部分人认为记者N的业主身份不能保证他在这起公共事件中发言的客观性,最后记者N主动退出该群。在这起事件中,我们可以将代表业主利益(个体利益或群体利益)的记者N的退出看成是记者群体在动机上的行业自律,代表公共利益的记者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优势,体现了行为动机上的公共性。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个体利益或群体利益与大多数记者无关,因而才使这种“公共性”作为一种“想象”得以彰显。真正的“公共性”行为准则应该是“与己有关”的记者对该事件回避,而非参与。
(二)行为技巧:话语的公共性表达
在传播体系中,话语代表一种行为方式。梵·迪克将话语分析分为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文本视角是对各个层次上的话语结构进行描述。语境视角则把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的各种特征如认知过程、再现、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文本分析时,文本视角与语境视角相互结合,才能准确考察文本的真实意义和话语主体的真实意图。在本文研究的网络社群中,记者的对话场景和内容比专业报道更加散漫,没有“审稿”带来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但是否这种非组织化,或者说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话语行为就缺乏公共性呢?可以继续从一些案例中进行考察。
带有个人色彩的话语更能适应互联网的语境,即私人性的对话场景,从话语分析的语境视角来看,私人性的对话无需顾忌伦理规范和组织约束,更适合表达情感和意见,更便于在公共事件中技巧性地展现话语主体的观点,甚至将私人性的体验运用在公共性话语中。结合语境视角与文本视角的话语分析发现:“与己有关”的记者在对话中表现“客观”,并尽量隐藏新闻事件与自己的社会关系或利益关系,试图对公共性进行“自我建构”,但实际上私利掩蔽了公共性表达的基础;而“与己无关”的记者由于本身具有中立性,其话语技巧则与前者相反,在个体对话中即使不回避主观感受,也能更恰当地表达公共性诉求,主观感受使他们的公共性表达同样是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从经验材料中总结出的私人性对话技巧包括“经验比较”“角色代入”“话题类比”等。在“J县抢棺”案例中:
记者J:抢棺材太野蛮了,我们老家那时候先从党员村官老师做思想工作。
记者W:但是不少基层党组织,已经脱离群众很久了,在群众眼中没威信呀。
将“我们老家”的经验与“抢棺”事件进行比较,从而延伸出更深层的社会意义。
记者X:丧尽天良,换我敢拼命的。
记者W:换我也敢。
“角色代入”是一种虚拟式的想象,但对观点表达更为直接和强烈。
此外,在“海鲜超市进驻小区”事件中,记者们通过“话题类比”的技巧将这起事件概念化为“邻避事件”,并借用以往“邻避事件”的舆论倾向,为批判小区居民的“非理性维权”获得了合法性,即历史案例中的事实依据。部分记录如下:
记者L:中国人什么都怕,身边开啥店都能臆断出不良影响。
记者L:我记得我们这去年还有人堵在电梯口,叫养狗的人都不要养了,把狗送走,因为他媳妇要怀孕。
记者H:大概怀的是哪吒。
记者T:(小区旁)要建消防站,也不能建宿舍。让消防官兵睡你家?
记者Z:着火自救就好了。
记者L:他们的真实目的是阻挠小区旁边的安居房开工,其实是怕房价受影响。
记者K:还是关心钱袋子。
记者J:差不多所有的维权最终目的都是这个。
这段对话看似散漫,甚至带有粗鄙言论,但实际上观点的对抗性非常明显,特别是一些反问句式言论,直接将小区居民置于对立面,也将其“维权不正当性”暴露出来,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性追求,不停留于小众事件本身,而是通过“话题类比”来提升其重要性和普遍性,使事件“大众化”,从而诉诸公共利益。
五、讨论与结语
记者群体在网络社群中的私人性话语与在规范化新闻生产流程中的公共性话语产生冲突,从而造成“网民”与专业媒体人的身份冲突,但“网民”身份的记者群体并非天然缺乏公共性原则,虽然个体特征明显,但他们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公众观点,延续媒体的社会公器功能和媒体人的公共追求。但是,本文的研究发现,记者在网络社群中的个体性夹杂了私人利益,而非纯粹的以公共利益为诉求。身份冲突决定了外在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内在自身行为的矛盾性。比如,记者与公关参与者既有亲密性合作,也存在对抗性心理,在这些关系中公共性特征并不明显;记者的个体利益或群体利益仍然是主要的行为驱动力,行为动机上的公共性特征也是在“与己无关”时才能显现出来。在“与己无关”时,记者群体在网络社群中有一套与规范性新闻生产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技巧性地展开公共性追求,通过一种“窃窃私语式”的对话生产和展示公共性。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在网络社群话语互动中发现了记者群体生产的“自我建构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与新闻生产流程中公开标榜“代表公共利益”的行为方式不同,而是隐藏于个体化的人际关系和私人性话语方式之中,其中的公共利益诉求随时受到个体利益或群体利益诉求的冲击。因此,“自我建构的公共性”是一种依据自身喜好和利益诉求而形成的缺乏伦理规范或组织约束的形态,它不会成为一种公开宣布的“规则”,而会成为群体行为的“潜规则”,在不同的语境和话题中呈现不同的存在形式。“自我建构的公共性”与文献综述中“公共知识分子”等“网民”的公共性是接壤的,但记者群体的新闻伦理的延续,使得这种身份更具有复杂性。
注释:
① 潘忠党:《序言: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第6期。
② 李良荣、张华:《参与社会治理:传媒公共性的实践逻辑》,《现代传播》,2014年第4期。
③ 朱清河:《论新闻职业公共性的实现困境与途径》,《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④ 王蔚:《公共性的迷思:微博事件中的知识分子及其社会行动——以钱云会案中知识分子观察团为例》,《新闻大学》,2013年第5期。
⑤ 袁光锋:《公共舆论中的“同情”与“公共性”的构成——“夏俊峰案”再反思》,《新闻记者》,2015年第11期。
⑥ 郑燕:《民意与公共性——“微博”中的公民话语权及其反思》,《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
⑦ Seungahn Nah.MediaPublicityandCivilSociety:NonprofitOrganizations,LocalNewspapersandtheInternetinaMidwesternCommunity.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2009,13(1),pp.3-29.
⑧ 冯建华:《公共传播的意涵及语用指向》,《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
⑨ Koennen,Elmar.TheVisibilityofPolitics:NewerStudiesaboutMediaPublicityofPoliticalCommunication.Soziologische Revue,2002,25(3),pp.258-265.
⑩ 胡百精、杨奕:《公共传播研究的基本问题与传播学范式创新》,《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