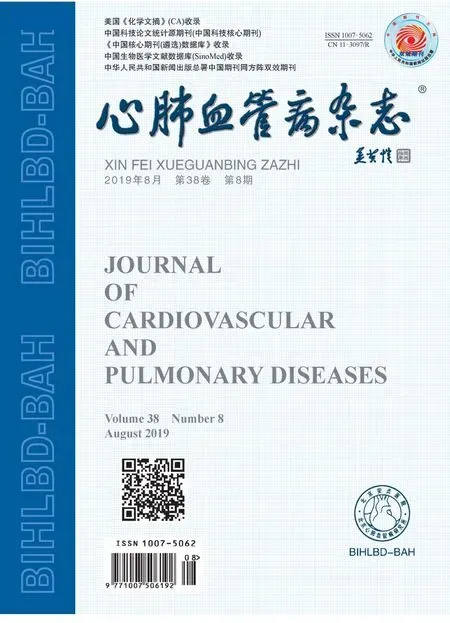心血管手术中血液应用的进展
陆良愿 卢家凯
自17 世纪血液循环概念的出现,并在动物实验上成功尝试血液输注开始,到20 世纪早期血液储存技术逐渐成熟,血液输注技术开始在临床得到大规模的应用。随着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对红细胞输注后可能引起患者围术期并发症和死亡的增加,血液管理策略的探索已成为全球研究的焦点问题。
近年来,全球心血管疾病患者数量不断增加,患者行心脏手术的数量也在逐年增长。在中国,由于人口众多,患心脏病和行心脏手术的数量也多。据2016年心血管疾病报告中估计,约2 900 万各类型心血管疾病患者行手术治疗,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性问题[1-3]。由于心血管手术难度大,耗时长,风险高,出血多,术中常常会采用多种血液管理策略来确保患者围术期安全,而其中输血成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成人心脏手术数据库的资料显示,50%的心脏手术患者接受输血治疗,心脏手术用血量占总用血量的10%~15%[4]。心脏再次手术、主动脉手术和心室辅助装置置入术中用血量更大。
本文作者回顾近年来国内外与心血管手术相关的血液管理文献,主要包括前瞻性、回顾性、综述类研究文章,旨在分析目前心血管手术领域血液管理技术的现状及研究进展。
1.心血管手术中的输血风险
临床上输血技术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失血患者的生存概率,但与输血有关风险,如感染、免疫系统病、急性肺损伤、肾损伤等合并症,常给患者的预后带来影响,尤其是合并严重心血管疾病的患者[5]。血液资源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认识到患者的出血风险和输血风险。心血管手术中合理减少术中、术后出血,以及输血干预是改进医疗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国际血液保护指南中指出,围术期出血或输血的主要风险因素为:高龄;术前红细胞体积减少;急诊或复杂手术,如二次手术、联合手术、主动脉手术等[4]。以外,术前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体外循环,合并严重的并发症同样会增加围术期输血的概率。虽然目前许多研究已证实了这些因素对患者围术期输血量产生影响,但对影响程度仍没有一个可靠的方法进行明确区分。
其中,术前抗血小板和抗凝药物治疗和管理是术前输血风险评估的重要部分,术前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可能会影响围术期输血风险。虽然患者对术前抗凝药或抗血小板药物的剂量(尤其是氯吡格雷)反应上存在很大差异,但证据支持在手术前3 d 停用氯吡格雷可以减少术后出血,而新型P2Y12 抑制剂(如替罗非班),药物代谢半衰期比更短,术前使用安全性可能更高[6]。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革新,微创技术的迅速发展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输血。如血管内支架技术的使用在复杂手术和高危人群的血液保护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7-8]。虽然有证据表明,在非体外循环(off-pump)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患者减少了出血和输血,但非体外循环CABG 远期预后仍存在疑虑[9]。2016年一项大型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中,体外循环与非体外循环CABG 患者的5年生存率未发现明显差异[10]。此外,少数患者因为宗教信仰或其他原因不愿意接受输血,也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因素。
2.心血管手术输血标准研究进展
直至目前,最佳红细胞输注标准值仍未确定。由于缺乏循证证据,各国输血指南中标准也不相同。最佳的血液管理应为输注的红细胞达到临床标准即可,避免不必要的输血,以免增加医疗费用和避免输血风险[11]。有学者建议,输血标准应将红细胞压积维持在30%,HGB 达到10 g/L 左右。但由于认识到输血的风险,随后开始重新考虑输血的标准[12]。
大多数指南中建议的输血标准值都是对非心血管手术的研究,而对心血管手术患者,为了确保心脏氧供,对于输血阈值的认识仍存在争论[13]。加拿大某心脏中心回顾11 812例心脏手术患者中有44%的患者接受了一个或多个单位红细胞,输血患者的比率28%~60%。在美国10 万患者在体外循环下行CABG 时,红细胞的输注率7.8%~92.8%。反映出在各类型心脏手术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中心对心血管手术患者术中输血率有很大的差异。
临床中对心血管手术患者输血研究工作存在许多困难点[14],包括:①对输血的认识程度不同;②输血标准与临床实践不相符;③错误认为输血是对于贫血的最佳治疗方式;④以往的随机对照试验中,对参与试验的医患关系好与否都直接影响手术患者输血研究的结果。
回顾性研究分析表明,术前HGB<12 g/L 或术中维持在5~8 g/L,可能增加并发症与死亡,心血管手术患者术后红细胞压积(hematocrit,HCT)高于 34%或 HGB>110 g/L 都可能增加围术期并发症。Nadine 等研究中发现,HGB 输注标准在8 g/L 与10 g/L 之间,心血管手术患者病死率与普通外科没有差异[13],随后开展的多中心随机对照实验中证实了之前的研究结果。另一项针对心血管手术患者的单中心、随机对照研究中,以红细胞压积为24%和30%为作为输血标准,虽然两组病死率没有差别,但限制性输血组心源性休克患者的数量明显增加[15]。Murphy 等对2 007 例心脏病患者手术后采取不同输血标准比较时,发现围术期与输血相关的感染和缺血并发症,虽然没有明显差别,但限制性输血组患者显示出较高的病死率[16]。
2016年的一项关于红细胞输注的荟萃分析中综合了31个临床试验,共12 587 例患者,以HGB 浓度(90~100 g/L)作为标准(自由组)和(70 或80 g/L)作为标准(限制组)。两组患者术后30 d 内病死率无明显差异。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无明显差异[17]。随后美国血库协会2016年输血指南中,对于心脏手术及存在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推荐限制性输血红细胞输注标准为80 g/L[18]。
2017年发表在新英格兰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Mazer 等对5 243 例中、低风险心脏手术患者术中用不同输血标准进行了随机、多中心、平行对照研究[19],术中限制性输血组HGB 浓度为7.5 g/L,非限制性输血组HGB 浓度为9.5 g/L,显示两组患者病死率无明显差别;并发症发生率,包括心肌梗死、卒中、新发肾衰竭等均未见显著区别。表明对于心血管手术患者,适当降低输血标准对患者围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及术后病死率并无显著影响。
3.心血管手术不同输血策略与预后
(1) 限制输血策略与开放性输血策略:在限制性输血概念提出前,临床上广泛认可的输血界限定义是HGB 低于10 g/L,或红细胞压积低于 30%。这个“10/30”的标准是由Adams 和 Lundy 提出,并且推广了数 10年[20]。但随着临床对于输血研究广泛开展,大多数临床输血研究及指南中提出,决定围术期是否输血应根据患者合并症进行评估,将输血范围修正为HGB 在6.0~10 g/L 内[21],并将这种血液管理的方式定义为限制性输血策略。
在一项针对限制性输血策略和开放性输血策略的Meta分析中[22],限制性输血策略使红细胞输注风险降低了37%。与开放性输血策略相比,限制性输血策略对不良事件发生率无影响;限制性输血策略与感染率的降低有统计学意义;使用限制性输血策略并没有减少住院或重症监护的住院时间。未发现限制性策略组与开放性输血组在30 d 病死率和合并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包括心脏不良事件,如心肌梗死,中风,血栓栓塞等。
在心血管手术中,限制输血和开放性输血最为主要的关注点,首先是对于贫血是心血管手术后发病率和病死率的危险因素的担忧,虽然,随机试验与观察性研究之间存在一些差异[23-24],但考虑到患者器官氧供和氧需的平衡能力等因素,目前多数指南中,对于心脏手术患者主张适当放宽输血指征。TITRe2 临床试验中,将术后 HGB 浓度< 7.5 g/L 定义为限制性输血阈值,HGB 浓度<9 g /L 定义为开放性输血阈值,两组患者输血率分别为53.4%和92.2%,限制输血组90 d 的病死率比自由输血组高,而在术后感染率发生上限制性输血策略组患者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优势。此项研究结果中证实对于心血管手术患者,往往处于心血管储备的极限,较高的HGB 水平可能对预后有益(术后HGB 输血阈值在9 g/L)[24]。TRICS III 研究发现75 岁或以上的老年患者限制性输血策略综合风险比开放性输血策略低,但在年轻组之间的比较中却没有差异,提示不同年龄、不同的输血策略,其结果可能会有差别。
(2)不良反应及预后:输注红细胞主要目的是增加体内红细胞数量,为器官供氧提供必要条件,但同种异体血的输注常常会面临多种风险。国际血液安全监测网络数据库纳入了25 个国家125 个数据库,确定血液制品不良反应发生率为660/10 万,其中近3%为严重不良反应。输血相关病死率是0.26 /10 万[25]。传染性及非传染性输血危害,包括非溶血性发热反应、败血症、过敏反应、溶血性输血反应、铁过载、输血相关急性肺损伤等,近60%的死亡是与输血相关,包括输血相关的急性肺损伤(transfusion-associated acute lung injury,TRALI)和输血相关的呼吸困难(transfusion-associated dyspnea,TAD)[26]。Harvey 分析了来自美国 77 家医疗机构的输血数据,输血不良反应比例达到239.5/10 万。过敏反应是最常见的类型,112.2/10 万,输血严重并发症比例为17.5/10 万,成分输血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排例是:血小板、悬浮红细胞、血浆、冷沉淀[27]。
免疫不良反应通常是发生在输入RBC、WBC、PLT 或血浆蛋白时,诱发抗原反应。这些反应包括急性溶血性输血反应(acute haemolytic,AHTR)、发热性非溶血性输血反应(febrile non-haemolytic,FNHTR)、过敏和类过敏性反应和 TRALI。非免疫反应包括输血相关的感染或败血症,以及输血相关性循环超 容 (transfusion-associated circulatory overload,TACO)。TACO 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肾衰竭(特别是透析的患者)、液体超负荷、心脏功能障碍、大量红细胞输注及输注速度过快等。2011年到 2015年,TRALI 和 TACO 分别占输血相关死亡人数的19.2%和26.9%[25]。此外,有证据表明输血相关性免疫抑制(transfusion-related immunosuppression,TRIM)与输注同种异体白细胞有关,产生免疫抑制部分原因是由于抑制细胞毒性细胞和单核细胞活性,前列腺素的释放增加,促炎和抗炎细胞因子和类二十烷酮浓度的改变,以及抑制T 细胞活性增加。导致机体对感染更敏感,减少细胞肿瘤防御,加强对输血抗原的同种异体免疫[28]。
4.心血管手术血液管理展望
为了减少心脏手术中异体输血,现阶段血管管理研究包括:术前促红细胞生成素的应用、自体血液储备、血液回收和血液稀释、抗纤溶药物、局部止血剂的使用、以及全氟碳等。此外,针对不同手术输血的预测亦是一种发展方向。
(1)心血管手术中的血液分离技术:现代血细胞分离技术开始于20 世纪初,最大优点在于仅提取血液中特定成分,并将其他成分无损保留并完全回输给患者。血细胞分离技术原理是通过离心机进行分离,将血液中的各种成分进行分离,可以“获取”或“去除”相应血液成分,从而达到“采集”或“治疗”相应疾病的功能[29]。
其中,自体血小板分离技术(autologous plateletpheresis,APP)是在麻醉诱导前后采集患者的全血,然后通过自体血液回收仪器将血液分离成贫血小板血浆、富血小板血浆和浓缩红细胞三部分,根据术中需求分别回输给患者[30]。因其相对其他血液保护措施更能减少体外循环中血小板的破坏而被广泛关注。系统研究发现[31],接受APP 治疗的患者,术中异体血小板和血浆的输注风险降低。在大血管手术中使用APP 能减少异体血的使用,改善患者凝血功能和全身炎症反应,降低术后早期肺功能不全的发生率,缩短拔管时间,促进胸骨伤口的愈合。但是,使用 APP 也可能导致低血压和心律失常,需要麻醉医师和技术操作者密切配合,目前该项技术远期临床效果研究还比较少。
(2)输血预测模型:心脏手术输血的预测研究早期多数选择在CABG 手术患者中进行,识别在选择性CABG 术中需要输血风险级别高的患者,有助于使临床治疗过程中更有针对性地使用血液保护方式,这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Karkouti 等[32]收集1 007 例初次行CABG 手术患者建立输血预测模型中,预测模型变量包括术前血红蛋白、体质量、年龄、性别及总的输血率在29.4%,外部验证的灵敏度82.1%,特异度 63.6%,阳性预测值 56.5%,阴性预测值86%,结论得出术前HGB 含量、体质量与输血风险成反比,年龄与输血风险成反比,女性输血风险高于男性。2010年,Welsby 等[33]建立的关于CABG 手术中输血预测的模型中,将5 887 例患者纳入分析,该模型,排除了交互项,将年龄、性别、LVEF、术前血清肌酐水平、Hct 和体质量确定为最终预测性指标,预测模型准确率达到21%,并且使意外输血比率降低了49%。并且研究中发现,输血策略的严格与否可能对模型的准确度有一定的影响。由于之前大多数关于输血预测模型都是单中心研究,Goudie 等[34]进行了多中心的多种心血管手术类型的研究,建立了两种类型预测模型,一是适用于任意红细胞输注量,另一种是用于>4 个U 红细胞输注的预测,弥补了单中心研究适用度低,以及其他干扰因素所造成的结果偏移,最终确立的两个模型的预测符合度中等,相比较而言,预测大量输血时的模型准确度更高。
对于心血管手术预测的模型受限于预测变量的可靠性,随访时间的定义,是否外部验证,以及对不同心脏手术类型是限制这些评分系统实际适用性的主要因素。随着跨学科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与云数据的日渐成熟,有希望借助多学科的发展提高此类模型的实用性。
5.结论
综上所述,尽管不同类型心血管手术的研究中,血液管理方式上存在一些差异,但仍然可以看出,临床需要结合患者自身病情做出不同选择。随着心血管手术血液管理研究的深入,技术的革新,围术期血液管理的方式将更加细致准确,更加完善,为心血管手术的患者创造更加良好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