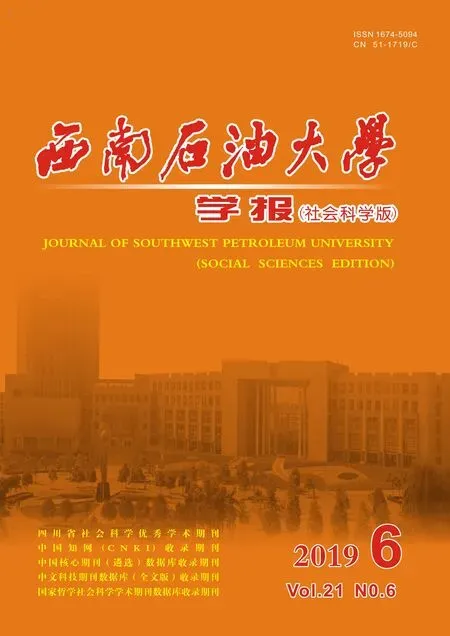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出版实践与思考
——以重庆出版集团“重述神话”系列图书为例
张 栋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引言
重庆出版集团在2005 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为作为中国大陆首个参与大型国际图书出版项目的单位,出版了“重述神话”系列图书。伴随这一主题活动的系列开展,重庆出版集团不仅以中国出版社代表的身份,展开与英、法、美、德等国家出版社的交流,也以与中国作家签约的方式推出一系列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通过版权输出等方式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推介给世界读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具魄力的出版策略,然而,在经历初期的狂热、中期的衰退乃至当下的沉寂之后,“重述神话”系列似乎早早夭折,当时出版集团声称的“每年推出5~7 位中国重量级作家重写的中国神话作品”的口号也成为一个永远难以实现的约定。就已经出版的当代作家作品来说,中国作家虽然也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作了重新整合,甚至进行了大胆的改造,但就小说整体呈现出的叙事效果以及社会反响来看,中国作家的神话重述与同主题的外国作品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作为一个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典型案例,重庆出版集团的“重述神话”系列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桩悬案,也留给读者及研究者诸多思考的空间。
1 出版盛宴:从狂欢到沉寂
参与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Canongate Books)发起的“重述神话”全球出版项目,是重庆出版社于2005 年在原出版社基础上组建重庆出版集团公司之后的首要举措。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是挑战更是机遇。重庆出版集团在创建伊始便抓住了这一机遇,据当时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罗小卫的介绍,集团在发展战略目标上即把对外合作与图书输出作为工作的重点内容,并把之前的“版权贸易部”升级改组为“版权及国际合作部”[1]。在上述举措的基础上,重庆出版集团展开手脚,在与国内其他出版社的竞争中胜出,其胜出原因也恰恰是“对该项目的认同以及选题的策划能力”[2]。从出版集团出版战略的顶层设计,到具体的选题调研、策划、论证、立项,乃至选题的宣传、图书发行、广告与营销等诸阶段,重庆出版集团一直在以国际化的标准参与“重述神话”这一出版项目。通过与国外知名的具有较大市场影响力的出版社合作,在选题与出版计划方面进行商议,借助国外出版社打开图书销售的国际市场,同时也能够将中国当代文学及时大批量地推介出去。重庆出版集团的准确战略定位,使得集团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能够充分结合,同时也有助于“重述神话”这一文学品牌的顺利创建。
按照重庆出版集团的国际化思路,作为出版核心的作家作品,显然更应该符合国际化的标准,集团更是以百万元的版税吸引作家的目光。对作家遴选的结果,苏童、阿来、李锐、叶兆言等四位作家成为创作主体。苏童通过《我的帝王生涯》等作品凸显出的想象力与虚构能力,张艺谋改编自《妻妾成群》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的国际影响力,阿来的民族身份与作品中民族特性的彰显,李锐作品的多语种翻译以及2004 年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以及叶兆言通过文学感知中国民族特性与历史的独特方式,都是遴选出的作家群体国际化的表现。重庆出版集团在不遗余力宣传所选作家的同时,也加紧翻译作家的创作,通过召开作家作品全球发布会的形式,扩大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从2006 年9 月苏童的《碧奴》出版,到2009 年9 月阿来的《格萨尔王》问世,中国作家的个人创作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并成功引起了大众与研究者的同时关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也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承载物,担当起文化传播的重任。
就“重述神话”系列的最初出版效果来说,重庆出版集团的出版战略是相当成功的。以作家苏童为例,苏童作为重庆出版集团重点推介的作家,其作品《碧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在还未出版之时就已经有15 个国家的出版社购买了版权,在出版之后,版权输出国家和地区达到24 个,其语种版本也已达21 种,半年时间销量就已达10 万册。另外,在作品的外文翻译方面,《碧奴》经过著名汉学家的翻译,在国际市场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度,如《碧奴》的英文版是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的,日文版则由日本著名汉学家饭宗岗翻译。国外汉学家基于国外读者审美与阅读兴趣基础上的翻译,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当代作品的影响力。另外,“重述神话”这一品牌的创建也离不开图书的装帧设计等技术层面的支撑。一种品牌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主题定位等元素,只有“凝练到品牌视觉形象外在表征中,不断触发受众群体的视觉辨识度和依赖度,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空间”[3]。重庆出版集团显然也关注到了这一点,在最先引进的《神话简史》《重量》《珀涅罗珀记》中,作品的封面图画由英国绘画师罗德瑞克·米尔斯等承担,平面设计则由书封设计师张孜滢完成,中外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促使三部作品获评2005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
将重庆出版集团的“重述神话”系列出版视为一场出版界的狂欢盛宴并不为过,集团在国际化出版的各个层面都为国内出版社做出了良好的示范。但遗憾的是,这一场盛宴维持的时间并不长。虽然《碧奴》《格萨尔王》都突破了印数10 万册大关,但普遍存在后期乏力的问题,四部作品中也只有《碧奴》与《格萨尔王》由重庆出版集团于2014年、2015 年重印修订本,而且社会反响程度明显不如之前热烈。叶兆言的《后羿》甚至出现了在重庆上架后一个月只卖出18 本的窘况,这还是在“重述神话”项目开展之后不久出现的现象。可以这样认为,“重述神话”项目启动伊始作品的大卖,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出版单位的策划与宣传,将出版事件打造成社会文化热点往往能够引起大众广泛的关注度,“重述神话”系列一时成为畅销书。但“畅销”并不意味着“长销”,狂欢仪式般的推介绝非营销手段的常态,当图书的宣传热度渐趋平静,市场对于图书的选择才逐渐理性,而外国读者对中国作家作品阅读反馈的缺乏,则使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走出去”陷入一种尴尬境地。
出版作品的被接受程度,印刷数量只能作为评判标准之一,因为涉及到版权输出问题,作品的印数并不能作为作品被广泛接受的直接证明。因此,一种客观、科学的作品评价机制应被引入到接受度考察之中。在国外读者接受情况尚不明晰的情况下,笔者暂以国内的学术评价为例,对四部作品的接受情况做出说明。国内的文学作品评价机制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大众评价,一类为学院派评价。大众评价多以感官经验与阅读趣味作为评价的前提,但其中也不乏较为专业的论断。以“豆瓣读书”网站的统计为例,除了李锐的《人间:重述白蛇传》达到8.2 分,其余作品均在8 分以下(《碧奴》6.6 分、《格萨尔王》7.6 分),叶兆言的《后羿》更是以6.1 分的成绩刚达到及格线,四部作品平均分为7.125(评价人数为9 231 人),这确实不是一个理想的分数。而在学院派层面,也能看出文本批评由集中趋向分散乃至衰微的过程。中国学界对“重述神话”系列的文本批评,大致从《碧奴》发行之后开始。每一本作品的问世,都会伴随一次学者的集中评论,之后这种评论便以零散的方式继续存在,乃至最终成为作家整体研究的附属。学院派批评与大众批评的不同点,在于学院派的观点更具专业性,对于作家创作要求更高,如果某些文本不能引起批评者持续的兴趣,该研究对象就会被研究者淡化处理,不再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从宣传热点到市场失利,重庆出版集团的“重述神话”系列经历了过山车似的体验,多年之后我们重新回顾这一极其吊诡的出版案例,会发现如果把出版盛宴从狂欢到沉寂的原因归结为出版单位的不作为,这显然是舍本逐末,只有把视角转向文本本身,才会理清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真正障碍所在,并进而探寻“走出去”的真正科学之路。
2 “重述神话”文本的学理性批判
重庆出版集团对“重述神话”系列的策划,虽然是以先行者的姿态介入,但其出版战略是相对成熟的。以雄厚的资本支撑出版计划,以现代传媒手段促进出版内容的多渠道传播、流通,以先进的科技手段引导出版的多元方向等等,都是使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重要前提,但在出版与市场的结合方面,显然存在一些问题。市场的推广与产品评价是图书出版的最终阶段,苏童等作家的作品虽然是以双向市场准入的形式进入国外市场,但从最终的市场表现来看,图书在国内外市场均未获得广泛的影响。这促使我们把反思的关注点集中于文学作品本身,并从学理性角度对文本叙事进行考察。
2.1 神话原型的置换变形错位
参与“重述神话”项目的中国作家均采用了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神话或传说原型,并采用神话叙事的叙事方法进行重构,其具体表现即对神话原型进行置换变形,并在其中熔铸现代人的思考,使远古神话在当下得以延续。学者程金城曾就神话的感性结构、理性结构与意态结构等三个方面,展开其与中国叙事文学之间的关联研究。这样由浅入深的三个层面较能科学地概括神话原型与叙事文学的深度关联,也能够作为神话原型置换变形研究的学理性依据[4]。
在神话叙事的感性结构层面,作家普遍地将原本记载资料稀缺的故事延展为长篇小说(阿来除外,他的创作是对口传民族史诗的凝缩),并为之补充了大量细节。另外,作家们也对主人公进行了重点改造,把他们从高不可及的神坛拉回到现实生活之中,在保留人物适度神性的同时,加重人物的世俗性、人间性色彩。丰富的细节固然充实了神话原本粗糙的结构,但对细节不加鉴别的运用,则往往使神话叙事变成神话“知识”的堆砌,而无创新的成分。叶兆言在《后羿》中将原始部落、西王母、野兽、战争等元素杂糅入文本之中,使最终文本呈现出大杂烩的效果,原型的置换变形成为原型的罗列,并未被系统地组织入文本之中。在理性结构层面,诸多原始神话的原型早已成为中国人历史意识与伦理认知的象征,一种原型的成功置换变形能够彰显出一个民族历史与伦理意识的变迁。在“重述神话”系列中,一些可以代表神话理性结构的原型虽被采用,如射日的后羿、寻夫的孟姜女、与法海争斗的白蛇等,但他们身上的现实成分要远远大于其本应承载的历史内涵,所谓的神话叙事也变为借用神话角色演绎的现代故事。神话叙事的意态结构,涉及到叙事者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深层反映,在远古神话中屡屡出现的构思方面的“模式”或“模型”往往成为意态结构的重点表现对象。因为有民族史诗作为支撑,因此阿来神话叙事中的意态结构较为成熟,但在其他三位作家的叙事中,叙事线索的过多采用反而消解了原始叙事模式的纯粹性,进而影响了深度伦理道德意识的表达。
2.2 短、平、快的媚俗写作
“重述神话”系列虽然是以商品的形态进入市场,但其承载的不仅仅是商业利益,而更多的是出版单位以图书出版的形式引导大众的审美取向,满足大众的审美需要。重庆出版集团对所选择的苏童等四位作家是颇有期待的,因为他们的创作都有各自独特的风格,更重要的是能在面向大众与个体精神坚守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使出版社在实现社会效益这一首要目的的同时,能够获取一定经济效益。但从结果来看,大多数作家以短、平、快的媚俗书写,违背了“重述神话”系列出版的初衷。
苏童的《碧奴》16 万字,写作历时4 个月,稿酬为100 万美元,这部书稿也使得苏童成功跻身百万作家之列,与他同样情况的还有叶兆言等其他三位作家。因为不管作品盈利与否,作家都能拿到巨额稿酬,因此这样优厚的创作条件对于作家来说显然是巨大的诱惑,创作尽快开始、书稿尽早完成便成为作家的首要选择。叶兆言在《新京报》的采访中就表示,“苏童写了《碧奴》,我就想一定要写一个至少在时间遥远程度上必须超过他的故事。其实我还有一个写独裁者的想法,写《后羿》满足了我的这两个欲望”[5]。李锐也认为他最终选择参与重述项目,也是试图表达“正面的走入中国”这一想法。也就是说,作家选择参与神话重述的初衷,都是为了实现自己某方面的创作目的,甚至“欲望”,而不是考察自己能否驾驭神话题材的能力,或者利用神话重述实现某种创作理念或社会观念。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重述神话”系列的中国作家普遍以一种浮躁的心态与短平快的创作方式进行写作,使得文本或是自说自话,或是刻意向恶俗趣味趋近。阿来的《格萨尔王》后半部分写作进程加快,有些细节经不起推敲;李锐的《人间》在虚构了一个煽情故事的同时,也以大团圆的方式刻意扭转故事方向,以满足大众的心理期待;苏童的《碧奴》则着意探讨碧奴的九种“哭法”,以一种琐屑、平庸的笔调描绘虚假的现实;叶兆言的《后羿》则在后羿与嫦娥的关系上做文章,以一种恶俗品味消解了神话叙事本应具备的神圣性。功利性的写作显然不是文学创作的常态,作家只有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审慎写作,在尊重大众审美趣味的同时坚守自己的创作底线,这种写作才是真正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2.3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匮乏
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版权输出与跨文化传播中,重中之重是作家要讲好“民族性兼具世界性的中国故事”[6]。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与对外传播,是把中国故事与世界分享的过程,中国作家对自身民族特性的充分彰显,其实也就是以世界性眼光建构民族文学文本的过程。在“重述神话”系列中,除个别作家达到了二者的兼容,其余作家则以强烈的个人话语遮蔽掉了民族色彩浓厚的传统神话传说,进而阻碍了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道路。
阿来作为一个藏族作家,口传英雄史诗“格萨尔王”构成其成长环境的文化背景,在这种前提下,加之阿来多年的资料收集,因此其创作能够在保证民族史诗恢弘气度的同时,以现代视角思考远古英雄在当下时代的生命力。而其他作家却普遍忽略了民族性,他们笔下的中国神话被涂抹上世俗的色彩,虽然苏童等人多次强调民间文化资源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在文本中体现出来。当外国读者试图从中国作家作品中找寻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时,只能读到一个个民族身份退隐的世俗故事,《碧奴》在国外的接受度显然成为一个问题,这也是《碧奴》的英译者葛浩文大量删减乃至重新改造碧奴形象,使之更符合中国民族身份并使外国读者接受的原因。
神话学家诺思洛普·弗莱把神话叙事理解为每一个时代中“一个由思想、意象、信仰、认识、假设、忧虑以及希望组成的结构,它是被那个时代所认可的,用来表现对于人的境况和命运的看法”[7]。也就是说,神话叙事的终极目标其实是关于世界的思考,以及对人类命运的看法,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在“重述神话”系列的外国文学文本中,外国作家普遍存在这一追问世界与人类的倾向。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在《重量》中探寻阿特拉斯对于神的重负以及人类存在的意义,A·S·拜雅特在《诸神的黄昏》中以孩童视角反思北欧神话与现代战争之间的关联,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在《神话简史》中以概述神话历史的方式,表达对人类理性时代神话思维缺失的隐忧,日本作家桐野夏生在《女神记》中重新思考男权制约下的女性命运。与外国作家相比,中国作家在对神话叙事文化功能和人类历史与生存的命运反思方面,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出版战略反思
出版是一种文化行为,它在带来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够促进一种文化价值理念的传播。重庆出版集团的“重述神话”系列,不仅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重要出版战略,也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进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文化外交行为。在国际化出版项目的合作中,版权输出与图书外销只是“走出去”的表面,文化真正能够实现交流是通过文本内容达成的,这就需要出版单位与作者的密切合作。但遗憾的是,在“重述神话”项目的出版中,出版单位与作家之间的合作出现了脱节现象,这不仅影响了图书在国内市场的评价,也阻碍了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进程。因此,重庆出版集团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出版战略,仍需要更具实践性的措施补充。
3.1 引入由出版社主导的学术论证与评价机制
在针对某一选题的策划阶段,论证是极其重要的工作。论证涉及到该选题的可行性、具体实施以及预计市场反应等内容。在文学类图书的出版过程中,学术论证显然更为重要,它是对文学出版图书的文学性与科学性的要求,使作家的创作符合一般的文学创作规律。在当代文学“走出去”这一大背景下,学术论证事关中国文学品牌的创造以及与国外图书在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有针对性的学术论证的缺乏,将导致中国文学话语权难以被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重庆出版集团的“重述神话”系列为例,所选择的四位作家显然是经过论证后的结果,但这种论证的依据,是以作家在国内外的市场影响力或者说所谓“文化资本”为主的,并未从作家的学科背景及对选题的驾驭能力等角度进行科学选择,这也影响了所选作家作品在市场的被接受程度。“重述神话”遴选的作者,显然应该具备基本的神话学、人类学等学科背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宗教与民间文化资源有清晰认知,且有把民间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学叙事的能力,这样才能保证作家与选题的契合度,以及作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被认可程度。但遗憾的是,“重述神话”所选作家基本上不符合上述标准。
在学术论证之外,由出版社主导的学术评价机制也应引入进来。这种评价机制是对学术论证的辅助,它通过对作家的文稿或已出版图书进行跟进式评论,对作家重述神话作品的创作特点、翻译研究、市场反响等层面提出专业性意见,使作家创作符合项目选题的大方向,而非以自己的创作风格随意改造。相对于学术界一般的自发性、分散性评论,由出版社主导的学术评价更具针对性、集中性,因此能够针对读者的阅读感受与市场反应及时作出调整,在文学图书的海外营销中,这种评价机制更为实用。“命题作文”式的出版计划,需要具有学术素养的图书编辑与作者之间的良性沟通,因此在出版单位的编辑队伍中,需要纳入具有文学、经济、翻译等专业背景的学术人员,这样才能保证出版图书的学术质量,进而使“重述神话”系列具备核心竞争力。
3.2 塑造神话品牌,产生规模效应
将品牌的塑造称为出版单位战略定位的核心,这一说法并不夸张。品牌是出版单位出版理念的凝结,也是良性企业文化的表现,成功的品牌营销是出版单位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之中,品牌的影响力体现在版权输出、翻译出版、海外营销等多个层面,重庆出版集团主导的“重述神话”项目恰恰是塑造中国文学“神话”品牌的绝好机会。在系列作品面世前的宣传阶段,重庆出版集团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重述神话”这一文学品牌,并取得了相当广泛的关注度。凭借广告宣传的力量,系列图书在出版之后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然而作品本身质量的参差不齐,使得以“集束弹”形式进入市场的“重述神话”作品未产生预期的规模效应。在质量令人堪忧的当代文学作品面前,重庆出版集团的品牌战略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
“重述神话”系列的失利,并不能作为出版社品牌战略失败的原因。重庆出版集团在品牌定位方面有成功的先例,比如由其开发的“读点经典”系列在2011 年的发行量就突破了2000 万册,实现了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在“神话”品牌的打造方面,重庆出版集团在坚持“走出去”的同时也积极“引进来”。几乎与“重述神话”项目开展同时,重庆出版集团就已开始对美国作家乔治·马丁的《冰与火之歌》系列的翻译、出版,随着美剧《权力的游戏》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收视狂潮,《冰与火之歌》的销售也从开始的遇冷到屡次再版,成为销量超越350 万册的现象级畅销书,这与出版集团极具前瞻性的品牌定位有着极大关联。在《冰与火之歌》之后,重庆出版集团着力打造奇幻文学书系,以“独角兽书系”为代表,集团将包括《冰与火之歌》《猎魔人》《迷雾之子》等奇幻经典纳入出版计划,构建了一个包容64 种图书且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奇幻、神话图书品牌。与“引进来”的巨大成绩相比,中国当代神话题材文学“走出去”陷入了瓶颈,这一残酷事实也证明了品牌的创建需要高质量文学作品的支撑,否则所谓品牌营销也只能是无人喝彩的自吹自擂。
3.3 文学的文化符号提炼与产业化转化
在第三产业占据经济发展越发重要位置的今天,文学创作显然在既有的认识、审美等传统功能之外,也开辟了一些学者认为的“产业性功能”。文学创作是文化观念的表现方式之一,是供读者鉴赏,同时在社会范围内传播的艺术创作形式。文学创作具备的读者接受与社会传播属性,决定了其绝非只停留于作家自我愉悦的阶段,而是具备被社会再利用乃至产业化转化的可能。学者范钦林认为,“文学的产业性功能是要靠文学消费者即读者或接受消费来实现的”[8]。也就是说,作品被市场接受的广泛程度,是其产业性功能实现的前提。以神话题材文学为例,其之所以能被读者接受,是因为承载人类共同记忆的神话资源在当下得到了再利用,且往往能够通过神话叙事升华读者的想象空间。通过对原始神话中文化符号的挖掘,作家将人类的原始记忆、符号承载的丰富信息凝结在读者的阅读体验之中,在获得读者认可的同时,也产生被产业化的可能。“重述神话”系列如果按照这一思路去实施,是可以产生更大效益的,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重述神话”文学系列的文化符号提炼,显然不能只局限于传统神话原型的当代再现,而是要善于“发掘利用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联想效应,成倍增加作品的知识含量和艺术含量”[9],从而使文学文本能够实现视听技术的转化,并以丰厚的神话、历史、艺术意蕴得到观众的青睐。但在实际创作中,苏童等作家创造的神话世界不仅充斥着与现实无异的世俗气息,而且对神话中文化符号意义的刻意消解,也使神话叙事的文化功能难以得到发挥。叶兆言笔下作为独裁者形象的后羿,苏童笔下邋遢、粗俗且毫无神话底蕴的碧奴,李锐笔下对于人物前世今生过于虚幻化的描绘等等,主体性过于浓厚的书写方式使本具有大众审美特性的文化符号难以被提炼出来,也难以被市场认可。与同样作为出版重点的《冰与火之歌》相比,在神话原型的提炼、文化符号的认可,乃至文本的艺术改编、文学形象的衍生品开发等多个层面,当代作家的神话重述距“引进来”的外国神话原创作品,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4 结语
在2016 年2 月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中国故事的讲法,他认为:“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要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事载体,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寓于其中,使人想听爱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10]在“一带一路”时代大背景下,学会讲故事、讲好故事、把故事讲好,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并实现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以传统神话等为代表的优秀文化资源,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特征与气质性情,而且内蕴着与世界其他民族相似的神话叙事肌理,以及共同的心理倾向。这是“重述神话”得以成立,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的重要前提。因此,这就需要重述者不仅对作为自身思想背景的传统文化资源有充分的了解,而且需要具备文艺创作的世界性眼光,在对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借鉴中,开拓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传播方式,创新中国故事的讲法。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中国特色文化的载体,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重任。以重庆出版集团等为代表的出版单位,则负责将中国故事输送出去。这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家只有明确自己的写作目的与社会责任,才能将讲故事的方法与凝练的精神力量熔铸于文本创造之中,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成功“走出去”打下坚实基础。这既是对出版单位劳动成果的尊重,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品牌创立的最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