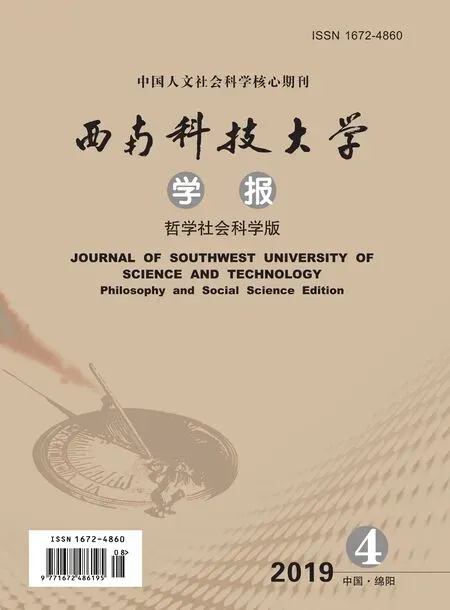自然复魅:藏族作家的绿色情怀
杨艳伶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环境污染、气候异常、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等问题渐趋凸显,“生态问题”“生态危机”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全球性问题。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借助科技进步,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显著提升,但因控制能力提高而带来的自豪感,却并未增加他们希冀从生活当中得到的幸福感,即“虽然人类在控制自然方面取得了不断的进步,而且完全有望取得更大的进步,但无法明确地肯定,在人类事务的管理方面取得了类似的进步;而且有可能在各个时期——如同现在一样,许多人一再扪心自问,已经获得的这点微不足道的文明是否确实值得保护”[1]。人类曾经沾沾自喜于对大自然的征服与胜利,殊不知,人类已经成为将所有问题都视为人的问题,并从人的角度去解决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奴隶,人因此失去了“从人之外的世界去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的能力,从而失去了对存在、无限和真理的真实的、确切的认知”[2],“人原先被笛卡尔上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结果却成了一些超越他、赛过他、占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历史力量)的掌中物”[3]。人类该怎样才能真正掌握从人之外的世界去理解与把握世界的能力?人类如何才能实现与自然的和解,是需要人们世代探索的世界性命题。
一、生态文学概述
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是“对人自身活动的历史,对文化的价值取向,对人类的目的性和人性的反省”[4]。早在1854年,亨利·戴维·梭罗就以散文集《瓦尔登湖》向世人展示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对人灵魂的净化与荡涤作用,以此来对抗泛滥的物欲对人的腐化与吞噬,“瓦尔登湖”因此成为了当代人孜孜以求的原生态生活方式的象征。奥尔多·利奥波德在1949年出版的被认为是堪与《瓦尔登湖》比肩媲美的自然随笔及哲学论文集《沙乡年鉴》,致力于在阐述土地功能基础上唤起人们对土地的了解、尊敬与热爱,“我们蹂躏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当我们把土地看成是一个我们隶属于它的共同体时,我们可能就会带着热爱与尊敬来使用它”[5]。188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在其著作《生物体普遍形态学》中,首次从生物学角度对“生态”“生态学”这两个概念做出了符合逻辑的界定。此后,生态主义被引入到了哲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生态文学也成为了人类文学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何谓“生态文学”?我国生态文学研究开拓者之一的王诺先生给出了这样的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理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是其突出特点”[6]。换言之,生态文学要有强烈的生态责任感和文化批判意识,要传达出人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要始终坚信在生态系统中人永远不是中心,人类利益也永远不能成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
绿色发展是当代中国的发展主流,绿色不仅是发展方式,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方式。生态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增长极,不少作家都将目光投注于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自然生态,探讨人如何才能真正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或许,可以将生态文学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形象化地称为“绿色文学”。而“绿色文学”在中国古已有之,综观中国古代文学,陶渊明、孟浩然、王维、杜甫、李白、苏轼、龚自珍等对自然的强烈热爱,对生命的深情礼赞,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积极践行,都是“绿色文学”“绿色艺术”得到历代文学艺术家重视与推崇的最好例证。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生态文学缓慢兴起,生态危机开始被一些敏感的作家关注,作家们大多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提出生态警示,如沙青《北京失去平衡》、麦天枢《挽汾河》、刘贵贤《生命之源的危机》、乔迈《中国水危机》、陈桂棣《汾河的警告》、徐刚《伐木者,醒来!》等。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西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思想以及生态文学作品的大量及系统译介,“中国生态文学作家的生态意识已经变得自觉”[7],他们创作出了大量具有鲜明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除报告文学外,小说、诗歌、散文、童话等诸多文体得到全面运用和发展,生态文学逐渐发展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支脉。
藏地、藏区,因其独特的地理构造、物种形态、资源禀赋以及文化源流等,是不少人魂牵梦绕的人间净土。这里不仅指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风情习俗等对人们的吸引力,更因为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的藏区相对完整地迎合了人们对绿色生态、绿色家园的美好希冀与憧憬,正如旅行家乔治·波格尔所言:“当开化民族陷入了无止境地追求贪婪和野心的时候,你们却在荒山的保护下继续生活在和平和欢乐之中,除了属于人类的本性之外,不再有其它需要了”[8]。但是,汇入人类文明发展洪流中的藏区正在面临一系列的生态问题,竭尽全力维护生态家园的绿意盎然还是任其自生自灭,是藏族作家们着力探讨的重要命题。关注藏区生态,重新认识和发现自然,重构和谐有序的人与自然关系,就成为全球化时代里众多从事藏地汉语文学创作的本土作家自觉的文化选择,以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以及自然复魅为核心的绿色情怀,折射出的是他们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担当。
二、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
世代生活在高寒青藏高原的藏民族,对高原生态环境之脆弱以及自然资源之珍贵,有着极为深切的感受与体验。如果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两大问题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的话,那么对高原藏族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这个问题”[9]。即便如此,他们却依然能化荒凉为优美,化寒冷为诗意,不断地将自己的故乡审美化和艺术化,这源于他们对生命世界和谐美以及自然万物崇高美的深刻领悟,他们深信故土的每一方山水都是神灵的居所,“破坏自然就是破坏神的家园”[10]。更进一步来说,在藏民族眼里,世间万物皆有灵性,而雪域文化也为民众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和善待生灵提供了理论依据。“阅读苯教经书、感悟苯教思想,你的脑海中不由会产生这么一个幻觉:青藏高原的山水会哭泣也会唱歌,青藏高原的树木会走路且会舞蹈。没有了它们的歌声,就没有人类的欢笑;没有了它们的舞蹈,人类就不知何去何从。这种人类幼年的思想,说它‘盲目’还不如说它‘绿色’”[11]。
佛教传入藏区以后,以更为规范的理论体系建构起了完备的自然人文生态系统,“在藏区建立了一种人与环境同生共存的系统思想,从理论上对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了阐述,从而使藏族保护环境的伦理规范纳入了佛教博大的思想体系中”[12]。“缘起性空”是藏传佛教最为核心的思想,“缘起”意为世间没有独存的东西,也没有常住不变的东西,一切都要靠因缘和合、因缘际会方能生起,而一切现象又都没有恒常性、独存性和主宰性,即“性空”。将“缘起性空”观运用于解释生命系统与生命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理解为生命存在于诸多因缘的联系当中,一旦因缘中断,生命将不复存在,生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亦是如此。
举起锋利刀斧的机村人不停歇地砍伐树木,不是为了煮茶做饭或烤火取暖,不是为了盖新房或修粮仓,“也不是为新添的牲口围一个畜栏,好像唯一的目的就是挥动刀斧,在一棵树倒下后,让另一棵树倒下,让一片林子消失后,再让另一片林子消失”[13]。“没过多少年,机村周围的山坡就一片荒凉了。一片片的树林消失,山坡上四处都是暴雨过后泥石流冲刷出的深深沟槽,裸露的巨大而盘曲的树根闪烁着金属板坚硬而又喑哑的光芒,仿佛一些狰狞巨兽留下的众多残肢。围绕着村庄的庄稼地,也被泥石流糟蹋得不成样子,肥沃绵软的森林黑土消失了,留在地里是累累的砾石”[14]。阿来以“机村”残酷的生态危机追问人性迷失、道德沦丧、价值观混乱及精神生态失衡的真正原因,反思人与自然割裂、疏远和对立的严重后果。荒芜的山坡、裸露的树根、砾石成堆的庄稼地,是自然向人类发出的愤怒呐喊,也是人类终遭天谴的预警。“机村”,乃中国千千万万藏族村落里的其中一个,而就是“这一个”,承载起了阿来对人与动植物、自然环境、同类乃至自身关系省察乃至重塑的文化使命。尊重自然、热爱生命、善待同类、尊重自身,原本是和顺生活秩序得以维系的根本,一旦出现失误或偏差,无论是自然万物还是人类,都将面临诸多考验、挑战甚至灾难。
不自知的机村人不但盲目毁坏森林,还将目光瞄向曾与人们祖祖辈辈和睦相处的猴群,猴群与机村人做了千余年的邻居,且“机村人与猴群之间,有一个长达千年的默契”[15]。但千年的默契与约定怎能敌得过能换钱的巨大诱惑,吃猴子肉、穿猴子皮、用猴子骨头泡酒等,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情景,在猎枪对准猴群开始疯狂射杀的那一刻,都被机村人悉数接纳。遭到机村人血腥屠戮的猴群逃遁至大山深处,不安和血腥氛围也只是短暂地笼罩过机村,经过一个冬天后,“每个人的心肠都变硬了。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多了几丝刀锋一样冷冰冰的凶狠”。[15]阿来对生态问题的隐忧和拷问极富震撼人心的力量,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支配下的生存法则也提出了深刻质疑,以牺牲自然万物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注定不会长久,当人类抛却对世间生灵和周遭环境的慈悲与敬畏之心时,天谴与惩罚都将不再遥远。
江洋才让《康巴方式》中的生态关怀则通过作为卡瓦神山守护者的南卡婆婆体现了出来,南卡婆婆是作家在小说里除叙述者斡玛以外最为独特的一个人物设置。南卡婆婆仿若跟神山一样长寿坚毅、沉稳慈悲,她善良睿智且洞若观火。她无怨无悔地看护着作为村里人精神寄托的卡瓦神山,也守候着这片土地上自然生态系统的融睦与有序。对于惹索瓦村长“野兔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询问,南卡婆婆给出了这样的答复:“难道,这个世间的任何事情都非得有答案吗?羊放养的好了会增多,这是自然对牧人的回馈。而野兔的增多,难道就不是野兔自个儿的福音吗?”[16]世间万物皆有其生存的法则与规律,人为的干预或介入必然会打破其原有的平衡秩序。对于觊觎卡瓦神山石头的外来卡车司机,南卡婆婆给出了不容辩驳的回绝性答复:“小伙子,都怨这些古怪的石头啊,它会使我俩结上恶缘的。……开上你的甲壳虫赶紧走吧!不要让我老太婆这根常敲山羊犄角的拐杖落到你的头上!”[16]或许有论者将南卡婆婆这样的反应看作是对现代性的隔绝与拒斥,但这样的阐释并没有关照到作家江洋才让深沉的生态隐忧情怀。作为现代事物的公路修通了,驮脚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寺庙修建起来了,康巴村庄和康巴农人的生活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人们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和睦关系能否得到持续保持还是一个未知数,尤其是外力强势介入后,南卡婆婆的话语是警告也是预言,即坚守本心、容纳新知、尊重万物、心怀善念,康巴人才有可能保留住专属于他们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及生活态度,与众不同的“康巴方式”是人文象征也是生态隐喻。
三、自然复魅
作为生态共同体的一分子,人类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生态责任,要始终保持与共同体内所有生命的平等对视和交流。换言之,人类要努力重建天人同构、万物一体的生态秩序,要确保地球上所有物种都能安全、持续地存在于大地上,要倾尽所能为自然复魅,要恢复对大自然原有的神圣敬意。而所谓自然的复魅“不是回到远古落后的神话时代,而是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统治下迷信于人的理性能力无往而不胜的一种突破”[17]。曾被远古人们推崇和敬畏的大自然神奇、神秘与神圣魅力,因技术工具理性对人的认知能力和主体性的无限放大而减弱甚至消隐,“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复魅成为针对祛魅种种病症的疗救力量”[18]。换言之,人类应当对孕育万物的自然长存敬畏之心,人自身的创造力、创造性不能以损害或戕害自然作为代价,要时时以自然之兴衰映照自己生存的本色,时刻将维护所有生物生命权及生态圈整体福祉作为行为准则,人类方能与自然休戚与共、相融无间。阿来、多吉卓嘎、达真等作家笔下的藏区有生态惨遭破坏之殇,也有人与自然相亲相融的温情画卷,后一种描叙让人看到了重建有序生态系统的希望与力量。
《空山》是最为集中地体现阿来生态忧思的长篇小说,小说中既有对人们盲目乱砍滥伐毁坏家园行为的客观铺陈,也有对大队长格桑旺堆与熊之间由搏斗交手至相知相惜的表现及情感的“复魅”叙写。“这头熊已经数度与村里数一数二的猎人格桑旺堆交手,缺掉的半拉耳朵就是他们交手的纪念。就凭这个,机村每一个人都可以认出它来。机村人都相信,当这样一头熊,与一个猎人数度交手后,就会像英雄相惜一样念念在心,对别的人就没有任何兴趣了”[19]。格桑旺堆与熊的惺惺相惜得到了全机村人的认可与肯定,因此,潜入树林的央金和情人——“蓝工装”同这头熊遭遇时,央金才会沉着冷静地拍着“蓝工装”的脑袋说一句:“不害怕,这是格桑旺堆的熊”[19]。“看来,我跟它,我们这些老东西的日子都到头了。”“也许,我的熊还等在那里,它会说,老伙计,林子一烧光,我就没有存身之地了,只好提前找你了结旧账。”[19]格桑旺堆的这些话语里充满了对作为自己对手的熊的怀恋与缱绻之情,这头熊是他的老相识、老朋友和老伙计,“他下意识摸了摸那熊在他身上留下的抓痕,眼前浮现出那半拉耳朵的老朋友,在林中从容不迫行走的样子”[19]。他们即便是要做了断,也仿佛是在期盼一场重要的“约定”,双方都满怀期盼且欣然前往。这样的人兽关系与机村人后来对猴群大开杀戒的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格桑旺堆与他的熊之间的关系原本是最贴合机村人价值理念的本真状态,自然万物的尊严和生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与维护。当机村人开始肆意毁坏家园、盲目破坏生态系统平衡时,大队长格桑旺堆与熊的故事也就只能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山已“空”,人们精神与内心的虚空和寂寥需要这样的故事去填充。
多吉卓嘎(羽芊)《西藏生死恋》中有一只与主人公公扎有着紧密关联的熊——喀果,在喀果重伤措姆并使其香消玉殒之前,公扎与喀果似老友般和睦相处,“它就在那片山谷里,公扎捡牛粪、找狐狸、放羊的时候能远远地看见它。有时它在找老鼠、抓兔子;有时在晒太阳,或是散步,没有交往,却像老朋友般熟悉”[20]。这样的场景就是一幅人兽和谐共处的草原美景图,双方互不干扰,各司其职。即便是后来公扎为复仇踏上了追赶寻找喀果的流浪之路,带着小熊并被狼群围困的喀果仍然被公扎所救。随着多吉卓嘎层层深入的叙述,公扎与喀果之间相识相知、相恨相惜的纠结状态逐渐得以呈现,一次次相遇,一次次错过,并非公扎无力复仇,而是他每次与喀果相遇,这只熊都是怀孕或带崽状态,好猎手的秉性不允许其在此时伤害猎物。多吉卓嘎擅长讲述藏北高原上百转千折、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但其对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人与同类之间关系的思悟同样颇具深度,这样的思考无疑提升了她的长篇小说的文化含量与深度,使她的作品不被贴上爱情小说的单一化标签。
达真《命定》里的贡布与爱驹“雪上飞”之间的关系似“恋人”更是“兄弟”,贡布不仅将良马的鬃毛剪下一缕装于嘎乌中并请活佛开光诵经,还郑重地与“雪上飞”结拜为“弟兄”。“当贡布从襁褓里掏出一根哈达戴在马脖子上的时候,他竟然为雪上飞流下了眼泪,那是令女人嫉妒的泪水。泪水涌出的瞬间,不可思议的神降出现了,笼罩拉雅雪峰的云雾朝四处散开,一束阳光穿越云层照亮刀尖一样的雪峰,直插雾霭散去的碧空蓝天,像是在聆听早已丢失的人与动物在远古时代以来开创的交流本初”[21]。人与马、人与自然生灵的交流与相处原本就应该这般无碍及和谐,康巴汉子贡布和良马“雪上飞”共同谱写出了人畜和睦的自然欢歌,静谧的拉雅雪峰以显示神降的方式为他们喝彩。之后出现的“人马同跪”场景更是极致地演绎了互尊互敬的真正含义,雍金玛和丈夫贡布“同时看见雪上飞的前蹄落地之后,竟然学着人的模样,艰难地跪下了前蹄。雍金玛控制不住激动竟然啊波波地尖叫起来,人马同跪的场面,是她的人生经历中还从未看见和从未听说的事”[21]。达真的述写中有血腥残酷的战争场景,也有如此感人至深的温情画面。不管是“以暴制暴”“以战止战”,还是保家卫国、守土卫疆,其目的都是为了守护一方水土的安宁,也是为了让贡布们与马以及所有生物能够安然生存于自然家园中。
阿来、江洋才让、多吉卓嘎、达真等作家生动呈现了藏区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的朴素生态意识,展现了自然之魅的神奇与广博,也提供了人与自然亲和相处的有益启示:复魅或返魅的自然破除了人与自然之间不可逾越的壁垒,当人们消减对现代技术文明的过度痴迷,舍弃对消费文化和物质积累的狂热追求,重新审视和思考人与自然关系,与所有生命为友,敬畏并善待自然,方能确保人类长久安居于大地之上。同时,所有地方的人们还都应该“致力于创造高效低耗的文化模式。高效是为了提高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低耗则有利于保障生态环境的长期和谐稳定”[22],进而有利于永续发展和绿色家园梦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