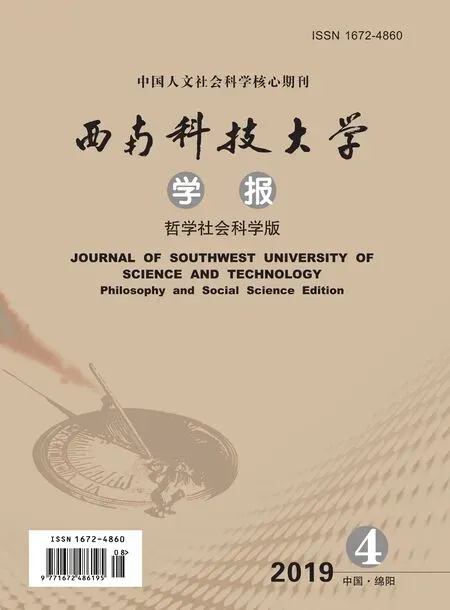《说略》与日本强占琉球
——基于外交“说理”的比较与反思
刘旭康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0)
《说略》的产生与清琉反驳的展开,其辩论核心便是“公理”层面琉球的归属问题,这场辩论既是清琉日三国自1879年日本变琉球藩为冲绳县以来说理成分最多且最详细的一次,也是学界所言之“球案”发展过程的重要一步。从涉及“球案”研究的方面来说,学界目前成果丰硕,①关于“球案”的起因、清日谈判的过程、“球案”悬而未决[1]的原因诸方面都有所体现。但从双方照会即从外交辞令的角度对日本占领琉球的强制性与侵略性的研究较为少见,而《说略》作为日本对琉球归属问题阐述最详细的外交文书,一直以来虽在史家的各种论著中有所提及,但因对其特殊性与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故而现今尚无一篇专题文章对其进行说理分析,并将其与清琉双方的反驳进行比较,从而探讨近代日本对外强制占领、侵略进而实现扩张的外交逻辑。这种外交逻辑既在日本侵朝的行动中体现,也在日本占琉的外交辞令中表达,看似符规遵约,实则不义不信。即日本虽然以“说理”的形式照会清国,但将琉球立藩—置县在先,捏造史事、张冠李戴而“说理”者在后,欲在实际控制和“万国公理”上都站稳脚跟,这就是清日在“球案”问题上反复交涉的主因。
一、 《说略》的提出与清琉反驳的展开
自日本明治维新确立“布国威于海外”的外交方针以来,对外扩张便成为日益迫切的需求,朝鲜、琉球、吕宋甚至中国都是其觊觎窥伺的对象,1870年4月,日本外务省官员佐田白茅在关于朝鲜事务的表奏中毫无忌讳地指出:“……故伐朝鲜富国强兵之策,不可容易以靡财蠹国伦却之也”“则不唯一举屠朝鲜大练我兵制又辉皇威于海外,岂不神速伐之哉”。[2]140这种扩张策略实际上是与日本国家的历史记忆密切相关的,白江口之战、万历朝鲜战争、1609年萨琉之战这三场战争都是日本囿于其国土狭小而主动发起的对外扩张战争,这种扩张心态千余年来一直在日本国家记忆中萦绕不已,近代日本更是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浪潮中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这也是日本强制占领琉球以致“球案”产生的背景和逻辑所在。
1879年3月,明治政府派遣松田道之及百余名军警并辅以军队前往琉球,在琉球首里王城宣布明治政府“废藩改县”的命令,并强令琉球王室成员离开王城前往日本,至此琉球便为日本所强占。清政府在得悉琉球为日本所废的消息后,于同年5月照会日本驻清使节宍户玑,认为琉球同时服属于中日两国并不有碍于琉球王国的独立性,日本“灭其国绝其祀”是“蔑视中国”而对中日友好规约有害,希望日本立即停止废琉行动,以全两国友好邦交。但宍户玑以“伺有核示辨覆”[3]179为由行拖延之策,直至8月才正式照会清政府,这便是对琉球归属作完整答复的《说略》。二十天后清政府就《说略》向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玑递交照会以作反驳,而琉球时值被受灭国之灾,也无法就此事发表意见。但自1876年阻贡事件以来,琉球国王尚泰就秘密派遣都通事林世功和紫巾官向德宏等人到中国求救,因海清颠簸等原因,向德宏等人于1877年2月到达福州,虽有闽浙总督何璟等人上奏,但李鸿章、奕等人不愿主动就此事与日本再生嫌隙。后因因国内情势危急,向德宏等人便“剃发上京”,前往天津参见李鸿章,但屡次不得,及至听闻日本向清政府递交“琉球属日”的《说略》消息,愤懑之极,在日本照会清政府不到一个星期,便就《说略》之种种论断逐条反驳,这比清政府照会日本提前了两周的时间,足见其状。
二、 《说略》与清琉反驳的比较
日本自明治维新伊始便逐步谋求吞并琉球,从其官员奏呈、政府文件等陈述关于日琉渊源的角度看,这种说辞是一脉相承的。从1871年鹿儿岛县地方政府的《调查报告》到1879年日本政府关于琉球归属总述的《说略》,日本所列举的“归属”理据似乎越来越充分,但其实都是经不起史料推敲的。从侧面也可以看到,日本为使吞并琉球为“内政之事”,为合乎“万国公理”之事,其言辞使用愈发严谨,真实目的就愈发隐蔽,而其行动就愈激烈。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在以公理示之各国的同时,其对琉球的控制程度也是不断加强的。而至关于琉球归属总述的《说略》提出,其已通过暴力强制手段实际占领琉球,事实上也印证了这种日本吞并琉球的外交逻辑。
就外交辞令而言,《说略》作为琉球归属日本“明证”的总述,其开篇便表明了“废藩置县”一事断不能停止的态度,再从地理、宗教、文字、萨摩“世管”琉球、1874年台湾事件、独立国家之形态等多种角度详细论述日琉渊源,最后得出废琉之举“是系我国之内政,宜得自主而不容他邦干涉”[3]184的结论。清政府在琉球藩属中国,日本废琉置县之举乃“灭人国绝人祀”立论的基础上,也就地势、文字、宗教、风俗等方面做一概论,犹在反复申明中琉间自明代以来的朝贡关系,驳斥了日本认为琉球并非自为一国的谬论,以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款为基础,希望日本在考虑中日和好的前提下停止废琉为县的举动。琉球方面向德宏作为本国高层官员,知晓本国史事,对日本的《说略》进行了逐条逐句的反驳。因此,对于《说略》中的诸多谬论,清琉双方反驳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清政府主要是在考量中日关系及琉球存续的前提下同日本辩论,而以向德宏为代表的琉球方面一因亡国切肤之痛,二因熟知本国国情,因此在具体论据上更为有利。现结合清琉的反驳及相关资料对日方的《说略》进行逐一对照:
1.就地理位置而言,《说略》中谓:“琉球谓我南岛久矣……地脉绵亘,在我股掌之间”,[3]183这其实是日本故意混淆琉球与中日之间的位置分布,事实上琉球群岛近于台湾而远于萨摩,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将萨琉间琉球所属的三十六岛占去五岛,造成了“股掌之间”的印象,实属谬误;
2.文字及语言方面,《说略》认为:“字母用我四十八字……与我同体”,言语“亦与我同种”,此种说法甚为牵强。琉球自1372年(洪武五年)即与中国通交并确立为藩属关系,明清两代中国前往册封多达二十三次,[4]而琉球向中国朝贡多达884次,其中,明朝537次,清朝347次,[5]如此大规模和长时间的交往若说文字、语言互不相通,实无可能。况且自洪武年间以来,明政府陆续迁闽地之民至琉球,当地人谓“久米村人”,[6]因此琉球本地有许多人说汉语,习汉字。再者遍观琉球外交文书,皆以汉字书写,且琉球许多国民仍操以土音,何以日琉于文字、言语上“同种”?是为谬矣。
3.《说略》以为琉球在宗教上有信仰日本的伊势大神,风俗上如席地而坐、社具另食等同日本相同,此为神教、风俗上相近。但在伊势大神信仰传入琉球前,琉球亦有掌管祭祀的君君、祝祝之官职,而且琉球信仰繁杂,佛道神教兼有,其中以佛教最盛,日本以一小支宗教信仰来囊括琉球的全部宗教,甚为肤浅;另外席地而坐、社具另食的风俗是由中国传至日本,日本何以据此来强行相近于琉球?若以此为论据,则日本归属于中国,实是谬论。
4. 《说略》就日琉在政治往来的论述最为冗长,也最为详细,但若仔细推敲则疑点甚多。其从隋唐时期南岛(琉球)朝贡事说起,及至唐中期太宰府施政于南岛,再到宋代绍兴年间日人源为朝渡海至琉球,后娶按司之妹,其子尊敦被奉为舜天王,期间历经数代,二百余年后日本将军足利义教将琉球赐给萨摩藩守,再至万历年间丰臣秀吉令琉球献兵献粮,琉球不从,遂命萨摩岛津氏讨伐琉球,其后萨摩藩“遣吏人、理岛政”,[3]183而后日本明治维新,对琉球“两属状态”无法坐视,因此于今日“废藩置县”云云。
这段论述看似时间紧凑,有理有据,实则牵强附会、不尽不实处甚多。据米庆余先生考证,日本所谓“南岛朝贡之事”实则上是指《日本书纪》中所载隋唐年间琉球群岛有民前往日本“归化”和被当做礼物赏赐给有功的战将,并非朝贡;而所谓“太宰府管南岛”及“在我政教之下”皆是夸大虚无之词,太宰府是日本于七世纪在九州地方设立的管理机构,隋唐时期中日交往密切,太宰府的职权也较大,而自“遣唐使”停止以来,太宰府的管理权限便只限于管理来日通商的外国船只,而且此处的南岛此时并非指琉球群岛,而是九州属岛内的岛屿。
此外,日方认为舜天之父源为朝为日人,舜天一统虽三代而亡,但二百余年后尚园即位,尚园即为舜天王之后裔云云。对此琉球官员尚巴志作了尖锐有力的回应,即舜天王之前琉球即有天孙氏,天孙氏共传二十五世,后权臣利勇叛乱遭源为朝之子尊敦剿灭,尊敦被推立为舜天王,但舜天王三世而绝,至今日尚泰王“凡三十八代,中间或让位于人,或为所夺,如此者几易五六姓”。[7]至于萨摩侵琉以来对琉球“遣吏人,理其政”,则是夸大之词。退一步讲,即使彼时萨摩对琉球具有行政上的管理权,那么这种管理权从何而来?《说略》中亦云:“授尚宁及三司官以法十五条,尚宁三司官各献誓书,自此其后世服萨摩吏治”[3]183云云,但这种誓文是萨摩藩羁押琉球国王及三法官等官员达三年之久才出现的,这些誓令是否是在琉球王自愿的情况下答应的,值得怀疑。就誓文本身来说,也多是要求琉球不得背叛萨摩,并要求在琉球的对外贸易利润中分一杯羹。因此,此时日本(主要是萨摩藩)对琉球的影响主要是在经济方面,琉球的政治、外交、文化诸方面仍是自为一体,这与日本方面所说的“遣吏理政”实是大相径庭。
5. 《说略》中不仅就日琉政治、文化、习俗渊源上做出了举证,也在道义层面有所表示。
其中有云:“我国保庇岛民,无所不至,有饥发帑赈之,有仇兴兵报之”[3]184此处的“有饥发帑赈之”有琉球官员向德宏考证,实为荒年时节琉球向日本借米借粮,等丰收时节立即偿还,从未有所短欠,但这种贷借却被日本解读为“发帑赈之”,实是强词夺理。“有仇兴兵报之”指的是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生番杀害琉球漂民出兵台湾的事件,在中日双方签订的《北京专条》中,清政府承认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此篇《说略》中日本以此为依据,实乃用心险恶。但从向德宏的反驳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所谓“兴兵保民”实际是日本为了一己私欲将此事端强加于琉球,琉球方面并未就此事向日本做任何请求,完全是日本一厢情愿而置琉球感受于不顾,何来“保庇”?
除上述对日琉渊源的各种赘述外,《说略》还在此基础上辩解了对于琉球并非为一国的逻辑。即“政教禁令,得自主自为者,可以自为一国”,[3]184反之则无。正如上述日本关于日琉渊源而言,若此为真,则琉球并非“自为一国”,且“废藩立县”之事乃是日本国内政治,与中国等外邦无关。观察日本的这种逻辑,其实大有问题。一是在拒绝承认近代以前东亚地区宗藩体制的条件下无视中琉间长达五百余年的历史关系,萨摩侵琉之前琉球的各项事务均由本国一应承担,即使中琉两国早在明代洪武年间就已确定宗藩关系,但这种关系仅限于政治名义上的册封与被册封,于琉球国内政治、经济诸项事务并无妨碍,琉球实际上是完全“自主自为”的;二是1609年萨摩侵琉以来,萨摩对于琉球的羁縻也仅限于朝贡贸易的利润分享上,远远达不到“遣吏理政”的程度。况且这种“管理”实是萨摩藩强加于琉球的枷锁,《说略》中美其名曰萨琉之役后琉球为“罪伏”,其实是以武力征服的方式迫使琉球臣服,此种言辞实在无理。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萨摩藩对于琉球的控制是通过隐蔽的方式进行的,主要表现在中国派遣使节册封琉球时,“所有萨摩藩的商人均要撤出日本本土,不得与中国人交相贸易”。[8]这种控制的隐蔽性恰恰表明当时的萨摩藩及日本畏惧中琉关系破裂而无法攫取中琉封贡贸易的利润,则今日日本无视中琉历史关系岂不是否定自己本身的历史,实是谬误;三是认为“其两属云者,则阴阳两国也耳”,[3]184琉球“两属状态”必不能存,那既然日方承认琉球有过“两属”的过往,那何以不正视中琉关系,何以否定封贡制度,何以认为琉球仅属于日本,实在前后矛盾,不知所云。
最后《说略》提出琉球事件与中日修好条规并无关系,这也是日本在认为琉球事务属于国内政治的基础上得出的。但正如前述,中琉封贡关系存续达五百年之久,又有闽人迁琉以成“久米村”者,两国言语、文字、习俗等通交既深且远,日本与琉球原本各自为政,互不干扰,而自1609年萨摩入侵以来被迫臣服于日本,此“两属状态”维持达二百余年之久,今日日本推翻前论,罔顾历史,直说琉球“久属日本”至今日琉球之事乃国内事务,实是强词夺理。
结语
今日反观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事实上也是逐步推进的,这与当时日本及清国的国力对比是密切相关的,日本在对中琉历史关系心知肚明的情况下,采取渐进的方式实现吞并琉球的目标。1871年4月,日本在全国推行“废藩置县”的制度改革,萨摩藩旧地被改为鹿儿岛县,同年7月鹿儿岛县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递交了关于查证日琉关系的《调查报告》,其以琉球“本属”萨摩藩旧地的立场首开明治维新以来“琉球归属日本”观点的先河,为之后明治政府对外宣传的统一奠定了基调。1872年担任大藏大辅的井上馨向日本天皇提出琉球应视作内地一隅的建议,这无疑代表着当时日本统治阶层对于明确占领琉球的意见与看法。随即日本中央政府就命令左院就井上馨的建议作详细讨论,制定出更为完备的行动计划,而日本左院在详细讨论后,建议可在实际控制上抓紧施行,而在形式上保存琉球的“两属状态”,即在考虑清国反应的前提下逐渐强化在行政、琉球外交等方面的控制。1872年,琉球王国按例前往东京拜见日本天皇,明治政府借此机会公然宣布琉球王国为日本一藩,琉球国王为日本藩王,列于华族序列,并为其设置了相应的官阶名目。[9]326-327如果说之前的《调查报告》、官员建议、政府计划是理念层面的设计,那么1872年将琉球“灭国为藩”则是日本吞并琉球于实操上的第一步。
1875年3月,明治政府传令琉球官员池城亲方、幸地亲云等来京听谕,以1874年台湾事件中日本政府“保民”为由宣布将在琉球设置兵营以保护当地人民,并赐以琉球一艘蒸汽轮船,在池城亲方等人拒绝接受的情况下,明治政府决定派遣官员前往琉球并当面向尚泰王等宣谕。同年6月12日,日本内务府六等出仕伊地知贞馨与琉球官员及“陆军少佐长嶺让、陆军大尉宫村正俊……等七十余名”[9]312乘坐日本所赐之“大有号”前往琉球执行中央政府的决策即阻断清琉交往,但琉球方面仍希望继续维持“两属状态”,不肯同意明治政府的命令。1875年9月,松田道之等人在谕令琉球断绝中琉关系无果的情况下返回日本,同年11月琉球官员池城亲方等人再次前往东京,请求面见天皇以期明治政府撤销琉球断绝中琉关系的谕令,维持琉球小国的“两属状态”,但琉球的请求遭到了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等人的拒绝,同时也引起了明治政府的警觉。在1878年11月松田道之向中央政提交了《琉球藩处分案》后,明治政府便于1879年3月对琉球进行“处分”,由此造成实际占领琉球的结果。
因而值得注意的是,《说略》的产生及清琉反驳的展开都是基于日本实际占领琉球的基础上展开的。而从《说略》的外交辞令本身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维度的差异:一是从史实角度而言,将《说略》与清琉两国的反驳言辞综合比较来看,日本外务省寺岛宗则令宍户玑转交给清政府的这份《说略》,不实之处甚多,但其中有一言为真,即“但至将废藩一事停止,断不能俯就”,[3]185不仅在行动上悍然,在外交辞令方面也是强横无理。这篇《说略》看似面面俱到,其实面面经不起推敲,假若琉球世代服属于日本,首先日本为何允许中琉交往且确定为宗藩关系,这岂非与日本言称的“阴阳两国”相悖?其次若谓世代服属,则世代相交,文化、风俗、政教诸方面皆相通已久,那何以仅有四十八字母、伊势大神、别具分食等寥寥小支相通,况日本文字与别具分食之法皆传于中国,如果以此推论,则日本也属于中国,岂不谬矣?第三日本言称琉球并非一国,那为何法、美、荷等国皆与琉球单独立约,不与日本照会商量,且中国并未干涉,实是说明中琉两国虽名义上为贡藩关系,但琉球内政全由其国内主持。这也从侧面说明古代所谓国家服属关系即是宗藩名义为实,内政干涉为虚,日本以郡县制度强行套换属国概念而将琉球藩属视作国内“以藩置县”,实乃一己私念,甚为无理。
二是从外交辞令的延续性来说,从1871年鹿儿岛县政府的《调查报告》到1879年明治政府的《说略》,其中关于日琉渊源的论述如出一辙,这数年时间从官员的呈奏到清日间的往来照会,都对琉球“世代服属”于日本的观点深信不疑。这种延续性一方面表现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举国急欲扩张的心态,无人肯关心史事考据,但凡于占领琉球有益的观点尽为采纳;另一方面这种说理言辞的盛行也表现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外交观念上的革新,即不仅要在实际行动上速战速决,也要在国际道义上站稳脚跟,二者要齐头并进。遂先行派遣官吏、警察、军队“处分”琉球,再向有关邦国发出照会以说明情由,最终实现了占领琉球的目标。
事实上在“球案”处置的整体过程中,琉球国因国小力微,固然其有在东京向各国公使求救,也有林世功、向德宏等人秘密前往中国乞求援手,但结果都不甚理想。清国作为琉球的宗主国,在“球案”的处置中基本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1878年,驻日公使何如璋向总理衙门报告日本阻贡琉球一事并提出应对三策,随后奕等人在陈述此事的奏章中认为“弃之……不足以宣圣朝绥远之恩……遣兵船责问……过于张皇……再四思维,自以据理诘问为正办”[10]10云云,李鸿章对于此事“意见亦复相同”。[10]10及至1879年日本强占琉球而清政府对日照会中仍希望日本“复加察度,善为转圜,”[3]187同时也认识到如果日本对中国的照会置之不理,则会“彼此徒事辩论,亦复何益”。[3]187客观的说,清政府在得悉日本出兵占领琉球的消息后于公理上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也预料到到此事若日本不肯退让,双方不免往来“徒事辩论”的结果。但从侧面来看,对于日本强占琉球一事,也隐现出其止于“徒事辩论”的态度,这表明清政府对于琉球被占一事寄希望于同日本政府的说理中,一旦在照会理据上占据上风,即为外交的胜利。
《说略》作为明治政府关于阐述“琉球归属日本”观点的总述性文件,意义重大。其若与清琉双方的反驳相比较,则日本罔顾历史而强占琉球的野心企图一览无余,但这种“公理”的虚假性并不能阻止日本强占琉球的步伐。其因一在于琉球国小力微;二在于清政府纠结于反复辩论而丧失了外交的主动权;三在于彼时的帝国主义扩张之国际环境于日本有利;四在于日本军事占领在先而照会“说理”在后,手段果辣。由此可见,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积极改变外交理念,在彼时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浪潮中将实际控制与契约相规并举,在壮大自己的同时深刻改变着东亚的国际秩序。而清政府自宗藩理念出发,过分依赖纸面条约所言之“万国公理”,纵如有何如璋等有识之士建言献策也难走出外交保守的藩篱,从而使形势由主动变为被动。这种于外交理念上的不适与落后,成为之后“球案”虽悬而未决然木已成舟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 硕士学位论文如清华大学孙洛丹的《黄遵宪的驻日外交活动和诗文论考》、南京大学刘宁的《清末“球案”交涉》、山东大学王万华的《琉球群岛的国家法律地位研究》、福建师范大学陈伏由的《“琉球处分”与近代中琉日关系》、福建师范大学林希的《“球案”与近代亚洲格局的演变》、山东大学吴艳的《论清政府对日本占领琉球的反应过程》、福建师范大学江岱莉的《琉球爱国诗人林世功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如南开大学山城智史的《明治初期日本对华外交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徐斌的《明清士大夫与琉球》、山东大学朱法武的《外力冲击下的中琉封贡关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刘绍峰的《琉球群岛地缘关系的时空演变及其区域影响》;较重要的期刊文章如戴东阳:《何如璋与早期中日琉球交涉》,《清史研究》2009年第3期、孙易红:《“球案”及其对中朝宗藩体制的冲击》,《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赖正维:《“球案”与近代中日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谢必震:《李鸿章与“球案”》,《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1年第6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