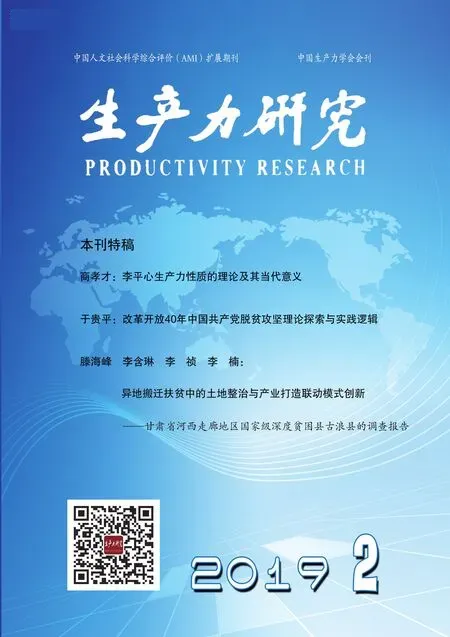乡村宜居环境下温州传统文化的困境与建设路径研究
夏志良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温州市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号工程”,以“四美三宜两园”为目标,以农村综合改革为统领,从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和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举办茶文化节,发展彩色稻田等文化活动,建设文化礼堂和隐宿,挖掘隐逸文化,“普遍推广型”模式进行乡村宜居建设,走生态发展道路。党中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目标,着力解决人居环境等问题,进行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生态宜居乡村,改善乡村宜居环境,提升乡村居民生活福祉。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温州乡村文化一直未得到有效开发,在城市推进过程中,2018年温州市区完成17个行政村、1.08万户以上整村改造,撤村并居,一个个村庄淹没在城市当中,精英文化资源流失,“空心乡村”逐渐增多,乡村人的乡愁不断加深,乡村文化和乡村生活“空心化”,乡村居民生命意义的感受与心理功能积极性减弱,这成为乡村文化复兴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西方《雅典宪章》的实施使世人反思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对于乡村来说,乡村文化根基牢固,根据乡村资源、生产和技术上的优势,开展风景旅游和特色文化建设,对不可再生的乡村文化资源加以关注和保护,以期改善乡村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局面[1]。为了防止乡村民间艺术、习俗的流失,保护文化遗迹和特色建筑,繁荣乡村文化,培育乡村居民意义感和自信,打好乡村发展的精神基础,创新温州瓯越文化,打造南戏之乡,温州需要铸就新时代精神重视宜居乡村文化建设,增强乡村社会凝聚力,提升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从多方位、多渠道、多途径扩大乡村文化教育,为温州现代化事业提供精神文化素质保证。
一、乡村宜居建设环境下的温州乡村文化困境
(一)主流意识形态尚待加强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进一步加强,在强调经济先行的过程中,乡村文化领域面临着弱化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需要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在思想文化交流领域必须占据主导地位、发挥引领作用,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性和协调性[2]。乡村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本。由于乡村居民的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再加上基层干部对乡村文化生活与封建迷信和非法宗教活动认识不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弱化,影响了社会主义主流艺术在乡村文化的主导作用。
(二)乡村文化产品供给不足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由于长期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乡村文化发展滞后,许多乡村过于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推进新型城市化建设,对发展乡村文化事业和乡村居民精神需求不够重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于松散,乡村公共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不足,需要健乡村公共文化网络,实施高效的乡村文化服务,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文化服务发展提供有效平台,避免乡村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发展缓慢,乡村文化生活环境得不到改善,导致乡村文化产品供给停滞不前。
(三)乡村文化价值取向产生问题
拉丁文对“文化”原意的解释为土壤耕作、耕耘,因此乡村文化是农民群众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劳动和生活中创造出来并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形态,由于传统的中国以农业为本位,农民对乡村文化具有崇拜的心理传统,历史的原因导致农民的小农意识,在面对大城市时暴露文化上的自卑心理。农民在认识、分析、解决问题时具有较强的片面性,情感大于理性,2010年调查显示,温州农民约有85%认为与城市居民有心理间隙,约90%感到孤独,约80%感到受城市人盘剥,约35%感觉命运不公%,觉得自己无能的约占30%,想家的占40%。他们心理上与城市人情绪对立,产生“边缘心理”,产生“城市失落感”,部分农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取向偏颇,过于依赖于乡村社会结构,乡村价值取向的失范,乡村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需要纠正与重塑。
(四)人口流失导致文化活力不足
农村人口结构影响了乡村文化的承载能力,农民工进程导致乡村老幼化严重,不能有效推进乡村文化建设,适当的人口结构是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保证。乡村人口的流失给乡村文化建设造成巨大困难,乡村文化传承有断裂的风险,人口的净流失也导致古村落消失、族群文化的弱化,乡土节日文化减少,需要根据乡村不同区位优势,引导农民返乡,发展乡愁经济,依托乡村文化资源禀赋,建设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园,激发返乡农民工创业创新,发展乡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二、温州乡村宜居的文化考量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温州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发展需要与乡村的的发展相辅相成,推动城乡一体化,乡宜居村建设可以减缓城市的压力,缓和城市的住房空间。建设温州美丽宜居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一部分,是温州乡村振兴的基本内容,是温州乡村宜居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乡村建设已经成为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和迫切需求。乡村文化是温州宜居乡村建设中重要的考量指标。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基本点,是宜居乡村发展的“软实力”。宜居乡村建设加强了乡村文化的建设,提高了乡村居民的文化自信和自觉性,有利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守住城市发展中的文化血脉,也是化解“乡愁”情结的重要手段,既可以乡村凝聚乡村居民,又可以增强乡村居民的民族自豪感。温州乡村文化中,宗教观念很强。《史记》记载“东瓯王敬鬼”、《瓯越野庙碑记》记载“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种种迹象表明,温州民众祭拜的对象很多,庄济庙、文昌庙、齐天大圣庙、太阴宫、马九宫、东岳殿、陈府殿、庙头殿、徐忠文祠等名人神庙遍布各地,外来众神诸如陈十四娘娘、马九娘娘、东岳大帝、上清灵宝天尊、圣母娘娘、陈法清等庙宇众多。《平阳县志·舆地下》记载:平阳鸣山周边的自然村几乎都有祭祀鬼神的神祠。
温州乡村文化是温州本土滋长的原生态草根文化,记载着温州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追求,是温州人的心理依托,代表了温州人的智慧,体现了温州人的凝聚力和美好祝愿,是温州人的精神乐园。温州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加强对乡村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是温州乡村宜居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温州的文脉传承与创新。温州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乡村文化容易遭受破坏,需要保护乡土文化的根基。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乡村宜居建设如火如荼,乡村宜居建设既要建设适合居住的村庄,更要建设具有温州特色的乡村文化,要解决温州乡村的具体问题,发掘和传承、创新乡村文化,引导乡村居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双丰收。由于根据温州乡村的实际情况,尊重乡村居民的心理诉求,有序推进温州新型乡村宜居建设,满足温州乡村居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需要,促进温州乡村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体系的确立,促进乡村宜居事业快速发展,因此,乡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体现乡村居民的价值追求,温州乡村的民俗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是温州的人文资源,是温州乡村文化基因与风土人情的产物,感受温州的人文情怀和文化环境,遵守温州市政府“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要求,加强乡村文化的保护、规划、建设和管理,使乡村宜居建设早日完成。
三、温州生态宜居的文化生态内涵
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是当前温州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内容,不断推进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文化服务协调发展,建设温州乡村宜居环境,是温州实施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要求。中央一号文件提出,2020年,农村基础设施有效提高,乡村人居环境得以改善,实现宜居乡村建设初基目标。到2035年,乡村生态环境初见成效,宜居乡村任务基本实现。2050年,全面实现乡村宜居目标。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乡村人居建设重要方向和目标,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前提,发展游憩休闲、健康养生、生态教育等服务,建设一批特色文化生态示范村镇和文化精品,打造绿色文化生态环保的乡村生态产业链。文化生态是温州传统文化宜居乡村的新思路,遵从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生态环境要求,建设集主体、环境、文化于一体生态乡村,完善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维护乡村文化生态均衡发展,重新认识温州人居智慧,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构建温州传统文化宜居生态结构,从自然生态、物质、生态建设传统文化智慧宜居乡村,以生态观进行乡村宜居的规模、空间选择,突出生态智慧,协调处理生态宜居的居住空间、交往空间、发展空间;在文化内涵方面,基于对瓯越社会关系和文化起源,从文化生态角度研究温州乡村宜居人文智慧,创新温州乡村宜居营造智慧。
四、营造乡村宜居文化空间的涵义
文化空间蕴含文化的存在感、时代感、政治感、安全感和意义感。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村,涵盖乡土、乡景、乡情、乡音、乡邻、乡德等。从人类空间记忆研究,空间记忆就是要激发人们对空间领域的记忆。Maccannell通过记忆符号体系理论,分析空间领域的记忆符号、符号的象征意义、记忆者构成,得出人们认识空间的过程可以唤醒对往事的记忆,从而引起回忆,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有利于乡村区域文化空间记忆的文化重构[3]。
乡村空间是一个物理的范畴,乡村文化空间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举行各种乡村民俗文化活动以及各种仪式的固定场所,它具有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判断宜居空间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能力[4],涉及到乡村文化地域的生活环境、文化设施、文化场所等空间环境,乡村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重要载体,是乡村文化发展和传承重要前提和基础。
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范畴研究,乡村文化的空间存在于自然和社会,类型包括“自然型态”、“生计型态”、“制度型态”、“意识形态型态”等型态。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包括环境环境和人类社会两个子系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地表环境,人与地在系统中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动态系统。我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人地系统与乡村文化之间关系紧密,存在物质与能量转换机制和规律,需要研究二者转换的功能、结构,在宏观领域进行调控,不同区域、不同型态的乡村文化类型进行区别对待,使乡村文化与人地关系协调发展。吴传钧教授的《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认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特点延续传承方式,需要研究不同区域乡村文化的构成和发展潜力,发现乡村文化的变化趋势,做好乡村文化的创新与传承。温州在进行乡村文化的传递和延续的过程中,做好文化类型的统计与分类,摒弃封建迷信,在温州这块不同民族的土地上,处理好人与人、人与地、人与文化的关系,使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促进乡村文化可持续发展,做好乡村文化的传承。
五、乡村宜居环境下乡村文化的建设路径
(一)优化温州乡村文化记忆空间
文化记忆依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优化温州文化记忆空间,需要重新布局文化基因空间,合理构思乡村文化空间的框架形式和功能,使人们对文化空间产生身份认同,获得连续性的空间记忆[5]。巴赫金指出,在艺术时空系统中,空间和时间记忆融合成一个整体。时间在这一空间静止,演变为可以认识的艺术,空间在时间、历史记忆之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时间记忆延伸在空间里,空间随着时间的变化二延展或缩小,在时间和空间维度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在时间里形成了自己的表征和记忆。梅洛·庞蒂认为,人居住在空间里。身体具有空间性,人和生活空间紧密联系,身体处于不断活动当中[6]。家是最重要的空间,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家把人的感情、记忆和追求联系在一起,家是最安全、最稳固的空间,文化空间要塑造家的感觉。
从乡村文化空间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分析,乡村居民需要适应乡村的社会环境,礼节人文环境、自然资源、自然环境,适应乡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因为乡村文化空间是一个动态系统,能够进行自我生产和再生产[7]。乡村空间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具有多维性、动态化,自然环境影响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人们需要认识自然、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优化人类生存空间,改善人类社会制度,力求维护自然和社会的稳定,创造优良的文化空间。乡村文化有着优良的社会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这个创新的过程是身处其中的个人和社会共同选择的过程,利用文化空间生产理论,做好文化空间实践、文化空间表征和文化空间再现,对乡村文化空间生产和再生产进行研究。立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对乡村文化再生产进行详细分析。找出乡村文化空间生产和乡再生产的内在规律,为温州乡村宜居建设与乡村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二)加强城乡文化融合,实现温州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资金投入和教育资源有限等是乡村文化发展面临的软硬环境限制。加强温州乡村文化,存在机制问题和能力问题。目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城乡融合协同发展瓶颈,需要加强全域联系,协调发展,激发全域发展动力,以文化建设为平台,提高整体生活环境和质量,建立城乡文化共同体,夯实乡村文化发展基础,增进对城乡文化共同体构建的认同度,依靠整体社会中各个社会主体的推动,实现城乡文化共同体的不断巩固与持续发展,为乡村宜居环境建设提高制度和资源保证。
六、结论
乡村文化传统给乡村宜居建设提供了精神资源,而且,乡村文化理念也给乡村宜居的建设路径提供了思想模式。乡村文化的生态性、传承性表现在乡村文化生产的不断循环、文化产品的再生产和乡村文化生产的多样性。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建设温州乡村宜居环境,不断改善温州乡村自然环境、乡村社会环境以及乡村文化生活方式,建立乡村文化生态体系,优化乡村文化、民间宗教、道德体系、民俗民艺、温州南戏、等乡村文化内容,丰富温州精神文化产品,建设乡村特定的宜居社会环境,以乡村文化教化功能引领乡村宜居建设,建立和谐的乡村文化价值体系,为乡村宜居模式,实现乡村发展,乡村文明,从乡村文化传统中衍生乡村文明智慧,与时俱进地建设温州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