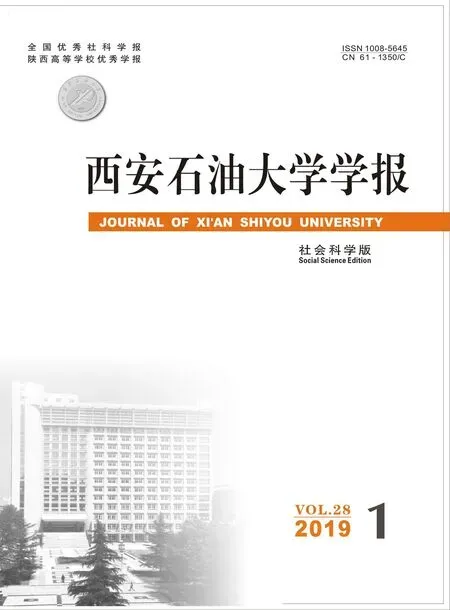被“误读”的“物语”
——民国时期 “物语观”的形成及其成因①
徐文君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0 引 言
“物语”,ものがたり(monogatari)一词的本义是“故事或杂谈。”[1]3自平安时代以来,日本产生了大量的物语类文学;“物语”又专指日本古典文学中一种独特的文体,即“物语文学”。从物语文学的产生到成熟,其文体形态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一般分为早期的歌物语和较为成熟的虚构物语(也称创作物语)。歌物语从和歌中发展而来,如《伊势物语》《大和物语》等,歌物语以和歌为中心,有少量的叙事性散文;歌物语成熟后,逐渐向虚构物语发展,如《竹取物语》《宇津保物语》等,虚构物语以简单叙事为主,和歌不再是文本的中心。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则是把和歌与叙事散文融合在一起,将物语文学的艺术性推向了最高峰,虚构物语也由此走向成熟,并影响了镰仓、室町两时代的文学,为后世日本小说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物语文学在引入中国后常被视为“小说”,即使是像周作人、钱稻孙这样精通日本文化的大家也不例外。其实“小说”这种体裁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物语文学的复杂性。如果说虚构物语因为具有“小说”的某些性质,还可以将之近似等同于“小说”,歌物语和“小说”则大相径庭,被归为“小说”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为什么物语文学在中国会被视为“小说”呢?
1 被“误读”的肇始
清末民初时期“物语”一词就已频频出现于报刊上:1903年《新民丛报》“谈丛”专栏刊载了《年华阁物语》系列,如《年华阁物语——新骨相学》(第32期)、《年华阁物语——说萤》(第33期);《结核菌物语》(《小说时报》1912年第14期)、《蒲公英物语》(中华童子界1915年第16期)。其中《年华阁物语》系列仅冠“物语”之名,与物语文学无关。《结核菌物语》《蒲公英物语》将事物人格化以介绍事物的物理属性,这一系列文章带有科普文的性质。另一类与文学相关的文章是使用“物语”作为标题的寓言小说或虚构故事,这类文章的共同特质是惯用拟人手法。如《铅笔物语》(1914年《中华童子界》第4期)用拟人的手法书写了一只铅笔的内心自述,标题上方注明“儿童小说”;《中秋物语》(1915年《余兴》第6期)将“月饼”、“芋头”、“螺”拟人化,记述了三者之间的对话,并在标题上方注明“滑稽寓言”;一位笔名为“懒僧”的作者在《中华小说界》第8期发表题为“物语”的文章,书写了一个录音机的独白,并在“物语”二字上面标注“寓言小说”;《物语小说:犬之自述》(1917年《小说大观》第9期)顾名思义是一条狗的内心独白。之后以“物语”冠名的文章则大多出现在诸如《儿童世界》《小朋友》《小学生》《儿童杂志》等儿童文学杂志中。
从这些文本中可以看出, “物语”总体上被默认为拟人的修辞手法,以“物语”命名的文学作品大多被视为“寓言小说”。清末民初的报刊上还发表了不少冠名为某某物语的文章,引一时之新,大有“物语热”的趋势。然而,这些文章与日本“物语”的含义相去甚远,折射出国人对于“物语”的最初认知,也是国人在创作中探索物语文学的滥觞。
2 周氏兄弟的“物语观”
在18、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将全球连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不断发生碰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政治上攫取了特权,也在世界文学的交流中搭建起话语中心权。巧合的是18世纪正是西方“小说”(novel)普遍兴起的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文体独特的物语文学很容易被纳入到小说的范畴之中,如《源氏物语》就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
1918年,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写道:
“日本最早的小说,是一种物语类。起于平安时代。去今约有一千年。其中紫式部做的源氏物语五十二帖(今为五十四帖)最有名。镰仓(十三世纪)室町(十四五六世纪)两时代,是所谓武士文学的时代。这类小说,变成军记。多讲战事。到了江户时代(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平民文学,渐渐兴盛。小说又大发达起来。”[2]1
为了介绍日本近三十年的小说,周作人追溯到一千年前的物语类文学,并将之视为日本最早的小说,他试图论证日本近代的小说书写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日本文学具有“模拟的独创性”[2]2,并非一味模仿西洋和中国。“日本最早的小说,是一种物语类”[2]2,他显然意识到物语文学应当独属于一类,但是他仍将平安至室町时代的“物语类”文学统归于小说。事实上,物语被囊括在小说中反而消解了它的独创性。
周作人曾多次赞叹《源氏物语》,“源氏真是可佩服的作品。特别从年代看起来,在世界上任何小说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那种伟大的作品之产生,实在是值得惊叹的。”[3]87他将中日古典文学进行对比:将《万叶集》比作《诗经》,将《古事记》比作《史记》,认为“平安朝的时代的小说又是一例。”[4]2
周作人不仅视《源氏物语》为小说,而且认为平安朝时代的文学特色就是小说的兴起。《源氏物语》是物语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凡是提到“物语文学”则必首推《源氏物语》。但也正是因为《源氏物语》的光芒压抑了其他物语文学的独特性,使得“物语”这种具有非常复杂形式的文体被忽视。《源氏物语》无论在刻画人物形象、心理,还是在细节描写与故事情节上,都不输于任何近现代长篇小说。 “《源氏物语》把物语文学提高到接近近代文学的水平。”[5]105从这些方面来看,不可否认它非常接近小说了,但是如果用《源氏物语》的特点来概括物语文学的总体特点则未免以偏概全。《源氏物语》的确是物语文学,但是物语文学不仅仅只有《源氏物语》,当《源氏物语》被当作小说时,不了解物语文学的中国读者就将“物语”也等同为“小说”了。
民国学者中,较早开始对“物语”一词进行推敲的人是鲁迅。鲁迅给周作人的书信中谈到:
“Karásek的《斯拉夫文学史》…….竟于小说全不提起,现在直译寄上,可修改着用之,末尾说到“物语”,大约便包括小说在内乎?这所谓‘物语’,原是Erzähǔng,不能译作小说,其意思只是‘说话’、‘说说谈谈’,我想译作‘叙述’,或‘叙事’,似较好也。”[6]100
这里所指的“物语”并不是指日本物语文学,而是《斯拉夫文学史》中的文体,鲁迅在这里只是考虑“物语”这一词的翻译。随后他在向周作人介绍波兰散文的信中,又这样写到:
“Adam Szymanski也经历过送往西伯利亚的流人的运命,是一个身在异地而向祖国竭尽渴仰的,抒情的精灵(人物)。从他那里描写流人和严酷的极北的自然相抗争的物语(叙事,小说)中,每飘出深沉的哀痛。”[6]103
鲁迅一开始不同意将“物语”译为“小说”,但随后又在括号中将“物语”注解为“叙事,小说”。在进行完白话文运动不久的民国,翻译文学大兴,许多西语词汇被引进到国内却难找到相匹配的汉译。严格来说,鲁迅不赞成将“物语”诠释为“小说”,但当时也没有更合适的词汇与之对应,鲁迅最终就默认了这一译法。日本文学对鲁迅影响匪浅,但是日本古典文学并不在他的关照范围之中,因此在他的翻译文学中没有再重新阐释“物语”及物语文学。
总体来说,周氏兄弟实际上默认“物语”为“小说”,同时他们对物语文学的关注度也相对较低,对物语文学的研究和译介也被其搁浅许久。这主要是因为物语文学的社会功用性不强,在建构中国新文学的运动中难以助力,且缺乏读者基础,因而在民国的翻译文学热潮中被逐渐淡化,使得“小说”最终取代了它的名称。
3 谢六逸的“物语观”
谢六逸是详细而系统介绍日本文学的第一人,他在1927年出版的《日本文学》开启了中国对日本文学史研究的旅程,并在1929年又相继出版了《日本文学史》和《日本之文学》。这三部著作对物语文学的介绍各不相同,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日本文学》的文学史分期以朝代更替为界点,将平安朝文学独立划分,将镰仓和室町时代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而“平安朝重要的散文为物语类(Monogatari)”。[7]112将《竹取物语》《伊势物语》《源氏物语》《大和物语》等作品均归入“散文”这类文体中。其次,《日本文学史》这本书的上卷中,中古文学就指的是平安朝时期的文学,并“总括这时代的文学,可以分为(一)小说(原名物语Monogatari),(二)诗歌,(三)随笔,(四)日记,(五)历史。”“平安时代的小说,有以下各种。(a)源氏物语,(b)竹取物语,(c)伊势物语,(d)大和物语……”[8]89此处直接用“小说”取代“物语”,架空了物语文学的存在,使“物语”等同于“小说”。在分析《源氏物语》时,谢六逸显然察觉到这部书的独特之处,“原书五十四卷联贯成为一部长篇小说,如将每卷分开,也可以当作短篇故事看。”[8]93谢视之为“形式方面具有特色的地方。”[8]94最后,《日本之文学》三册一改编年体例,转为文体体例。其中第三编“小说”,从第十二章至第二十章共九章,下分物语类文学和小说。并在“物语”这一章中诠释如下:
“在日本文学中,物语二字的原始涵义就是‘语说事物’的意思,因为上古还没有文字,所以不能记载相传的故事,只得使用口传的形式,互相传说,以保存上代的故事,因此这些口传的故事,为语说着的事物——即物语”。“物语文学以话的故事,人物,背景,为其构成的要素。”……“到了平安朝后,因为有了假名文字的存在,遂能利用它来记述或写作;所以在一般的文学史中,对于‘物语’的概念,都是认为有了假名以后的作品。亦即从平安朝到镰仓时代出现的传奇小说,以和歌为骨格而组成的歌物语,以写实为内容的恋爱小说,以记述历史为目的历史物语,以及记述描写战争的战记物语”[9]245
这三部日本文学史对之后的中国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书中对物语文学存在三个不明朗的界定:一是对日本中古文学的分期不确定;二是对物语的文体类型不确定;三是对“小说”和“物语”的区别不确定。特别是对于“物语”和“小说”的认识上,第一部文学史将物语视为散文,第二部将物语等同于小说,第三部中古典物语和日本近现代小说虽被分为两类,却还是将物语文学纳入小说的文体总类中。正是由于这三部奠基性文学史的书写差异,使得国人对 “物语”和“小说”的区别愈发模糊。
物语文学的叙事性较强,而当时又未被译成中文,因此谢六逸的《日本之文学》对各古典物语文学的介绍加入了故事梗概,有了故事性,这使得物语文学更容易被看成“小说”。因为中国小说的起源和故事有着很大的联系。鲁迅讲道:“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10]238鲁迅的小说起源观应当说极具代表性,中国学者大多将带有故事性的文本视为小说,物语文学也不例外。
晚清至民国时期,许多日本小说被介绍到中国,这其中包括一些名为某某物语的日本小说。如梁启超翻译了矢野龙溪的《浮城物语》,周作人介绍过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1934年《图书季刊》介绍的《异国物语》等等。这些披着“物语”外衣的日本近现代小说,某种程度上也模糊了古典物语与“小说”的区别,当它们以“小说”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读者的阅读视域中以后,古典物语文学再想重申自己的文体形态已变得十分艰难。
4 文化帝国主义下的“物语观”
中国对日本文学的关注度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而改变。在战争环境下全民族一致抗日,往日对日本文学译介的热情不再,抗日民族情绪高涨,加之战火摧毁了大量出版社,从1937年至1949年,日本文学在中国的主动传播骤然凋敝。然而日本古典文学却是在文化渗透的背景下第一次大规模地被介绍到中国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日方操控下的杂志刊物。
《中国公论(北京)》是当时较有影响力和复杂背景的刊物之一,其中充斥着不少的媚日文章和崇尚物质享受的萎靡文学,也不乏专注于发扬日本文学的篇章,例如《紫式部与<源氏物语>》,以介绍《源氏物语》为目的同时展开了对平安朝文学的介绍,他将“物语”也解释为“小说”:
“如‘物语’、‘日记’、‘随笔’等,也都是平安朝时代日本的独特的文学形式,所谓当时的物语者,即是现在的小说,当时的物语文学,都是用新兴的假名文字写成的,以‘竹取物语’为最早,又有了‘伊势物语’、紫式部的‘源氏物语’。”[11]158
《华文大阪每日》创刊于1938年11月,是沦陷区影响力最大的中文刊物,也是日本人在沦陷区推行文化渗透的手段之一。尽管处在文化帝国主义的特殊场域中,我们却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华文大阪每日》引发了一场早期最大范围的中日文学交流,实现了日本古典文学在中国的首次大规模传播。其中“日本古典文学鉴赏”这一版块,首次大量介绍日本古典文学,包括日本书纪、歌谣、俳句、物语等等,并专门介绍了《源氏物语》《伊势物语》《平家物语》《竹取物语》。许颖在《日本古典文学鉴赏3》中谈到物语文学:“‘物语’实有小说,故事,传奇,别记,或是传述等,种种的意味。”[12]15许颖并没有将“物语”简单理解为“小说”,她是较早意识到物语文体复杂性的研究者。
民国初期,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开设的日本小说课程由于选修人数不足导致停开,可见当时中国学生对日本小说并没有很大兴趣。抗战时期,大量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使得国人对物语文学的了解更加深入,虽然总体上仍倾向于将物语文学视为“小说”,但已有个别学者认识到物语文学是有着多种意味的文体集合,说明文化渗透在客观上推动了国人对物语文学的进一步认识。
5 物语文学翻译的失真
《<异国物语>考译》解释道:“物语者犹之吾国庄生之寓言,讲说故事之书也。”[13]46国人试图用自己熟知的文学为“物语”塑造一个具体的比较文体对象——庄子寓言。这恰恰说明在未读具体文本之前,国人对日本“物语文学”的认知尚处于概念化、片面化的抽象理解阶段。
民国时期除了少数精通外语和熟悉日本文化的留日名人外,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机会阅读物语文学作品,直到1943年钱稻孙用文言文翻译了《伊势物语》的部分章节,物语文学才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像《源氏物语》这样的大作只能经由日本人转换成现代日语后才得以传播。因此,当时的中国读者对于古典物语文学,存在着语言文化的障碍。
早在1931年傅仲涛就点出了语言差异对文学的影响:“然日本语本身是一种膠著语Ggglutniative,与孤立语Isolating的中国语根本不同,故所构成的文学在形式技巧上具有根本的差异。”[14]74但是当他谈到“物语”时说道:“所谓‘物语’乃文学作家及其所见所闻为根基的叙事散文。放广义上说来,物语为广义的小说,从狭义上说,乃指由平安朝时代至室町时代之小说类的作品。”[15]126他与谢六逸《日本之文学》中的观点一致,均将物语归为“小说”,这个观点实际上和物语文学的语体有着密切关系。
日语最早是借汉字记音,通过汉文体书写传承着本族文学。但是到了假名文字的出现,日本人开始用音假名文字创作和歌,以和歌为中心的歌物语又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文体:和歌嵌入到说明和歌所吟咏状况的散文文字(汉文体)中,逐渐自觉形成了固定形式,即以“昔(人物)……也”[5]133的开头形式,这种散文每每会表述一个完整的故事。随着歌物语逐渐发展成熟,说明性的文字也就从散文慢慢转向为另一种详细叙事的文体了,虚构物语由此开始产生。
平假名文字的出现改变了物语文学的书写形式。之前以“昔(人物)……也”开头的固定形式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大部分文章变成以“昔(从前)”开头和助动词“けり”[5]134相组合的语言方式。例如《伊势物语》第一句便是“むかし(往昔)”[16]1等同于《竹取物语》开篇:“いまは昔、(过去)”[16]29在《大和物语》中则有“けり”和“ける”。这种开头形式和结句表明作者要讲故事,并且在讲述时会随时根据需要切换不同的时态。脱胎于讲述方式的物语文学,保留了口述的文本痕迹,这是物语语体的重要特点之一。
物语文学被翻译到中国之后,我们发现在文章开头的第一句总是“从前……”或者“昔”。例如钱稻孙翻译的《伊势物语》,所有的故事开头都是“昔”字;又或者会在《源氏物语》的字里行间发现“却说”、“话说”这样带有说书体色彩的字样出现。但这样的发现并不足以引发中国读者的怀疑,因为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讲故事的小说本就可以使用“从前”、“话说”来叙述。
因为翻译的缘故,物语文学这种固定文体模式被消解在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中。这也是物语文学传入中国后不可避免地被看成是“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
6 小结与反思
“物语”最先以修辞手法的形式呈现在国人面前,周氏兄弟首次定义“物语”,此后物语就主要被视为“小说”。谢六逸意识到物语文学具有一定的散文文体特征,但最终未能跳出“物语是小说”这一说法。抗战时期,文化渗透推进了国人对物语文学的认识,然而由于翻译的滞后,使得国人无法更深入地了解物语,“物语”是“小说”这一观念代表着民国时期的“物语观”。到了20世纪80年代叶渭渠将物语文学定义为日本古典文学体裁,并细分物语为“歌物语”和“虚构物语”,体现了国人对物语文学认识的不断深化。
与民国的学者观点相反,日本学者古桥信孝却将“小说”视为“物语”的一部分。在他的《日本文学史》中,首先将古典物语分为歌物语和物语文学(即虚构物语),并让它们各自独属一章。第三章为歌物语的历史,第四章为物语文学史。其次,日本近现代的小说反而被囊括在“第四章为物语文学史”的最后一节。也就是说,他认为物语文学是日本民族独有的一种文体,不属于“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小说”反而是物语文学的分支。同时他将物语文学的历史从平安朝延伸到了19世纪,即认为日本的近代小说实际上就是物语文学。对比来看,古桥信孝将“小说”这种文体归纳于物语文学中的这个提法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反思:民族文学文体的独特性如何与世界文学文体的普遍性相兼容?
早在1885年坪内逍遥就提出:“以期我国小说从现在起逐渐取得改良与进步。笔者殷切希望看到我国物语最终能凌驾西方小说(novel)之上,看到我国物语能和绘画、音乐、诗歌同时在艺术上焕然一新。”[17]18古桥信孝的文学史写法足以体现出自坪内逍遥以来本民族文学主体论的思想,即把外来文学特色容纳、整合到本民族文学中,从而继续壮大本民族文学。纵观日本古代文学史,尽管一直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但其并没有失去民族文学的自信心和创造力,物语文学就是最好的例证,《源氏物语》就是对世界最独特的贡献。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以来也深受他国文学潮流影响,在取得一定文学成就的基础上,中国文学也需要更多发自内心的文学自信,从而发扬本国文学的特色。
直到今天,物语文学依然被很多读者当作“小说”来看待。随着物语文学被大量翻译,中国人对这种文体的认识逐渐加深。正是物语文学的复杂性让一代代的研究者长期求索,才有了我们今天对“物语”的进一步认识。物语文学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文类,研究者有必要先明确“物语”的概念,认清物语文学的体裁,这将为今后深入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方向。我们应当仔细斟酌民国研究者将物语文学视为“小说”这一判断的可行性。民国时期,可能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物语”被解释为“小说”,而今我们则要在民国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不断揭开物语文学的面纱,描摹它的轮廓,确定它的属性,使得物语文学能够清晰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