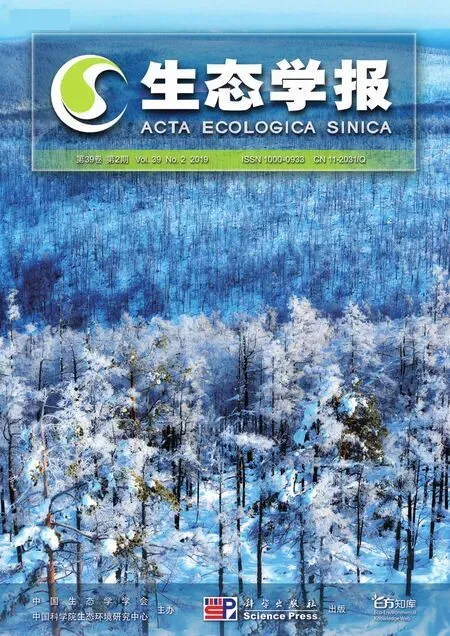基于本土参数的流域生态足迹评估与不确定分析
李金城,严长安,高 伟,*
1 云南大学生态学与环境学院,昆明 650091 2 昆明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昆明 650032
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膨胀和经济的迅速增长,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人类活动日益逼近甚至超过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制约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自1987年WCED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人类共识的发展理念和战略。然而,必须通过定量测度可持续性状态才能将发展理念转化为可操作性模式[1]。为此,众多国际组织和相关研究人员从多个角度探寻测度国家和地区发展可持续性的方法和指标,如:世界银行提出的“国家财富指标体系”[2]、Daly[3]等提出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Prescott-Allen等[4]提出的“可持续性的晴雨表”等。以上研究方法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应用,但基于指标体系的可持续性评价方法侧重于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状态的评估,且在评价指标选取、权重确定和指数计算方法等方面尚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如何定量测度可持续状态始终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难题。William Rees 1992年提出了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的概念[5],生态足迹将可持续性量化,通过具体指标确定人类生存是否处于生态系统承载力范围之内,很好的解决了生态影响与承载力的测量问题[6]。
生态足迹模型主要是用来计算区域内维持资源消费和吸纳人类活动所产生废弃物所必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7- 9],将生态足迹与区域所能提供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进行对比,从而判断一个区域是否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10]。生态足迹计算过程中,将不同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费类型转化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设用地、能源用地6种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11]。不同地区和不同土地类型生产力不同,计算时需乘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是生态足迹核算中最主要的参数,对生态承载力的评估结果有重要影响。目前,国内的生态足迹案例研究大多借用全球或国家等大尺度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12- 15],如张志强等人采用Wackernagel对全球生态足迹计算时所取的产量因子、均衡因子计算了中国西部12省(区市)的生态足迹[16],邱寿丰等人采用国家生态足迹账户计算方法和参数对福建省生态足迹进行了研究[17],谢文瑄等采用谢高地计算中国的生态空间占用研究所采用的均衡因子计算了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生态足迹[18],尚没有形成基于流域中小尺度实际土地生产力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这直接影响了生态足迹模型核算结果的可靠性和可比性。在流域尺度上,采用本土参数与大尺度(国家或全球)参数的计算结果是否存在差异?差异的不确定性有多大?这些问题尚未得到系统和充分的研究,不利于生态足迹方法的推广与应用。
基于此,本研究基于生态足迹模型,以牛栏江流域为案例,计算牛栏江流域本土生态足迹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评估了2014年生态足迹、生物承载力和生态盈余,并分析了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不确定性对评估结果的影响,为生态足迹的不确定性研究与小尺度生态足迹评估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牛栏江为金沙江右岸支流,发源于昆明市嵩明县杨林镇,干流长423 km,落差1660 m,流域面积13320 km2。牛栏江流向大体由南向北,流经云南的嵩明、马龙等县(市)和贵州威宁县(25°02′—27°24′ N,102°53′—104°05′ E),在昭通市的麻耗村附近注入金沙江[19],水系成树枝状。牛栏江流域是一个生态自然环境相对完整的区域,位置及土地利用如图1所示,流域内主要土地利用类型(2014年)为:耕地2145.78 km2,占16.12%,林地8652.98 km2,占67.26%,草地2151.92 km2,占16.17%,建设用地39.07 km2,占0.29%,水域21.47 km2,占0.16%。2014年牛栏江流域总人口数为2672133人,流域生产总值为704.5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26367元,其中第一产业93.32亿元,占13.25%,第二产业283.98亿元,占40.31%,第三产业327.20亿元,占46.44%。近年来,随着流域内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流域生态压力不断上升。加之2012年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启动,流域每年向滇池补水5.66亿m3,流域资源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牛栏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关乎本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下游昆明市也具有重要影响。

图1 牛栏江流域位置Fig.1 Location of Niulanjiang Watershed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2.1 生态足迹模型
生态足迹模型是用来计算区域内维持人类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通过等价因子转换,将资源、能源消费项目折算为耕地、草地、林地、建设用地、能源用地6种生物生产性土地,其中能源用地采用能源折算系数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消费项目进行折算。采用的计算公式为[17]:
(1)
式中,EF为流域总生态足迹(ghm2);N为人口数(人);ef为人均生态足迹(ghm2/人);rj为均衡因子;aaj为各类生物生产土地面积(hm2),j=1,2,3…6表示6类生物生产土地面积;ai为人均i种消费项目折算的生态生产性面积(hm2);i为消费项目类型;pi为i种消费品的平均生产能力(t/hm2);ci为i种消费品的人均年消费量(t/人),n为消费品类型的数量。
1.2.2 产量因子
在生态足迹的计算过程中,同种生物生产性土地所提供的潜在生物生产空间是不同的,为了能够对比流域某种生物生产性土地与全球此类土地均值的差异,需乘产量因子[20-22],从而将流域生产力转化为全球生产力。目前国内对产量因子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中的产量因子采用流域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平均生产力与全球此类土地利用类型平均生产力的比值来表示,综合反映流域内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计算公式为[20]:
(2)
式中,yi指第i类土地的产量因子;Pi指流域第i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109J/hm2);GPi指全球第i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109J/hm2);Qi指流域第i类土地的总产出(109J);Si指流域第i类土地的总面积(hm2);GQi指全球第i类土地总产出(109J);GSi指全球第i类土地的总面积(hm2)。
1.2.3 均衡因子
在生态足迹的计算过程中,不同生物生产土地类型的生产不同,为了便于比较,需乘均衡因子将其转化为统一的可比较的生物生产力面积[12,20- 21]。本研究中,在流域土地生产力转化为全球生产力的基础上,乘以均衡因子,从而转化为能够统一对比的生物生产力面积。因此,均衡因子应采用全球均衡因子。国外对均衡因子相关研究较多,本文采用的计算公式为[18]:
(3)

1.2.4 生物承载力
生物承载力是一个区域所能提供给人类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用此来表示该区域生态容量[22-25]。计算公式为[20]:
(4)
式中,EC为流域总生物承载力(ghm2);N为流域总人口数(人);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ghm2/人);aj为实际人均占有的j类生物生产土地面积(hm2);rj为均衡因子;Yj为产出因子;Ylj为流域j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109J/hm2);Ynj为流域j类土地的世界平均生产力(109J/hm2)。
根据WCED报告,生态供给中减去12%的生物多样性土地面积来维持生物多样性[26]。
1.2.5 生态足迹核算指标及数据来源
生态足迹核算指标具体分类如表1所示[27-30]。为了客观的反映牛栏江流域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的特征,考虑材料的可靠性、可获得性等因素,选择2014年作为研究年份,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云南省2015年统计年鉴》、2015年云南省各州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5》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5》;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主要来源于UCL-Geomatics (Belgium)(http://maps.elie.ucl.ac.be/CCI/viewer/index.php),数据采集年份为2015年,空间分辨率为300 m。

表1 牛栏江流域生态足迹核算指标
2 结果与分析
2.1 牛栏江流域2014年生态足迹评估及分析
2014年牛栏江流域生态足迹及承载力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人均生态足迹为0.730 ghm2,人均生物承载力为0.643 ghm2,人均生态足迹大于生物承载力,存在生态赤字,流域人均生态赤字为0.087 ghm2。这表明当地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超出了生态承载力的范围。牛栏江流域进出口贸易不大,流域可能通过消耗自然资源存量来弥补生态承载力的不足,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从空间分布看,会泽县生态足迹所占比例最高,为23%,其次是威宁县14%,官渡区12%和宣威市11%,这与当地人口数量和发展程度有关。

表2 牛栏江流域2014年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计算结果汇总表
表中ghm2表示全球公顷

图2 牛栏江流域各县市生态超载率统计表 Fig.2 The ecological overload rate statistics table in all cities of Niulanjiang Watershed
通过对比不同县市的生态超载率(图2)发现,官渡区的生态超载率最高,为1659%,是寻甸县(超载率为59%)的28倍,官渡区的生态足迹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态承载力,处于严重的不可持续发展状态。这与官渡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有关,2014年官渡区全年GDP达到了866亿元,其中位于牛栏江流域部分的人均GDP达到了9.55万元,为流域内人均GDP最高,是寻甸县的6.2倍。由于官渡区在本研究区域内的面积很小,因此没有计算官渡区进出口生物产品的实际数量,这也是官渡区生态超载率偏大的原因之一。
通过对比图3、图4以及万元GDP生态足迹计算发现,不同县市的人均GDP及万元GDP生态足迹差异很大,其中人均GDP为9.55万元/人,万元GDP生态足迹为0.138 hm2,是生态超载率和人均GDP最高,万元GDP生态足迹最低的区县;巧家县人均GDP为0.88万元,万元GDP生态足迹为1.502 hm2,是人均GDP最低,万元GDP生态足迹最高的区县。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官渡区对资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远高于巧家县。对人均GDP与万元GDP生态足迹相关分析发现,人均GDP与万元GDP生态足迹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76,这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对资源的利用效率越高。

图3 牛栏江流域各县市总生态足迹及人均生态足迹Fig.3 The total and per capita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all cities of Niulanjiang Watershed

图4 牛栏江流域各县市生产总值及人均GDPFig.4 The gross product and per capita GDP in all cities of Niulanjiang Watershed
2.2 牛栏江流域生态足迹不确定性分析
在生态足迹计算中,为了便于比较和计算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和不同区域的生态承载力,采用产量因子和均衡因子两个参数对生产力进行修正。产量因子是根据本地产量与全球产量比值,将本地某种土地面积转化为此类土地利用的全球公顷,以便与其他地区研究结果比较。均衡因子是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生产力的比较,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乘以相应的均衡因子转化为统一的度量单位。本研究先根据研究区的产量因子将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转化为全球公顷,再乘以相应的全球均衡因子,统一度量。
根据产量因子计算公式,即本地某类土地的平均产量与全球此类土地的平均产量比值,本地某类土地平均产量为此类土地产品总产量与面积比值,产量数据通过统计年鉴获得,全球土地平均产量通过查阅世界农粮组织(FAO)获得,计算得到牛栏江流域耕地产量因子为0.97;林地产量因子为1.76;草地产量因子为0.77;水域产量因子为0.77;建设用地产量因子为0.97;能源用地产量因子为0.00。对比不同研究标准的产量因子可以发现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表3)。其中与Wackernagel等[7]研究中的全球平均标准差异最大,除了标准与方法不同之外,全球尺度忽略了地区性生物生产力的差异,因此大尺度(全球平均标准)并不适用小尺度(流域)计算。对比全国范围,差异较小,说明在计算过程中需要进行详细分类。与刘某承基于净初级生产[24]力云南生态足迹产量因子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原因是云南地形上以山地为主,海拔由低到高,地区之间温度、降雨等气候因素差异明显,因此相同的土地利用类型的生物生产力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草地、水域的产量因子与刘某承基于净初级生产力云南生态足迹产量因子的研究差异很大,主要原因是草地的面积占整个流域面积的16.12%,畜牧业发展程度很低,牧草资源利用率低下,导致草地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牛栏江流域水域占总面积的0.16%,面积少且渔业发展程度低,基于NPP的水域产量因子计算的是浮游生物的生产力,而伴随着水华等水环境污染问题,此项产量因子计算偏大,因此与本研究差异很大。由此说明,云南省省级尺度的产量因子不适合流域尺度生态足迹的计算,在计算小尺度生态足迹时需进行详细的分类。
本文采用的均衡因子来自Venetoulis和Talberth[31]的文章:耕地为2.11;林地为1.35;草地为0.47;水域为0.35;建设用地为2.11;能源用地为1.35,该均衡因子是全球多年平均值,与本研究的计算方法一致。通过统计国内引用量前20的文章[6,10,32-46]中采用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发现不同研究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存在很大差异(表3),其中耕地的均衡因子最大值是最小值的4.16倍,草地的产量因子最大值是最小值的4.16倍。与刘某承等基于净初级生产力的中国各地生态足迹均衡因子测算中的云南省生态足迹中云南省生态足迹均衡因子差异最大,这是由于研究方法和标准不同,本研究的均衡因子基于全球多年平均生产力,而刘某承基于云南省净初级生产力。与Wackernagel、谢高地等研究中的均衡因子存在一定差异,说明均衡因子在不同研究尺度及时间上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3 不同研究中的均衡因子、产量因子对比
采用不同研究中最大和最小均衡因子、产量因子以及本研究中均衡因子、产量因子计算得到牛栏江流域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赤字,结果如表4所示。在3种不同因子计算下,牛栏江生态赤字都大于0,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采用最大值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计算所得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分别是最小值计算所得的2.5倍、3.9倍、1.4倍。本研究所得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介于采用最大值和最小值因子所得结果之间,但生态赤字均小于前两者。
在引用量较高及近期的文献中,与刘某承等[22]基于净初级生产力云南生态足迹因子计算的生态赤字与本研究的最为接近,其次是Wackernagel等[7]提供的全球平均值,最后是谢高地基于净初级生产力全国生态足迹因子平均值。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各地区土地生产力差异很大,在计算流域尺度的生态足迹时不能采用全国平均值。

表4 不同研究均衡因子、产量因子下牛栏江流域生态赤字/ghm2
3 结论
基于本土产量因子参数计算,牛栏江流域2014年人均生态足迹为1.126 ghm2/人,可利用人均生物承载力为0.872 ghm2/人,人均生态赤字为0.087 ghm2/人,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流域生态超载率存在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以官渡区最高。
生态足迹模型中的均衡因子及产量因子在不同文献中取值差异较大,对核算结果具有显著影响。采用最大值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计算所得牛栏江流域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分别是最小值计算所得的2.5倍、3.9倍、1.4倍。
根据牛栏江流域本土参数所得的产量因子与大尺度研究采用的因子差异较大,主要原因是云南地形上以山地为主,海拔由低到高,地区之间温度、降雨等气候因素差异明显,相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物生产力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加之畜牧业、渔业发展程度很低,因此差异明显。由此可见,计算小尺度生态足迹需要进行详细的分类,不能直接借用全球或全国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