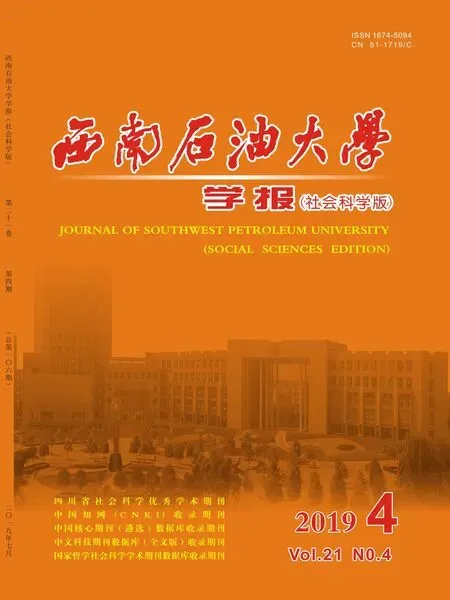国内外媒介素养研究综述
谷生然,魏茂琳
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引 言
随着现代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媒介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媒介之于人,就如同水对鱼的重要程度。尤其是年轻一代,几乎人人都可以利用媒介获取信息,人人都是媒介信息的传播者。媒介以其特有的吸引力,前所未有地影响、改变着人们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在此背景下,媒介素养已被认为是21世纪公民所必需具备的一项技能。媒介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们能否理性对待媒介,能否有效识别媒介信息所隐含的价值观念、政治观点。因此,笔者对当前国内外媒介素养的研究现状作了初步梳理,并总结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期深化媒介素养相关理论的研究,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
1 国外媒介素养研究现状
国外最早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要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1933年,在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利维斯·F·R(Leavis F R)及其学生丹尼斯·桑普森(Denys Thompson)所著的《文化与环境:培养批判意识》一书中,首次提出将媒介素养纳入学校课程之中的建议,随后逐渐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西方国家都把媒介素养置于国家的教育体系之中。在此基础上,国外对媒介素养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1.1 关于媒介素养的定义
虽然国外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早于国内很多年,并且涉及新闻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但是媒介素养的概念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演变,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例如,英国著名的媒介素养理论学者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在其著作《媒介教育:素养、知识与现代文化》(Media Education:Literacy,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中指出,媒介素养是有关媒介的读写能力、参与能力,这种素养既能促使年轻一代去判断分析媒介,也能使他们成为媒介的生产者[1]。美国媒介素养理论专家大卫·康西丁(David Considine)认为,媒介素养是人们使用、分析、评价和传播包括印刷和非印刷等各种形式媒介信息的能力[2]。学者帕特里夏·奥夫德海德(Patricia Aufderheide)和查尔斯·费尔斯通(Charles M Firestone)指出,媒介素养就是使用各种媒介形式进行访问、评估、制作和交流的能力,它的重点在于学会批判性思考[3]。在美国学者朱莉娅·伍德(Julia Wood)看来,媒介素养就是理解大众媒介的影响,并且主动地以多角度的、批判性的方式,接近、分析、评价和响应大众媒介的素养[4]。综合以上国外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媒介素养首先是一种能力。
1.2 关于培育公民媒介素养的目的
加拿大媒介素养联合会主席约翰·彭金特(John Pungente)认为,培育公民媒介素养之目的就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商业动机对媒介的影响,注意这种影响如何侵蚀媒介讯息的内容、技术和资源的分配[5]。英国教育科学部在1989年的考可斯报告中指出:“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更积极、更有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者,他们将要求媒介产品的更大范围和多样化并为此作出贡献。”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认为,媒介素养的培育是为了消除媒介的神秘感,帮助学生学习解读媒介文化中的象征意义,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媒介的控制[6]。美国学者沃里·博文(Wally Bowen)认为,“媒介素养教育致力于培养公民的能力,并将他们与媒介的被动关系改造成积极批判性参与的关系,它能帮助他们挑战私有化的商业媒介文化的传统和结构,并能帮助他们找到公民言论和话语的新路径”[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媒介素养教育不仅要教会青年人如何应对各种媒介,而且要鼓励学生为建立具有真正民主精神的高质量的大众传播体制而努力[8]。
1.3 关于媒介素养理念的变迁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各种媒介认识的不断深化,媒介素养的理念也在发生着变化。从全球范围来看,人们对媒介素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9]12。第一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者们基于保护主义的立场,认为大众媒介传播的内容是“文化病毒”,会给传统文化、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学者们贬低所有以计算机为载体的媒介文化,提倡通过培养人们对书籍、高雅文化、真理与美的鉴赏力,以避免年轻人媒介成瘾和受媒介操纵。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者们认识到文化的表达方式应是多元的,大众文化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种观点,媒介素养更强调理解媒介,将媒介文化作为文化现象来分析。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认为媒介建构了一个虚拟的媒介环境,而受众却将这种虚拟环境视为现实环境,这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由外部文化强加的价值观念,因此,媒介素养更强调培养受众的批判解读能力。第四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基于参与式文化角度,认为人们已不仅是媒体内容的消费者,也是媒体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媒体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成了所有人共同的责任[10]。因此,培育公民媒介素养不能只停留在受众的媒介批判能力层面,也应注重媒介参与能力、交往能力的培养。
1.4 关于媒介素养的内容
由于各国媒介素养理念、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媒介素养的内容亦有所不同。例如,欧洲媒介素养宪章中列出了媒介素养的七项关键技能:有效利用媒介;访问并明智地选择媒介内容;理解媒介内容创作;分析媒介技术和信息;利用媒介进行交流;避免有害的媒介内容和服务;利用媒介促进民主权利和公民目的[11]。加拿大媒介素养的内容则以培养学生的自我认同能力和公民意识为主。澳大利亚媒介素养的内容涉及媒介表达能力、媒介分析能力、媒介审美能力、媒介理解能力、媒介参与能力等方面[12]。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将媒介素养的内容确定为:媒介信息获取能力、媒介信息分析能力、媒介信息评价能力、媒介信息创作能力、媒介参与能力[13]。
1.5 关于媒介素养教育实践
公民媒介素养的培育,离不开媒介素养教育。由于各个国家国情上的差异,因而媒介素养教育在各国的具体实践上也有所不同。当前,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已经相当成熟,涵盖了从小学到大学教育体系的全过程,并逐步成为终生学习的重要内涵,成为正式教育体系中的教学科目,而且有完整的评价系统[14]。美国各州不但以法规、法案的形式来保障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而且一些州甚至规定教师必须从提供教育学位的正式机构得到有关的媒介素养教育认证培训。另外,美国成立了众多的媒介素养教育组织,这些社会力量已成为促进美国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州都将媒介素养教育单独或放在英语课中作为学生的必修内容,一些州还专门为进修教师设立了媒介素养教育学位[15]。日本作为亚洲地区较早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国家,主要通过加强中小学的新闻教育和鼓励新闻媒体向大众传授新闻知识这两种途径来进行大众媒介素养教育。日本不仅形成了包括高等新闻教育、在职新闻教育、大众普及教育在内的高度发达的新闻教育体系,而且还开展了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教师培训,出版了许多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书籍[9]42。
总之,从国外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外媒介素养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颇丰。媒介素养理论的相关研究大多立足于新闻学、传播学、公民教育等方面,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内容涉及较少。另外,国外研究对媒介素养的定义尚未达到一致的认识。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在媒介素养方面的经验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例如国家政策层面的有力支持、社会力量的积极推动以及媒介素养理念的及时更新等。
2 国内媒介素养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国内学术界对媒介素养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7年,卜卫在其发表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一文中,阐述了“媒介素养”在西方发展演进的历程。随后,各研究领域的学者相继发表了一些关于媒介素养的论文,并逐步引起更多的人对媒介素养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各种新媒介层出不穷,它们在便捷人们生活的同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突出。因此,国内对媒介素养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媒介素养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与日俱增。
2.1 关于媒介素养的内涵
“媒介素养”的内涵随传播媒介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有的学者从信息处理角度出发对“媒介素养”作了界定,如张开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的各种讯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性应变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媒介信息的能力[16]。蔡琪、李玲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媒介素养的重点应该从媒介批判能力转向信息管理能力,而信息管理能力又包括筛选能力、甄别能力、整合能力[17]。也有学者从其他方面给出了“媒介素养”的不同内涵,如陈龙认为,在媒介全球化背景之下,传统媒介素养的能力结构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调整,新的媒介素养结构应包括文本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跨文化交往沟通能力,而培养公众理性的民主意识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18]。在吴勇看来,媒介素养是指公众对媒介及媒介相关知识的认知能力,对各种媒介信息的选择、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利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19]。
2.2 关于培育公民媒介素养的意义
孔祥渊认为,培育教师媒介素养的意义在于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促进教育教学活动与时俱进、助力提升教师个体媒介生活品质[20]。陶喜红指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有利于提高其媒介素养,有利于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方针,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21]。在王雅灵看来,我国公民媒介素养教育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能够提升公民的整体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能够促进形成良好的媒介生态,能够抵御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22]。蒋晓丽认为,在我国推行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不仅有利于保持网民的自主批判能力、增强对负面信息的免疫力,而且有利于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3]。
2.3 关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媒介素养
近年,国内学者也注意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媒介素养进行研究,如教师、农民、政府官员、留守儿童、青少年、大学生等群体。其中关于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研究成果最多。
(1)关于教师的媒介素养。谢美芳指出,幼儿教师在对幼儿进行媒介素养启蒙教育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提升幼儿教师的媒介素养,从而建立起符合幼儿特点的培养实践[24]。高国伟、张光华认为,微博具有冲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削弱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工作效能、增加思想政治教育难度的负面影响,只有通过多种渠道着力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媒介素养,方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25]。
(2)关于农民的媒介素养。牛新权指出,在农村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能够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加快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因而要从媒体培训、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培养意见领袖四个方面着手提升农民的媒介素养[26]。袁军认为,相对于城市公民而言,当前农民的媒介素养相对较低,二者在媒介的接触、认知能力方面和运用媒介传播信息实现自身发展的能力方面差距较大[27]。
(3)关于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周大勇、王秀艳认为,地方官员媒介素养不够高的原因在于新闻发言人制度使官员不愿说、官员本人顾虑太多而不敢说、一些地方行政保护主义的“护短”致使官员不能说,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培育官员的媒介素养,以维护好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28]。庞亮认为,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提高有利于政府应对公共危机,因此要通过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展媒介素养培训与考核等方式增强官员媒介素养[29]。
(4)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杨靖、黄京华受到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的启示,提出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四级阶梯:第一级阶梯主要是通过亲子媒介识读的途径来帮助儿童了解媒介;第二级阶梯则是通过将媒介学习内容融入到信息技术课和语文课之中的方式帮助儿童理解媒介;第三级阶梯是以课堂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儿童审视媒介;第四级阶梯是通过农村社区行动的实践活动来帮助儿童利用媒介[30]。郑素侠指出,留守儿童接触媒介的动机在于获取心灵上的慰藉,而电视、网络是他们最常使用的媒介,可以通过参与式学习方法、确定留守儿童的媒介参与层次、拟订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来完善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工作[31]。
(5)关于青少年的媒介素养。臧海群认为,媒介素养在当代青少年的素质教育中尤为重要,其首要任务在于培育具有信息理性的公民,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经验启示我国应在媒介教育方面突破专业教育的局限,让素养教育成为通识教育[32]。秦永芳指出,我国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既要借鉴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与原则,又应实现本土化,使之具有中国特色[33]。
(6)关于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冯支越、唐诗等人指出,以微博为代表的媒介平台日益影响着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表达方式、行为方式,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通过培育素养、创新形式、促进互动的方式来培育学生的媒介素养[34]。另外,也有学者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现状作实证调研,进而根据调查结果提出针对性更强的媒介素养教育策略。例如,生奇志和展城的《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调查及媒介素养教育策略》、吴鹏泽和杜世友的《中国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研究》、谢利霞的《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及对策研究》等。当然也有学者将大学生群体中的师范生单独作为研究对象,如谢壁如的《Web2.0环境下师范生媒介素养培养模式研究》、刘芳华的《高等师范院校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及提升策略》。
2.4 关于媒介素养的跨学科研究
国内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成果虽然大多是基于新闻传播学的视野,但是目前仍有一些学者注重对媒介素养的跨学科、多角度研究。例如张新明、王振等人从心理学视角分析了感知、思维、人格对青少年媒介素养产生的影响,并提出要推动我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从传统的技能型向素养型转化[35]。王帆、张舒予从教育学视角对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作了分析,并指出虽然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在概念起缘、内涵变迁过程、培养方式三个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二者却呈现出相互融合之势,提倡以教育技术作为二者的融合桥梁[36]。杨克平、徐柏才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上有融合的可能,因此要借鉴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理念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与内容[37]。罗国干认为,美学教育是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有效方法,应将美学教育融入媒介素养教育,进而增强大学生的审美能力、思辨能力、媒介信息驾驭能力[38]。
当前,从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比较关注媒介素养的相关问题研究,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媒介素养已逐渐成为21世纪合格公民的必备素养之一。但是,国内研究目前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研究对象虽然多元化,但是缺乏对老年人媒介素养理论的研究。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相关研究也应加强对老年人群的关注度。其次,媒介素养研究的本土化程度仍显不足。当前研究大多还是以国外的一些理论和实践经验为借鉴,媒介素养研究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程度仍不够深入。最后,虽然各学者都基于特定视角对特定对象媒介素养的提升给出了具体建议,但是对于把媒介素养教育上升到全民教育层面的提议相对较少。
3 媒介素养研究的几点展望
根据以上国内外媒介素养的研究现状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未来我国媒介素养的研究应注意以下方面:
首先,应加强对社会其他群体尤其是老年人群的媒介素养研究。2015年7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未来十年内要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智慧健康养老产业[39]。事实上,智慧健康养老目标的实现除了依赖智能化设施和专业人才以外,还有赖于老年人自身媒介素养的提高。尤其是伴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快速到来,相关研究也理应将关注点放到老年人群之中,关心关注老年人的媒介素养状况,推动老年人媒介素养的提高。可以说,在信息化、数字化日益加速的当今社会,老年人媒介素养的提高,对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推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其次,应加强媒介素养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在全球化浪潮之下,关起门来搞研究是不可行的,不加辨别的“拿来主义”也非明智之举。客观来讲,国外媒介素养研究起步较早,理论体系较为成熟,实践经验也较为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经验。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各个国家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别国的成功经验不一定适宜我国的发展。因此,我国在借鉴国外媒介素养的先进理念及实践模式之时,要更加注重将国外的有益经验与我国的具体国情深度结合,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理论,促进媒介素养理论的本土化。
最后,应树立全民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身处媒介化社会,每个人每天都在使用各种各样的媒介工具,每天都被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所包围,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在复杂的媒介环境之中,媒介素养不再只是媒体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素养,也应是每一位社会公民必须具备的一项素养。与此同时,媒介素养教育不应只面向新闻业、传播业人士,也应面向每一位公民。事实上,发达国家早已设置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向本国国民尤其是青少年普及媒介素养知识,以增强国民的媒介运用能力。因此,相关研究人员也应该树立起全民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呼吁政府尽快把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推动全民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开展。
4 结 语
总之,关于媒介素养到底是什么、它究竟应包括哪些能力、它具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应该如何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等问题,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参与了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涉及许多学科领域,如新闻传播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并且已经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理论界对媒介素养理论的多维度研究表明,媒介素养理论具有综合性特点,它已经超出了新闻传播学这一学科本身,而成为多种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但相较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热门研究课题,以及社会对媒介素养的现实需要,该方面的受重视程度还稍显不足。另外,虽然学者们就公众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一些实践路径,但是真正的实践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思考。尤其是在当今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新媒介迅速发展的时代,个体具备了“传者”与“受者”双重身份,媒介信息也越来越碎片化,人们可能无法依赖某一则媒介信息或某一家媒介机构就知晓新闻事件的全貌。这就需要个体提高对媒介信息的获取、辨别、传播等能力,做到“兼听则明”,才不致于在信息海洋之中迷失方向。因此,现实迫切需要我们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更好地融合并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这无论是对于个体媒介素养的提升,还是媒介环境的优化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