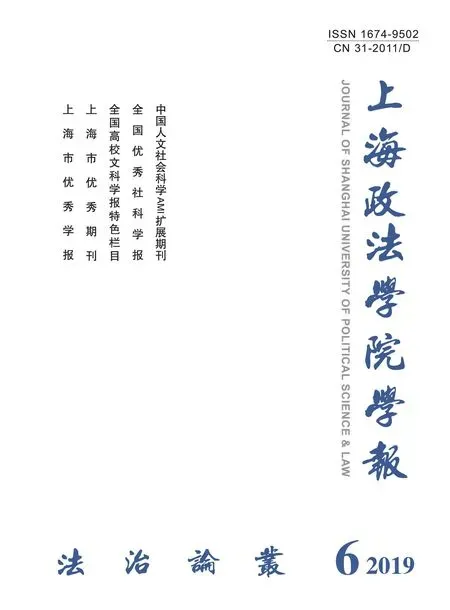论合宪性审查权的性质
雷槟硕
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44 条将我国《宪法》第70 条第1 款中的“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结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要求,为加强宪法实施与监督,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机构改革后承担合宪性审查的职责。《决定》与《方案》在宏观上为合宪性审查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计指明了方向。同时,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职责决定》”)将《决定》与《方案》的要求吸收并明确规定于其中,将执政党的政策文件通过程序的方式转化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法律)。但对于如何实施合宪性审查,如何发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功能,如何在现有制度体系范围内协调各机构与职权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进一步研究说明,更需要在当前宪法法律制度框架内进行设计。这是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同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强调:“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即进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制度设计,推进宪法与法律监督,落实合宪性审查,必须在现行宪法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因为现行的宪法法律秩序确定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职能定位,也确定了合宪性审查权的性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必须符合合宪性审查权性质的要求,合宪性审查权的性质构成解决合宪性审查主体、行使机关、范围、程序、对象等问题的基础。因此,回答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的相关问题,首先需要在现行宪法法律秩序的背景下确定合宪性审查权的性质。
从2018年进行的宪法修改以及现行《宪法》的修改频率来看,全国人大在短时间内不会再进行宪法修改。因此,面对当前合宪性审查的实践需求,以及党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性要求,要同时兼顾“于法有据”与推动立法适应改革的需求。一方面,这需要通过解释论的方式进行融贯,借助宪法解释“使宪法适应社会现实的变迁,协调宪法的现实性价值与规范性价值”①韩大元、张翔:《宪法解释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 页。。另一方面,可以进行必要的理论探讨,在宪定秩序的前提下,明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以及合宪性审查权的可行发展方向。宪定秩序是当前宪法和法律委员开展合宪性审查的前提。只有确定“开端”与“出发点”,才能更好地立足当下与向前迈进,否则很容易出现“娜拉出走”的困境。基于此,本文着眼于探讨现行宪法法律秩序语境下的合宪性审查权的性质,确定当前合宪性审查开展的基础。
一、宪法规范视野下的权力性质重申
在修宪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析清合宪性审查权的性质,首先,需要确定合宪性审查权是新设独立权力还是原有权力的重申。若合宪性审查权属于新设独立的权力,就需要明确其规范性基础、其在国家机构构造中的归属、其与其他权力的区别与协调、合宪性审查权的构造。导致合宪性审查权被认为是新设独立权力的原因是:一方面,合宪性审查顺应《决定》《方案》的要求,结合宪法变迁的时代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另一方面,《宪法修正案》第44 条明确将我国《宪法》第70 条第1 款的“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决定》《方案》指明的改革方向,以及《职责决定》关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规定可能使人们认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获得一项名为“合宪性审查权”的新设独立权力,作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开展合宪性审查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但在公权力的领域,“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法理已然确定了合宪性审查权的基本前提。其一,作为一项宪定权力,如果合宪性审查权为新设独立权力,需要宪法明确规定,即使采用宪法解释的方式亦不能说明合宪性审查权为新设独立权力,因为宪法解释以宪法教义为基本前提。其二,在制度设计的逻辑中,规范性文件很难赋予下位机关高于上位机关的权力,进而对上位机关进行合宪性审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属于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在闭会期间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便存在“脑体倒挂”的困境。这既不符合我国的政治制度基本安排,亦不符合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因此,合宪性审查权并非新设独立的权力。
其次,合宪性审查权是对原有宪法监督权的重申。现行《宪法》第62 条第2 款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第67 条第1 款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监督宪法与解释宪法的权力。根据该两款规定,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宪法监督的权力,而合宪性审查便是宪法监督的具体方式之一,因此,合宪性审查权已为宪法条文明确规定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即是说,合宪性审查权并非新设独立权力,而是原有宪法权力的重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属于宪定的合宪性审查权行使机关。其规范性基础便是《宪法》第62 条第2 款与第67 条第1 款,而且,第70 条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属于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定位使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不能作为完全独立的新设合宪性审查机关,这3 条宪法规定确定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的规范性前提。
最后,改革后的合宪性审查权是对原有规定的强调与适用扩充。根据《方案》与《职责决定》之要求,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需要“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职责”。这说明合宪性审查权的行使以前着眼于统一审议法律草案,即主要着眼于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法律或者下位法是否违反上位法。①参见范进学:《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功能与使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 期。但合宪性审查的含义以及范围明显广于合法性审查,即广义的合宪性审查包括合法性审查与狭义的合宪性审查。在合宪性审查的视角下,2018年修宪之前的合法性审查只是法律委员会对其中一部分审查对象进行了广义的合宪性审查,即法规的批准备案。但在整合合“宪法”性审查与合“法律”性审查之后的合宪性审查,不仅使狭义上的合“宪法”性审查成为主要可能,突出《宪法》第5 条与《立法法》第96 条之合宪性要求,而且,合法性审查的要求因应时代发展得到进一步的明确。为防止宪法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宪法化,在原有法规备案审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合宪性审查权力的功能与更广泛的合法性审查。②参见韩大元:《从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体制与功能的转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 期。因此,改革后的合宪性审查权既是对以前合宪性审查权的重申,同时,也对合宪性审查权充分行使提出了要求,强调合宪性审查,并在适用上不仅局限于合法性审查,将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充到《宪法》原已包含的合宪性审查对象上,以回应合宪性审查权在实践中的适用需求。
二、合宪性审查权的权属与运作
合宪性审查权作为一项宪法规范视野下的重申权力,不同于新设独立的权力,其依赖于宪法规范的规定。同时,基于宪法变迁、实践需求与改革趋向,该项权力具备了新时代的新目标。一方面,根据《宪法》第62 条第2 款与第67 条第1 款规定,合宪性审查权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另一方面,根据《职责决定》的规定与《决定》《方案》的设计方向要求,需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因此,为明确合宪性审查权的性质,还需要明确合宪性审查权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之间如何具体分配行使。因为,合宪性审查权的设计影响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具体行使合宪性审查权。以宪定秩序为基础,应该从2 个宪法规范的角度出发理解这一点:合宪性审查权权源规范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规范定位。
(一)合宪性审查权的权源主体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首先,《宪法》第62 条第2 款与第67 条第1 款明确了宪法监督权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合宪性审查权主要属于宪法监督权,因此,该两款为合宪性审查权的权源条款。既然宪法明确规定了该项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且作为公法领域,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条款中,通常采用反向推理,“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没有被表达出来的东西要被理解为排除在外的东西”③[美]弗里德里克·肖尔:《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法律推理新论》,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 页。。因此,通过文义解释以及反向推理,可以确定合宪性审查权在宪法规范上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这种权力归属在法律规定上具有排他性④参见叶海波:《设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法治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 期。,使得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无法在权源上直接获得合宪性审查权。
其次,在我国,宪法监督权的性质决定了其应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权起源于议会对政府财政的监督,而议会监督的背后体现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最具有民主代表性的机构便是议会,因为其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作为常态性机制和机构监督政府,实现宪法规范国家机关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的目标。①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372 页。其中,监督权最核心的内容便是宪法监督。因此,在我国的政治制度框架内,宪法监督权性质决定了其应归属于直接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相反,虽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组成人员为人大代表,但其宪定地位以及代表性低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使其很难直接负担监督权所需的代表性。
再次,合宪性审查权涉及合宪性决断,合宪性决断需要由宪定的决断机关来确定。宪定的决断机关存在位阶化的判断主体排列顺序,依次为立宪机关、特定条款的修宪机关、宪定最高民意代表机关和其他。立宪机关在立宪之初最了解条款之含义,因此,其具备决断的最佳正当性;若该条款经过修改,尊重条款原意,其次则是修改该条款的机关,即修宪机关;若两者都不存在,则当属宪定最高民意代表机关,因为宪法是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结果,对于民意之判断应为宪定最高民意代表机关。若立宪或修宪时,明确规定相应机关为合宪性决断机关,则该权力属于宪定之机关。而我国《宪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其他机关作为合宪性决断机关,则只能确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合宪性决断机关。
最后,合宪性审查权的改变需要宪法明确规定。根据《职责决定》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2018年修宪前的法律委员会的职责。即《职责决定》将《方案》之内容转化吸收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具有推进合宪性审查的职责。“这个决定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它容易让人搞不清楚合宪性审查的主体究竟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还是人大常委会。”②刘松山:《备案审查、合宪性审查和宪法监督需要研究解决的若干重要问题》,《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 期。但仔细推敲,可以发现合宪性审查的主体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方面,《宪法》规定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性质决定了其并非直接的宪定合宪性审查权归属主体,后文关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辅助行使合宪性审查权会具体论证这一点;另一方面,作为职责主体不等于权力归属主体。作为一项宪定权力,合宪性审查权必须由宪法明确规定归属主体或者改变归属主体。
因此,在尚未再次修宪之前,作为宪法监督权的合宪性审查权的权源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这也是监督权的性质的必然要求。即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律或者决定,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发挥合宪性审查的职能,不能将狭义合宪性审查权权属转移,也不能将合法性审查权之全部权力转移给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辅助行使合宪性审查权
在权源方面,合宪性审查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宪定地位也使其无法单独作为合宪性审查权的权源主体,因为合宪性审查权具有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不可承受之重,不符合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定位。
首先,《宪法》第70 条明确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为专门委员会,根据该定位,可以确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辅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作为专门委员会,宪法委员会的职能在于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工作。”③韩大元:《关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几点思考》,《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 期。宪法没有明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专门宪法监督机关且专有行使宪法监督权是经过充分考虑的,这不仅是因为在宪法规范上没有明确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宪法监督机关;若确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宪法监督机关也不符合其专门委员会的定位,因为专门宪法监督不仅在于监督机关之专业性,更在于其权威性、正当性与制度体系的内部融贯性。否则,首当其冲的便是如何处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之间关系的问题①参见刘松山:《1981年:胎动而未形的宪法委员会设计》,《政法论坛》2010年第5 期。,为解决或者规避该问题,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定位为专门委员会,并根据《宪法》第70 条规定,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因此,为更好地保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以发挥其辅助作用。同时,这意味着尽管合宪性审查权的权源主体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但仅是指权源归属,不等于其职权不能交由其他主体行使。但若能使其他机关行使合宪性审查权,需要对合宪性审查权的程序以及权力构造进行设计,在理论上协调不同主体分别行使合宪性审查权不同权能与合宪性审查权归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的关系。
其次,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辅助行使的合宪性审查权并非合宪性审查权全部。《宪法》第70条明确规定,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若将“研究、审议和拟定有关议案”理解为完整的合宪性审查权的内容,会导致合宪性审查权成为“无牙的老虎”,因为,审查机关在对规范性文件或行为之合宪性判断之余,还需要对审查对象作出决断,甚至给予相应的惩戒,如依据《立法法》第97 条进行撤销、更改。若缺乏必要的后果或惩罚性构造,很容易导致审查落空。因此,为保证合宪性审查权的有效运用,必须构造完整的权力,将权力不同权能交由不同主体行使。其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特定的权能,同时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并非完全独立行使完整的合宪性审查权,或言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并非“终局性的决定机构”②参见秦前红:《合宪性审查的意义、原则及推进》,《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 期。。同时,这也反向说明,为符合现行宪法法律秩序,推进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可以对合宪性审查权的权能进行分割,交由不同主体行使。
再次,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中的判断权。根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的前两项特征可以确定,尽管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并非合宪性审查权的权源主体,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一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机制与合宪性审查的特征使它们无法切实有效地独立开展合宪性审查,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因为其专业性、常设性、事务性可以使其发挥实质审查之功能。另一方面,《职责决定》进行了授权,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方式将合宪性审查权授权给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同时,《宪法》第70 条规定的“研究、审议和拟定”确定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的限度。即是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将合宪性审查权分为判断权与决断权。判断权授权给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而自己保留决断权,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审查对象判断的基础上行使决断权。之所以将决断权保留给自己是确保合宪性审查权的根本——合宪性审查对象之效力的决断。由此,不仅可以将合宪性审查权的权源限定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符合现行宪法秩序的要求,还可以解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与会议特点带来的审查困境。
最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的判断权包括研究、审议与报告和说明。此处的判断权是指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具体负责审查对象的实质合宪性问题。根据《宪法》第70 条,该项判断权内容应包括研究、审议有关议案。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2 条规定,专门委员会(此处指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议之后还需要提出报告;第37 条第1 款第1 项、第3 项、第4 项和第5 项则规定了审议的具体内容,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交付的议案、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交付的质询案以及自己主动进行的调查研究;第2 款则规定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的要求。除此之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32 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23 条、第24 条第1 款、第2 款与第26 条第1 款、第2 款,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4 条第2 款与第15 条都明确了专门委员会的审议职责。从合宪性审查的视角看,审议、研究是合宪性判断的主要过程,但合宪性判断之判断权不仅包括研究、审议,还包括报告或提出意见,必要时,提出修改稿。即是说,合宪性之判断,不仅要求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通过审议、研究的过程作出合宪与否的判断,还需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判断的理由和依据,进行充分的说理。否则,一方面,仅提供合宪性的判断会使得判断权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决断权无法区分;同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决断权的行使需要依赖判断之理由与论证,仅借助权力的决断特征无法保证合宪性审查的正当性与可接受性,尤其是对于全国人大而言。全国人大代表的非职业立法者身份使其需要通过必要的说明,辅助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最终作出合理的决断。另一方面,合宪性审查权属于宪法监督权,尤其是在被动启动的场合,尽管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的是具体的审议,但最终可能需要对审查要求主体和审查建议主体进行反馈。通过详细的理由说明,无论符合宪法抑或不符合宪法,都“十分必要,既回应了社会关切,保障审查建议人的知情权,也有利于增强公民、组织提出审查建议的积极性,提高社会公众对备案审查工作的关注度与参与度,同时还会督促制定机关尽早纠正违法问题”①张春生:《立法实务操作问答》,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 页。。故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中的判断权,应着眼于研究、审议过程中的实质内容判断。
因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的合宪性审查权并非完整的,而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赋予它行使的部分职权,尽管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着实质审查的工作。但基于合宪性审查权的监督权性质,合宪性审查之决断仍由权源机关作出,这是宪定化与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同时,为保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更好地行使合宪性审查权,需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判断之中提出报告和说明,提升合宪性审查之判断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
三、合宪性审查权的内部构造
在解决合宪性审查权性质问题之后,还要探讨合宪性审查权存在的原权和授权、从判断到决断等内部构造问题。为促使合宪性审查权有效运作,需要析清合宪性审查权的内部结构,这有助于解决合宪性审查权的具体权能分配、审查程序设计以及机关内部设计等问题。
首先,合宪性审查权分为狭义的合宪性审查权与合法性审查权。这种划分不仅是单纯的分类,而是根据权能在内部分工之不同,进行权力的内部适度分割。狭义合宪性审查权是指对法律的审查,但该类审查很难在现行体制下展开。因为,根据《宪法》第70 条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闭会期间,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以对行政法规等其他规范性文件展开审查,无论事前还是事后,即合法性审查。但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却无法实现真正的事后审查,因为判断权的指向对象来自决断权归属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很难期冀下位主体对上位主体的事后审查能获得上位主体的确认。同时,接受领导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文件在理论上存在自我审查的问题,也存在无法真正实现审查的困难。
除宪法之外的其他文件都存在不符合宪法的可能性,行政法规和效力低于行政法规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此前主要借助合法性审查的方式展开,而且相对较为成熟。基于相对成熟的实践运作方式能够更有效地推进合宪性审查的开展。①参见张春生、秦前红、张翔:《推进合宪性审查 加强宪法实施监督》,《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 期。可将此种审查(合法性审查)归属于改革后的广义合宪性审查,为合宪性审查吸纳和提供引导。但困难在于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即狭义的合宪性审查。基于合宪性审查权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且法律亦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仅是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且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使得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合宪性审查工作很难展开。
为解决该问题,需要充分利用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内部构造的设计展开。其一,“考虑在委员会内部设立法律草案审议部和合宪性审查部”②韩大元:《从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体制与功能的转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 期。以及合法性审查部。合法性审查部负责行政法规与效力低于行政法规的规范性文件,采用原有的合法性审查运作方式。法律草案审议部主要负责事前(狭义)合宪性审查,合宪性审查部或事后审查部负责事后(狭义)合宪性审查。其二,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非基本法律可以展开事后的合宪性审查,由事后审查部负责,即事前审查中未发现或者随着宪法变迁带来的问题可以在事后进行审查,只是此时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接受全国人大的领导,在开会期间提出审议报告,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表决,行使合宪性审查决断权。其三,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则不能开展事后审查,因为不存在高于全国人大的机构,可以行使合宪性审查决断权,确认基本法律违宪,这导致制度上无法形成闭环。但后二种审查只是在理论上进行构造,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相关主体更可能借助其他方式来规避后二种合宪性事后审查的出现,在立法阶段通过三读程序、立法之民主约束机制等方法防止不符合宪法情形的出现。即经由法律草案部以事前审查的方式审议法律草案,排除明显违宪的情形。但需要注意的是,广义合宪性审查以合法性判断为前置条件。③参见胡锦光:《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体系化》,《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 期。一方面,可以过滤不必要的狭义合宪性审查,因为,合宪性审查不等于合法性审查,合宪性审查主要着眼于超越立法权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等情形。④参见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和联系》,《中国法学》2019年第1 期。另一方面,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内部部门分立设计的功能充分区分开来,使得各部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相反,若将狭义合宪性审查权同合法性审查权混同在一起组成合宪性审查权,合法性审查权可能因为狭义合宪性审查权存在的困境被裹挟着无法有效展开。而将合宪性审查权进行分工,使得合法性审查权能够切实有效地被运用,同时,借助其他方式以及新的理论构造解决狭义合宪性审查权问题,保证当前广义合宪性审查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实现。
其次,合宪性审查权需要协调好决断权与判断权的行使。根据前文论证,合宪性审查决断权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判断权则授权给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其中,判断权不同于决断权之处在于:判断权需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审查对象内容之合宪性进行实质判断,这涉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审查对象合宪性的理解与解释。因为研究、审议都是合宪性判断之过程,在研究、审议过程中,判断主体对审查对象是否符合宪法的内容进行判断,即实质解释性理解。而审查对象是否符合宪法首先存在对宪法的权威理解,特定主体对宪法的权威理解通常被认定为正确理解。能被认为是正确理解的机关只能是民意代表机关。因此,决断权也只能归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即判断权无法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带来民意机关之决断权威,判断权拥有的是基于内容判断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性。借用拉兹的权威理由论来说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的合宪性审查判断权属于一阶审查权,依赖于审查内容之理由;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合宪性审查决断权属于二阶审查权,是不依赖于审查内容之理由。①参见[英]约瑟夫·拉兹:《实践理性与规范》,朱学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2-40 页。尽管判断权之内容通常同决断权之权威是重合的,但却不能将两者等同。因为判断权依赖于判断之内容,若使得合宪性审查之判断成立,需要给出内容判断之理由,使其在“量”上相对于对立理由更具说服力。因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之后需要提出报告与建议。但判断权无法替代决断权,因为决断权是在“质”上优于判断权,尽管判断权之理由可能在“量”(实质内容说服力)上强于决断之权威,但权威依赖的是权威本身。也正是因为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无法独立审查法律。
再次,基于判断权“质”(权威性)上的弱势,需要依赖内容。因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研究、审议审查对象需要具有更强势的理由,针对审查对象之理由进行审查判断。否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面对审查对象与针对审查对象之报告与说明时,无法基于内容做出恰当之判断,此时陷入平衡状态,合宪性之判断完全取决于决断之民主性。即判断权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过程便是研究、审议,研究、审议过程的实质内容便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审查对象内容之合宪性进行理解性解释,过程与实质内容的结合形成报告、说明,提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决断,完成最终行使合宪性审查权之表决、决定。
最后,合宪性审查权的逻辑结构。在霍菲尔德的基本法律概念中,权利是一种法律关系,而权力属于关于法律关系的关系。②参见[美]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2 页、第52-70 页。霍菲尔德的学生柯宾将“权力”进一步解释为主体A 改变其与主体B 或者主体B 与主体C 之间关系的能力。③See Arhur L Corbin,Legal Analysis and Terminology,Yale Law Journal,Vol.29,1919,p.168.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行使合宪性审查权时,意味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改变某种关系。因此,合宪性审查权是某种改变的能力,这也使得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不能以辅助机构的身份独立行使合宪性审查权。相对应的,审查对象的归属主体有责任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断之改变,即是说,改变之发生并非审查对象之归属主体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负有责任。质言之,合宪性审查权之判断权行使为合宪性审查权内部程序,具有内部性,不足以对抗审查对象,即不具备基于权威的决断力,仅具备判断之理由的说服力,为合宪性审查权的决断能力提供理由证成;而面向审查对象的决断权则是作为合宪性审查权的外观形式权力,吸纳内部之判断,构成整体之合宪性审查权,使得审查对象负有同合宪性审查权相对应的责任,具有外部性,足以对抗乃至压倒审查对象,具备的则是撤销、改变或发回—失效的决断力。
综上所述,合宪性审查权内部构造可以分为狭义合宪性审查权与合法性审查权,当前的宪定秩序下,狭义合宪性审查缺乏必要的实施制度环境,仍需要着眼并做好合法性审查工作。再者,为充分发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功能,并结合《职责决定》之授权,可以将合宪性审查权分为判断权与决断权。这一划分为合宪性审查权的内部构造,即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不具有独立对抗审查对象归属机关的外部性,需要借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决断权形成整体合宪性审查权,产生外部对抗的决断力,完成合宪性审查之形式化决定或表决工作。即总体而言,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并无独立开展合宪性审查之完整权力。一方面,充分尊重当前的宪定秩序与政治体制,协调好权源机关与实质审查工作操作机关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专业优势,沿着《决定》与《方案》明确的方向,推进合宪性审查,提升合法性审查的质量,进行充分的判断(研究、审议),提出报告与说明,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最终的决断权行使提供理由,构造完整的合宪性审查权。
四、结 语
宪定秩序下的合宪性审查权是合宪性审查展开的前提。只有析清合宪性审查权的性质才能使得合宪性审查的主体、机关、范围、对象、程序等问题得到明确解答,相反,混乱的权力性质界定很容易导致合宪性审查开展的名实不符。合宪性审查权本质上是对原有宪法监督权的重申,而非新设独立权力。因此,合宪性审查权并非修宪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背景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获得的宪定新权力。因为,当前的宪定秩序明确宪法监督权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必须依托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狭义的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但行使的权力内容为判断权,对审查对象进行过程的研究、审议,在内容上开展理解性的宪法解释,并提出报告、建议,权源主体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借助判断之理由进行权衡,最终进行决断(决定或表决)。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合宪性审查最具可操作性的仍是合法性审查部分。对狭义合宪性审查权部分,制度允许的空间更多的是做好事前草案的内部控制,防止明显违宪的出现。即当前主要着眼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合法性审查权,这既符合现行宪定秩序的要求,也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活力。对于狭义合宪性审查权,需要进一步进行理论探讨与制度构造,促进合宪性审查的有效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