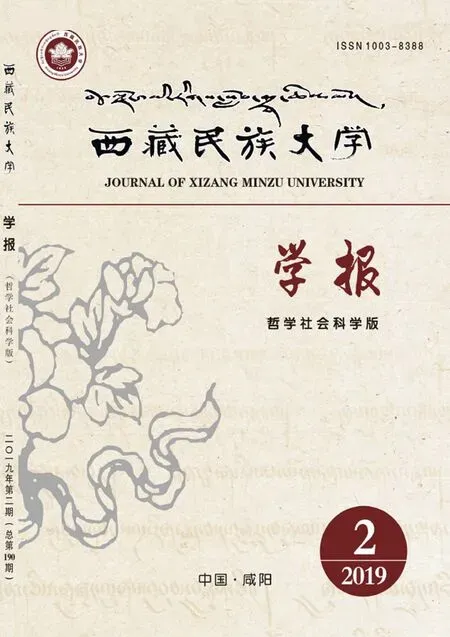“高原丝绸之路”路网结构的考古学构建与文化内涵
余小洪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陕西咸阳 712082)
21世纪以来,西藏西部的系列考古新发现,证明早在汉晋时期,绿洲“丝绸之路”已延伸至西藏西部地区,形成了“高原丝绸之路”,霍巍[1]、仝涛[2]、张云[3]等就这一问题已有论述。至唐代吐蕃时期,“高原丝绸之路”已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融为一体,并逐渐形成了许多次干道、支线。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图进一步讨论汉唐时期“高原丝绸之路”的路网结构及文化内涵等相关问题。
一、秦汉以前的高原通道
石器时代,西藏高原旧石器遗存与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已有联系;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曲贡文化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等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联系,形成了若干条高原通道,即东向甘青川滇地区、南向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区。这一时期的高原通道,霍巍[4] (P1-10)、吕红亮[5] (P65)等已有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公元前一千纪至公元前3世纪(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在西藏的中部、西部、东部、北部,都发现有少量考古遗存。在西藏中部,以拉萨曲贡遗址晚期石室墓为代表;在西藏西部,以格布赛鲁墓地、东嘎V区石丘墓遗存为代表;在西藏东部,以贡觉香贝石棺墓、昌都小恩达石棺墓、昌都热底垄石棺墓为代表;在西藏北部,以安多布塔雄曲M1为代表。西藏中部曲贡遗址晚期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等文物,反映了与川滇地区、欧亚草原地区的文化联系。西藏西部的格布赛鲁墓地的材料较为关键,该墓地于1999年进行了调查,采集到大量石器和带耳圜底陶器,简报推测其处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初;[6] (P39-44)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7年对该墓地进行了正式发掘,据夏格旺堆研究员在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举办的“2017年度公众分享会”上介绍,格布赛鲁墓地2017年度一共发掘了9座墓,墓内出有圜底带耳陶器、铜饰等,测年数据显示这是西藏年代最早的竖穴土坑石室墓,其早期墓的年代上限可能至公元前一千年。[7] (P11)从公布的少量出土物来看,其文化面貌总体上与1999年的采集品近似,反映了与周边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东嘎V区朗布钦石丘墓出土物较少,推测其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左右,东嘎V区M1出土的圜底小罐、单耳圜底钵在扎滚鲁克文化较为常见,故我们推测东嘎M1的出土物可能来自新疆南部扎滚鲁克文化或更早期的察吾乎文化。
近年西藏那曲地区文化局与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在西藏安多布塔雄曲墓地M1发现有1把无格铜短剑、1件铜钺形器、1件双耳陶罐,布塔雄曲墓地的测年数据为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约当中原的战国时期。[8] (P1-18)无格铜短剑,柄部无纹饰、缠绳,通长20余厘米,这种无格铜短剑在川西高原的茂县城关 DM7:1[9] (P377-380)、宝兴瓦西沟 M4:2[10]已有发现,形制完全相似,柄部缠绳的使用方式也相同。铜钺形器,在云南出土较多,[11]川西、藏北地区的铜钺形器当来自云南地区。布塔雄曲墓地出土的双耳陶罐,器表施一层黑色陶衣,这种形制的双耳罐也是川西高原地区“石棺葬文化”中常见的器物。[12] (P282-288)总体而言,西藏东部、北部的石棺墓遗存,与川西高原的石棺墓属于同一文化圈,文化性质相同或相近。
公元前一千纪至公元前3世纪,石器时代业已形成的东向、南向通道,仍在沿用;连接欧亚草原的北向通道,初见端倪。故,在秦汉以前,西藏高原可能业已存在东、南、北三条高原通道。
二、“高原丝绸之路”的凿通与发展
根据考古发现,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汉唐时期的“高原丝绸之路”,经历了初创、形成、繁荣三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
公元前3世纪—公元1世纪(约当秦、西汉至东汉初),在西藏西部、东部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考古遗存。西藏西部,以皮央墓地和曲踏墓地II区墓葬[13]为代表;西藏东部,以边坝草卡墓地、洛隆柔旺卡墓地[14] (P200-241)为代表。
在西藏西部皮央墓地和曲踏墓地II区墓葬,墓葬形制较为丰富,有带竖穴墓道洞室墓、竖穴土坑墓、石丘墓。流行二次葬和丛葬,以编织物、石“尸床”、箱式木棺为葬具。墓内流行动物殉葬,偶见殉马坑。墓内出土物较为丰富,陶器全为圜底,无平底器;耳、流发达;绳纹较为发达,稍晚时期刻划纹增多,出现彩绘;流行浅腹圜底小罐、喇叭口圜底罐、侈口高领圜底罐、带流罐,陶器特征明显、组合清晰、形制演变规律较为清楚。墓内流行竹木器,有木腰牌、箱式木棺、木案、木桶、纺织器、木弓等。本地区出土金属器数量不多,但特征鲜明,以双圆饼首铜剑最具代表,此外还有少量圜底铜盆、徽章形带柄铜镜、铁剑、铁镞、铁马衔、铁带扣、木柄铁锥、铜珠、铜镯等。这一时期,西藏西部和塔里木盆地扎滚鲁克文化B群晚段遗存(包括扎滚鲁克一号墓地西汉时期的M14、M27、M54等[15]、扎滚鲁克二号墓地[16]、山普拉西汉晚期墓[17] (P2)等)都使用洞室墓,葬具种类都包括编织物、尸床、木棺,墓内都盛行殉牲,墓地都有专门的殉马坑。西域地区常见的竹木器大量传播至西藏西部地区,两地都流行圜底陶器、珠饰,两地都出土少量徽章形带柄铜镜。反映了两地文化交流较为频繁。
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公元前3世纪—公元1世纪时期的皮央格林塘墓地,出土双圆饼首铜剑(PGM6:4)一把,其最显著的特征为剑柄首为两个双圆饼,通长30厘米,剑身长20厘米、剑柄长10厘米,扁茎,“山字形”剑格,剑格上饰鎏金三角形纹和小点纹。这类铜剑比较少见,不过在川西盐源老龙头墓地[18] (P70)、内蒙古等地已有发现[19] (P437-447)。2018年,四川大学考古队在西藏阿里新发现了四川汉代铁三脚架,进一步说明了西藏西部与四川地区的紧密联系。
西藏东部边坝草卡墓地、洛隆柔旺卡墓地出土的菱口漩涡纹双耳罐,与川西高原吉里龙文化晚期遗存(汉代)的双耳罐如出一辙。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西藏高原与川西高原的文化联系。
这一时期,西域塔里木盆地已开始出现丝绸、汉式铜镜、漆器等典型汉文化器物,说明绿洲“丝绸之路”已凿通,考古发现与史籍记载相符。西藏西部的发现,说明绿洲“丝绸之路”已开始向高原延伸。西藏东部石棺墓遗存延续了早期的文化传统,与川西高原石棺墓处于同一文化圈,川西高原与藏北、藏西地区的具体交通线路,较早期更为清楚。这一阶段,当为“高原丝绸之路”的初创阶段。
(二)形成阶段
公元1-5世纪(相当于东汉至魏晋时期),在西藏西部、东部发现了一批考古遗存。西藏西部,以故如甲木墓地[20]、曲踏墓地I区墓葬为代表。西藏东部的边坝冬卡都、冬玛通石室墓[21] (P239),可能早至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西藏西部的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石室墓、洞室墓两类。墓内流行单人葬、合葬;葬式多为侧身屈肢葬;葬具有长方形四足箱式木棺、石尸床、编织物等。墓内流行动物殉葬,还可见独特的墓内立石遗存[22]。墓内出土物较为丰富,陶器大幅减少,仅见数件平底杯,为冥器。竹木器也大幅减少,出土有方形四足彩绘木案、纺织棒、素面箱式木棺等,还有少量圆形漆盘、漆木奁。金属器增多,尤其是青铜容器的数量和种类突然大幅增加,有平底铜盘、曲柄铜釜、壶、铜勺、铜单耳杯、铜碗、铜钵等,还出土有汉式一字格铁剑、铁箭镞。此外,还出土大量丝绸,少量料珠、茶叶。与塔里木盆地扎滚鲁克东汉墓、山普拉晚期墓、尉犁营盘墓地[23]、洛浦比孜里墓地[24]等考古遗存的文化内涵相同或相近。两地都依旧使用洞室墓、竖穴土坑墓,葬具种类都包括箱式木棺、尸床,墓内都盛行殉牲。都出土大量丝绸、汉式一字格铁剑、漆器,说明在这一时期,绿洲“丝绸之路”深入影响至西藏西部。
西域地区在这一时期,已出现汉式陶器、汉式铜镜、汉式弓矢、花押,漆器也开始在本地生产,说明汉文化已在各方面深入影响到西域地区。而西藏西部尚不见这些器物,说明汉文化在西藏西部尚未本地化。这一时期,西域地区仍在使用大量竹木器,而西藏西部出土竹木器数量不多,代之以青铜容器。青铜容器内还出土有在这一时期较为罕见的茶叶,霍巍认为这些青铜容器可能是熬茶器皿[25],本文同意这一看法。有学者认为西藏西部的青铜器可能与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有关[5] (P65),这一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西藏西部出土的这些青铜容器,也有可能来自其他地区。从青铜容器的形制来看,较为大型的平底铜盘、曲柄铜釜、壶,与汉代关中、西南地区的同类铜器较为接近,尤其是带柄的青铜容器,在汉代较为常见。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些青铜容器与汉代青铜容器并不完全相似,应是经过改造之后,再传入西藏西部。
藏东边坝冬卡都石室墓与炉霍城西石棺墓都出土甚为少见的海螺,其文化内涵相近;滇西北德钦永芝采集的带流单耳罐,在西藏腹地山南、拉萨较为常见,在藏北安多芒森也有出土。这一阶段,可视为“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阶段。
根据前文的分析,不难勾勒出一条战国至汉晋时期,从川西高原经过怒江或澜沧江通道,到达藏北安多,再延伸至西藏西部的通道。这条“西南丝绸之路”[26]也促进了“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发展。我们认为,西域至西藏西部、川西高原至西藏西部这两条通道,在西周、春秋战国至汉晋时期是并存的,两条通道对“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繁荣阶段
吐蕃时期(中原唐代),吐蕃与唐等周边地区的交流十分频繁。伴随着吐蕃对外军事扩张、唐蕃和亲、蕃尼和亲等系列活动,吐蕃时期的古城古堡、摩崖石刻、石窟壁画、金石碑刻文书、墓葬等文物考古遗存,广泛分布在西藏及四川甘孜,青海玉树、海西,甘肃敦煌、张掖,新疆南部,不丹,巴基斯坦北部等地。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既包括物质文化交流,也包括典章制度、宗教信仰所代表的精神文化交流。这一阶段,可视为“高原丝绸之路”的繁荣阶段。
三、“高原丝绸之路”的路网结构
秦汉以前的高原通道,大致有东线、南线、北线三条。石器时代的通道,主要是南线:甘青川滇地区—西藏中部—尼泊尔;和北面的欧亚草原地区,可能也已有间接联系,具体通道尚不清晰。两周至战国时期的通道,主要是东线:川西甘孜—藏东贡觉、昌都—藏北安多—藏西;北线可能已存在:塔里木盆地—西藏西部,但中间环节尚不清楚。“高原丝绸之路”的路网结构,即在此基础上形成、延伸。
(一)初创阶段
公元前3世纪—公元1世纪(秦、西汉至东汉初),是“高原丝绸之路”的初创阶段,有三条线路。
北线:西域叶城/于阗—拉达克(今克什米尔列城)/喀喇昆仑山—西藏西部。此条线路在早期可能业已存在,在这一时期,这一交通线路逐渐清晰起来;
东线:川滇——藏东边坝、洛隆——藏北安多——西藏西部;
南线:尼泊尔木斯塘—西藏西部。
(二)形成阶段
公元1世纪—5世纪(东汉至魏晋时期),是“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阶段,有三条线路。
北线:西域叶城/于阗—拉达克(今克什米尔列城)/喀喇昆仑山—西藏西部;
东线:川滇—藏东边坝—西藏中部/藏北安多—西藏西部;
南线:尼泊尔—西藏西部。
关于西藏西部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的通道,仝涛提出拉达克是两地的中间环节,[2]笔者还提出了两地通过喀喇昆仑山的山间小道直接来往的可能性,[27]霍巍也认为可通过喀喇昆仑山直接往来。实际上,“高原丝绸之路”的初创、形成阶段,也应该存在西线,不过目前缺乏经过系统发掘的考古证据,我们暂且不论。
(三)繁荣阶段
唐代吐蕃时期,是“高原丝绸之路”的繁荣阶段,有东、西、南、北四条干道。
东线:即后世所称的“唐蕃古道”[28] (P1-175),包括主干道、南北干线及各条支线。[29]主干道即文献记载的官道,大致线路为:长安(西安市)—临州(临洮县)—兰州(兰州市)/河州(临夏市)—鄯州(西宁)—截支桥(玉树市)—閤川驿(那曲县)—逻些(拉萨市)。[30]还有南、北两条干线。北干线,指鄯州(西宁)到沙州(敦煌)的道路。包括两条支线,其一,鄯州(西宁)—甘州扁都口(张掖民乐)、肃南—到沙州(敦煌)。其二,鄯城(西宁)—赤岭(湟源日月山)—都兰—沙州(敦煌)。南干线,指玉树经藏东到拉萨的线路。大致线路为:玉树—四川石渠、炉霍、道孚—昌都察雅、芒康—工布江达—林芝—逻些(拉萨)。包括三条支线:其一,逻些(拉萨)—吐谷浑或党项(甘青川交界地区)—白兰(青海玉树/果洛、四川阿坝)—松州(四川松潘);其二,逻些(拉萨)—“多康六岗”(西藏昌都)—截支桥(青海玉树)—“邓”(四川石渠)—炉霍(四川炉霍)—道孚城堡(四川道孚)地区。其三,逻些(拉萨)—林芝—工布江达—西藏察雅、芒康—江达—四川石渠—青海玉树。[29]
实际上,唐蕃古道与丝绸之路多有重合,唐蕃古道主干道东段与丝绸之路陕甘段基本重合,唐蕃古道主干道西段向西南延伸,与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相接。唐蕃古道北干线,主要沿祁连山北麓地带铺开,与丝绸之路中国段北线重叠。唐蕃古道南干线与“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也多有重叠。
南线:拉萨—吉隆—尼泊尔—印度。西藏西南部(日喀则市)发现的查木钦吐蕃墓地[31] (P105-124)、吉隆王玄策“大唐天竺使出铭”[32]等考古遗存,以及古籍文献的记载,反映了吐蕃、唐与南亚地区的交通通道。故“高原丝绸之路”,也是“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线:拉萨—藏北/藏西—西域。吐蕃在西域曾统治过一段时间,直接参与绿洲“丝绸之路”的经营与管理。[33]并在米兰[34] (P1-150)、尉犁咸水泉古城[35]等地留下了珍贵的古藏文简牍文书。
西线:拉萨—西藏西部/西域—中亚(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吐蕃征战西域及中亚地区[36] (P1-120),留下巴基斯坦吐蕃碑刻[37]、喀喇昆仑南麓沿线吐蕃石刻等[38] (P88-136)。
经过初创、形成两阶段后,在繁荣阶段,“高原丝绸之路”最终形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路网结构。
四、“高原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流的内涵与层次
“高原丝绸之路”沿线的物质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不仅于此,还包括了大量精神文化交流的内容,体现出文化交流的不同层次性。
(一)“高原丝绸之路”沿线的物质文化交流
初创阶段,与西域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以“S”纹木牌、木梳、木盘等竹木器为代表。与尼泊尔木斯塘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以黄金面具、竹木器、珠饰等为代表。与川滇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以双圆饼首铜剑、铜钺形器、无格铜剑、球腹双耳罐等为代表。
形成阶段,与西域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以丝绸、箱式木棺、漆器、汉式铁剑等为代表。与尼泊尔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以黄金面具、箱式木棺、竹木器等为代表。与川滇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以漩涡纹菱口双耳罐、单耳带流圜底罐、青铜容器、“茶叶”类植物等为代表。
繁荣阶段,与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已脱离单纯的物质文化交流,吐蕃从各方面吸纳周边地区的文化。与西域乃至中亚地区,接纳逃难的于阗佛教僧人[39] (P48-63);吐蕃在制度上还曾学习过突厥的管理制度[40] (P60-67),其中吐蕃王冠与突厥王冠较为相似[41] (P81-88),进一步说明吐蕃在制度上也曾吸纳过突厥的制度文化。与尼泊尔及南亚地区,通过联姻、征战、迎请等方式,带入了佛教(经书、雕塑)[42] (P22-30);一般认为,在松赞干布派吞弥·桑布扎前往古印度学习梵文,并在此基础上创制的古藏文。[43] (P1-50)与唐代中原地区,通过和亲、征战等方式,全面学习中原的典章制度、政治体制、宗教、文化、艺术、军事等各方面。[44] (P45)
(二)“高原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流的层次
从文化交流的层次来看,既包括物质文化层面,还包括思想、观念层面上的精神文化交流。以物质文化交流为主体,在物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也能反映出部分精神文化交流的问题。物质文化交流,可能是通过贸易、交换、赏赐、进贡、战争等手段达成,层次较低。精神文化交流,主要通过思想、文化的传播而达成,层次较高。
关于“高原丝绸之路”沿线的物质文化交流,前文已述。在此,我们着重讨论“高原丝绸之路”沿线的精神文化交流。汉晋时期,西藏西部与西域地区在精神层面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两地都使用洞室墓,可能是为模仿墓主生前的居住空间,墓内布局往往有规划;
2、两地都陪葬食物,当是模仿墓主生前的生活情景,希望墓主逝后也能享用;
3、两地都盛行动物殉葬,墓地还有专门的殉马坑,可能反映了墓主和动物间息息相依的亲密关系;
4、两地都可见使用各种材质(棉麻、丝绸、金)的“覆面”[45],可能代表了灵魂升天的观念;
5、两地都流行各类尸床(编织物、石板、木架)、木棺(原木、箱式)作为葬具,没有葬具的墓葬较少,可能反映了对墓主遗骸放置空间的重视;
6、两地都出土木腰牌,腰牌的用途或与墓主的身份、地位有关,或与墓主的族属有关,抑或仅仅是一种装饰品;不过腰牌在西藏西部,都出自高等级墓葬中,故我们认为腰牌与墓主的身份和地位有关,腰牌当是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或是作为一种“威望物”,在两地间流传。
前文提及了反映西域与西藏西部两地间思想、观念层面文化交流的六个方面,如果放在整个欧亚草原文化的框架中来看的话,除第五、第六点之外,其他几点可能是欧亚草原地带人群的共同文化特征。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其相似的生态环境、生计方式密切相关。故而我们讨论西藏西部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在上述地区,我们还应注意到西藏西部与整个欧亚草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吕红亮在关于西藏岩画[46]、立石遗迹[47]的研究案例中为我们做了比较好的示范。正是由于欧亚草原地带文化面貌的趋同性,更要求我们必须具备细致入微观察的敏锐视角,以捕捉最能反映不同族群间确有进行深入层次文化交流的痕迹,如前文提及的第五点,两地在各个阶段使用的葬具都近似,异于周边地区其他文化的葬具,这当是两地人群在思想、观念方面深层次文化交流的例证。如上述第6点中提到的出土的腰牌,反映了两地上层社会间的思想文化交流。
汉晋时期,川滇地区与西藏地区更多的是少量“奢侈品”的交流,目前我们还找不到属于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交流痕迹,文化交流的层次较低。实际上,如果我们将墓葬作为一个“文化综合体”来看的话,西藏西部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远比与川西高原的联系更为紧密。从文化交流的途径来看,西藏西部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更为直接,中间环节较少(拉达克地区属于广义上的西域地区);西藏西部与川西高原的文化交流,需要数个中间环节才能达成,当是间接的文化交流。
唐代吐蕃时期,吐蕃和周边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以宗教信仰、典章制度为代表的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交流,更是深入影响到吐蕃社会的各个方面。关于这一点,前贤著述非常多,本文无须赘述。
不难看出,在汉晋时期,西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以“奢侈品”为主的物质文化交流层面,不过西藏高原与广义上的“西域”地区,已有少量精神层面的文化交流。进入唐代吐蕃以来,西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是全方位的,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其与南部尼泊尔、东部中原地区的精神文化交流,迄今仍对西藏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五、结 语
汉唐时期的“高原丝绸之路”,是在石器时代以来业已形成的高原通道上发展而来的,经历了初创、形成、繁荣三个阶段。在初创阶段,形成了东、南、北三条通道,以北向“西域”的通道最为清晰。在形成阶段,仍是东、南、北三条通道,东向通道的线路逐渐清晰、完善。在繁荣阶段,形成了东、西、南、北四条通道,“高原丝绸之路”的路网结构完全形成,其东向通道——“唐蕃古道”最为发达,也最为清晰。
“高原丝绸之路”沿线的文物考古遗存,不仅反映了西藏高原与“高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频繁的物质文化交流,也反映了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交流。“高原丝绸之路”的初创阶段,西藏西部地区与西域地区除了较为频繁的物质文化交流之外,在葬制葬俗等六个方面的相似性,可能还代表了两地间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交流。在排除欧亚草原文化的共同特征之后,我们认为墓主使用的葬具,和作为身份象征或作为“威望物”的木腰牌,最能体现两地间在思想、观念方面的文化交流。“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阶段,已开始本土化的西域汉文化对西藏西部仍保持着有一定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物质文化层面的交流,思想层面的文化交流似已减少;这一时期,以青铜容器、茶叶为代表的汉文化,通过川西、藏北高原,也可能已影响至西藏西部地区。来自西域和川西高原两个方向的双重影响,最终促成了“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唐代,“高原丝绸之路”进入繁荣阶段,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交流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与南部尼泊尔、东部中原地区的精神文化交流,迄今仍对西藏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