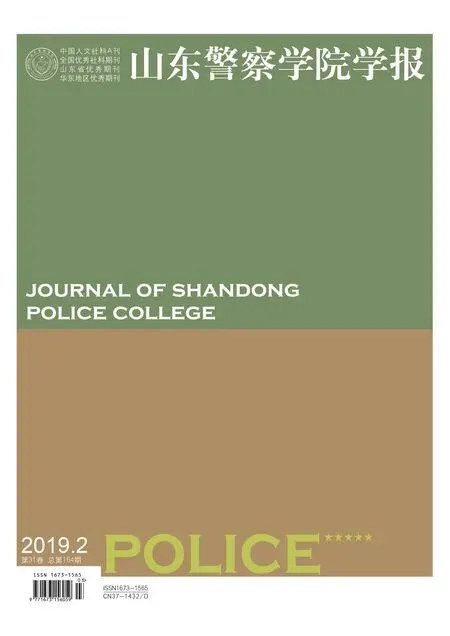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制度逻辑研究
陈 卓
(浙江警察学院社会科学部,浙江 杭州 310053)
作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典范,“枫桥经验”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制度的运行体现出一定的逻辑,制度逻辑取决于场域中各种制度要素所占的比重以及彼此之间的作用过程。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审视“枫桥经验”,需要对制度要素进行分析,尤其是新制度主义所关注的制度的文化—认知性要素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区分了文化资本的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1]以此为基础,可以区分出3种治理形式:具体化的治理、符号化的治理和制度化的治理,它们分别强调嵌入性的文化形式、文化的语义符号性和制度框架制约下的文化。通过对上述3种治理形式的分析,可以更为深入地把握“枫桥经验”的制度逻辑。
一、具体化的治理:嵌入性的文化形式
所谓制度的认知—文化性要素,首先指的是嵌入性的文化形式,它与文化资本的“具体的状态”密切相关。“比起那些我们常常视为文化的较柔软(或更‘鲜活’)的领域来,这是一种凝结的文化,不太需要人们的维护,不太需要通过仪式来巩固,也不太需要用符号来阐释。”[2]嵌入性的文化形式启示人们: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当关注制度所处的现实环境,以及制度运行所遵循的实际法则。它强调的是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枫桥经验”迄今为止已发展到第56个年头,期间虽有起伏,但总体上一直持续发展。制度变迁的过程摆脱不了路径依赖,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被赋予新内涵新价值新生命的同时,也无法彻底摆脱历史习惯、传统文化等诸多要素的作用。这些要素以文化观念等形式,深深地嵌入每个具体行动者的观念和行动之中。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嵌入性的文化形式强化了场域中各类行动者的角色意识和主观感受。审视“枫桥经验”可以发现,嵌入性的文化形式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主要通过文化资本和卡里斯马权威体现出来。
(一)文化资本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诸多关于“枫桥经验”的研究都十分强调枫桥的历史积淀、传统文化、乡约习俗的作用,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文化—认知性的制度要素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枫桥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人文积淀,不仅历代有名人志士光顾,而且在近现代也散发着浓厚的革命气息。枫桥人秉承了古越人“崇尚刚果且民性质直”的品质,率真倔强、果敢利索,敢为天下先。近年来,枫桥在社会治理方面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精神实质,有效培育了具有乡土精英性质的基层社会自治力量,基层社会自治力量在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枫桥镇成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精心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社会活力,充分发挥他们在参与矛盾化解、治安巡逻、社区矫正、公益慈善、为民服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规范管理,加强引导,确保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3]嵌入性的文化形式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断强化着社会场域中各类行动者状态化的体验。鉴于此,之前许多研究关注法治与传统的冲突与融合,在此基础上,最近研究者逐渐聚焦于自治、法治与德治“三治融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文化资本是一种“非正式的人际技术、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程度、格调与生活方式”[4],就其运作机制而言,美国学者希恩(Edgar H.Schein)提出了三层次文化模型,将文化分为“人工制品”(Observable Artifacts)、“信仰与价值”(Espoused Values)和“基本隐性假设与价值”(Basic Assumptions)3个层次。[5]作为“枫桥经验”一大亮点的调解机制很好地体现了文化资本的作用机制。枫桥的调解中心墙壁上挂着很多标语,这属于希恩所说的文化的“人工制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的物化形式。标语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枫桥经验”自身的制度逻辑:在具体的调解过程中,显在的规则不是必须遵循信奉的对象,而是可以选择、利用的资源。这才是“枫桥经验”中的“基本隐性假设与价值”。在这样的逻辑下,调解中灵活运用的各种政策、民意、习惯、法律、村约等,都不过是一种服从和服务于化解矛盾和社会治理的资源。[6]这种制度逻辑下的社会治理“不需要内化、自我奖赏或其他干涉过程,就可以确保文化的持续,因为社会知识一旦被制度化为一种事实,作为客观实在的一部分而存在,就能够在此基础上直接扩散开来”。[7]从这个意义上说,“枫桥经验”很好地体现了“基本隐性假设与价值”在文化系统中的重要作用。
(二)有效的社会治理与卡里斯马权威有着密切关系
在“枫桥经验”的实践过程中,嵌入性的文化形式往往与卡里斯马权威(又叫超凡魅力型权威)联系密切。作为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韦伯(Max Weber)区分了正当支配的3种纯粹类型:法理型权威、传统权威和卡里斯马权威。对卡里斯马权威而言,服从的对象是被证明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本人,凡是他的启示、他的英雄品质、他的典范特性影响所及,相信他的超凡魅力的人们就会因此而服从。[8]枫桥镇推出以派出所民警杨光照命名的“老杨调解中心”,就是卡里斯马权威的典型代表。“老杨调解中心”负责人杨光照具有诸多形成卡里斯马权威所需要的品质:办事公正,工作从不讲条件,具有高度的耐心、韧心和信心,用真情换真心。对待普通群众,老杨总是坚持以诚相待,热情相帮。在老杨担任过责任民警的辖区内,老人、青年、妇女甚至学生都乐意对老杨掏真心话,他们把老杨看作自己的亲人、朋友、长辈和师长,有事无事都喜欢找他聊天。老杨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不是“威严的警察”,而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干部;老杨在平安治理的过程中不仅赢得了群众的赞誉,更得到了群众亲人般的关照和爱护。如今,退休7年来,仍每天起早摸黑,奋战在化解矛盾的主战场,成功调解矛盾纠纷1000多起。2014年,“老杨调解中心”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杨光照也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9]如今,退休后的杨光照仍在负责“老杨调解中心”的工作,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注]与“老杨调解中心”(之前名为“老杨调解工作室”)相类似的还有“老蔡调解工作室”。“老蔡”名叫蔡福宇,曾担任中共三门县沿赤乡沿江村支部书记10多年,熟悉乡里乡情、纠纷调解内行,群众威望高、办事公道,富有治安工作热情、具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处事能力,在农村是一个“吃得开”的干部,也是一位具有卡里斯马权威的调解能手。他实实在在为民解难,真真切切贴近群众,扎扎实实筑牢防线,替群众说话,为群众办事,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参见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员会,浙江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枫桥经验”在浙江[M].(内部发行),2009.125-126.由此可以看到“枫桥经验”中涌现出来的这些典型人物在知识能力和道德品性方面具有诸多共同点,符合长期以来群众心目中的优秀共产党员“认真、包容、实干”的形象。
老杨的事迹的确令人感动。然而,卡里斯马权威天生就是不稳定的。秉持者可能会丧失他的超凡魅力,或者被他的追随者认为“他的力量已经耗尽”。[10]当被问及什么时候真正退休时,杨光照回答:只要有人需要我,身体条件允许,就会一直干下去。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老杨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虽然“老杨调解中心”会继续存在,但后继者是否有足够的魅力继续擦亮这块“金字招牌”,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杨光照本人坦承调解工作中的困难:村里有些群众对村干部不信任,认为村干部倾向一方,不公平,村干部自身可能会有倾向性;有些村干部责任心不够强,素质有待提高,要有服务群众的心,需要宽容,能够受得了气。[11]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政治与经济需求的满足日益理性化,规范、制度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中发挥着作用,这种普遍现象越来越多地限制了超凡魅力,也限制了构成个体差别的行为的重要性。一方面,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卡里斯马权威的作用;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治理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的趋势已势不可挡。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整合历史文化资源,提炼升华传统的卡里斯马权威要素,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二、符号化的治理:文化的语义符号性
除了嵌入性的文化形式作用下的具体化的治理,制度的文化—认知性要素还关注文化的语义符号性层面,它对应于布厄迪尔所说的文化资本的“客观的状态”和希恩所说的“人工制品”。在这里,文化不仅被视为主观的信念,也被感知为客观的、外在于个体行动者的符号系统。“事实上,任何人类制度都是意义的沉淀,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都是意义的结晶化和客观化。”[12]“在这种认知范式中,作为被创造者的人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此人对其环境的内在表象的一个函数。”[13]从这个意义上说,“枫桥经验”提供的社会治理经验又是一种典型的语义符号性的表现形式。
(一)符号化的治理体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符号学家沃洛辛诺夫(Valentin Voloshinov)建立了符号学和意识形态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没有符号,就没有意识形态……一切意识形态性的东西都具有符号价值。”[14]具体而言,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语言,都不可能被看作独一无二的一套意义或文本,以一种绝对的方式自上而下强加;相反,社会的特点是斗争、冲突以及不断进行着重新协调的关系所赋予的,而且符号活动以其典型的形式反映出这个过程。“枫桥经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和重要的意识形态价值。这种意识形态融合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面的历史积淀,以及当前特定国内外形势和社会发展状况,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时代话语下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影响遍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枫桥经验”往往被视为社会自治的典范,然而,多数场域都重视报酬和激励的作用,以此来鼓舞行动者的士气,保持组织稳步前进。物质激励显然有它的价值,但它们并不能真正成为社会自治的黏合剂。圆满达成工作目标固然非常关键,有了一两次成功之后,人们对自己、对自身力量的看法都会不同;但是有的场域由于资源相对匮乏,无法长期提供足够的报酬,因此它要取得成功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物质激励。对社会治理而言,为了维持组织的存在,实现长期目标,它必须考虑个人发展问题,必须有一种超出个人利益、能给人以目标感的意识形态。[15]它还必须致力于提高群众的知识、尊严和自信,让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属于一项更大的事业。[16]鉴于此,强调社会资本的治理主体(政府机构)重视“枫桥经验”的同时,以浙江菲达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富润控股集团为代表的一些强调经济资本的企业也积极投入“枫桥经验”的学习和推广之中。
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不仅体现了管理学意义上的价值,还发挥着社会学、文化学方面的功能。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几乎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枫桥经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因而符号化的治理逻辑在整个社会治理谱系中的地位就显得十分突出。所以,社会治理中管理者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创造出一种和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与明确的要求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新意识,一种具有进步倾向的反对意识。历史学家鲁德(George Rudé)指出,就所有成功实现社会改造目的的社会运动来说,它的意识形态都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流行的、指向内在的意识形态,它扎根于民众的各种传统中;另一个是派生的、主要指向外部的意识形态,以使运动所关注的问题能和超出个人经验的那些力量和事件联系起来。[17]一个强调社会习俗,一个强调时代脉搏,两者共同为抵抗和反叛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基础。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为“枫桥经验”的不断创新提供了正当性,并起到了动员并维系群众参与的作用。“枫桥经验”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内涵更新和转型升级,就是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对社会习俗的回应。
(二)文化的语义符号性从两方面发挥作用
典型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经验。“枫桥经验”从产生开始就已经成为全国先进典型,自始至终引人注目,作为全国学习的榜样,直至今日,仍光芒不减,风采依旧。通过符号系统所传播的文化意义具有不同时间或抽象层面的内涵,也就是不同的意义世界。[18]“枫桥经验”以其无可争议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成就将符号化治理的象征性作用发挥到相当高的程度,在社会治理的实际过程中则具体围绕“枫桥经验”的“群众性”展开,在正反两个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枫桥经验”作为“群众性”的象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03年、2013年两次针对“枫桥经验”的指示批示中,均强调群众性。郭声琨同志也提出,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也是“枫桥经验”50多年来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新时代,要把握好“枫桥经验”的精髓。[19]在很多人眼里,“枫桥经验”对于社会治理的最大启示就是“群众性”,“枫桥经验”甚至成为了“群众性”的同义语。首先,理论研究上,为了群众是“枫桥经验”的出发点,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支撑点,服务群众是“枫桥经验”的归宿点。[20]其次,在实践探索中,不少地方学习创新“枫桥经验”是围绕群众性展开具体工作的。在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突出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参与意识方面,出现了诸暨的“村务简报”、绍兴县的“夏履程序”、嵊州的“八郑规程”、新昌的“乡村典章”、上虞的“警示公约”等一批典型。[21]作为一种象征着“群众性”的文化符号,“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另一方面,“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可能导致符号化治理的负面效果。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确立了符号系统中“能指”与“所指”相分离的原则,并指出制约符号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符号的任意性。[22]“能指”与“所指”的分离以及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导致“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若干偏差和问题。首先,“枫桥经验”有可能成为少数群众满足个人利益、规避法律责任的借口。枫桥派出所的一位在职民警A在访谈中说:“在日常工作中,有的老百姓觉得民警办案时间长,有拖延的嫌疑,就会对民警发脾气:‘还说有枫桥经验呢,这点事情还办不好!’对此,不同民警处置方式不同,有的民警会进行解释,有的民警知道解释无效会不吭声了。”民警B谈到他处理的一起妨碍执行公务案件:民警查酒驾时,当事人不配合,其亲属也参与阻挠民警执法,有拉扯行为发生,并帮助当事人逃逸。几天后当事人主动来派出所,在传唤其他参与阻碍民警执法的人员时,有群众说:“枫桥经验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点事何必还来抓人呢?!”“枫桥经验”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所谓“矛盾不上交”,决不是所有的矛盾都不上交,不管矛盾性质、对象如何,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并不符合法治精神。对于触犯刑律的,就要依法打击;对于必须由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来处理的,就要依法由这些专门机关和部门来处理。[23]但对一些群众而言,“枫桥经验”可以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代名词,至于“化解”的方式手段是否合法合理,则往往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这恐怕是“枫桥经验”的创造者、命名者、宣传者、倡导者,以及大部分枫桥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然而,这就是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部分群众直观而又片面的认识,是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真问题。其次,符号曲解容易造成管理上目标与手段的倒置。“先进”光环下的枫桥似乎时时刻刻充满了典型激励力量,“枫桥不能出事”,这是从上到下各级政府人员甚至是部分群众的共识。这就导致同样一件矛盾纠纷或刑事案件,发生在枫桥和发生在其他地方,其影响力和象征性作用是大不相同的。由此带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枫桥的干部有“保典型,怕出事”的思想。换言之,“枫桥经验”鼓励了信访这种行政手段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承担者的非法治倾向。[24]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度符号化的社会治理有可能发生本质上的异化,它并没有消减或者消除不稳定因素,反而在“保典型”的指导思想下破坏了法制和规则,损害了社会公正,酝酿着新的、更大的不稳定。
三、制度化的治理:制度框架制约下的文化
综上所述,一方面,符号以及符号系统在展开文化秩序上具有承载的关键性角色,宗教、艺术和科学等所构成的文化现象也必须借助符号以及符号系统来揭示;另一方面,承载文化意义世界的符号以及符号系统在朝向文化现象的具体化过程中,必然地涉及所谓的制度化。文化通过符号化的过程在社会当中被建构,并且也通过符号的过程在社会当中被维持。[25]制度赋予社会关系以秩序,减少行为中的机动性和可变性,并限制了片面追求私利或欲望的可能性。[26]现代社会治理从根本上说就是制度化的治理,制度化的治理包含了制度的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三者缺一不可,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制度化的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与归宿,它强调的是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体制的状态”。
(一)传统社会中制度对文化的制约作用
社会治理最直接也是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社会场域内各类行动者的行为,它往往包裹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与之相比,制度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换言之,在强调“文化传统”、“本土资源”的同时,人们很容易忘记“认知—文化”关系的发生机制其实受到各种制度框架的制约。当前“枫桥经验”探索和研究中的一个特色是强调乡贤调解,有研究者总结了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中乡贤文化的4个方面的功用,并认为制约乡贤调解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礼法思想和道德伦理”[27]。这种试图在文化—认知领域寻找破解之道的想法固然善良,但也难免失之于浪漫。其实,无论是在体制层面还是在技术层面,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情况都存在一定出入。
首先,在制度层面,中国传统基层社会并非和谐自治的小共同体。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农民战争”机制是“乡村和谐论”无法解释的,只有放到“儒表法里”和“法道互补”的制度框架中,对传统社会的理解才可能客观、全面和深入。实际上,哪怕是从历史传统、文化习惯上说,“民本主义是传统社会的一种理想,而远不是一种现实。相反,官本主义则是一种客观实在,是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践形态。”[28]这也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理念与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治理观之间的本质区别。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当时的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不可能以人(民)为本,更不会“以人民为中心”;相反,这种“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的制度维护的是专制王朝“一家一姓”之私利,“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实则为一种常态。这与“枫桥经验”的价值倡导和现实做法都是背道而驰的。有研究者批评目前许多基层干部并没有真正领会“枫桥经验”的实质内涵,所以在实践“枫桥经验”过程中,仅重视工作载体、信息平台和制度考核等外在形式,忽视入情、入理、入心地做群众工作的内在方法。[29]实际上,这种现象也属于一种“文化”,是脱胎于中国传统历史,并与当前的基层干部任命、日常管理和考核等一系列制度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这是需要反对和扬弃的部分。
其次,就技术层面看,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在“枫桥经验”的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村规民约中的自治性与合法性冲突,该冲突如不加以解决会影响到社会治理的效果。[30]具体而言,一方面,村规民约中部分习惯内容成为引发新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村规民约在实践运行中存在若干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剔除源自传统的文化—认知性要素中与现代民主法治社会格格不入的内容,使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承认,“非正式规范是多元规范结构的支撑”,但同时也要看到,“正式规范是多元规范结构的基础”,“国家法律等正式规范在乡村治理规范系统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他规范均应以正式规范为基础展开,不得与正式规范相冲突,这也是解决规范冲突的基本原则。”[31]就制度的文化—认知性要素而言,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和本土资源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是“枫桥经验”的一大亮点;与此同时,也需要防止以“传统”、“文化”为名对公民权利进行侵害。创新“枫桥经验”需要按照合法、规范、实效原则修订完善村规民约,这就涉及到制度化地整合表达利益诉求、化解矛盾冲突的途径和方法。
(二)以法治化思维和制度化建设推动社会治理
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认为,制度可以界定为工作规则的组合,在现实社会中制度的构成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具体看可以分为操作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和宪法选择规则。[32]为了避免操作规则演变成贬义的潜规则,从而与正式法律制度中的法理权利和义务相对立,有必要强调宪法选择规则的重要作用。宪法选择规则一方面具有制度的规制性要素强调的强制作用,另一方面还体现了法律上的最高权威。在逻辑上,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也是衡量一切宪法价值包括自由、效率、秩序的基本尺度。[33]奥斯特罗姆之所以没用“法律选择规则”而用“宪法选择规则”,应当是为了通过突出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地位来强调宪法选择规则的根本性作用,而宪法选择规则的根本性作用又主要是通过对权利的保障得以体现的。因此,对正式组织制度化过程中的规则的分析,便从逻辑上演化为对权利问题的关注。确立和遵守宪法选择规则,就是要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
如何看待和处理维权与维稳的关系,这是当前以法治化思维和制度化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不管研究者对“枫桥经验”发展阶段作何种概括,“枫桥经验”定位于“维稳器”这一角色,在今天社会治理过程中并没有过时,其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有目共睹。从总体上看,“枫桥经验”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功地从发展与稳定的辩证统一中探寻到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新思路,在发展中实现稳定,在稳定中推进发展,稳定与发展同时获得螺旋式上升。[34]与之相比,长期以来不少地方“维稳至上”,不顾对象和条件地强调“稳定”,面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与冲突,一味地重“维稳”而轻“维权”,造成社会日益加重的“潜在性焦虑”,进而使得原本可以让人们喜庆的各种节日、会展、庆典,正在逐渐成为人们敏感与紧张的日子。[35]学习和借鉴“枫桥经验”,需要辩证地处理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实施维权式维稳。维权式维稳内蕴着一种科学的矛盾冲突观,并把人本身作为目的,它主张通过对人民群众利益的观照和参与权利的彰显来维护社会稳定;而群众路线及作为其政治形态的协商民主则为维权式维稳的实现提供了制度载体。[36]
具体到治理过程中,保障落实群众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利,这是制度化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和根本落脚点。就“枫桥经验”的产生发展历程而言,群众参与过程中体现出的“民主性”是其突出特征。1963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中,枫桥人民群众在浙江省委工作队的指导下,敞开思想开展“文斗好还是武斗好”的讨论,大多数群众认为:“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可以说,“枫桥经验”的产生充满着民主精神,是群众智慧的结晶。[37]在当前的社会治理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在处理事务时独断专行,违背民主集中制;还有的干部由于怕担责而不愿管、不敢管,导致了懒政怠政现象突出。这些行为都造成了消极甚至严重的后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时代“枫桥经验”再次提供了学习样板:枫桥镇枫源村为了避免上述问题,在推动“枫桥经验”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充分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把决策权交给群众”,创立了“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机制。该机制为枫源村村民有序参与村庄事务,合理表达诉求提供了平台,让他们从村庄事务的“旁观者”转变为了“广泛的参与者”。这一做法体现了时代特色、地方实际和法治精神的统一,代表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趋势。以此为基础,可以探索建立以司法调解为本的多元调处机制,这种思路一方面与“枫桥经验”中的“三治融合”密切相通,另一方面又突出了制度框架制约下的文化要素的作用,有利于开展制度化的社会治理。不管形式如何,在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过程中,“为权利而斗争”,这是一个仍未过时的命题。
———记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