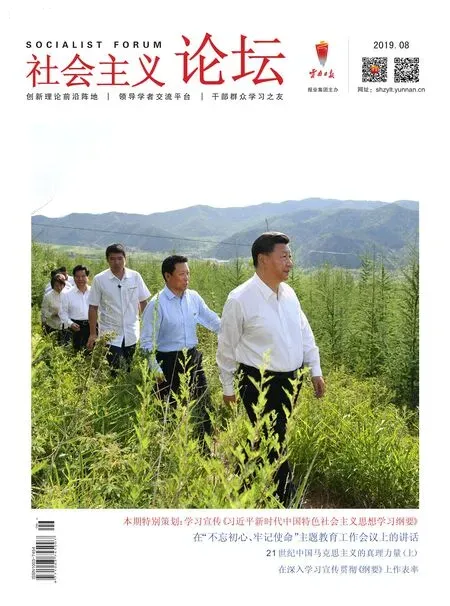长江第一湾的柳树林(外二篇)
原 因
原名袁鹰,春城晚报原副总编辑、高级编辑
浩浩长江从青海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东雪山启程,历经万壑千山,来到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的石鼓镇,行程已不下两千公里。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由北向南的长江,在这宽深的河段,竟然猛地掉头向东流……这里,是长江第一湾!
神奇宏阔的江湾,生长着一片遮天蔽日的柳树。
色调同样的浓稠茂美,堆烟砌玉般扯起重重绿帘,如隋堤的柳。枝条同样的柔韧飘逸,缱绻多情地梳着骀荡东风,如苏堤的柳。但它们毕竟是生长在长江第一湾的柳树呀!也许由于溅跳的江涛日复一日地浇灌,也许由于沉积的泥沙一年一年地壅培,它们每一株都特别高大、挺拔、壮伟。再加上当初等距、密集的栽植,这些柳树五六米以下的枝条全都自行脱落了。这又使它们显得简明干练、俊逸清奇。
你思羡骑着白马驰骋沙场所向披靡的白袍小将吗?你敬慕仗剑负琴行吟长啸衣袂飘飘的白衣少侠吗?如果别处的柳树是女性的,那么在长江第一湾,它们每一株都是英姿飒爽的美少年。
但它们当中的一些已有百年寿数了。
据说还是上世纪之初,一位名叫袁廷芳的农人就在这里种下了第一株柳树。而他的儿子袁锦、儿子的儿子袁清品不断续写着前辈的绿色诗篇。这里的柳树终于逶迤为一幅流波溢翠的长卷。
人世多少浮华和纷争都已云烟般散去。这些柳树却年年吐露新绿,岁岁繁茂如初,成为古老江湾劳苦功高的呵护和矢志不移的守望,成为一片永不凋萎的坚韧。
来到这片柳林,是一个暖风扑面的暮春。抚摸着一株柳树笔直的干,透过那青色绸缎般光滑坚韧的表层,我感觉到了一道绿色暗流的汩汩流淌。而抬头仰望树梢,可见翠色铺叠,绿波涌动。任有多少燥热浮尘,也会被它的一袭清凉拂扫殆尽。
在临江的柳林边,我还看到几株倒地的柳树。那是某年夏秋江洪肆虐留下的痕迹。我却惊讶地发现,它们朝地的一面,蓬蓬勃勃长出了很多根须。朝天的一面,则茁然冒出了条条新枝。而每一枝条上,都睁着无数被称为“青眼”的叶蕾。它们正悄然涌绽鹅黄色的嫩叶……一株老柳倒下去,一排新柳站起来。
阳光的斑点依然静静地四处飞翔,照看着我徜徉林间留下的足迹。蝉鸣如泼,菜籽雀的叫声一次次穿透厚重的绿荫,冲向蓝天。一切都那么真切,一切都那么明晰。只有江水的低语隐秘而浑厚,仿佛激荡在岁月深处的渺远鼓韵,或者回响在天地胸腔的悠长咏叹,于无边的柳色和我漫溢的思绪中。
龙山湖:龙陵人的梦湖
一左一右被怒江和龙川江夹抱,高黎贡山逶逶迤迤直插其境内。
保山市的龙陵县,一俯一仰间,皆是水意山情。其西南因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迎风而多雨,故县城龙山镇被称为滇西雨城。
虽然从地理气候上看,这里不乏淋漓水汽,但现实却是,整个小镇内没有一个湖池,这不能不使人深深抱憾。
因此长久以来,沿湖漫步倾听涟漪絮语,临湖荡舟搅动潋滟波光,是龙陵人的一个绮梦。
令人惊喜的是,近年来,在县城最低凹的开阔地带,一个东接龙玉大道、南临环城西路、西至龙瑞高速公路边、北接龙华西路的圆梦工程分两期破茧成蝶了。
它,就是新建的自然风光秀丽、人文蕴含丰盈的龙山湖公园。走进公园,只见一汪清亮明澈的湖水巧妙地镶嵌在天地间。湖的四周,高大挺拔、层次分明的银杏、香樟等珍贵植物密集种植;湖堤上,花坛鳞次栉比,似锦繁花此落彼开。
这是一叶充满活力的肺,日夜不停地吐纳呼吸,给城镇带来恒常的温润和清新。龙山湖,龙陵人的梦中情人,让每一个来到它身边的人流连忘返,恋恋不舍。
从空中俯瞰,龙山湖与东南方三座相连的小山(从南到北依次是张家坟坡、文笔坡、白坟坡)刚好形成一个首尾相吻的阴阳八卦图。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是它靓丽的“白卦”。东河像极了一条鱼的脊背,这条鱼头大尾小、肥硕丰腴的,蔚为神奇。三座相连的小山则如刚刚腾飞的小龙,欲游入龙川江,形成青瘦的“黑卦”。
站在七孔状元桥西端放眼东南,近有文笔坡,远处东山山腰则耸立着一座雄伟的高塔。
文笔坡上,原在清朝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建有一座文笔塔,塔高12层。抗日战争时期,曾驻龙陵的远征军称其为“白塔”,后其遂以白塔而知名。
阳光透过郁郁葱葱的树林投下斑斑驳驳的光影,正如沧桑历史留在这片大地上的斑斑印痕:1942年5月4日,龙陵沦陷于日寇的枪炮,白塔之下的这块土地淌满鲜血。1944年9月,中国军队在光复龙陵县城时,遭到了日军的垂死顽抗。白塔所在坡地因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成了日军的主要据点。经过多次浴血奋战,直至11月3日才收复龙陵,白塔终得脱离魔掌。它见证了中国军人多少抛头颅、洒热血的壮怀激烈和前仆后继。
可是,命运多舛的白塔在1966年,伴着一声沉闷的轰响,庄严高洁的白塔颓然倒塌了,它砖石四溅,支离破碎,仅剩一个“白塔”的地名警醒着人们去进行冷峻的思考,有时也会让人想起明代抗倭名将邓子龙所作联句“百战归来、赢得鬓边白发;千金散尽,只余湖上青山”而慨叹不已。
东山之上的三层高塔是龙陵重新打造的文笔塔。龙山湖为砚台,湖畔的亲水平台像墨锭,塔如笔,大地当纸,这里如今文房四宝皆备,正在书写唯美的华章。而即将建成的龙山书院,对传承中华国学遗产,弘扬中华国学精粹,推动中华国学发展,打造历史文化名城文脉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龙陵的墨客骚人为龙山湖题写的联语是:“龙山灵水润文笔,书院馨风拂砚池。”
水光山色掩映,绿树草地相融;龙山书院、魁阁、七孔状元桥等历史文化建筑古色古香;游步道、休闲广场、特色美食店、酒吧、会所、村落及艺术产品展馆等商娱服务设施错落相间;游船码头、跨湖栈桥、花廊、休息长廊等设施也一一给人贴心的服务和透心的愉悦。龙山湖公园已经成为一道具备良好自然条件、丰富人文内涵和多功能服务体系的城市风景线。
好梦业已成真。人们可以在公园走上跨湖的平板桥,看细小的波浪轻轻拍打着大石块铺筑的湖岸,看湖里放养的各式各样的景观鱼,甚至抛一把鱼食,惹鱼群争相抢食,激起朵朵浪花。当然,泛舟清波碧浪,对唐代诗人王维“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的清欢意境作一番细细的咀嚼,也许是更惬意的选择。
这座楼,为了围棋而永昌
在保山市隆阳区,走进古称清华海的清华湖,最让人流连不舍的,是建在西湖南段一个岛屿上的一栋楼阁。
正是夕阳西下时分,于一片浮动的绿荫和鲜花之上,以燃烧在天边的晚霞为背景,那名为“永昌阁”的仿古建筑,高翘的飞檐分五层相叠,如金翅张开,似跃然腾空,格外壮观和生动。它投影在被夕晖染色的湖波中,以自身的瑰丽融入透亮的斑斓,随湖面涟漪轻轻晃动,恍如仙宫神殿,美轮美奂。
与我国古代的很多名楼相比,眼前的永昌阁虽为新建,却同样规模宏大、建造工艺精湛,同样特别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体、融洽相亲。它充分承袭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审美情趣,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强调传统意境的营造,以传统“阁”建筑手法承接边地人文特质和建筑风格,并嫁接以现代手法表达时代特征。它典雅精致庄丽地镶嵌在山水花木之间,几乎成为天地的一部分,寄寓了人对自然的无限留恋。
永昌阁是以脚下的土地名其名的。永昌是保山的另一个称呼。西汉时,为打通前往大宛、印度的商道,汉武帝意外地发现了这块叫“乘象国”的土地。司马迁将其名为“滇越”。东汉时,勐掌王慕汉德广,率众举国归附,后杨终写《哀牢国传》时,名之曰“永昌”,此称谓自此时被确定。
为使之更具中华文化的神韵,永昌阁在建造时还有一些颇有深意的安排。比如楼高为44.99米,寓意:事事如意、长长久久;楼外观5层,内部实际有9层,寓意:九五之尊;如此等等,玄妙尽在其中。
这栋楼主要是为承载和弘扬“永子文化”而建成的,是坐落于西湖景区的永子棋院的最主要的建筑。
“永子”是一种优质围棋子。它诞生于明代,可考证的历史在五百年以上。它是永昌(保山)人李德章在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用当地盛产的南红玛瑙、黄龙玉、翡翠和琥珀等珍宝玉石烧制的。《一统志》中说“永昌之棋甲天下”。《徐霞客游记》卷十八亦有云:“棋子出云南,以永昌者为上。”明代刘文征所撰《滇志》在记载永昌府的物产时,特别提到了“料棋”,即用矿料烧制的围棋子。清代陈鼎撰的《滇黔游记》也记载:“永昌出围棋子,光润如玉琢。”又据清刘昆《南中杂说》:“滇南皆作棋子,而以永昌为第一。其色以白如蛋清,黑如鸦青者为上。若鹅黄、鸭绿,中外通明者,虽执途人而赠之,不受也。烧棋之人,以郡庠生李德章为第一,世传火色,不以授人也。”
永子外形古朴圆糯、色泽谐调悦目、质地细腻坚韧,犹如天然玉石磨制而成。它冬暖夏凉,触之滑润,入手舒爽,是古往今来公认的棋中圣品。由于原料珍贵、工艺独特,它的产量极为有限。五百多年来,不仅为达官显贵、文人雅士所珍爱,还一度作为进献皇室的上乘贡品,堪称国宝。
遗憾的是,清代咸丰年间(1860年),由于战乱,永子技术部分失传。
1964年3月,当时兼任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到云南视察,得知多年来保山已无人烧制永子时,心情沉重地指出:"传统的工艺要恢复,我不相信保山就无人能再烧出永子来。"
1988年3月,成立了永子围棋厂,该厂组织和抽调李氏家族的后人,遍处搜集关于“永子”的史料,深入挖掘关于“永子”的工艺,重金购买了一副明代的老永子作为研究实物。经过两代人20多年的努力,终于复活了失传百余年的永子烧炼技术,使之凤凰涅磐。
重新问世的永子圆融润滑、晶莹剔透。经原中国围棋协会主席、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鉴定后,为之作了“国宝永子,棋中圣品”的题字;中国围棋棋圣聂卫平在仔细鉴赏后也为之题写了“永昌永子甲天下”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