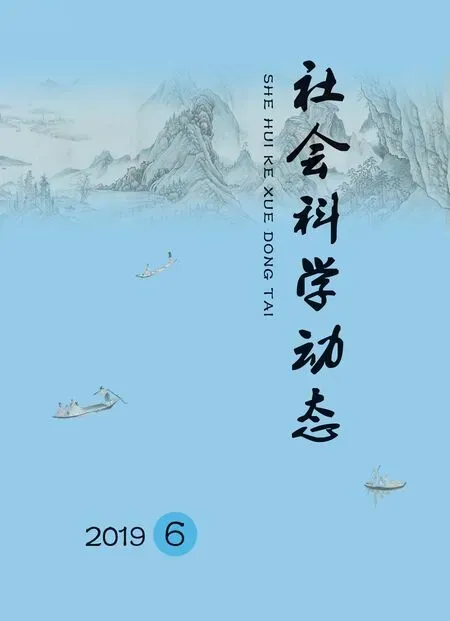论费正清筹款才能与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
黄 涛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终身教授,他不仅是 “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创建之父”,还是享誉中美关系学界的 “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生前兼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许多重要学术职务。在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费正清致力于中国、东亚区域以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并取得了他人难以超越的学术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出版和主编了60多部著作,发表了200多篇论文、60多篇书评,并撰写了50多篇序言及大量的专访,成为“ 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他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及其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和其他一系列著作,不仅成为当代西方汉学者的学术基础,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巨大关注。费正清所创办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世界上最富盛名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作为一代中国学巨擘,费正清孜孜以求、诲人不倦,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研究的人才,他的学生遍布全球70多所著名大学、研究中心以及欧美亚非各主要国家的外交部门。而这些中国研究机构的出现和大量人才的培养,都与费正清的“ 学术企业家”的高度智慧密不可分,在经费充足的条件下,这位赢得了个人至高的学者荣誉,也为美国中国研究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费正清是一个募捐能手,这不仅充分体现在他的“ 学术企业家”素质上,也体现在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特别是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发展方面的不朽贡献上。他的筹款才能,最初显示在美国政府将刚成立的新中国视为苏联伙伴而予以孤立政策之际,加上麦卡锡主义在国内以 “丢失中国”为由而兴风作浪之际。费正清着眼于中美关系的未来,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研究。而这种新兴领域的发展,往往首先需要获得理解,后来才会有稳定增长的财源。
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一开始也是没有雄厚的资金来源。他在这方面煞费苦心,四处化缘,跟金融界人士和政府部门负责人会谈,并且提出一些可能引起有关方面兴趣的课题。费正清寻求各种基金会对研究项目的支持,正式开始于1951年。在刚开始的五年内此种方式收效甚微,但有一个项目还是取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即在赖肖尔的配合下编制了一份哈佛大学与东京东洋文库研究所之间的交流计划。这个计划是费正清在1952年至1953年逗留日本期间就产生的打算,这个计划可以同时促进太平洋两岸的研究。费正清在给福特基金会的康德利夫的信中说:“一个由日美联合管理的共同基金,它能够拯救日本人的思想,这个计划大概要比我们拯救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还要快”①。这期间也存在一些失败的研究计划,包括在1951年费正清所设计出的在哈佛大学发起的2项有关当代中国问题的协作研究计划,其一是有关“ 货币和信贷在近代中国经济中的发展”,其二是“ 现代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意识及社会变化”,这两个课题的设计就是为了筹款。要实现募款成功,费正清在提出项目之前曾建议集中一些教师的才智对各种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包括从印度尼西亚意识形态的变化及其政治表现到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此外,他还不断重申要不择手段地获得基金的设想,正如他在1950年夏对其同事杰罗姆·布鲁纳所言,我们急需在“中国问题研究与宣传的艺术性之间,实现某种合法或不合法的结合”,他将上述计划比拟为“ 对中国人民作宣传的实际问题”,这个问题介于学术研究与情报研究之间,并包含了一种对“ 与西方接触之前的中国思想传统”的评价,以及对“ 美国政策和宣传成果”的概括性研究。费正清对这种 “合法或不合法结合”意图的更直接阐述,出现在给赖肖尔的一封信中,“ 我们在反对俄国扩张及共产党人颠覆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正在证明社会科学在指导政策、解决重要问题中作为研究工具的价值”,这个领域和这个国家都需要一种更大的研究努力,因为我们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困难重重,在作出重要的战略性决策的过程中深受挫折。②可惜的是,尽管使用了冷战的词藻并强调了与政策的关联性,但福特基金会一时还不理解他的观点和心情,拒绝为这个计划拨款10万美元。不过,与福特基金会这种断然拒绝资助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刺激人的还有漫不经心或不屑与鄙视的冷漠。如1951年晚些时候,费正清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保罗·巴克提出用一小笔预算出版一份有关远东问题的中西方新书目录通讯,这一要求被婉言拒绝了。向俄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德·克拉克洪提出的给酝酿中的研究民众信念的项目提供一个办公场地的请求,得到了一个不怎么礼貌的答复。克莱德·克拉克洪对他这位少年时代的朋友的本领或长远目标并不抱有幻想: “以你平时熟练使用的本领,你已用一种使拒绝变得困难的方式陈述了你的情况和理由。坦诚地说,亲爱的先生……我并未因那种无根据的怀疑而感到吃惊,即你正在使用那种被俗话称作为 ‘向上爬的老手法’。以下是最正式的通知:俄国问题研究中心无论如何不会准备为围绕在你辉煌的亚洲帝国周围的各种各样可尊敬的个人,提供20张或甚至是2张书桌”③。
资金暂时缺乏没有使费正清气馁。1955年,他特别大胆地提出了两个项目,一个是以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和政治思想为主题的研究课题,另一个以近现代中国经济为主题的研究课题。这两个研究计划在范围和题材上与1951年设计的两个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是集中在一个国家,即中国,并被限制在具有中国问题知识的学者范围内。在申请论证书中,费正清重申了有关学术的价值和国家安全问题的老调,他认为从学术观点来看,中国政治(思想)研究有可能把中国介绍给政治学家,并探索“ 未来中国的潜力”,从国家安全观点来看,置“这个最大的极权主义国家”于不顾,不再是安全或明智的了。而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有助于 “国家急需测试中国共产党的潜力,并阻止该政权要求履行的权利”。这两个研究项目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下于1956年结合起来,产生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研究”。令人激动的是,这次研究基金的申请,费正清获得了个性化的成功。卡内基基金会拨出20多万美元支持他提出的第一个课题,这笔捐款使得他在1955—1965年间能够组织人力展开有关中国政治方面的研究。虽然资助条件暗示着要求联系当代,但研究仍大量集中在前共和时期,在20多篇论文中,仅2篇是考察共产党时代。1959年秋,在新罕布什尔州拉科尼亚,距离费正清的富兰克林避暑别墅仅几英里的斯蒂尔山庄,费正清组织了一个题为“ 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的学术讨论会。会议邀请了一位政治理论家朱迪思·施克拉和15位对中华帝国政治有兴趣的中国问题专家,并就一个稍作改进后将在未来几年中取得显著成就的方案进行了讨论。会议进行了五天,提交的论文虽然有所整理,但论文集的出版商却没有遴选好,没有出版论文集。第二个课题引起了福特基金会的兴趣,该基金会在1955年捐出27.8万美元,1957年追加拨款30万美元(包括准备研究员基金,帮助已经培训过并愿意开始或继续从事语言学习的经济学家学习语言,以及设立一个永久性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教授职位)。两笔款项使费正清及其同仁、学生得以对研究中国经济的理论、方法、范围等方面进行探讨。同样,有关中国经济的讨论会也在斯蒂尔山庄举行。尽管有一个广泛详尽的会前计划和令人兴奋的讨论过程,但也一样未能产生一本适宜出版的论文集,这使费正清深感失望。后来他对这种局势作出这样的解释:“ 时机尚未成熟,或者更确切地说,论文提交者的文章还没有达到一个同等成熟的程度,产生一个足以引起共同兴趣的兴奋点”。也就是说,主要是因为参与者的水平有限,费正清的首批两个研究计划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它没有多学科的或具有当代战略意义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实际上表明,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事业的内部结构以及起步成长缺乏时间的磨炼,“ 我们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出版的东西,已比在当代中国方面出版的要多,因为在中国问题研究成长的这个阶段,较杰出的工作正在该领域的这个部分进行”④。福特基金会资助费正清的第二个申请项目,实际上是它捐助中国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两个专项之一,另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现代中国的人与政治研究”,哥伦比亚大学的项目获得了42万美元资助,哈佛大学获得了27万美元,其数额都相当惊人。不过福特基金会觉得物有所值,因为这两个项目是研究现代中国而不是古代中国,是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只是历史研究。⑤
值得指出的是,二战后美国经济经历了繁荣,像福特基金会这样组织也愿意慷慨解囊支持学术研究。福特基金会是由美国“汽车大王”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在1936年设立,总部设在纽约。该基金会自称以研究美国国内外重大问题,如教育、艺术、科技、人权、国际安全等方面课题为宗旨,用出资创办研究机构、颁发奖学金、向国外派遣专家、捐款、捐赠图书仪器等方式,向国内外有关组织、研究单位提供资助,以影响美国社会生活、文化教育事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福特基金会决心支持中国学,是在1950—1954年冷战风云愈演愈烈的岁月里一系列历史事件发展的结果。美国政坛关于“失去中国”的争吵和麦卡锡主义的恣意横行,使得中国学成了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学术领域,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现象。中国学的两大经济靠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也不得不撤出了这一领域。就是在这种险象环生的政治形势下,福特基金会决意逆流而上,挽救几乎频临绝境的美国中国学。⑥在保罗·兰格对美国中国学现状进行调查后,福特基金会在1955年正式制定了该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开始了重振中国学的努力方向,强调社会科学、当代问题研究、专业领域的地区知识、学科基础建设以及学术界的协调合作,使得中国学不仅比传统汉学和前现代研究,而且比纯粹的政策研究,更能全面而有效地服务于美国当前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到1959年,福特基金会成功地阻止了中国学在美国主要大学的进一步滑坡,还帮助了美国中国学者克服麦卡锡主义在他们中间造成的长期分裂,共同组建了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使之成为协调当代中国研究的全国性组织。结果,福特基金会在中国项目形成过程中所作的一切,不仅挽救了美国中国学,而且为其在后 “十年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实现真正的大飞跃,提供了充分准备。⑦正是在福特基金会等机构慷慨捐助中国研究的良机中,费正清确定了募款的对象和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中国研究计划, “我们在中国的灾难不是行动上而是理解上的失败。我们在解决我们头脑中的中国问题之前,解决不了我们的共产党问题……研究中国是关系美国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要回避只是一厢情愿而已”,然而“国会图书馆已被国会弄得空空如也,我想这只好由私人基金会来做了。”⑧
有趣的是,费正清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现代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的设想来源于曾在联合国和美国政府工作过的亚历山大·艾克斯坦。亚历山大·艾克斯坦1955年到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做副研究员时,第一次与费正清等人谈及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可能性。为此,保罗·兰格建议费正清负责把亚历山大·艾克斯坦、杨联升以及其他人找到一起为这个项目起草计划书。福特基金会把历史学家费正清、汉学家杨联升和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艾克斯坦这“三驾马车”看作是一种专长虽不完全一致但互相匹配的最佳组合,靠他们可以开始他人无从下手的工作。该项目之所以是以现代中国经济史(1840—1940)而不是以共产党中国为对象,是因为直接研究共产党中国既缺乏合格人员,又没法保证有关当前中国发展的数据资料来源,因此项目主要在三方面入手:一是在编写《现代中国经济史纲要》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全面分析,二是就具体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三是定期举行学术会议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指导。结果,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政治研究项目大功告成,而费正清和他的哈佛大学同事只是虚晃一枪。原因除了这个领域本身的问题之外,费正清、杨联升和亚历山大·艾克斯坦这“三驾马车”都忙于其他事务,没有集中精力来写现代中国经济史。费正清只好把完稿时间一推再推,到1965年他索性在作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写的十年报告中承认,由于这个领域尚不成熟,美国的东亚研究仍然未能有收获较大成果。尽管未能完成现代中国经济史的写作,但在专题研究和学科发展上,费正清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望尘莫及的成功,到196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13本有关中国经济的专著和28本其他内容的东亚研究专著。这样大量专著的出版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使哈佛大学在美国主要的中国研究中心中脱颖而出,奠定了在这一领域的学术领导地位。实际上,费正清是想方设法地要把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与东亚研究在哈佛大学“本地的发展”联系起来,使哈佛大学在中国经济领域有一个永久性研究与训练学科项目,并进而将中国学扩展到社会学和政治学专业。因此,费正清最终获得了福特基金会董事会的支持。1957年12月,福特基金会批准给予哈佛大学30万美元以支持现代中国经济方面的训练与研究,其中20万元是按照费正清的请求增设新的教授职位的基金本金。若干年后,哈佛大学的中国经济教授职位由富有才华的年轻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获得。对哈佛大学的中国学学科建设来说,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使它在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哈佛大学的中国学声誉一天天上升。⑨
在1957年福特基金会追加拨款的鼓励下,1959年费正清开始了一项较大的努力,以期获得一笔长期拨款,推动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约翰·林德贝克的配合下,费正清为此编制了一份广泛详尽的研究计划,以满足未来十年中预期的需要。这次,福特基金会反应更加积极,为一项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十年规划拨款75万美元以上,为在哈佛大学的社会学系设置一个教授职位拨款41.6万美元,在历史系设置了一个研究近代日本的永久性职位拨款20万美元。这种募款的成功,再次显示出了费正清杰出的辩才和事业心。在申请谈判所花费的几个月中,费正清在拨款机构和他的学术同事之间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经纪人的角色。福特基金会的办事人员描述了他们所期望实现的大致目标,并未提出具体的研究项目,费正清在此极力消除了福特基金会对于师资缺乏和资费分配不公的疑虑,尤其是对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中可能产生的分裂。他坚决主张,在投资近代问题研究并在社会学、经济学方面设置教授职位的同时,应拨出款项,在朝鲜问题研究和远东语言研究方面设置新的有任期的教授职位。正如他对福特基金会的约翰·斯科特·埃弗顿所说的那样:“如果哈佛大学把如此大量的精力集中于当代中国问题而导致其他的东亚问题研究被扼杀的话,这将是得不偿失的”⑩。
二
自此以后,费正清的 “基金会外交”就一路顺风。在他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近20年间,该中心一直财源广进,雄厚的经济基础为现代中国学的建立及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他自诩这种赢得基金会慷慨赠与的成功为 “基金会外交”,并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他通常承认的机遇。1958年以后,当代中国问题已经成为福特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优先考虑的事,它们捐款给几所大学,不只是哈佛大学,以开拓这个领域的研究。福特基金会在1959年开始实施“ 中国问题研究与培训”发展项目,福特基金会的董事们认为,首要问题是组织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以及一批优秀的专家,这是根本任务。此后十年时间内,福特基金会为发展当代中国研究项目,重点资助了4所大学的科研院所或研究中心。这4所大学是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和华盛顿大学。这四所大学拥有较为成熟的东亚研究中心和丰富的馆藏资料与图书。同时,福特基金会还支持一些专业研究机构,如胡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中的东亚研究中心及那些缺乏机构资源的个人和学者。因此,有人评论,即使孔子再现,费正清还是将一事无成,假如他的请求没有被福特基金会优先考虑的话。不过,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哈佛大学的受惠之所以多于其他大学或中心,部分是因为它得惠于已经具备的大量人员、资源优势,只要福特基金会等机构想看到成果,费正清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哈佛大学已经在向最优秀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想这样去做。其次,他个人记录极佳,他的同事中几乎没有人比他更赞成多出成果和那种孜孜不倦的精神的了,而且没有人比得上他那顽强的耐心和顺利完成研究项目的能力。⑪除了不断精进的交际才能之外,费正清还逐渐锻炼出一种把多种研究项目作为一个整体一起提出、研究以及把个别研究者的计划并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的才能。这种才能使他在觉察如福特基金会等拨款机构所优先考虑的事情以及他们颇为敏感的问题方面成为行家,因而,费正清所提出的经费申请,是把具有眼前战略重要性的东西与具有长远学术价值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小小杰作。“ 由认真负责的捐赠人所提出的关于研究应对当前问题和未来的人类幸福具有‘ 实质意义’的真诚要求,应当毫无疑问地被接受。但另一方面,该捐赠人那种想在一个区域研究的领域内详细说明什么是‘ 有实质意义’的善良愿望,本质上是无意义的和有害的,因为它想预先判断正在被支持的智力冒险的结果”。对于这种“ 实质意义”,费正清写道,它 “并非是一个年代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分析的问题。依我看来,整个历史对现今的舞台都可以具有实质意义的。历史只不过是我们现今对过去的理解,因而它是现在的一个方面(而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实际上,在福特基金会等捐款机构的需要和学术上有限考虑的事情之间,费正清的辩术倾向于强调前者,而他的行动则倾向于后者。可以说,费正清的独特成就是他可以利用一对如此突出的矛盾,并将这对矛盾转化为既对他有利,也对这个领域有利的事情。⑫
正是本着深刻的洞察和全盘运作的考虑,身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费正清充分发挥了他的募捐能力。就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项目启动之初,费正清和麦克·邦迪一起访问福特基金会,并提出哈佛大学希望从福特基金会获得一笔奖金来支付中国研究的全面要求。那是一个极好的要求,但是福特基金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对他们要求的数量大吃一惊,而且指出他们想要的这一数目,几乎等于基金会估计可以给予四所有影响的大学的最初拨款的总数。费正清和麦克·邦迪大胆地回敬到,既然这样,那么很明显,福特基金会的问题就在于增加它支持中国研究的预算(最终它还是那样做了),而不是少给哈佛大学所需要的资金。无论人们把这种态度称作自信还是狂傲,有人会说两者都有,但确实显示了费正清是一位在中国研究领域中最有效的学术组织者的责任感。同时,费正清还比他同辈中的任何人,更能够表达出全国性的需要,超越地方观念,在不同的观念中架起一座桥梁,并且把合作和共同目标注入这一领域。⑬这段回忆实质上再次说明了这样的观点,即在说服福特基金会捐资赞助中国学研究方面,费正清不仅具备哈佛大学应该担当起主要的领导角色的高度自信,同时又具有超越哈佛大学狭隘利益的眼界,尽力支持其他机构和全国范围内的有关中国研究的活动。由于费正清募款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经费便主要来自于福特基金会。此外,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尽管由哈佛大学的教授任教和管理,但它的支持资金几乎都来自校外,这些资金足以允许给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教师、研究生、来访的同行以及各种研究助手,都分发少量的补助。在第一个十年中,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筹集资金125万美元,用于帮助出版书籍75种以上,并对70多位个人分别提供了超过1000美元的资助。⑭1970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约翰·林德贝克教授出版了他为福特基金会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状况的调查与分析报告,他着重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现代中国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这个研究涉及中国学领域的组织机构分布情况、学者和学生的数量、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的发展历史、该领域的资助状况和实际存在的问题、对未来中国学领域持续发展的评估等方面。约翰·林德贝克指出,中国学“ 发展的十年”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当时美国的学术群体,福特基金会在资助该领域的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仅在1959年至1970年间,福特基金会就通过发放奖学金、拨款等方式捐赠了2300万美元以赞助了美国和国际上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和研究项目。除了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研究领域的投资外,美国政府也提供了大约1500万美元的资金,这笔资金主要用来为学生、学者提供奖学金。⑮
据估计,来自各个基金会和美国政府的好几亿美元进入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这些雄厚资金对于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经济基础作用。同样也不能否认,雄厚资金之所以投进费正清所在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除费正清的募款才能之外,美国政府和实业界的自身动机也有重大作用,它们可谓珠联璧合,又各取所需。新中国的崛起,朝鲜战争的败北,苏联的全球扩张,欧洲盟国的分庭抗礼,都使美国朝野感到有关中国的信息价值,一些重要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纷纷出钱资助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福特基金会率先在1955年为哈佛大学提供资助去研究中国经济。这种援助以及校方的支持,使费正清及其同事建立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不甘落后,先后慷慨解囊。根据统计,1958年至1970年间,美国各界资助中国研究的数目达4000万美元之多。其中哈佛大学得到550万美元。这样的巨款帮助了260余名学者到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其中近一半的学者来自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1955年至1975年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跟哈佛大学出版社密切合作,出版了151部有关东亚研究的学术专著,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不但掀开了二战后美国研究中国风气之先,而且其规模之大、出版之多与影响之巨,在整个西方也是首屈一指的”⑯。对东亚研究的兴趣大增还不只限于哈佛大学,其他如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名牌学府也都竞相设立了亚洲研究和中国研究的课程。至于费正清的个性化募款总数,难以分类或笼统统计,但他认为,东亚研究的兴旺尽管没有理工科那样可视的显著成果,却在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和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显示出了发展前景和希望,“虽然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相当紧迫,但如果没有经济上的资助,便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成果,所以,我们必须把赞誉也给予该项事业的资助者”⑰。
费正清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因为财源广进也容易被人把它跟美国政府和垄断财团的意志联系起来,由于与政府和企业界的配合,费正清也被说成是堕落文人。这样就产生了一些对其批评的文章,包括里查德·卡根的《麦卡兰的遗产:亚洲研究会》(1969年)、朱迪恩·科伯恩的《亚洲学者和政府:剑上的菊花》(1969年)、戴维·霍罗威茨的《政治与知识:非正统的近代中国史研究》(1971年)、莫斯·罗伯茨的《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组织和趋势的几个问题——答费正清教授》(1971年)、哥伦比亚大学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的《美国的亚洲研究机构》(1971年)等。费正清激烈地反驳了对他的指责,在私人通信和印刷品中,尤其见他在《关心亚洲问题学者会会刊》的一篇《评论》中的关于自我的澄清。⑱费正清反驳了最令他恼火的攻击,即认为哈佛大学和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联合委员会已经成了政府和各个基金会操纵的工具。这种激烈的回击,部分原因是他觉察到了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的指责突出了“阴谋问题而不是价值观问题”,含有与“麦卡兰委员会对太平洋关系学会的‘调查’的惊人的相似之处”。费正清关心大学与外部机构包括私人基金会、政府和商业集团之间关系的观点,是与他的中国学研究事业的整体计划相关联的,虽然明知有外界的道德上的非议,但他的非常实用主义的宗旨使他勇往直前而无所顾忌。正如他对学生詹姆斯·佩克所言:“哈佛大学是随着美国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如果它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继续得到美国商界的资助”,如果美国资本主义的馈赠是靠不住的,如果商界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引起了“现实的道德困境”,“我认为,哈佛大学是值得支持的,而且很显然,在我们目前的世界上必须这样去做”。因为费正清相信,万恶的金钱只要好好支配,会对学术和社会两者都有贡献。20世纪70年代,费正清在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建设上遭受的攻击相对弱化,尤其他在1973年促进的美国历史学会关于美国—东亚关系的计划因福特基金会资助款项期满后而宣告终止。同年3月,费正清致信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指出,由欧内斯特·梅所领导的美国—东亚关系委员会在成立五年后因资金短缺而解散,但它成为一个填补空白的主要研究项目。美国—东亚委员会最终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的庞大机构中找到了一个新家,并在学会自主下,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不过,美国—东亚关系委员会的终结似乎印证了费正清的中国研究的组织规模化的重要性,他曾建议该委员会容纳一些“ 左翼”学者的建议被拒绝,他的中国研究多元化的模式因此不能付诸实践,这令他感到失望。后来费正清对菲利普·德维利尔斯说道:美国—东亚关系委员会表明了“美国的自我研究是文化约束”,在重新评价美国的动机和作用方面并不成功,因为“ 除了新左派的某些更年轻一代外,美国学术界对越南劫掠和惨败的看法是感情用事多于理智。”⑲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冷战时代,学者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据费正清的学生、加拿大学者埃文斯回忆:费正清的这种治学方法招致了他的老熟人约瑟夫·艾尔索普的批评,按照约瑟夫·艾尔索普的说法,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应该是中央情报局的事,与严肃的学术活动无关。这种观点颇能代表一部分人的认知,并且得到了包括费正清的老朋友博德和学生史华慈的附和,只不过后者的批评要比约瑟夫·艾尔索普委婉得多。由于约瑟夫·艾尔索普等人反对福特基金会等组织继续对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提供经费,费正清被迫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立场:首先,费正清说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得到的资助使用超出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研究领域,其次,他说明自己的研究关系到国家的利益,使美国在世界性的权力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一句话,他的工作旨在增进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不是由于他自己别出心裁。正如费正清在给史华慈的信里写道:“ 是毛泽东提高了(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的地位”⑳。耐人寻味的是,费正清在回忆录中几乎未曾提及这样的插曲。
三
通过长期的现代中国学研究和募款雄厚的学术企业化运作,以费正清所领导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全美现代中国学研究事业取得了举世震惊的学术成就。就费正清本人而言,他的论著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如《中国口岸的贸易与外交》、《清代行政:三个研究》、《美国与中国》、《中美关系中中国的形象和政策》等;二是为教育美国公众、帮助美国了解中国而撰写的著作与教材,如《东亚文明史》、《伟大的中国革命》、《东亚:传统与转型》等;三是各种学术工具书,如《清季史料入门》、《近代中国中文书目提要》、《中共文献史》等。三类论著的有机结合,构成了费正清的整个学术体系,展示了他的中国学研究的三大特色:一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它在国际关系中亦应受到特殊处理;二是侧重清代以来中国历史的研究,认为不研究清代历史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三是强调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传统与现代化两个主题。美国《评论》杂志指出: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且无与匹敌的人物。㉑正是因为有如此众多而精深的学术成果,费正清奠基了他的独特学术地位,在20世纪美国汉学界无人能与之相比,这使他成为美国中国学界的无冕之王,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研究的泰山北斗,即便到今天的国际学术界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然而,费正清并不希望他学术地位不被日后的学者所突破,不被超越就意味着中国研究事业限于停顿,或者后继无人,他需要的是源源不断的中国问题研究的代有人才出,并将中美关系置于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地位,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充分发挥两种异质文明各自的积极价值和最大贡献。
作为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基地的“ 费正清时代”的核心代表,费正清还在世的时候就毫无悬念地成为世界众多学科领域里的学术研究对象。1977年,在哈佛大学执教40年之后光荣退休的费正清在他的哈佛大学同事和学生们为其举行的退休宴会上,目睹着他一手创办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更名为“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新牌匾时,他怀着一贯的幽默和历史感来看待这种殊荣:“ 如果能保持我们中心的经费源源不断,我的名字即可与研究中心一道长存于世间。我意识到,我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正逐渐取代我本身,我从历史舞台消失之后它们依旧留在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而又令人着迷的工程。相比之下,‘ 我与我的影子’这个主题要比‘ 我与我在公众中的形象’简单得多。公众形象的产生不决定于人们的意志,但或许我还可以尽可能补充一些有益的东西。从1968年开始,美国历史协会设立了 ‘费正清奖金’,并规定每隔一年评选一次。现在这里又出现一个费正清研究中心。这种局面究竟能维持多久呢?仔细分析一个作家在其作品中所占的份量,便可以发现,我现在的处境与我在本书中所担当的角色一样,正在从费正清的中国问题研究滑向单纯的费正清研究”㉒。显然,费正清的自我预见或先见之明确实是不同凡响的,也是名符其实的。1991年,当费正清不幸病逝之后,国际学术界在哀悼的同时,更揭开了费正清研究的学术帷幕,他的上述有关 “魂系中国”的杰出著作,有不少已在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等翻译出版,这些翻译作品成为中国学者进行费正清研究的重要资料。
在半个多世纪的“费正清时代”里,费正清以其独特的视角考察、审视中国,在中国研究的学术园地里开拓耕耘,成绩斐然,被誉为“ 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创建之父”。费正清的学术经历就是美国现代中国学发展的一个缩影。首先,费正清带领他的学术团体和其他中国研究学者们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美国现代中国学。其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费正清以哈佛大学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基地,借助哈佛大学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学术品牌,把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变迁作为中国学研究的重点课题,创立了中国研究的新模式。在他辛勤开垦的这片园地中,他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这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中国学家和西方汉学界,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
费正清除了著作等学术成果之外,还像古往今来的所有优秀学者一样,将中国研究和高等学府的中国学教学结合起来。在执教哈佛大学历史系的大半生时间里,费正清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研究的人才,他的学生遍布全球70多所重点大学、研究中心以及欧美亚非各主要国家的外交部门。费正清还带领他的同事和学生,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不仅使美国汉学(中国学)这一学科领域跻身于美国历史学界的前列,而且使中国研究成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里最活跃、最浩大、最丰富多彩的领域。这种世界学术界史上的奇迹,跟费正清个人的研究和组织工作能力密不可分。㉓此外,费正清还积极倡导建立中国学的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培养中国学研究人才,使美国成为了海外研究中国的第一大国。因而,费正清的中国研究是美国中国学在现代发展的一个缩影,代表了积极而正确的学术方向,具有开拓和启后的巨大意义。
正因如此,费正清成为享誉世界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生前历任美国的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研究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学术职务,毕生致力于中国、东亚区域以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等问题,推动了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研究事业。
1991年9月12日上午,费正清亲自将生平最后一部书稿《中国新史》送交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心脏病突发,两天后平静辞世,享年84岁。但是,就在他去世前四天,费正清致信祝贺他的一位60岁学生詹姆士·小汤姆森的生日,发自肺腑地表达了他对中国研究的坚定信念:“ 1955年,你第一次来见我的时候,你说你编过《耶鲁日报》,现在你想来研究中国,是为了能找到你的奶妈。我说我也在找一个奶妈,但是好的往往是难以找到的。当你说你是偎在赛珍珠膝前的唯一的汉学家时,我也告诉你,我正在等待着你成为中国研究的‘ 皇帝’。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愉快相处,不时地在当地人面前显示我们的成果,乐趣无穷”㉔。实际上,费正清就是中国研究的“ 皇帝”。他的逝世如同中国皇帝式的驾崩,是美国乃至世界中国学界的一颗陨星坠落,正如欧美媒体称,费正清的逝世是西方中国学学术史上 “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一种“ 费学”的情结却在后世学人之间酝酿、创造和成熟,在美国乃至全球性的汉学或中国学发展上不断得到深化,并引领不同的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和共同福祉的源源而至。
注释:
①②③④⑩⑪⑫⑭⑲ [加]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229—230、230、232、235—236、236—237、233、394、375—376页。
⑤⑥⑦⑧⑨ 韩铁:《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1950—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13、72—73、77、98—102 页。
⑬㉔[美]保罗·柯文、默尔·戈德曼主编:《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朱政惠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163、93—94页。
⑮ 王建平、曾华:《美国战后中国学》,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⑯ 郝延平:《费正清》,《近代中国研究通讯》1988年第5期。
⑰㉒[美]费正清:《费正清自传》,黎鸣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0、572—573页。
⑱ 转引自[加]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页。
⑳ 费正清给内森·普西的信,1961年2月3日;费正清给史华慈的信,1961年3月6日,参见 [加]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206页。
㉑ 叶兴艺:《费正清:美国汉学奠基人》, 《21世纪》2002年第2期。
㉓ [美]邓鹏:《费正清评传》,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