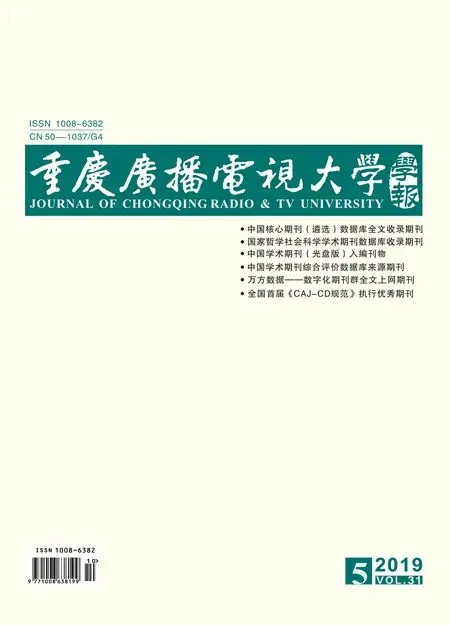论梁实秋的杜甫研究
熊飞宇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1331)
作为作家和学者的梁实秋,其成就集中表现在三个领域:一是散文创作和文学评论;二是英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三是英汉、汉英词典的编纂。其读书,一向主张要读“长久被公认为第一流的作品”[1]256。外国文学方面,经胡适倡导,梁实秋选择了莎士比亚研究;中国文学方面,则自主选择了杜甫研究。杜诗1349首,梁实秋均曾圈点一遍。由此可见,梁实秋可称“杜诗迷”。不过遗憾的是,对于梁实秋的杜甫研究,目前学界鲜见有专文论述。
首先来回顾一下梁实秋研读杜甫的历程。1987年,梁实秋在回答《联合文学》记者丘彦明女士的提问时,对此曾有系统的梳理。(1)访谈的题目“岂有文章惊海内”,语出杜甫《宾至》。题下有小序:“‘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是杜工部的名句,也是他谦己之语。当时杜公四十九岁,自嗟老病。我今年逾八旬,引杜诗为题以自况,乃系实情,并非谦为。丘彦明女士惠然来访,我如闻跫音。出示二十二问,直欲使我之鄙陋无所遁形。秉笔覼缕,不能成章,惭愧惭愧。”该文原载《联合文学》第3卷第7期(总第31期),1987年5月1日出版。简言之,其兴趣和心愿的萌发,是受到好友闻一多的感染。1928年6月,闻一多在《新月》发表《杜甫传》(未完);1930年4月,又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发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梁实秋认为“杜甫号称‘诗圣’,‘屈指诗人,工部全美,笔追清风,心夺造化’(韩愈语)”,“喜欢诗的人若是不对工部加以钻研,岂非探龙颔而遗骊珠?”[1]256此后,梁实秋就开始研究杜诗,搜集有关杜诗的版本。1936年5月25日,梁实秋游北平东安市场,廉价购得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系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因有标点,且“取携便利”,随身已50年。而琉璃厂和隆福寺街的旧书铺老板,知其好杜诗,遂将书不断送来;同时,他购得洪业(William Hung)主编的《杜诗引得》,乃依其长序,按图索骥。“但限于赀力,不能从心所欲。”[1]257其好友亦多相助,如冰心去日本后,曾为其购得日本版杜诗一本。经多方查寻和友人帮助,梁实秋总共搜集杜诗版本60多种[2]73。
梁实秋的杜甫研究,虽酝酿于抗战之前,但初试啼声却在抗战期间,而“真正开始是在抗战胜利之后”[1]257。现就其主要篇目,略述梗概。
一、《关于李杜的两本新书》
该文发表于《星期评论》第36期,1941年10月30日出版。长期以来,此文一直未得到研究者的关注,至2002年10月,由鹭江出版社出版的《梁实秋文集》方将其收入第七卷“集外拾遗2”。
所谓“两本新书”,一是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二是朱偰的《杜少陵评传》(青年书店1941年版)。书评开篇指出了两书共同的特色,即两位作者都采用“概括叙述”的方法,“从大处着眼,不局囿于考据的藩篱以内”[3]13;然后分别指陈其得失。
对于《杜少陵评传》,梁实秋首先赞同朱希祖在《叙》中有关李杜的比较,同时对于朱偰的部分观点提出批评。一是朱著将杜甫尊为“民族诗人”,在抗战时期,不少人亦将屈原奉为民族诗人,此一荣誉如何归属,论者虽不愿论列,但问题却值得进一步深究。二是朱偰认为,中国古诗“多个人之抒情诗,少民族之叙事诗”,“自少陵出,以其高华之才气,博大之体势,创为长篇记事诗”[4]159;梁实秋则认为,中国过去诗人,鲜少“以创作为终身事业”,并且于一篇作品,“亦往往不用全部精力去应付”。梁实秋认为,杜诗虽有长篇纪事之作,但最长者不过千字,余则三四百字,“以视西洋伟大之诗篇,几不能相提并论”[3]14。三是朱偰将杜甫比作“法国之拉马丁(De Lamartine),英之摆伦(Byron),德之歌德(Goethe)、许勒(Schiller)”[4]159,梁实秋认为,这种“强勉”的比较“似属不必要”,而且拉马丁、摆伦(编者注:拜伦)尚不足称为“民族诗人”。进而指出,杜诗早有定评,“诗圣”“诗史”均非过誉,“民族诗人”之“洋式徽号亦可不加”[3]14。四是朱著内容虽较丰富,但其“编制排列”类似“手册”式的教科书,“不甚符合评传之体裁”[3]14。
梁实秋反对以现代称号加之于杜甫,认为会致其失却本来面目。这也是其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特点,即“很少在中西文学之间相互阐发”,纵然是谈论莎士比亚,也未将中国的文学现象硬性牵扯进去[5]230-231。
二、《杜甫的〈客夜〉》
该文发表于《文艺与生活》第4卷第4期,1947年5月1日发行。
原诗如下:“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
梁实秋首先阐明选析此诗的理由。该诗并非杜工部“顶出色”的作品,但对于那些在乱离中有过类似“客夜”经验的人而言,读到此诗时都会觉得“非常亲切有味”[6]1。因为《客夜》是从战乱流离的经验和感受出发。
次言其写作背景。该诗大约作于宝应元年(762)秋,诗人时年51岁,家眷留成都,自己独身随成都尹严武还朝,至绵州,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此诗是才到梓州时作。是年冬,即将家眷接到梓州。故此诗并非“久客在外忆家之作”,而是乱离中初到生地,夜里难眠所发的感慨。金圣叹的《唱经堂杜诗解》云:“久客不归,最无以自解于老妻”,梁实秋认为“殊非事实”[6]1。
再看其语言风格。此诗“清楚明白,很近于白话”,诗中无典故和“特殊的诗藻”,可算杜诗一格。“在感情强烈而真挚的时候”,“用浅显的文字和写实的手法直截了当地抒写所感,比较的更容易动人”,此即其中一例。如首二句“全是几乎没有什么剪裁的大白话”。对于有关解读,梁实秋认为,《九家集注本》所引赵彦材语,指陈恰当;但黄生《杜诗说》,却有故弄玄虚之嫌[6]1。
该诗版本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三。其一,首句“客睡”二字,自南宋版《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以降,诸本均是如此,但《杜诗引得》所据宋版郭知达九家集注本,却作“客夜”。梁实秋不免发出疑问:“究竟是引得铅印之误,抑是翻刻之误,抑是宋版郭著确是如此”,尚难断定。不过,以意度之,“客夜”于义未安,恐有误[6]1。今查《杜甫全集校注》,亦作“客睡”。其二,第三句“入帘”,郭本注“一作卷”,嗣后各本“入”“卷”参半[6]1。具体而言,“‘卷’,钱钞本与底本同;馀本俱作‘入’;宋九家本、蔡甲本云:‘“入”,一作“捲”。’宋千家本、元分类本引希曰:‘“入帘”,一本作“捲帘”。’元千家本引希曰:‘“捲”误作“睠”。’”[7]2664梁实秋认为,两者均可,不过“在对仗上稍有问题而已”,但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引洪仲注所云,则“似嫌牵强”。该句之“月影”,张远的《杜诗会稡》作“月色”,但不知何据?其三,第四句之“远”,仇本注“一作送”,而李文炜(雪岩)的《杜律通解》作“听”,则应是“手民之误”[6]1。
继之,梁实秋对此诗作出诠释。首二句是说“秋夜漫漫”,客中躺在床上,“张着大眼害失眠,盼着天亮便好”,无奈“老天故意捣乱,偏不肯明”!次二句写景,“但见残月之影入帘而来,枕上只听得远江之声,是一片秋夜凄凉景况,更加助人悲苦”。第三句写身世,“直说”“客中衣食无着,毫无办法,只好寄人篱下,靠朋友提携”。此中问题在于“友生”到底是谁?顾宸(修远)在《辟疆园杜诗注解》中认为应指高适,朱鹤龄在《杜工部诗集辑注》中所附的《年谱》则对顾说提出质疑,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完全抄袭朱说”,进一步主张“友生”或即章彝。梁实秋认为,章彝虽“最为可能”,且章、杜“交谊不恶”,但疑问犹存。也许可以确定此诗作于宝应元年,但须知章留后此时并不在梓州,据《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黄鹤注,“宝应元年及广德元年之春”,“守梓州者乃李使君”,是年之夏,方为章侍御。然则“友生”是否即李梓州,梁实秋认为,“此亦不可武断”,进而认为,“杜工部一生都是靠了朋友,何必但在这一首诗里要确认其人”,所谓“友生”,应是“泛指一般朋友”[6]1-2。《杜甫全集校注》或曾采纳梁说,其注释云:“按诸说以友生确指何人,似欠妥。甫暂入梓时所交接者恐非一人,如严二别驾即其一,故友生乃泛指在梓之友人,不必泥定为谁。”[7]2662
最后两句亦有问题。“书数纸”,究竟是杜工部写给老妻,还是老妻写给杜工部,各家解释,殊不一致。顾修远认为是“老妻数纸自成都而来”;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认为“此因得家书后有感不寐而作,家书中定有催归之语”,“旧以数纸为寄妻之书,恐非”;杨伦的《杜诗镜铨》则抄袭浦说。而仇兆鳌、黄生的《杜诗说》、吴见思的《杜诗论文》、边连宝的《杜律启蒙》、金圣叹等,均将其解作寄妻之书。梁实秋认为,后说“较为妥当而深刻”,其理由如下:“大抵乱离之中远出作客,不能不忆家中妻小”,但“客中所最苦恼的事,倒还不是忆家”,“乃是唯恐家里惦念自己”。杜工部送严武至绵,“阻兵入梓”,如同平地风波,担心老妻一旦听得川北用兵,心内着急,故一到梓州,便连发家信,报告自己行踪,以使老妻放心,但又不知其是否收到。想到此处,更加难以入睡。因此,“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乃是自己心里盘算之语”[6]2。《杜甫全集校注》也认为,“‘老妻’句,张潜、边氏所解较为顺通,似更切诗意。顾、浦所解未免迂曲”[7]2663。
三、《杜审言与杜甫》
该文发表于《文潮月刊》第4卷第1期,1947年11月1日出版。编者所作《作者介绍》云:“作者梁实秋先生,国立师范大学教授,曾译莎士比亚全集等名著数十种。”[8]
梁实秋认为,杜审言与杜甫祖孙之间,虽从未见面,但从作品和生平观之,两人在性格和作风上关系密切[9]1391。
首先来看性格。一是矜夸。初唐诗坛,杜审言与崔融、李峤、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然恃才傲物。《新唐书》曾记其三事,可见其“自负甚高,出语夸大”。以其现存四十三首而论,对五七言绝律之体,虽不愧为前驱,但“以屈宋作衙官”,似嫌“不伦”;又虽较沈宋略高一筹,但何至“不见替人”?[9]1391胡适《白话文学史》以之为“诙谐的风趣”[10],梁实秋却认定是“矜诞夸大”。梁实秋认为,此种性格,杜甫亦得其遗传。如《壮游》“自夸早熟”,《进雕赋表》也不少“自吹自擂”[9]1391。
二是好游玩。杜审言踪迹所至,《新唐书》所记者,有襄阳、隰县、洛阳、吉州(属今江西吉安市)、峰州(属今越南)、长安;诗中可见者,有岚州(属今山西吕梁市)、江津(属今重庆市),湘江、石门山、南海(广东)等地。其中峰州、吉州都是谪居之所。杜甫亦曾客游吴、越、齐、赵、蜀、湘。祖孙均非“死守甕牖”之人[9]1391-1392。
其次来看作风。杨万里《杜审言集序》已注意到“祖孙之相似”,梁实秋则认为二者的相似,“不仅是一两句的偶合”,而是“确有一脉相承的迹象可寻”。据《进雕赋表》的自白,杜甫早年学诗,必曾观摩祖父的作品。其后来的诗中,也屡有提及。如其一则曰“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再则曰“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三则曰“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9]1392-1393。
就二人整个的诗集而论,其相似处有两个。
一是“诗的取材”。初唐诗坛,“率多拟古之作,很少写实之篇”,相较而言,杜审言则与众不同。其诗“差不多全是临时即景抒怀之作”,“凡有赠和皆实有其人,凡有临眺皆实有其地”,故其题材“亲切”。如杜审言的《登襄阳城》与杜工部的《登兖州城楼》,杜审言的《旅寓安南》与杜工部的《戏作俳谐体遣闷》,“都是随时随地拈取事实,不假词藻,自然生动”,体现出“独创的写实的作风”。统观杜集,很少“拟古之作”,更少“无病呻吟之作”,“几乎全是实际生活,实人实事实情实景”。此等诗才,杜审言“已露端倪”,至杜甫便“登峰造极”[9]1393。
二是对偶。对偶成为诗中要素,始自律诗。杜审言于此道,即颇为高明。其五言律诗,“差不多通体皆是对偶”,如其《经行岚州》《秋夜宴临津郑明府宅》。其妙处在于“对仗工整之外,了无堆砌之痕,一气呵成,意义连串”。杜工部对此更是运用自如,常“驱使大量的典故辞藻,对得平平稳稳,而把一股诗意贯穿其间,不枝不蔓,不滞不板,于富赡(2)原文作“膽(胆)”,有误,径改。典丽之中有生动洒脱之妙”。如《登高》《春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大气磅礴,一泄如注”,为“律诗之最上乘”[9]1393-1394。
杜审言对杜甫的影响,由以上可以见得,体现出“家学渊源”。但二人的诗艺造诣,却不可相提并论,简言之,“杜甫的眼界胸襟学识技巧都远在乃祖之上”[9]1394。
四、《杜甫与佛》
该文发表于中国台湾《自由中国》第2卷第1期,1950年1月出版。后收入《梁实秋论文学》,由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9月出版。
“杜甫是一个生活经验极丰富的人”,“每饭不忘君”是其一面,与佛亦有颇多关系[11]555。梁实秋撰写此文的目的,即在于对此有所说明。
杜甫与佛教发生关系是在40岁以后。天宝十载,杜甫“进三大礼赋,踏入宦场,蹭蹬失意,随后即遭天宝之乱,开始流浪,度陇克秦,入川游楚,于戚戚风尘之际,开始接受佛家思想的熏染”。而在40岁之前,杜甫虽也不得意,时有“隐沦之志”,但其思想只是“近于道家,与佛无涉”;而且这种“求仙隐遁”的情绪,终其一生,都多少有所保持,直到临死,还有“葛洪尸定解”的谶语。因此,40岁以前,杜甫“只有神化隐逸的思想流露于字里行间”;40岁以后,才有佛家思想[11]555-556。
杜甫佛家思想的来源,或有如下数端:一是房琯及房相之客赞公,二人好佛,可能对杜甫影响甚大,尤其是与赞公往返之后,入佛渐深;二是当时禅宗正当全盛,杜甫“在颠沛流离之中不能不接受其影响”;三是“饮中八仙”之一的苏晋以及王维,都是杜甫朋友,且杜甫另有不少方外知交。因此,杜甫40岁以后的作品,“常有得道之语和佛门典故”[11]556。
对于杜甫所信禅宗,论者有南宗、北宗之议。如仇兆鳌力主杜甫信南宗,周篆则认为杜甫信北宗[12]。梁实秋则认为,杜甫所倾服的是南派禅宗。何以见得?《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云:“许生五台宾,业白出石壁,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此处所云,当是泛指南禅。而《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有句云:“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更明白道出其信仰在曹溪。“七祖”二字,注家聚讼,或指天竺七祖总称,或指普寂(大照),或指荷泽。梁实秋认为,“六祖以后衣钵不传,七祖云云当然无据”,不过可以肯定的,则是南禅无疑[11]556-557。
杜甫信佛的深浅也值得研讨。是“行文方便,偶然摭取释典,阿附风尚”,还是“真正有所了悟,虔心皈依”?苏东坡评其《谒文公上方》,曾说“知子美诗外,别有事在”;而所谓“别有事在”,亦即杜甫《望牛头寺》中“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之意。《上兜率寺》中的“庾信哀虽久,周颙好不忘”,也是同一心事。《望兜率寺》中的“不复知天大,空馀见佛尊”,极力赞叹佛法的博大超过了儒家,则是“更坦率的自述”。《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表明“出峡求禅之旨昭然若揭”;而《陪李梓州王阆州苏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义寺》之“谁能解金印,潇洒共安禅”,“直是劝人解脱”;且“本自依迦叶,何曾藉偓佺”(“夔府百咏诗”),明言“神仙之事缥缈不可求,惟禅方是归宿”。杜甫老年,万念俱灰,身躯衰谢,“确是有意于诗酒之外钻研禅理”。另一方面,“杜诗于激愤处常有非孔语,而对佛则从无讥评”。再一方面,杜诗释典的运用,“灵巧丰赡”,据此以观,其对于若干大乘经典“必定精通”。梁实秋认为,综合来看,杜甫于佛,当具有“相当信仰”[11]557-559。
杜甫或有意逃入禅门,但毕竟不曾遁入空门。究其原因,应为三事所累:诗、酒、妻子。“所谓诗,即是情,即是爱憎,即是对于人世的留恋”;对于酒,杜甫因肺气亦已“辞谢痛饮”。唯对于妻子,“无法安排”。杜甫一生,浪迹江湖,然室家之乐,每每笔之于诗,“鄜州望月,梓州失眠”,俱写得“情致缠绵”。其为妻所累,求仙不成,求佛亦然。故杜甫的求禅,“大概是只限于观经听讲”[11]559。
最后,梁实秋总结,杜甫本热心仕进,但历尽挫折,“始无意用世,于坎壈漂泊之际,随缘感触,接近禅门”,进而达到宗教境界的边缘,却因眷念人世而不得解脱[11]560。若从白璧德“自然的、人道的、宗教的三境界”来看,杜甫最终还是停留在人道的境界中[5]231。
五、《读杜记疑》与《剑外》
据梁实秋答丘彦明问,《读杜记疑》前后共两辑。第一辑有5则。1.“月是故乡明”。语出杜甫《月夜忆舍弟》。2.“‘浮瓜’与‘裂饼’”。见于《信行远修水筒》。3.“杜甫诸弟”。杜诗从未提及其兄,或是早故;但数及诸弟,有颖、观、丰、占,其行列如何,若仔细探究,“似尚可略得消息”。4.“灯前细雨檐花落”。语出《醉时歌》。5.《槐叶冷淘》。诗分两段,各十句。上段“述冷淘制法”,下段则“不忘献芹之意”。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则是“路远思恐泥”之句[13]。
20世纪70年代初,梁实秋又应友人之邀,在中国台湾《中华日报》副刊开辟《四宜轩杂记》专栏,发表读书札记60篇,《读杜记疑》第二辑与《剑外》均系其中篇章[14]。第二辑有11则:1.“卖药与药栏”。前者见于《进三大礼赋表》,后者见于《有客》。2.“况余白首”。语出《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文。3.“乌鬼”。语出《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4.“他日”。语出《秋兴八首》之“丛菊两开他日泪”。5.“不觉前贤畏后生”。语出《戏为六绝句》之一。末署“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六日”。不知此一时间是单指第五则的写作时间,抑或包括前四则?6.“鸡狗亦得将”。语出《新婚别》。末署“一九七三年三月一二日”。7.“漫与”。语出《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对于“漫与”与“漫兴”之别,俞樾《茶香室丛钞》曾引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认为其意为“即景口占,率意而作”,而梁实秋则深表赞同[15]。8.“丧家狗”。语出《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9.“不是烦形胜,深愁畏损神”。语出《上白帝城二首》第一首。末署“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四日”。10.“天子呼来不上船”。语出《饮中八仙歌》之“李白”。11.“藤轮”。语出《赠王二十四侍御契》。末署“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日”[13]294-301。
《读杜记疑》观点新颖,启人良多。访谈中,梁实秋曾向丘彦明表示,“此后仍将继续发表我的疑点”[1]257,但在其逝世之前,未再见有关文字发表。
至于《剑外》一文,则是针对杜诗“剑外忽传收蓟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剑外”提出新解,认为当指“剑门以北长安一带”,其理据有二。一是亲身历见。“按剑门天险”,“是自广汉穿过剑阁而入汉中必经之地”。抗战时期,梁实秋曾途经其地,“因为汽车抛锚,在县城外一小茆店留宿一夜,印象益为深刻”。二是据李白《蜀道难》《上皇西巡南京歌》及张载《剑阁铭》,“剑阁是蜀之北方门户”。而杜甫作此诗,时在梓州,“剑阁即在梓橦之东北”,“捷报是从河南河北传到长安,再由长安传到剑南”,以此推断,故得出上一结论[16]。不过,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广泛认可,一般论者,仍坚持认为“剑外”是指剑南蜀中[17]。
梁实秋对于杜甫和杜诗,由热爱转化为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在于抗战。如其在评论《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和《杜少陵评传》时所说,李白与杜甫均曾“遭遇乱离,流寓巴蜀”,“吾人于颠沛之中”读此两本评传,“当然倍增兴趣”[3]14。正是在抗战时期,大批文人学者流落西南的经历,与杜甫当年“漂泊西南天地间”的生活颇多相似之处,因而对杜诗的体认尤为深切。基于这种异代而心通的同情与共鸣,进而引发了杜甫研究的热潮,梁实秋的杜甫研究,即发轫于其中。虽然此一时期,其论杜之作甚少,成文者目前仅见一篇,但此间创作的《雅舍小品》中对于杜诗的引用与化用,却比比皆是。而梁实秋此后的杜甫研究,如对《客夜》的赏析、对“剑外”的新解等,都彰显出抗战的影响。
梁实秋研究杜诗,重在理解诗义。“历代注解,率多在‘无一字无来历’说法影响之下,致力于说明某字某词见于何书,对于诗句之意义常不措意。仇注、钱注、朱注、九家注、千家注,莫不皆然”,在他看来,“这是一大缺点”,并追问道:“中国字词只有这么多,诗人使用字词与古人雷同,未必即是依傍古人。纵然是依傍古人,庸又何妨?指出其雷同之处,又有何益?”[1]257正因为如此,梁实秋更关注的是杜诗意蕴的阐发。
总的来看,梁实秋论杜,颇见学术功力,既考证详明,辨析清晰,又洞烛幽微,发人未见,间或援引西说,稍加引申,便精彩纷呈,故其见解较之旧日朴学,更显圆活通透。这也使其对杜诗的论述,呈现出崭新的研究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