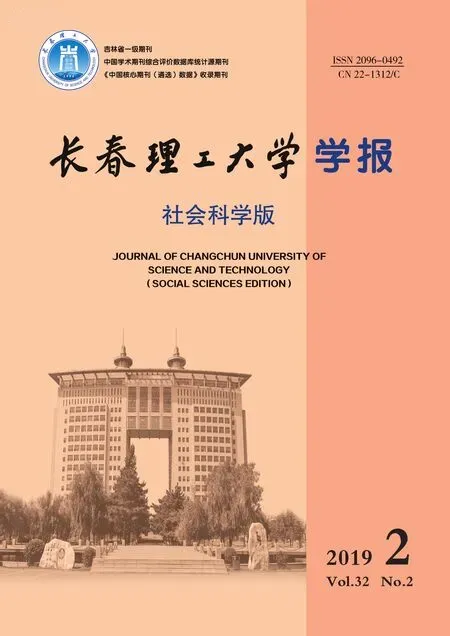《月光下的旅人》的爱情伦理与死亡想象
符 晓,陈瑞莲
(长春理工大学,吉林长春,130000)
瑟尔伯·昂托是匈牙利20世纪文学代表人物之一,1901年出生于一个皈依天主教的犹太家庭,1945年死于纳粹枪下。他编著的《匈牙利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至今仍是匈牙利学术界的经典之作,《月光下的旅人》在匈牙利更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讲述了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米哈伊为了寻找爱情而经历的一系列奇遇故事,他在与新婚妻子的旅行中临阵脱逃,为了追寻年少时的感情和回忆在异乡颠沛流离。在小说中,爱情伦理和死亡想象是两个重要的主题,也是主角米哈伊看似中规中矩的人生中不那么平凡的两个关键词。米哈伊一方面与三位女性产生了情感纠葛,爱情使他的内心痛苦不堪;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想象的方式不断经历并寻求着死亡。他在这二者中反复挣扎,最终选择向现实妥协,回归到了原有的生活。《月光下的旅人》,看似是一部畅销小说,但是小说深处却泛溢出了诸多思想和哲学。米哈伊为何会在爱情和死亡中产生痛苦和犹疑?爱情伦理和死亡想象在小说中分别有着怎样深刻的内涵?二者最终又是如何产生和解的?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矛盾的欲望选择:昂托的爱情伦理
《月光下的旅人》无疑是一部爱情小说,匈牙利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称这部小说无论是对人类有爱的人、对自己有爱的人、对存在有爱的人还是对学术有爱的人都能从中获益。[1]286昂托笔下的爱情不是单纯美好的,主角米哈伊分别与三位女性产生了情感纠葛,表现了其不同的情感和欲望追求,这使得《月光下的旅人》中的爱情主题不仅停留在情感本身,还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伦理内涵。
艾娃是米哈伊欲望选择中自由意志的体现。米哈伊对艾娃的爱是隐晦深刻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渴望,这种渴望表现在艾娃之于米哈伊的遥不可及上,艾娃的置之不理使他内心的感情越发强烈。这种爱情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纯粹的自由意志,米哈伊爱上的是她的神秘和距离感,是他自己所不具备的自由和神秘。因此,米哈伊对艾娃的爱情可以看作是对自由的追求,他将对自由的渴望投射在艾娃身上。由于投射是一个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主体对客体的情感转移是不受控制的[2]50,因此在小说中米哈伊对于艾娃的爱情是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的,也就是说,在看到艾娃的那一刻起米哈伊就将这个女子和自由关联在了一起,并产生了发自内心的纯粹的爱慕。从某种意义上说,艾娃对于米哈伊而言是博克所谓的崇高,是夹杂着痛感的快感,是由痛感转化来的快感,也就是当对象与主体保持一定距离时才是崇高的对象。[3]在艾娃面前,米哈伊一直保持着一种受害者的形象,这种关系使得双方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扩大,艾娃给予他的伤痛越多,米哈伊对她产生的崇高感就越强烈,这种情感经过堆积之后便发展为了无法抑制的欲望,促使米哈伊打破束缚,踏上追寻之路。
爱尔琦则代表了米哈伊内心欲望挣扎下形成的伦理悖论。所谓伦理悖论,指的是在同一条件下相同选择出现的两种在伦理上相互矛盾的结果[4]262。米哈伊选择爱尔琦原本是服从欲望的行为,但是最终却演变成逃离的结果。一方面,与有夫之妇通奸是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米哈伊对于爱尔琦的追求是遵从内心情欲的表现;另一方面,尽管与爱尔琦的感情始于不合道德的通奸,但是米哈伊最终仍然选择符合法律的婚姻形式来处理这段感情,可见在与爱尔琦的感情中,他最终选择以道德情感来完成伦理的选择,这种带有道德约束的情感选择最终以欲望寻求失败而告终。事实上,爱尔琦的性格和行为方式与米哈伊十分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样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爱尔琦在爱情上并非是完全自由的,她就是米哈伊的化身。因此,米哈伊对爱尔琦的爱与其说是两性之间的感情,不如说是拉·罗什福科意义上的“自爱”。“自爱即对自己以及适合于自己所有东西的爱。”[5]爱尔琦作为米哈伊的投射,是其自尊却软弱的性格化身。米哈伊在爱尔琦身上看到的是自己行为模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正如罗什福科所言,“我们只是依照我们的自爱来感觉自己的善和恶”,[2]416与爱尔琦的爱情其实是米哈伊对自我压抑的一种认同,这意味着他与爱尔琦作为同被道德约束的命运共同体,在欲望追求上注定会是失败的结局。
米莉珍是米哈伊欲望暂时转移的表现,代表了他的性欲本能和冲动选择。冲动是自由意志的表现形式,往往从非理性意识转化而来[4]247。米哈伊与米莉珍的交往显然只是因为一时兴起,在精神情感长期寻求失败的情况下他选择暂时转移了目标,在这一刻他的理性是缺失的。事实上这个美国女孩的外形并不符合米哈伊的审美要求,但是这位异国女子唤醒了米哈伊心中压抑已久的肉欲。吕克·费里认为,“情欲的爱的特殊性在于,有时候它更多的是靠不在场,而非在场;在消费情欲时,人一方面被在场的被爱对象滋养,同样也依靠不在场的被爱对象。”[6]也就是说,米哈伊在沉迷于米莉珍肉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艾娃的追求,米莉珍的愚笨更凸显出艾娃的崇高和神秘。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肉欲的一时释放反而加深了米哈伊对于精神世界的渴求,从而将剩下的情感继续投射在艾娃身上,因此他对于米莉珍的感情不是持久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米莉珍对米哈伊而言毫无价值,正是这段偶然的邂逅让他意识到米莉珍只是偶然出现的意识参照体,他最终只能回归到自己原有的生活。这实际上是米哈伊与自己内心斗争的一次妥协,米莉珍代表的偶然性促使他想要迫切地找回自己年少时期的渴望,也就是对艾娃所象征的那种有距离感的爱情和自由。
由此可见,艾娃、爱尔琦和米莉珍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伦理结,伦理结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矛盾与冲突的直接体现[4]258,这三名女子形成的伦理结代表了三种爱情可能存在的方式,即崇高的精神上的爱情、带有妥协性质的无爱的婚姻以及建立在肉欲之上的心灵慰藉。而三种爱情的产生正是由米哈伊性格中的矛盾性所导致的,他一方面对过去的爱情有所怀念,一方面却迟迟不肯回到故乡;他对爱尔琦心怀愧疚,却仍然选择离开她;他对艾娃一往情深,但是又能毫无心理负担地和米莉珍发生性关系。米哈伊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充满了矛盾性,他在爱情伦理之中是摇摆不定的,而正是他个性中的矛盾和延宕使得他的每一段感情都以悲剧收场。同时,米哈伊的三段感情经历也是其内心三种欲望的表现。艾娃代表着米哈伊“本我”中崇高的部分,表明他对精神层面上的情感有所渴求;米莉珍则是其“本我”中力比多的象征,能发泄其长期压抑的性欲。而当他追求艾娃无果、肉体欲望亦无法满足之际,就将自我的欲望暂时压抑,转而把情感投射到爱尔琦身上。因此,爱情在《月光下的旅人》中就被昂托赋予了多种内涵,作者借米哈伊的视角将爱与欲结合起来,形成了其特有的爱情伦理。
二、“向死而生”:戏剧表演和幻觉下的死亡想象
在爱情纷纷以悲剧收场的前提下,米哈伊开始选择死亡,其性格中的矛盾性不仅导致其情场失意,也促使了他在追寻死亡的道路上犹豫不决,停留于想象层面。死亡,一直都与主人公米哈伊相生相伴,“病理性死亡想象”成为他的重要标签。[7]是做一个平凡的人,回归现实,还是像托马西一样以自己理想中的状态死去,这两种想法撕扯着米哈伊的心,由于无法在二者中作出抉择,因而最终只能让死亡停留在想象阶段,无法真正地付诸行动。因此,死亡与爱情一样,也是小说中一个重要的主题,那么,昂托为什么要在一部爱情小说中着重表现死亡想象呢?这种死亡又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呢?
可以肯定的是,早年在匈牙利的往事是米哈伊死亡想象的来源。一方面,托马西和艾娃的戏剧游戏是米哈伊对死亡最原始的印象。托马西和艾娃兄妹对死亡的潜意识体现在戏剧中的方方面面,那些戏剧游戏的高潮总是有惨烈死亡的场景。[1]25在观看兄妹俩表演的同时就为他以后的死亡想象和渴求埋下了种子,而当他亲身参与戏剧表演时又作为当事人直接参与死亡。表演毫无疑问是需要想象力的,尽管米哈伊不具备什么表演天赋,但正因为他在这方面的愚笨才使得他练习如何死亡的经验更加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哈伊的每次练习都经历了一次死亡想象,因此,尽管真正的死亡具有不可经验性,[8]13在表演不同的死亡情节中,他却对死亡不再陌生。另一方面,埃尔文的宗教哲学和死亡哲学也对米哈伊的死亡想象产生了影响。埃尔文使他对死亡有一种本能的“好感”,所以对他来说,“向死而生”和赴死都是自然而然的事。[7]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生命存在意义的源泉,人生就是一个逐渐趋向死亡的过程。埃尔文的这种面对死亡的态度显然在米哈伊心中埋下了死亡快感的种子。同时,在米哈伊与做了神父的埃尔文重逢时,他真实地感受到与宗教融为一体的埃尔文的那种神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使米哈伊获得了新生,埃尔文对于死亡的泰然弱化了其心中对于真实死亡的渴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米哈伊的死亡想象。
同时,还应注意到的是,托马西的几次自杀和最终死亡也是促成米哈伊追寻死亡想象的重要原因。托马西共尝试过三次自杀,其中米哈伊亲身参与了第二次自杀行动的全过程,这次死亡行动与他之前参与的戏剧表演具有相似之处。在醉酒的状态下,米哈伊进入了一种眩晕的状态,这种状态与戏剧表演时一样,都是不真实的;托马西自杀用的吗啡来自艾娃,这与此前的游戏一样,都是由艾娃扮演施虐者,米哈伊充当受害者。因此,这次死亡行为实际上是一次死亡表演,自杀失败也就意味着想象失败,表明米哈伊在那个阶段尚且无法从死亡想象中获得真正的满足。米哈伊在托马西的死亡追寻上看到了一种死亡快感的可能性,他对于死亡的最初印象来源于托马西对于上吊窒息的愉悦。在死亡想象的层面上,托马西始终是一个引导者,他先于米哈伊而死,从某种意义上给米哈伊建立了一个实践死亡的榜样,促使其在追求死亡的路上渐行渐远。
在《月光下的旅人》中,米哈伊的“死亡”与他的幻觉息息相关。米哈伊死亡想象的源头来自故乡匈牙利,而他真正开始实施想象的高潮却发生在意大利,特别是他产生的几次幻觉,在其死亡想象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米哈伊将自己的幻觉当成是一种病症,但是这些幻觉和臆想对于情节的推动发展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一是米哈伊与托马西开始成为朋友的时候,在米哈伊的幻觉中,他被漩涡擒住马上就要死去,而此时托马西的出现成为了他倾诉幻觉的对象。在这次幻觉中,米哈伊经历了一次死亡想象。二是米哈伊邂逅米莉珍之后,在广场上他再一次感受到了漩涡,这次死亡幻觉让他重遇了厄尔斯利医生,开启了去古比奥的契机。三是米哈伊在济慈墓前将几个英国人看成了木偶、机器人,他在不可名状的存世恐惧中失魂落魄,[1]165尽管是白天但是依然感受到了死亡的黑暗恐惧,而这个英国人恰好是艾娃认识的对象。四是在完成教父的职责之后,米哈伊醉倒在床上,发觉周围的人想要对他谋财害命,在意识极度模糊的状态下他一方面畏惧死亡,一方面又对即将发生的事充满期待,而事实上这都是他臆想出来的幻觉而已。在这四次幻觉中,米哈伊的死亡想象程度是逐渐加深的,从一开始的广场恐惧和漩涡恐惧,逐步发展为一种被害妄想,他最终在第四次幻想中获得了满足,在那户意大利人家里,他在恐惧和幻象中实现了少年时代以来困扰着他的欲求,[1]281也就是说,对于此时的米哈伊而言,可惧的不是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恐惧,[9]他之于死亡的需求最终仍停留在想象层面,尽管他对于死亡的想象越发阴暗和残酷,但是这种消极发展到极致时,便意味着其内心的欲望已经通过臆想和幻觉完全释放了,因而不通过实际行动也能获得一种满足。正如荣格所言,“幻觉是真正的象征,是某种有独立存在权利,但尚未完全为人知晓的东西的表达。”[10]幻觉在小说中并不是一种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病征,而是米哈伊内心真实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只是这种表达表现为死亡想象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死亡在小说中不仅代表着生命的终结,也是文明和历史的重要象征。米哈伊在与瓦尔德海姆的对话中曾讨论过文明与死亡的关系问题,后者认为“文明越强大,死之爱就越好地埋藏在意识下方。”[1]188越是文明的时代,人们就越惧怕提及死亡,因此,米哈伊对于死亡的追求和想象实质上是对于现代文明的一种无声的抵抗,他怀念过去并对现在和未来表现出了消极的态度。也就是说,如果死亡观念代表了过去的传统,避讳死亡象征着现代,那么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米哈伊显然是倾向于前者的。同时,发生死亡想象的地点匈牙利和意大利在小说中也形成了对照,米哈伊一直憧憬着意大利的古旧传统,因而迟迟不愿意回到故乡匈牙利接收家族生意。从这个层面上说,意大利之于米哈伊是传统的象征,而匈牙利则代表了现代。因此,米哈伊最终选择回到故乡放弃爱情和死亡实质上是对于现代的妥协,尽管他渴望传统和死亡,但是由于性格的矛盾,使其最终选择了一种自我和解的方式,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和解不是米哈伊一个人的个例,而是昂托通过小说人物想要展现给读者对于匈牙利历史的问题和思考。
三、“从众”:自我与超我的和解
不论是在爱情追求还是死亡追求上,米哈伊都显然是一个失败者。在爱情方面他一无所获,不仅和爱尔琦离了婚,也没有追求到艾娃;在死亡方面他一心求死却最终活了下来,依靠对死亡的想象获得满足。米哈伊一直生活在生活和情感两方面的摇摆之中,这实际上是其自身犹豫延宕的性格所致,事实上最后表现出的是一种妥协,也就是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和解。所谓“本我”指的是个体的潜意识,代表人类最原始的欲望,追求为乐原则,[11]135而“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12]“自我”则是“本我”和“超我”最终调和的结果。米哈伊事实上一直生活在这种所谓的“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最终“从众”成为通往澄明的必然路径。[7]在面对爱情和死亡时,他的内心始终有两股力量在来回拉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条符合大众价值观的平凡之路。
小说中的三位女性分别代表了米哈伊心中感情欲望的本我和自我,在与三位女性的情感经历中,米哈伊在本我和超我的对立中进行了两次和解。对于米哈伊而言,爱情的本我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艾娃为代表的精神上的崇高,二是以米莉珍为代表的肉体上的欢愉。米哈伊对于爱情不是简单的肉欲满足,艾娃的神秘和距离感催生了他心中对于更高境界的爱情的向往,米哈伊显然从这场爱恋中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艾娃对他的爱答不理使其内心情感更为强烈,是促使他离开爱尔琦的直接动因;而在米莉珍那里,米哈伊获得的是纯粹的性快感,在与米莉珍的欢爱中他的本我中属于力比多的部分在此彻底解放了。但是,米哈伊并不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人,他的家庭教育背景和现实压力让他无法完全遵从“本我”去选择爱情,在感情方面,米哈伊无疑是一个略显懦弱和延宕的人,他必须依靠家里的经济条件来支撑自己踏上追寻之旅,也不得不面对外界的社会舆论和压力,因此,对于家庭的责任和道德良心就构成了其心中的超我。选择爱尔琦作为妻子是米哈伊对“本我”和“超我”的第一次和解,爱尔琦的美丽符合米哈伊“本我”中对于美的部分追求,同时她良好的出身也符合家庭对他的婚姻要求,爱尔琦作为这两者的结合体是米哈伊“自我”的体现。也就是说,“自我”作为理性和常识结合的思想,[11]101融合了“本我”的欲望和“超我”的约束,最终化身为爱尔琦本人。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米哈伊对于艾娃的向往超越了“自我”的选择,这意味着“本我”和“超我”的第一次和解是不完全的。当艾娃与米哈伊再次重逢并亲口说出自己受不了和米哈伊相处时,她与米哈伊之间的距离被无限扩大,这种不可感的距离使艾娃在米哈伊心中不再是可感的崇高,而是遥不可及的。这意味着米哈伊追求的“本我”对象已经不复存在,因而不得不与现实第二次和解,也就导致了其最后爱情的一无所获。
死亡作为米哈伊在小说中始终追求的元素之一,也经历了这样一种“本我”和“超我”从对立到和解的过程。一方面,米哈伊对于死亡的欲望实际上是一种死亡本能的表现,米哈伊寻求死亡,其实是对生命个体性的追求,用弗洛伊德本人的话说,“如果我们必须去死,那么服从一种至高无上的必然性,总比屈从某种本来或许可以避免的偶然遭遇要让人好受一些。”[8]124但是,米哈伊对现实世界是存有依恋的,在参与托马西的第二次自杀时,他却想到了艾娃,他的“自我”很难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平衡,导致他成为一个怯懦、敏感、孤独和游移的人,体现出来的是歌德所谓哈姆雷特的那种“软弱”。[7]因此,在米哈伊身上充分体现了他对死亡感受的两重性,首先它似乎是令人向往的解脱,其次它是一个可怕的阴影,[8]107因为一旦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对于米哈伊而言,死亡对他来说是对爱情,或者说对艾娃的一种背叛,这是属于他死亡层面的“超我”,这种“超我”本身几乎等同于罪恶感,[11]120约束着米哈伊对于死亡的“本我”欲望。在这种对立下,米哈伊只能选择在想象中体验死亡,因而可以说他的死亡想象实质上是“本我”和“超我”的另一种和解结果。另一方面,死亡所代表的传统观念是米哈伊内心所追求的,米哈伊之所以“迷恋”死亡,完全是出于对传统的“忠贞”。[7]异乡的古旧和文化是其所向往的,因此,米哈伊“本我”中仍是一个传统的人,故乡匈牙利所代表的现代资本社会是他无法接受的,他企图通过死亡的方式来抵抗现代发展的侵蚀,但最终无力反抗而选择了妥协。对于米哈伊而言,束缚他的“超我”不仅是自己性格中延宕矛盾的一面,也来源于社会的舆论以及家庭施加的压力,他无法通过死亡完全回归传统,因而只能通过想象的方式达到一种不完全的死亡,最终完成对现代的妥协。
因此,《月光下的旅人》实际上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即人究竟能否与自己和解?人应该如何实现自我和解?事实上,米哈伊在分别进行爱情和解与死亡和解的同时,在更高层面上也完成了一次爱的本能和死亡本能的和解。赫林认为,生物体中存在两种一直在发生作用的过程,这两种过程向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一个过程起到建设或同化的作用,另一个则发挥着破坏或异化的作用。[11]32同样,对于米哈伊而言,爱情象征着一种生命的希望,他对爱情的追求大体上是前进性的;而死亡则是彻底的破坏和毁灭,是一切的终结。他一方面受死亡本能引导,在幻觉和臆想中企图走向毁灭;另一方面则在努力使自己拥有真正的爱情,使自己的情感获得新生。这两种本能看似互相对立,实际却可以相互融合。破坏的本能通常是为了得到宣泄,它的惯常做法是为性的本能服务,[11]112在米哈伊早期进行的戏剧游戏中,他的死亡表演由于艾娃的加入而掺杂了情色行为,可以说他的死亡想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爱的影响;而他对艾娃的爱情是以一种近乎受虐的心理状态进行的。因此,死亡本能与爱的本能绝不是独立分割的两个个体,在爱情与死亡的对立中,米哈伊却让二者互相交织在一起。正如小说最后所言,“只要人活着,总还可能发生点什么”,而昂托正是用米哈伊的故事向读者揭示了生命的真实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