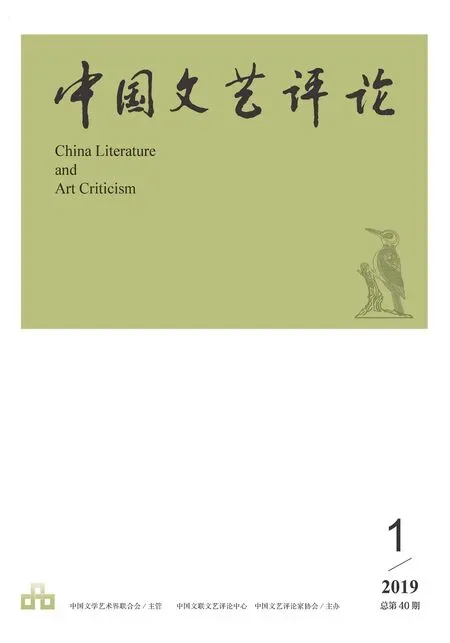曲之鸣心者方能铭心
——访作曲家杜鸣心
采访人:班丽霞

杜鸣心简介:
当代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湖北潜江人。1928年生,早年就学于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1954年赴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归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至今,是该学院十名特聘教授之一、终身学术委员。共创作各类体裁音乐作品近百部,代表作有舞剧《鱼美人》《红色娘子军》(与吴祖强等人合作)、《牡丹仙子》,三部钢琴协奏曲,两部小提琴协奏曲,交响幻想曲《洛神》,交响曲《长城颂》,低音提琴独奏曲《随想曲》等。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采》曾获第八届全国交响乐比赛金奖。作为作曲专业教授,为中国音乐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音乐人才。其学生之一、作曲家王立平对恩师的评价是:“乐章传天下功成名就,德艺育后人桃李芬芳”。一、乐之源:莫斯科与民间
班丽霞(以下简称“班”):
杜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专访。在准备采访资料时,看到已有不少访谈和纪录片对您传奇般的习乐经历做过详细介绍,今天主要想跟您谈一谈具体的音乐创作和代表性作品。您从事作曲已有六十余年,能否谈谈对您的创作和观念影响最大的作曲家有哪些?杜鸣心(以下简称“杜”):
我过去的专业是钢琴演奏,正式学习作曲是到了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之后才开始的。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楚拉基,他是全苏艺术家协会的主席,后又当过莫斯科大剧院的院长,由他管理的两个剧院和管弦乐队每天都有高水平的演出。我通常是去他的剧院办公室上主课,课后他就安排我在他的专用包厢看演出,这个观摩学习的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若说对我的创作影响最大或者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像柴科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是我在莫斯科听的最多的几位作曲家,他们的音乐非常有特点。柴科夫斯基不必多说,这是国内听众都很熟悉的。普罗科菲耶夫再怎么写,骨子里都有俄罗斯的音响和灵魂渗透在他的作品里面。肖斯塔科维奇要比普罗科菲耶夫走得更远一些,音乐手法更前卫,但你若仔细地多听几遍他的作品,还是能感受到俄罗斯音乐与文化的根。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大音乐厅现场听过他的《第十交响曲》,这个音乐厅建造于十月革命以前,是俄罗斯最好的音乐厅,许多世界著名的乐团来此演出。《第十交响曲》(1953)刚刚写完不久,由当时著名的指挥家穆拉文斯基带领列宁格勒交响乐团隆重演出,肖斯塔科维奇本人也在场,演出效果非常好,震撼人心。尽管这部作品写得很现代、前卫,但大家聆听时很受感染,完全被音乐给吸引住了。现场听众觉得这完全是俄罗斯的,是俄罗斯自己的现代音乐,虽然技术上很前卫,但完全可以被大家接受。所以,我在莫斯科的这些学习机会非常难得,当时在国内是不可能有的。
图1 1958年在莫斯科大剧院前
另外,我在这座大音乐厅还听过美国费城交响乐团的演奏,由奥曼迪指挥,当时演出的是美国作曲家巴伯的《弦乐柔板》,弦乐队的音响效果非常细腻,与俄罗斯管弦乐队有很大的不同。俄罗斯的弦乐你能听到za-zaza-za换弓的声音,铜管再怎么响亮也盖不过弦乐的声音,那种相互之间的张力和整体性,是国内管弦乐队所欠缺的。我对我们的乐队最不满足的就是弦乐,声音太弱,铜管一出弦乐声音就没有了。这既跟演奏方法有关,也跟我们弦乐器本身的音质有关。我在写乐队作品的时候特别注意弦乐,我自己能演奏小提琴,这个经验对于创作非常重要。
班:
为了创作的需要,您是否经常去做音乐采风,能否谈一两个令您印象特别深刻并对您的创作有直接影响的民间音乐类型?杜:
作曲系的学生在大学期间至少有一两次下乡采风活动,我因为创作任务比较繁重,学校没安排我带学生去采风。但在创作《红色娘子军》期间,我自己多次去海南岛采风,听了很多当地的民歌和黎族的舞曲,有一首黎族的民歌围绕Sol Do Мi Sol四个音展开,我就是用这个素材写了那段《快乐的女战士》。它既是海南的、黎族的,又是我自己的。我们作为专业的作曲家,应该多向自己的民族民间音乐学习。对于民歌,要学会吸收、消化,汲取营养,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创作出新的音乐。班:
《红色娘子军》中家喻户晓的《万泉河水清又清》也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吧?杜:
对,《万泉河水》的民歌原型是一首五指山区的山歌,我在去海南岛之前就知道这首民歌了,在海南岛又听了民间歌手的现场演唱,印象就更深刻了。所以在创作《万泉河水》时立刻就想到这首民歌,歌曲前两句跟民歌基本接近,后面则经过了我的变形和发展,同时又转了一个调,使得它更明朗,更有力量。班:
优秀的作曲家能把一条河变成音乐,像小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斯美塔那的《沃尔塔瓦河》、冼星海笔下的黄河,还有您创作的万泉河。有一次我去海南岛琼州看望一位老师,他指着窗外的一条河说,这就是万泉河。我和同行的朋友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唱起了“万泉河水清又清”。杜:
是这样,万泉河看上去并不宽,就是很平常的一条河,但是用音乐一表达,这条河就变得亲近了。老百姓即使没见过这条河,也能通过音乐记住“万泉河”的名字。关于民间音乐还有一个例子,解放初期,我们去过河北定县一个民间音乐比较活跃的村子,名叫子位村,这里盛行吹歌会,村民们都很喜欢音乐,农闲时就在一起吹吹打打,作为一种自我消遣。我在创作《鱼美人》时,中间第二幕有一个鱼美人与猎人的婚礼场面,先是一个集体的舞蹈,之后就是“拜天地”。“拜天地”是一个民俗的礼仪,我就想到了在子位村听到的吹歌音乐,但是那次采风距离我写《鱼美人》已过去近10年,具体音调已记不得了,但我对吹歌会的印象还在那里,我就凭着这个印象写了“拜天地”的音乐。所以说,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对于创作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是说让你移过来就用,而是回想那种情景和气氛,农民聚会时吹吹打打的那种神情,也就是要抓住民间音乐的神韵,在自我消化之后重新创造新的音乐。
二、乐之魂:旋律是情感交流的媒介
班:
除了刚才提到的舞剧《鱼美人》和《红色娘子军》的选段,还想听您谈谈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采》 ,这是一部公认的雅俗共赏的经典作品,您个人对这部作品有何评价?杜:《
春之采》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我用了简单的四音素材Sol Do La Re贯穿整部作品。当时陈佐湟在匈牙利指挥演出这部作品,由一位匈牙利钢琴家担任独奏,陈佐湟回来后很激动地告诉我,大家听了这个作品觉得很有意思,乐队成员反馈说,作品的材料很精练、节约,但是里面有音乐。班:
我很喜欢宁静的第二乐章,可以单曲循环地听上一天。您的主题设计很是巧妙,第一句把人的目光引向远方,第二句的倒影又让思绪倒转回内心。这一远一近,无比简洁又寓意深远。这个主题听起来有一点中国风格,您是否受到哪首民歌的影响?杜:
没有,这个主题没有明确的地域风格,完全是我自己创作的。这还是要感谢我的老师的指导。在莫斯科,我们一周要上两次作曲主课,每次都必须有新作品。楚拉基老师每次上课都在钢琴上弹奏我的作品,告诉我哪里少一小节,哪里多一小节,这完全基于一种对结构合理性的内在感觉。楚拉基自己也是一位很好的作曲家,创作过各种体裁的作品。所以他对音乐非常敏感,听了我的作品之后马上就能指出其中的问题,这里面有结构的问题,有和声的问题,也就是怎样才能让和声更有色彩和变化。他让我把他改过的地方和我自己写的部分相互比较,弄清楚为什么这样改。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我的作曲技巧才逐渐提高。正是得益于此,我的《春之采》用非常简练的素材来创作,但在全曲中有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乐曲最后结尾的时候,综合了第二乐章的主题,这让作品听起来非常完整,前后素材都是互相有联系的。班:
杜老师,您在2016年88岁高龄时还给学生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名为《器乐曲与旋律写作》,能否谈谈您开课的初衷和旋律写作的主要思维?杜:
是这样,现在国内常用的分析作品的方法比较老旧,一般还是先找到动机,然后是乐汇、乐节、乐句、乐段,对贝多芬、浪漫主义甚至现代作品的分析都在用这套方法。但是我在莫斯科留学时,作品分析老师是斯克列普科夫,他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理论教研室的主任。他的分析方法是先找到主题核心是什么,然后分析它的结构安排(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命运”主题为例),其中第一步是主题核心的呈示;第二步是主题核心的巩固,目的是加深对主题的印象;第三步是主题核心的展开;最后是主题核心的结束。以这四个发展步骤来分析主题,比前面所说的分析方法要更合理、更有说服力。但是我当时对这种分析方法并没有完全消化,直到后来我才慢慢发现我作品中的主题基本是按照这个思路创作的,所以我是在2001年之后才在作曲课上给学生讲授这个新的分析方法的。通过这样分析主题旋律,同学们才能更好地掌握旋律写作的手法。班:
谈到旋律写作,一般情况下,好听的旋律能给听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这涉及一个音乐可听性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大部分西方现代音乐排斥旋律的倾向?在有些作曲家的观念中,优美的旋律已属于过时的19世纪。杜:
西方现代音乐追求无调性,不重视旋律的写作。而我们中国的音乐非常重视旋律的委婉、优美和动听,作曲家与听众的情感交流主要是通过旋律来进行的。如果只写那些听不懂的、陌生的音乐,怎么能跟听众交流呢?现代音乐即便是采用无调性、泛调性或序列,其旋律也有自己的走向和过程,这个走向与旋律优美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完全不顾这个传统,一味追求全新的、陌生的音响,写出来的作品只有自己喜欢,别人都听不懂,只有极少人欣赏,大多数人都不能欣赏,一般只演奏一次就被丢进垃圾箱,这只能叫“一次性音乐”。那种认为只要有调性、有旋律的音乐就是保守或守旧的观点,我是不认同的。旋律与我们自己民族千百年来慢慢形成的欣赏习惯和传统有着血肉的联系,我们应该认真地去消化、去体验、去感受,然后再去创作新的作品。我觉得有旋律、有调性的音乐并不落后,也不保守,新的时代会有新的想法、新的结构和新的变化。
图2 1986年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音乐会
三、乐之色:配器要严谨,色彩要考究
班:
您的作品除了旋律优美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色彩性极强,听起来灵动、斑斓,您能否分享一下配器方面的经验?杜:
我觉得乐队作品写的多了,就能在配器上把握得更好一点。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配器老师是非常有名的作曲家、音乐学者瓦西连科,他的配器老师是伊万诺夫,而伊万诺夫的老师就是强力五人团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这个一脉相继的师承体系在配器上要求非常严格、严谨。科萨科夫在配器上有极深的造诣,音乐历史上有那么多的配器教科书,唯独他写的教科书中的例题全部是自己的作品,他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经验总结来教学的。斯特拉文斯基也是他的学生。我现在经常看到一些发表的乐队作品在全奏中用木管去重复铜管,特别是用黑管去重复小号的音乐,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这就是从科萨科夫的理论中学来的,如果用黑管同度重复小号,就把小号金属般的色彩抹掉,铜管辉煌的音响效果就出不来了,就好像涂上了一层灰暗的颜色,得不偿失。如果在全奏中想用木管去重复铜管,可以用双簧管重复小号,这样既可以让小号的音色变得柔和,同时又不会抹掉小号辉煌、亮丽的音色。在乐队全奏时如果想得到非常结实、辉煌和整体的音响效果,就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木管与铜管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乐队的配器色彩非常细致和考究,这方面我深受瓦西连科教授的影响。班:
您刚才提到国内乐队作品中的弦乐较弱,您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杜:
当主题出现在弦乐声部时,我常常采用第一提琴组和第二提琴组同度演奏的方式来加强弦乐的音量,这其实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原本第一提琴和第二提琴应该有声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应该有不同的层次,但为了加强弦乐声部的力量也可以采用同度的方式,这在一些国外作曲家的作品中也能见到这种用法,例如让三个声部的弦乐(一提、二提与中提)同度演奏旋律,从而产生结实、有厚度的声音效果。但是在我们平常配器的时候,特别是在弦乐的中低音区,还是应该充分发挥弦乐组四个声部的层次,其中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经常采用八度的关系以增强低声部的力量。现在国内有些年轻作曲家很忽略弦乐队的写作,经常用一大堆铜管,听的人累,吹的人也累,不仅缺乏音色上的变化,也缺乏音乐的歌唱性,但情感的流露主要依靠弦乐,木管和铜管主要是色彩性的,木管有时可以吹一些田园式的旋律线条,铜管的音色是号角式的、辉煌的,经常是作为背景来使用,而深情、动听的旋律还是要靠弦乐来表现。班:
去年(2018年)6月初我在学校听了一场室内乐音乐会,开场作品就是您为低音提琴创作的《随想曲》,若不是看到曲目单上写着您的名字,我会认为这是一位中青年作曲家的作品,构思很有新意,技术上也有很大难度,与您往常创作的那些雅俗共赏的作品有明显区别。杜:《
随想曲》是我校低音提琴专业的教授陈子平委约的,他要去美国演出,托我写一部新作品。国内专为低音提琴创作的作品非常少,想到他是去美国演奏,我有意用了一些泛调性的、比较现代的手法。但其实我还写过比《随想曲》还要复杂一些的室内乐作品,有一首弦乐五重奏采用了不少新技法,后在叶小纲的建议下改写成钢琴与弦乐队作品,编制是一提、二提、中提、大提,另加两个贝斯和钢琴,并且改名为《布达拉宫之梦》,以原有的五重奏做底稿,整理改编之后展开得更充分一些。2015年中国交响乐团演奏过一次,之后我又做了一点修改,看看能否找机会再演一次。四、乐之维:把握结构与时间的分寸感
班:
您曾经对您的学生瞿小松讲到过音乐的结构感、时间的分寸感,或时间上的恰到好处。大型的音乐作品犹如建筑,其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是在时间中建构起来的,您是如何把握这种分寸感或结构感的?杜:
这就是我们为何要学习作品分析的原因,我们要分析古典乐派、浪漫乐派以及近现代作曲家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在音乐结构上非常严谨、完善或者说专业化,我们要学习他们是如何来安排结构框架的,什么样的音乐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才是合理的。2018年8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在国家大剧院听了上海爱乐乐团今年(2018年)音乐季的开幕音乐会,第二场是马勒的第一交响曲,乐队规模很大,有六支圆号、四支小号,但在段落结构的安排上有一点松散,段落之间快慢强弱的交替显得拖沓、不够紧凑,四个乐章下来快一个钟头,听着很费劲儿。马勒的作品与俄罗斯乐派很不一样,俄罗斯音乐在结构上很严谨,没有任何多余的“话”,听起来非常集中。这种结构是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古典交响音乐传承下来的,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大家公认这种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大多数交响音乐都采用奏鸣曲式,它有两个对比主题,这恰到好处,因为如果主题太多会分散听众的注意力,一个主题出现之后,你要去经营它、深化它,从各个侧面将其立体化,充分挖掘它的可能性,这样才能让观众对这个主题有深刻印象,被主题所感染,不能刚把一个主题介绍给听众就扔在旁边另起一个主题,那就跟“拉洋片”一样了。班:
您写过大量的舞剧音乐,如《鱼美人》(1959)、《红 色 娘 子 军》(1964)、《玄 凤》(1996)、《牡 丹 仙 子》(2004)、《凤 凰 涅 槃》(2011),能否谈一谈在创作中如何处理好音乐与舞蹈、戏剧的关系?杜:
舞剧音乐有自己的艺术特点,与写交响音乐不一样。我们在写作的时候,首先是把舞剧中的重要人物先抽出来,为这些人物创作主题。例如《鱼美人》中有三个主要人物:鱼美人、猎人和山妖。鱼美人的主题柔美纤细,像水中的女神;猎人的主题是彪悍的,充满阳刚气质;山妖是一个阴险的反面人物;还有一个人物是善良、和蔼的人参老头,他始终在帮助鱼美人和猎人。我们写鱼美人和猎人的音乐时很顺利,当时的苏联总导演古雪夫听了很满意,但写山妖时遇到了困难,主要因为最初的山妖主题过于脸谱化,一连换了五六个方案,以致于整部舞剧的音乐都快写完了,山妖的主题还没拿出来。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先用一个打击乐的特性节奏做铺垫,然后在这个节奏背景上出现山妖的主题,这样就把山妖凶狠阴险的性格刻画出来了。人物主题设计好了,一成不变也是不行的,随着人物和剧情的发展,主题也要不断发展和变化,到最后,这些主题会越来越立体化、越来越饱满,人物形象也就更丰满了。班:
这些音乐写出来之后,舞蹈家在编舞时会不会要求您在某些段落上做出调整或修改?杜:
有时候会有的。比如哪段音乐略微长了一些,哪段又短了一点,都会适当做一些调整,但是《鱼美人》中像《水草舞》《珊瑚舞》这类比较完整的音乐是不需要改动的。为了能及时做出修改,我们必须先写出钢琴谱,舞剧导演用钢琴谱的音乐给演员排练,排练过程中会注意音乐与舞蹈的关系,看看哪些地方需要调整。当然,并不是每一段都要调整,如果我们写的音乐非常完整,形象上与剧情内容也很贴切,就不需要再改动。基本上我们很少回过头来再改,因为我们的舞剧大多是分段结构,比较传统,可以一段一段地切开来写,不像一些现代的舞剧是一气呵成、中间不分段落的。五、构思新作:与冼星海的不解之缘
班:
您写过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唯独没有写过歌剧。美国长寿翁作曲家卡特在90岁时写了他的第一部歌剧《接下来是什么?》,多有意味的题目!据我所知,您早就有创作歌剧的心愿,目前是否已找到心仪的剧本?杜:
我正在构思一部关于冼星海在苏联的经历的歌剧。我在莫斯科留学时,在一家乐谱书店偶然遇到曾照顾过冼星海的俄国女士莱娅,估计国内只有我一个人见过这位女士。冼星海1940年离开延安赴苏联,为一部反映敌后游击队抗日的新闻片配乐,但第二年就爆发了苏德战争,他既不能公开身份,又没有条件回国,生活一下子就变得穷困潦倒。他曾经想搭乘来苏联访问的林彪的飞机回国,但遭到拒绝。后来他被迫撤退到哈萨克斯坦,粮食匮乏又疾病缠身,为了生存下去他不得不把自己值钱的手表、毛衣、大衣都当了,处境很惨。在这种情况下,他认识了会讲英文的莱娅,她是出生在美国的俄罗斯犹太人,19岁才随父母回到苏联。她对冼星海的生活非常照顾,在得知他是一位作曲家之后,将其介绍给哈萨克斯坦的一位音乐家,并由其为冼星海安排生活,这样才让他的处境有了起色,两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产生了感情。
图3 1988年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前
在莫斯科的乐谱书店里,莱娅看到我后轻声问:“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是啊。又问:“你是学音乐的吗?”我说是啊,我在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作曲。她听了很高兴,接着问:“你知道中国有位作曲家叫冼星海吗?”我说,当然知道,他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作曲家,写了很多音乐作品,尤其是《黄河大合唱》(我在育才学校就会唱“风在吼,马在叫”)。她接着又问我,“你愿不愿意去看看冼星海的骨灰放在哪里?”我说,当然愿意啊!就这样,我们一起打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我才知道她就是在冼星海去世前陪伴在他身边的莱娅。在陈列艺术家骨灰的大厅里,我看到了冼星海的骨灰盒,上面用俄语拼写的他的笔名“黄训”,我郑重地向冼星海的骨灰三鞠躬。遗憾的是,当日从郊区墓地回来,我和莱娅匆匆忙忙告别,没能留下她的地址,所以后来和她就没有更深一步的联系和交往,可是这段往事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后来《人民音乐》委托一位俄籍华裔音乐家左贞观先生调查冼星海在苏联的情况,他亲自去了哈萨克斯坦采访过莱娅的亲戚,后来发表了两篇相关文章。
班:
或许正是因为这次偶遇,您才对冼星海一直“情有独钟”,我们知道您曾为电视剧《冼星海》写过配乐,现在构思的这部歌剧,是您个人的创作意愿,还是有歌剧院委约?杜:
没有委约,完全是我自己的想法。目前剧本是我跟一位女诗人合作在写,我把整个结构告诉她,我们一道来写,写完之后我再来调整。中国歌剧舞剧院听说我在写歌剧,愿意与我合作,我说等剧本写出来给他们看看。题材上肯定没有问题,江泽民、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都充分肯定了冼星海在中哈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贡献,哈萨克斯坦还将阿拉木图的一条街命名为“冼星海大街”,并为他立了塑像。我们构思的剧本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冼星海临终前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正值1945年苏德战争结束不久,窗外在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到处都是焰火啊,合唱啊,而窗内的冼星海却已奄奄一息,他没能享受到胜利的果实。就在这强烈的对比之下,冼星海过世了。这个场景很揪心,也很有戏剧性。六、 心系未来:建立“中国乐派”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班:
近些年来国内一直有关于创建“中华乐派”或“中国乐派”的提法和争论,您作为音乐界的老前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杜:“
中国乐派”当然是一个很宏大的题目,我们现在提是可以提,但这不是三两天的事情,恐怕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和积累,才有可能建立起在世界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乐派。目前我们尚处于过渡阶段,还在学习国外新的技法。而“中国乐派”首先要有我们自己民族的、现代的、站得住的作品来说话,光靠演唱、演奏是不行的,像郎朗、吕思清等演奏家都是世界一流的,但建立真正的“中国乐派”还是需要有厚实的、由中国作曲家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要经得住时间考验,并真正获得世界的承认,这才是最重要的。没有站得住的作品,所有的演奏、分析和评论都是别人的。所以说,“中国乐派”的形成至少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班:
在当下活跃的国内作曲家中间,您觉得哪些比较有影响力?杜:
北京这边的叶小纲是一个有想法、正当年的作曲家,他的《大地之歌》直接挑战马勒。马勒的这部声乐交响曲,歌词选用了李白、王维等人的唐诗。但这些诗词经过法文和德文的两层翻译之后,很多内容都走样了。由中国作曲家来“正本清源”可以说是义不容辞,要和马勒相比,虽然要靠时间来印证,但他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是很不容易的。叶小纲还写过第五交响乐《鲁迅》,有独唱、朗诵和乐队,歌词都来自鲁迅本人的著作,像阿Q、祥林嫂、狂人日记等都在里面。上海那边的许舒亚也是一位有影响的作曲家,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和叶小纲就在“齐尔品作曲比赛”中获奖。现居海外的周龙、陈怡也很有影响力,一直都在写作品。我们学校的郭文景和秦文琛也是才华出众的作曲家,郭文景没有出国留学,完全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秦文琛是从德国留学的,学习了很多现代技法,但他一直在探索怎么和我们民族自己的传统相结合,作品很有新意。我听过他的唢呐协奏曲《唤凤》,高中低三支唢呐与乐队一起演奏,有独特的表现力。当然,要建立“中国乐派”只靠这几位作曲家是不够的,还需要后面的年轻人继续巩固和发扬。文化部曾请我和卞祖善、唐建平等六人去听一位青年作曲家的作品,他叫龚天鹏,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曾在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作曲。我们听的是他的第九交响曲《启航》。我对他说,我都要90岁了还没写到第九交响曲,真是望尘莫及啊!他在《启航》中用到了合唱,应该是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一种呼应,歌词取自革命先烈李大钊。我听过之后觉得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国际歌》《大路歌》等曲调的借用,有流于标签化的倾向,没有很好地融到自己的音乐里去;二是配器的某些细节还不够细致。我给他的建议是,你未来的创作道路还很长,有的是时间,要试着放下自己的光环,总结自己的经验与得失,才能在创作上更上一层楼。
班:
您从事作曲教学已近70年,对当下作曲专业的学生和年轻的音乐评论者有哪些建议和期望?杜:
年轻一代学作曲的同学比较敏感,普遍对国外作曲技术的学习热度更高一些,对国内音乐的关注反而不够。这也没什么问题,他们有的是时间来进行各种创作实验。这中间肯定有好的,也有失败的,甚至只是“一次性的”作品。年轻人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和音乐理念,思考作为一个中国作曲家如何能写出现代的、动人的中国音乐,相信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会逐渐完善自己的创作。好的音乐作品也需要评论家们的介绍和推广,鼓励和帮助作曲家们总结创作上的经验。理论家们也很重要,他不仅仅要介绍作品,还要给予一定的批评和指导,帮助作曲家看清自己的方向,否则写出的作品听众都不喜欢,只是作曲家在那里自我欣赏,变成孤家寡人是不行的。音乐就是要跟大家见面,艺术就是要有感情的交流。作品中既要有自我的表现,也要为大家说话。在创作过程中,有时会很顺利,有时则会很艰难,甚至会走一些弯路,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家们要指出一条更正确、更宽广的道路让他们走下去。评论家既要鼓励他们写出好作品,还要指出他们创作中的不足,帮助他们走向更广阔的创作道路。这样,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和付出,才能逐渐建立起我们的中国乐派,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和欢迎,否则就只是说说而已。
访后跋语:
给音乐家做专访总有不可避免的缺漏,因为文字只能如实地记录“说”,对于“唱”却是无能为力。杜先生在交谈中提到的音乐,无论是自己创作的还是其他作曲家的作品,都是张口即唱,声情并茂。谈话时的杜先生还是恬淡温和、娓娓道来,但只要一开唱,立刻就变得神采奕奕,容光焕发,一边唱着一边像指挥家那样挥舞着拍子,整个人完全融进音乐之中,正可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先生对于音乐的敏感与热情生动地体现在他的吟唱中,常给我一种返老还童的即视感。
先生对于不同来源的音乐素材与风格有着极强的包容心,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民间与学院都被他兼收并蓄在自己的创作中,并且不是简单的摘引或并置,而是带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加以创造性地吸收与转化。当下在音乐学院作曲系中,有不少青年学生崇尚西方先锋派音乐的技法与叛逆精神,老一辈音乐家大多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但杜先生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理解与宽容,他更愿意给年轻人充分的时间与空间,让他们在不断的探索与实验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先生曾对日本作曲家团伊玖磨的观点深表赞同,即“作曲家应该站在一个纵横交叉的中心点上,一边吸收传统,同时要眼看八方,来吸收世界的现代技法”。这种多元包容的态度也贯穿在他的作曲教学中,受莫斯科作曲教学体系的影响,杜先生对于传统作曲基础的要求非常严格,他相信只有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才有足够的专业功力去探索更具个性化的创新之路。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前苏联教学体系一味排斥西方新音乐的缺陷,鼓励学生广泛学习和吸收各种现代技法,只是他对于那种罔顾传统、只为标新立异的倾向持明确的批评态度。其学生中像王立平、徐沛东、叶小纲、瞿小松、刘索拉等都是极具个性、各有成就的作曲家,这与杜先生严谨而开阔的教学理念是分不开的。
杜先生创作的《鱼美人》(尤其是其中的《水草舞》)、《红色娘子军》、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采》、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等,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公认的音乐经典。其成功的原因,除了访谈中提及的旋律优美、色彩斑斓、结构严谨等艺术特色之外,还得益于先生始终坚守的两个创作理念:一是在细节上精益求精,每个音符都师出有名,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其精练与细致经得住演奏家的反复推敲和理论家的条分缕析,这是当下许多作曲家都欠缺的艺术品质;二是自始至终心系听众,执着于创作“动情”的音乐,这在“谁在乎你听不听”的现代音乐主流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先锋派音乐的势头减退,新音乐的创作重新开始接纳调性、重视情感及与听众的交流,杜先生对音乐抒情传统的持守反而显现出一种可贵的前瞻性。大浪淘沙,沉者为金,杜先生的创作生涯与艺术之路终将证明,曲之鸣心者方能铭心存世,成为代代相传的音乐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