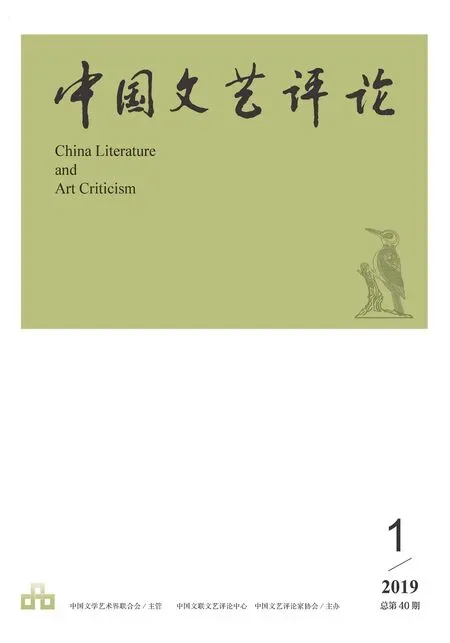论艺术创作中的感性
童 强
感性是美学的基础性问题,也是艺术发展的重要环节。要理解中国艺术与美学,必须充分考虑感性在中国历史文化环境以及表达传统方面的独特性。只有以这种意识的自觉,才可能使我们的感性表达以及独特审美融入整个人类的经验当中。
本文试图讨论艺术中的感性,但界定这一关键性的概念非常困难。人们多少可以感受并显露自己内在的感性,同时在各种艺术及交往活动中感受到他人的真情实感,这一事实使得感性的社会交流成为可能,并且成为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即使如此,它仍像无线传输中的电磁波一样,我们无法看到它。简明起见,这里的“感性”“感受性”“激情”“情感”等词都被认为是在相当重合的意义上指称我们所讨论的对象。我们不再拘泥于术语上的一致,而是强调对象本质上的统一。
艺术创作依赖特定的感性形式。中国传统的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都通过完美的艺术形式,在实现艺术功能的同时给人以最大的感染力。但艺术形式经常处于一个竞争的过程,各种表现形式经过淘汰筛选、融合吸收,最终有一些艺术表现形式获得典范的地位,成为人们充分肯定和仿效的对象。通过对这些表现形式的学习模仿,诗人、艺术家获得了文学艺术上的成功。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度的模仿,原来生动的形式变得空洞,不仅不能反映现实,而且与人们当下的感性形成较大的距离。艺术的经典样式已经不能感染人,也不能真切地反映感性的真实状态。
通常,不同的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典范;同一艺术领域,不同历史时期也都各有典范。书有钟繇、王羲之,画有吴道之、黄公望,还有元四家、清四王之类,宋代以后格律推崇杜甫,明代古文称颂唐宋八大家,又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当然这些说法在不同艺术家群体中存在争议,而且事实上对于典范本身,人们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所以重要的不是典范本身,而是后代的诗人、艺术家群体一致认为要向古人学习的观念。这一倾向构成了中国传统诗文以及书画艺术创作特有的面貌,即继承的多,创新的少。
贡布里希说,“静态社会往往重视扎实的手艺和精湛的技能,而动态社会则可能喜欢那些未曾试用过的、尽管还不成熟的方法”,当然这样的概括是受到某些条件限制的。在他看来,相对于西方绘画而言,中国传统画家偏于保守,重视传统技巧。尽可能保持传统不变,不仅在艺术领域中减弱或转移了艺术家对自我感性的密切关注,使他把创作冲动集中在技巧技能层面上,而且充分遵循了传统社会的基本法则,实现了与礼制、权力的同构。传统诗人、艺术家在社会生活中所习得的法则很自然地体现在艺术的保守理论上。
在文学艺术领域中,诗人、艺术家需要依托一个崇高的经典形式来表达,它既是作者自我的表达,又是源自伟大传统的表达。“代圣贤立言”不仅体现在内容上,实际上也体现在艺术的形式上。这种状况下,真正的自我始终处于某种模糊含混的状态中,它找到了一个使自我感性内容得以模式化的表达,但又不是使自我感性完全浮现出来的一种更为个性化的形式,所谓“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这与传统时代的“情感管理机制”完全一致。没有浮现在话语领域中的感性处于集体潜意识状态中,它们还不是感性。它们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以一种极端个性的艺术形式偶尔表现出来。
在个体化时代到来之际,固守传统经典的艺术形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艺术需要多元的表达形式。艺术家需要重新回到自我感性的层面展开对形式的探索,使感性的表现能够结合艺术的个性形式得以真正显现。自我感性是艺术面对的第一社会现实,正如桑塔耶纳所说:“任何判断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判断以人类的感情为根据。”所以回到感性,肯定不是倡导艺术家的创作使用私人语言。
一、可见的感性
我们无法看到感性本身,只能看到感性的各种表达。一般地说,感性是基于身体感觉的反应形式,我们虽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某种自身内在的活力、协调统一以及不可思议的身体自控,但无法像指证一个实体那样指认它,描述它。严格说来,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它是人的某种内在感觉。
但人的各种活动,特别是身体的活动都能够体现出一定的感性。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平常的感性形式早已被我们忽略,诸如聚会中偶尔出现一两个引人瞩目的人,会引起大家对其“神气”“性感”的赞叹。我们有兴趣讨论的并不是感性本身,而是艺术中的感性表现,艺术中感性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舞蹈。
就艺术表现的感性而言,舞蹈最为基础。科林伍德甚至认为,“舞蹈是一切语言之母”。他把语言视为“一种姿态体系”(a sуstem of gestures),发声只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功能,而不是其全部。“每个姿势都产生出一种有特征性的声音,从而使它既能通过眼睛又能通过耳朵加以领会”。基于这种“一切不同种类的语言与身体姿势都具有这样一种关系”,绘画、器乐等不同的语言都是专门化形式的身体姿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舞蹈是一切语言之母”。这一说法当然可以商榷,但在各门类艺术中,舞蹈最接近感性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文学,是作家通过语言与读者的交流,它的中介就是语言,而且诗歌中所表现的情感并不一定就是诗人自己当下的情感。按照现代诗人Т. S.艾略特的说法,诗人应该避免直接描写自己的情感。“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自然,只有有个性和情感的人才会知道要逃避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造型艺术,是艺术家通过特定的外观形式来表现情感,它有一个中介,是绘画或雕塑的材质创造的形象。同样很难说,绘画或雕塑作品的情感表现就是艺术家创作时自身的感性内容。总之,这些艺术在表现感性内容时都比较间接,只有舞蹈直呈感性、直指人心是个例外。哪怕它正在讲述一个娘子军、或者害怕纺锤的公主的故事,舞蹈本身还是让我们立刻感受到舞者身上最直接的感性特征。舞蹈的中介就是人的身体本身,所以,不论舞蹈说什么,它都会直接显现舞蹈者自己的感性。
格罗塞划分原始舞蹈为两类:摹拟式和操练式。前者多摹拟爱情与战争,性质上比较接近更早的巫术功能的舞蹈,后者接近娱乐。他认为,摹拟式舞蹈的爱情舞“实为产生戏剧的雏形,因为从历史演进的观点来看,戏剧实在是舞蹈的一种分体”。这样来看,舞蹈实有两层表现,一是纯粹的舞蹈动作本身,也就是操练式舞蹈;一是纯粹的舞蹈动作经过特定的编排,结合其他因素形成叙事语言。它用于讲述一定的故事、爱情与战争。所以摹拟舞蹈中必然包含操练式舞蹈,简单地说,舞蹈是由舞蹈动作构成,而动作是人的身体完成。“舞蹈先于所有其他艺术形式,因为它采用的不是什么器具,而是每个人永远随之携有的,说到底是所有器具中最有力的和最敏感的身体本身”。正是最有力、最敏感的身体动作体现出人的感性。这一基本的特征使得舞蹈与其他各类艺术相比更接近感性,并且直接就是感性本身。
当然,不同的舞蹈——芭蕾或广场舞的感性表达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芭蕾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在所有舞种中最为程式化的舞蹈,它积累了无比丰富的形式语言和艺术经验,能够借此展开特定的情节以及大量炫技的舞姿。即使包含大量的形式化、程式化因素,它仍然能够直接表现人的感性。坚持个人情感的抒发是舞蹈艺术唯一合法主题的观念,所以舞蹈家邓肯认为芭蕾是“一种虚伪的、荒谬的艺术”,但她看到克舍辛斯卡娅、巴甫洛娃的表演时又不能不为之倾倒。这或许可以作为高度形式化、专业化的舞蹈仍然洋溢着感性感染力的一个例证。邓肯即兴自由的现代舞蹈,则更直接生动地反映了人的情感天性。
不同于专业舞蹈,广大群众皆可参与的广场舞是民众表现自我感性的重要渠道。舞者不需要受过什么专业训练都可以跳。动作相对简单,易于掌握。但不论多么简单,不论官方正式界定的广场舞是被归为健身类活动,还是民众舞蹈,广场舞毕竟是一种舞蹈。尽管它没有看起来更简单却更专业化的Т台时装模特的表演复杂,但它肯定不是通常的走路,总是具有比行走更复杂、更富表现性的形式,具有比日常行为复杂的动作形式,有着日常生活中不存在、也不需要的按照音乐节奏做出的连贯动作。正是这种相对自由的形式使得普通民众的感性得以自由地呈现,使广场舞成为很多女性热衷的业余活动。
在众多的广场舞群体中总有一些网红(多数是女性),她们之所以“红”起来,通常都是依赖于网友的称赞与传播——观众的“投票”。除掉身高、长相、服装以及过去的训练等条件之外,她们确实是以富有个性的舞姿赢得了观众,人们不得不赞叹她们的身体天赋。许多人共同跳的广场舞,在同样的舞步中,你却几乎一眼就可以把网红分别出来。同样的舞步,但与其他人相比,正是极小差异化的动作、姿态、表情,赋予了网红舞者舞蹈以全然不同的个性。熟练的动作,协调的舞步,恰到好处的姿态,特定的技巧等,当然是业余的,然而正因为是业余的,所以整个舞蹈动作(或者说健身动作)并不需要担负多少艺术上的使命,或者情节的叙事,它只是纯粹的动作,让自己跳起来,跳得开心。由此在协调统一的动作中体现出一种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感性,一种活力、兴奋、欢快,以及一种身体的智慧。身体的美感以及协调统一显然不是大脑控制计算的结果,而是身体智慧自然而然的表现。
现代艺术已经相当抽象化了,某些抽象艺术、观念艺术、装置很难令人理解,但舞蹈作为一种艺术,不论它多么抽象,永远不会脱离人。舞蹈是因人而在的艺术,它始终都是人的舞蹈,人在舞蹈。“机器舞蹈”“鹤舞”是不存在的,是机器、动物,就不可能舞蹈,即使它们看起来像在舞蹈。就像语言、情感,舞蹈是人的本质。在诸多艺术形态中,舞蹈最接近人的感性,从根本上来说,舞蹈就是感性本身。它既是舞者激情的表现,又是对观者感性的激发。
在一般的观察下,可以确定感性还有如下的特征。首先,对于感受者而言,感性是直接而真实的。感性是以感官的感觉为基础,感觉对自身而言,始终是真实的,即个体可以确实感受到对特定事项的特定感觉。感觉有可能是错觉,如同样长度的线段,另一根看起来更长之类。但即使是错觉,对于感受者而言,它仍然是真实的,只是从感性那里所得到的判断不符合实际。康德说,感官并没有欺骗人。按照他的哲学,感官本身并不判断,判断是知性的功能。因此错觉是知性判断的错误造成的。在他看来,感官知觉(有意识的感性表象)是一种内心的现象,依靠知性把杂多的感性材料统一在一个思维规则之下,形成某种秩序。现在来描述感性,可能要复杂得多。康德对感性概念的界定偏于简单与机械,与我们日常的感性经验不尽吻合。
其次,我们认为,感性是协调融合我们与环境之间、与对象之间的一种综合能力。它本身可能就包含着某种判断、计算、选择等类似知性的功能,但这种类似知性功能的运用常常又不在我们意识的控制之下,或不为我们意识所了解。轮扁斫轮的经验,庖丁解牛时不以目视而以神遇的感性经验,都包含着某种规划、判断、计算等“知性”因素在其中,但它们无法用理智来分析,无法数据化、量化,是迈克尔·波兰尼所说的一种“未可明言的知识”。这意味着感性本身包含着某种智慧,就像身体具有智慧一样,按照尼采的说法,身体比大脑更富有智慧。
二、艺术典范与感性
感性的表达具有非常复杂的机制。笑容作为一种自然的形式表现了内心的喜悦,人高兴的时候身体是舒展的,痛苦时身体则是收敛的。人们当然还可以通过语言表达情感。上文提及科林伍德甚至把语言视为一种受到控制和具有表现性的人体活动。这样语言就不是简单的发声系统,而是姿态系统,跟身体动作有关。这意味着在自然状况下,人的表情、手势、肢体、语言在情感表达中都是相互联系、协调一致的。总之,表情、手势、肢体、语言以及图像的、声音的艺术符号都是人的情感表达所需要的形式。
语言表达有两大类型:一是信息传达(指称、观念、引起行动),二是情感表现。纯粹的机器语音即使在说“我爱你”,也只能实现信息传达,无法体现情感色彩。相反人类的语音,仅仅是音色、音质就能够带有情感,如果结合语言中的语气、形象化的表述以及动作姿态则更能充分地表现人的情感。情感、感性的表达需要具有艺术表现力的形式,它重点不在信息,而是在传达语言之外的东西,它需要依赖某些形式因素。“那种构成作品的独一无二、经世不衰的同一性的东西,那种使一件制品成为一件艺术作品的东西就是形式。借助形式而且只有借助形式,内容才获得其唯一性”。简单地说,“更具表现力的语言”就是更具有感染力、能够打动人的语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从字面上看,没有任何情感信息或者实在的内容,但这种情景的想象一下子使人感受到与恋人(假设)难舍难分的感情。
当诗人在表达史、文学史上第一次说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样的诗句时,一种人们仅能模糊感受到,但却始终未能说出的情感仿佛从岩石的禁锢中挣脱出来,变得清晰而可感。艺术作品本质上就是情感表现的形式。这不仅是艺术形式的进步,也是感性的解放。“杨柳依依”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情景交融的修辞手法,更重要的是使得离别的感受变得可以指称,可以交流。这是情感更高级交流活动的基础。没有诗歌、艺术,人们的情感交流仍然被固化在日常生活自然呈现的层面上。高兴,仅仅只是一个笑脸与手舞足蹈,而不会是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样一个复杂的表意系统所传达的丰富的情感蕴含。就我们的感性史而言,《诗经》是划时代的经典,它最早呈现出中华民族对自然、社会、人自身的感受经验;唐诗使这一经验表达更加丰富生动。
当然,感性与形式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高度发展、逐步形成一种范式的艺术形式既使感性内容得到充分的表现,同时又拒绝了新的感性呈现。
优美生动的表现形式很容易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后来的作者极尽变化之能事,使其进一步拓展、提高、精细化,成为某种流行的艺术样式,成为典范。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为感性、情感的表现提供了重要的载体,众多艺术家、诗人通过学习,提高了整个民族感性表达的水准,大大促进了艺术手法、艺术技巧的进步发达。从南北朝诗歌声律的讲究,到唐代格律诗的定型,诗歌的表现手法日趋成熟,诗体的完善为唐诗的繁荣做好了准备。唐诗的鲜活生动,在于民族心智的成熟,语言的成熟,文化上的成熟。唐代诗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弱化为纯粹书生文人,如李白之粗犷,杜甫之倔强,高适、岑参之行动热情,王维、韦应物对山水感受之灵动,皆虎虎有生气。各种感受、意象、想象都径直闯入诗歌当中,有些还是第一次在诗歌当中得到描述。诗人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机智、恢谐,诗歌更多地融入了诗人的真情实感,而不是来自书本古诗推衍而来的感受。唐人的感受性与形式之间有着直接而充分的衔接与平衡。
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经验、表现手法不断积累,直至唐代诗歌迎来了一个高峰。唐诗充分体现出它的示范意义,成为后来诗人不断学习的典范。如安史之乱中,诗人杜甫返回鄜州羌村探望妻儿。兵荒马乱之际,亲人相逢,已是喜出望外,深夜相对,更觉不可思议。其《羌村三首》之一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梦中无数次重逢的“欺骗”以至不敢相信真来的喜悦。正是这种情感的揭示,使这两句诗一再成为后人模仿的榜样。如中唐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北宋晏几道《鹧鸪天》:“今宵剩把银红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皆本于杜诗。正是在后代诗人不断学习模仿的过程中,诗歌形成了它的典范。文学史就是文学典范史。在中国山水画、花鸟画等领域中,都有类似的现象。当某种表现形式与文人情趣形成统一时,这种表现形式就成为典范。典范是伟大传统的开端,而悠久的传统就是典范的传承史。
范式一旦形成,就不太容易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传统环境中,如近体诗在唐代逐渐定型并得到充分的发展,送别、思乡、怀古、叹老等主题都形成了相对比较固定的表达模式。从意象典故到对偶章法,从格律修辞到风格手法,都有非常成熟的素材、语汇、表现样式供后来者选用模仿,由此引导了一条相对比较容易的创作路径。只要熟记一定量的诗歌名篇,写一首诗甚至是不错的格律诗就不会是难以办到的事情。发展到极端,则是诗人、艺术家仅凭传统的形式素材就可以进行创作,《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谓“心非随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为文而造情”。创作不再依赖于诗人、艺术家实时的、具体的感性状况。艺术家不再关注自身在新的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的新体验、新感性,不再寻求现实感性与形式结合的新途径,文学艺术就失去了形式革新的真正动力。真正的形式创新不在于冥想巧思,而在于活生生的现实新感性所带来的契机。传统生产生活形态的相似带来了整个近体诗、甚至可以说整个古典诗歌创作的家族相似性。
宋代之后,古典诗歌的创作虽然仍有进步与变化,但形式的根本性变创几乎从没有发生过。它所表达的感性内容实际上也容易随之趋于模式化、概念化,趋于凝固,直到新兴词体出现,新的感性内容才有可能随着新的表现手法得到呈现。宋词出现,使得诗歌传统中一向反对描写女性妩媚娇羞情态、儿女情长的内容在词当中得以充分表现,形成了“诗庄词媚”的格局。近代白话新诗出现,一改格律体式,以白话自由的形式组成诗句,情感表达有了新的生动形式。新形式意味着新感性。
崇尚师古的时代,典范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与排他性。这至少无意间使得其他可能的艺术形式的探索发展受到忽略或阻碍。通常的情感、感受性的表达在经典作品的引导下会更鲜明,更容易获得艺术上的成功,这不自觉地抑制了其他异于范式的感性表现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那些不能够纳入到引导路径的感性内容不是受到忽略,就是遭到拒绝。不过,典范的排他性并不容易觉察。典范的引领与权力的支配不一样,人们在接受典范影响的时候丝毫没有意识到自身受到支配,这是礼教在传统社会一直受到大力支持的重要的感性基础。一个放弃了感性领域影响力的社会很难长久保持稳固的秩序。范式只需凭借自身美学与形式上所达到的高度,在人们的一致称赞之中即可实现感性的统一,它甚至不需要出面直接反对那些新起的、并不成熟的样式,因为在对范式一致膜拜的语境中,人们很难想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感性表达形式的可能性,更缺乏丝毫的觉悟与意识挑战范式。晚清古典诗歌主导地位的丧失并不是它自身范式的原因,而是外在革命引起的。只要在实际的创作领域中继续保持对经典艺术形式的欣赏与崇拜,典范就很容易实现对其他新兴艺术形式的消解。
三、感性管理机制
艺术中的典范与礼制中的规范有着相同的结构与机制。它们都是对感性的柔性管理。
礼仪中,各种仪式在本质上都有一个类似的功能,即对于人们复杂变化的情感给予有效的规范。传统理论认为,控制一个人的情感比控制其理智更有效。当一个标准的仪式得以举行时,标准之下各种不同的情感实际上都被指称、被表现了。这就是现实中千差万别的个体情感被礼仪形式统一表达的基本机制。可以春秋时代盟会宴享时“赋诗言志”以及与丧礼中有关“哭”的仪式为例。
上古文教未能如今天这样细致专门,用于教育的材料非常有限,《诗》成了当时最好的教材,所以《毛诗序》中就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此所谓“诗教”。正因为这一普及,贵族阶层多数熟悉《诗经》,能够在特定的礼仪或社交场合借用其中篇章来表达自己的情志、意愿。《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荀子·乐论》亦有“君子以钟鼓道志”。朱自清谓:“‘道志’就是‘言志’,也就是表示情意,自见怀抱。”通过古典诗歌来表达自身的意愿、情感。
但借用《诗经》来表达自己的情志,只取意思大概相合。赋诗言志,常常只是断章取义。如《野有蔓草》,原是表现男女爱情,《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郑国的子大叔赋此诗,实际上只取其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两句,对晋国赵孟表示欢迎之意。有时甚至是借用喻义。如《左传·昭公元年》郑伯享赵孟,鲁穆叔赋《鹊巢》,杜预注以“鹊巢鸠居”“喻晋君有国,赵孟治之”的意思。赋诗的寓义与原诗存在着差距。
古代礼仪中,标准的仪式动作通常构成了参与者某种情感、意愿表达的范式,尽管这种范式并不能全然表达个体情感,但它们作为标准的、合乎礼义的行为,成为必须遵守的规范,由此实现礼制中非常特别的“情感管理”功效,实现对人的情感加以引导和规范的根本目的。丧礼中,让现代人看来最难理解的就是“哭的控制”:在人抑制不住哭泣的地方,它需要制止哭泣;在人并没有哭泣但礼制规定需要哭泣的地方,人又必须哭泣。人因悲伤而哭泣本是不必加以限制,但古代礼仪有着颇为明确的规定。
首先是哭泣的位置。当人们听到噩耗,一定要找到与哭泣的对象关系恰当的地方来哭泣。丧礼上也有各种哭泣位置的规定。《礼记·曲礼下》曰:“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同书《曾子问》亦曰:“即位而哭。”《檀弓下》曰:“……哭之適室……哭之妻之室……哭诸异室。”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哭泣。
其次是哭泣的时间。这在现在颇难理解,欲哭之时何以能够止住,而不哭之时又何以能够痛哭?但丧礼上却是安排了具体哭泣的时间。《礼记·檀弓上》:“父母之丧,哭无时。”任何时候都可以哭,这不难理解。《礼记·檀弓下》记载敬姜的丈夫亡故,她昼哭;儿子去世,昼夜哭。孔子曰:“知礼矣。”
第三是哭泣的程序或方式。如何哭泣,在一般礼仪的意义上加以规定。有的时候仅仅只是哭泣,有的时候是哭号,有的时候哭泣加捶胸顿足。《礼记·曾子问》曰:“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这是哀伤表达的极致。哭泣之时,女性捶胸,男性顿足。大约长哭一声,跺三次脚;最多只能有三次这样的动作。
在没有哭泣之时如何来哭?大体只是做出哭泣的样子,并不要求流泪哭泣。《礼记·檀弓上》中记载孔子在卫国时曾住过客栈的主人去世,“入而哭之哀”,就是伤心而至落泪。于是让弟子给客栈人家送一匹马助丧,弟子觉得这礼太重。孔子说,刚进去吊唁,“遇于一哀而出涕”,一下子动了哀情而流泪,不想让别人觉得那泪水是假的。这意味着礼仪上规定的哭,并不要求出泪。
所以,有时哭泣是“命之哭”而哭,在统一号令之下集体来哭。《礼记·檀弓上》记载季武子建房,而杜氏有墓葬在他家的西阶之下,请求迁移,但杜家人“入宫而不敢哭”,季武子“命之哭”,才开始哭。《礼记·檀弓上》:“士备入而后朝夕踊。”这是说国君去世,群臣早上和晚上都要进入殡宫哭踊。等到士全都进来,群臣一起顿足号哭。《南齐书》卷四一《张融传》载领军刘勔战死,祠曹议“上应哭勔不”,张融议“宜哭”,于是始举哀。
礼制这样设计,形成了礼制化下统一的表达:在需要哭的时候,不论是否哀伤,都要礼仪性哭泣;而过于悲痛、哭泣过分的人则需要加以节制。所以《礼记·檀弓上》载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艺术中典范的确立以及礼仪中赋诗言志、哭泣的引导,看起来完全分属不同领域中的现象,都有着共同的结构和策略。
四、感性的多元表达
什么是“表现”?一件艺术作品、一个仪式动作究竟怎么表现情感?这一向存在着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А如果表达或表现B,那么А与B肯定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从表达总是与原来情感根本区别的角度来说,它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呈现情感。仪式化的哭泣与情动而哭已有区别,仪式化的哭泣只是真情恸哭的抽象性、形式化的形式,但它却是一个统一的情感符号。真情恸哭作为个体的情感表达形式是与自身情感本身相统一,哭泣就是悲哀,悲哀就是哭泣。仪式化哭泣却是从情感那里分离出来的一个形式,它归属礼仪系列,而不是纯粹的个体行为,尽管看起来两者形式上多少是相一致的。
这里可以把表达当作一种理论模型来讨论。如果每个人的悲哀都有一个自己的表达形式,那么,人们就无法交流。这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私有语言”(private language)的状况。类似的观点是克罗齐的看法,他认为每一件艺术品都是个别的、“自足的”,不能互比。贡布里希反驳说,这将“导致我们的世界分崩离析,因为不仅每一幅画、而且每一棵植物、每一昆虫都是个别的,都可以看成是独特的,‘个别无法形容’这句指语言网络无法捕捉个别事物的经院哲学的滥调就可以用于它们当中的一切。因为语言必须通过概念即通过普遍性才能起作用,而退缩到唯名主义中,拒绝使用除了个别事物名称之外的任何字眼,并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可以设想个体与群体、完全表达与完全不能表达两个相互垂直的轴线形成的区间中,与完全私人化语言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可以是这样一种假设,即群体的统一表达完全不能代表任何一个个体成员的情感。当然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现实是统一的表达能够不同程度地代表每个个体的真实感受。这意味着,艺术的表达是在两极之间寻求某个平衡点,即艺术的语言不能仅仅是艺术家个人化的,他的个性表现形式能够赢得至少一部分群体的充分共鸣,这也表明即使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实际上也有某种传统的来源,它属于时代艺术、民族艺术的一部分。显然,如果宏大统一的表达是由子系统下不同类型的表达组成时,每个类型的表达就可以更真切地表现一部分相似个体的感性内容。这是艺术需要多元化发展的感性基础。
感性的统一表达,在文化上具有这样的作用。首先是维持了共同体的情感。遵循文学艺术典范的创作思想以及礼仪当中赋诗言志、哭泣的引导,都是感性统一化的过程。可以把保持感性的统一表达看成是共同体时代共同仪式行为的残存形式。共同体艺术中,艺术是所有成员都参加的活动,艺术激发所有人共同的情感。所以,统一的痛哭形式就是哀伤情感的激发,而不是表达。随着共同体的瓦解,统一的仪式化哭泣成为形式化的行为,越来越不能成为个体情感的表达。在个体化不断发展的今天,这种统一的哭泣模式就变得完全不能理解了。
但其次,它使个体感性差异化发展变得迟缓。在共同体艺术激发成员共同情感的时代,是没有个体感性差异的概念的。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差异总会浮现出来,人们会意识到“我的感觉”与其他人不一样的事实。但个体意识到“我的感觉”,到使“我的感觉”进入话语系统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历史性统一表达的延续中,人们仍处于整个范式或仪式化表达既表达自身又与自身真情实感不甚关联的状况。它替你说了,但说得不很清楚;它代表了你的愿望,但与你真实的感受之间还有一些距离。在没有经历人的个性化发展的时代,人们必然会满足这种状况,就像春秋贵族那样满足于断章取义地赋诗,并且真切地认为典型的《诗》充分表达、传达了自己的情感;画家在模仿典范风格样式的时候,也从没有怀疑过它是否代表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在惯于“山寨”各种创意时,甚至也没有意识到“山寨”中的“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此时理论家声称,代表着美学崇高理想的典型风格能够一再地表现所有诗人、画家的感受性就再自然不过了;艺术家把注意力从对自己感受性的体验和表达方面转移到在对传统风格(或者西方风格)的集中模仿上,人们只须背诵《诗经》而无需创造新形式的诗歌来表现自身个性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只有充分肯定个体时,个体才有“胆魄”肯定自己真实感受的客观性以及“我的感觉”的不可剥夺性。“我的感觉”才可能真正引导艺术家集中探索内在的心灵世界,为自身独特的感受探索新形式,寻找表现的突破口。艺术家才可能专注于自己的创造,而不必专注于对占据支配地位的崇高形式表示膜拜。艺术需要对个体感性的充分肯定以实现形式的突破。事实上,“感觉欲望的发展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保持足够的坦诚与敏锐,就不难体会到“我的感觉”从来不是主观产物,它是我所独有的公共印迹,它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是“我”与社会环境交互铸造而成,所以它是诗人、艺术家首先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放弃了个体感受性来看社会现实对于艺术而言,只能是抽象主体的虚构。
理论上讲,典型的艺术形式总是时代精神的代表、时代最鲜明的标志。但它一旦成为人们趋之若鹜模仿的对象时,必然会走向衰落。然而,一种形式的衰落并不必然催生新的艺术形式。新形式的产生依赖多种社会条件,尤其是人的感性的觉醒,感性力量的释放。如果感受力是社会生产力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感性作为艺术创新力量就必然依赖于人作为社会新人地位的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