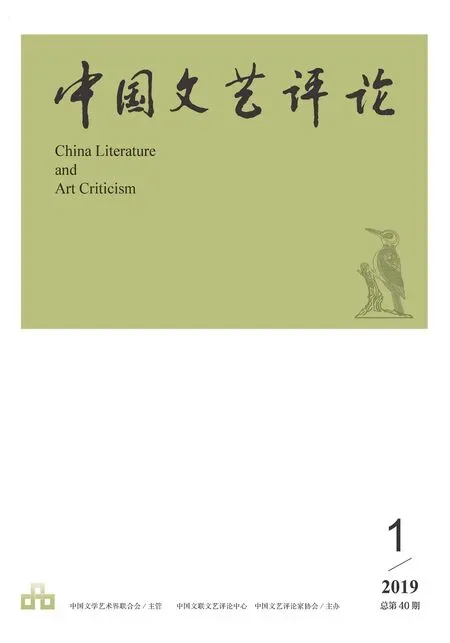《中西古典哲理名句:张世英书法集》序
张世英
大约是九岁到十二三岁时,父亲教我临帖习字,我一拿起笔来,父亲就站在一旁,说我这不是,那不是:不是腰未挺直,就是笔未竖正。我心情紧张,习字多年,字从来写得不好。
1938年秋,武汉沦陷,我离开家乡和父亲,直至2011年,我年届九旬,七十余年之久,除了应邀为某些报刊杂志题字外,极少有机会拿起过毛笔,先前是用钢笔,近几十年来都是用圆珠笔。一支破旧毛笔老是塞在抽屉的杂物堆里,书房里己很难找到一张用毛笔写字的纸张。
大约从91岁起,我开始有精力不济之感,脑子里的哲学和人生问题却还是连连不断,但要想写成一篇学术性的研究论文,那真是只有“力不从心”四字最能形容我的心境。有一天,枯坐终日,突发奇想:练练毛笔字吧。奇怪,手有些发颤,字却还显得有点功力!于是自我得意了一番。两个儿子看后说:“爸的毛笔字还不错嘛,练吧。”就这样,我又回到童年,习起字来了。没有父亲的严厉管束,我这才体会到了书法中的自由之境。
我小时临摹的字帖,主要是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文》。这次翻箱倒柜,又找出了几十年前的这个旧本,幸未缺损一字,而且父亲的藏书图章还清晰可见,我视之为传家珍宝。开始一两个月,我真像幼儿习字一样,一笔一画地用心临摹,越写得像,我越觉得好。有一次,我有点感到不耐烦,太不自由,便甩开字帖,随意画了几笔,一看,跃然纸上,生动活泼;对比之下,原来那些一笔不苟地临摹的字便显得实在太死板。这突然让我想起我小时父亲经常教我的一句话:“习字要讲究神似,不能貌合而神离。”原来我死死板板地临摹,就会犯貌合而神离的毛病。两个儿子也曾提醒我:“爸,索性放开来写,反而更好。”不过我还是牢记一句老话:先要下死功夫打基础,然后才能创新。学术研究如此,书法亦然。我现在大多不再一笔一画地临帖,而是花更多的时间读帖,拿着字帖反复地看,细细体玩其笔姿和意态,吸收其神韵,转化为自己胸中的“成竹”,等到拿起笔来,却根本不看字帖,挥毫自如,达到一种潇洒自由的境界。我现在深深体会到,写字要写出自己的字体,就像写文章要写出自己的思想风格一样。书法和文章都是一个人的灵魂的直接体现。
近三四年来,我写了几十幅条幅,还在客厅里挂了一幅,自我欣赏。有几位朋友来我家做客,居然称赞一番,向我索字,我更加得意,天天磨墨练笔。起先都是学一般书法家写四书五经名言或唐诗宋词,有一天我无意中写了一句黑格尔的名言,没过多久,友人陈越光先生看到了,竟大加赞赏,认为很有特点,要我给他写一条黑格尔名言的条幅。我不胜惊喜,于是开始以中国书法写西方名人名言的条幅。另有一两位朋友也赞赏我的这一“创新”。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心想:干脆编一本中西名哲名言,写成书法出版吧。几个子女都爱好文学,极力鼓励我,并在生活上照顾我、支持我。就这样完成了这本集子的编写。

张世英先生书法作品
中西名哲名言,浩如烟海,我主要是根据我个人的思想倾向和爱好来编选的,客观性不够和挂一漏万之弊,显而易见,尚希读者鉴谅。
我原来没有想到要给每条名言做注释,是著名美学家叶朗先生在看了我的书法原稿后,建议我逐条注释,以扩大读者面,并建议注释的文字内容要体现我个人的哲学思想和风格。我有感于叶朗先生的高见和盛情厚意,便欣然接受了他的这项建议。我选择的中西古典名言共一百五十余条,我深知这项工程需要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广泛翻阅古籍的繁杂工作,而我年老力衰,特别是记忆力减退,实在力不从心,便找了我二三十年前的博士生、西方哲学史家李超杰先生来担此重任。他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日夜兼程以进,终于完成了这六七万字的注释;他写作时所遵循的“三性”——准确性、学术性、通俗性,尤令我感佩。
我还要衷心感谢文艺理论家顾春芳女士,承她的厚爱,主动给我介绍出版社,否则,我还真不知像这样的集子该向何处投稿哩!
译林出版社编辑和设计师刘晓翔工作室做了特别精心的编制工作,谨此一并致谢。2017年 10月 于北京北郊静林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