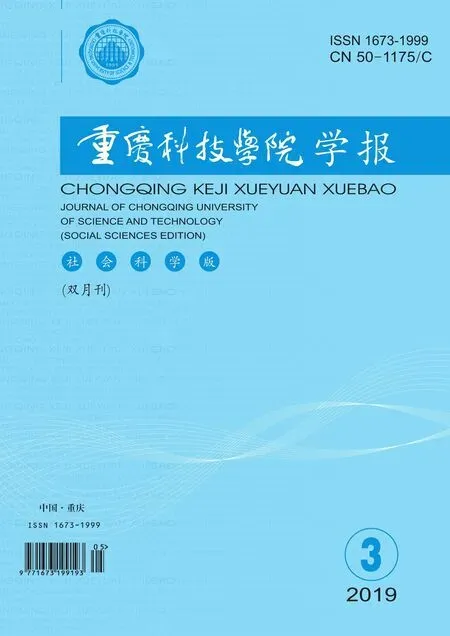自媒体时代网络反腐娱乐化的现实表现及应对策略研究
张 欣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博客、论坛、微博、网络社区、BBS等自媒体平台蓬勃兴起,网民通过各种自媒体平台曝光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经过网民的讨论与转载,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从而引起反腐部门的注意并介入查处,以达到反腐的目的。在这种网络反腐模式下,大批腐败分子纷纷落马,尽管网络反腐效果显著,但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呈现出的娱乐化倾向愈发明显。2013年6月20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指出:“网络反腐存在严重的低俗化、娱乐化倾向,给网络舆论环境带来负面影响。”[1]本研究在分析网络反腐娱乐化倾向及现实影响的基础上,研究其娱乐化倾向产生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减少其不良影响,从而引导网络反腐健康发展。
一、自媒体与自媒体娱乐化概述
自媒体(We Media)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是由美国新闻学者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在2003年联合发表的关于自媒体研究报告中提出的。自媒体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的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的途径[2]。简言之,它是人们用以发布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的网络技术载体。自媒体平台主要包括博客、微博、微信、百度官方贴吧、BBS以及新兴的视频网站等。
自媒体娱乐化是媒介娱乐功能的异化现象。大众传播媒介自诞生之日起,不但具有向受众提供信息、引导舆论、教育大众的功能,还具有放松身心、娱乐大众的功能。但是,随着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媒介的娱乐功能不断被放大,其弊端也日益彰显。20世纪80年代,尼尔·波兹曼以美国电视为文本,对电视影响下的人们的思想、认知方法及大众文化发展趋向等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娱乐至死”的命题[3]。他警告人们: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呈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波兹曼的观点原本是针对电视时代人们的理性思考能力被娱乐信息所淹没的现象,但在自媒体时代,这种现象愈加显现。如今,网络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借助现代媒体强大的传播力量,“娱乐化”这一文化病毒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4],甚至是严肃的反腐领域,表现出来的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混乱和理性思考能力的丧失。
二、民间网络反腐娱乐化的问题呈现
自媒体时代,网民借助网络平台摇身一变成为反腐斗士,掀起了全民反腐的浪潮,使腐败分子无处遁形,挤压了腐败空间,提升了反腐效果,但是,反腐这一神圣而严肃的事情,却越来越呈现出娱乐化、低俗化的倾向,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
(一)网络谣言泛滥,造成反腐资源巨大浪费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迎来了自媒体时代,在网络空间中,人人手握麦克风,每个人既是参与者、围观者,也是创作者、表演者。网络信息量之大、信息量之杂让人目不暇接,面对庞杂的信息,普通网民常常在缺乏专业判断的情况下就对其进行转载传播;有部分网民为了从庞杂的信息中脱颖而出,博取大众的关注,在进行反腐举报时,不惜编造谣言、添油加醋,进行不实举报,不明真相的“围观”网民更是以讹传讹,助推事件偏离了本来真相。如在2012年的“房婶”事件中,有人在网络上举报广州城建系统退休领导李某某坐拥24套房产,在网上引起一片哗然。后经中共广州市纪委和市监察局预防腐败局调查证实,李某某并非领导干部,只不过是城建系统的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其购房资金来源清楚、房产均为合法所得。2015年南京“6·20”重大车祸发生后,警方依法逮捕了肇事者王某某,该事件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不断被刷屏,“警方包庇宝马车主”“肇事者王某某是替人顶罪”“涉嫌酒驾或毒驾”等劲爆消息被传得有鼻子有眼,最后虽经警方辟谣,但仍有部分网民对传言深信不疑。在2016年的“金山表哥”事件中,有网民称上海金山区副区长手上戴的是一块价值30万元到100万元的百达翡丽名表并附图证明,认为其有贪污腐败之嫌。后经官方调查证实,当事人并非副区长,而是山阳镇党委副书记蔡某某,其所佩戴的手表为价值16 000元的浪琴表,是由个人购买的并与其正常职务收入相配……像这样的网络谣言不胜枚举,这种打着反腐旗号进行的虚假信息传播,使反腐利器沦为了造谣工具,不仅对被举报人名誉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使网络反腐陷入真假难辨的无序状态,相关部门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信息进行甄别查证,造成了有限的反腐资源的巨大浪费。
(二)聚焦官员情趣偏好,消解反腐工作的严肃性
近年来,大量的反腐举报信息以曝光官员的穿着打扮、消费嗜好、情趣偏好等为反腐线索,反腐举报信息总能与吃穿打扮、居住房产、情妇二奶等因素扯上关系。如“天价烟局长”周某某、“微笑门表叔”杨某某、“房姐”龚某某等都在网民的曝光下被打上了标签。乐思网络舆情监测中心采集了2012年1月至2014年3月百度首页的新闻20 972篇,分析后发现,关于官员负面报道的新闻达1 270篇,其中性、房、钱、酒具有曝光度高的特点[5]。特别是对官员的情色事件、桃色新闻更是大肆渲染,甚至配以不雅视频和图片进行传播,以满足大众的猎奇心和窥视欲。近年来,在网民的爆料下,腐败官员纷纷陷入各种“门”,如原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法院院长范某某的“开房门”、原广西烟草局局长韩某的“日记门”、原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道办主任刘某的“裸聊门”等桃色事件被网民们一一扒出,其中不乏网民对官员情色故事绘声绘色的描述,像亲眼所见一样。在这样的网络反腐氛围下,网民只关心官员们戴了什么名表、住了什么豪宅、包养了多少个情妇,而对其贪腐行为本身、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却显得不那么关心,这严重偏离了网络反腐的本意,消解了反腐工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网络侵犯个人隐私,突破了道德和法律底线
隐私权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然而,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的政府官员因其职务的特殊性,其某些隐私可以直接反映其廉洁程度,因而他们不可能完全享受和普通公民一样的隐私权,其隐私权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克减。官员的许多隐私都是可以被公众监督、评价,甚至是批评的,这种评价或批评的言论自由也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但是,如果明知其言论是虚假的,却故意捏造事实、恶意污蔑就是“真正的恶意”,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网络反腐中,网民对涉腐官员的举报常常会超出合理的边界,不能聚焦腐败行为进行举报,一些举报人为了增加信息的吸引力,或基于社会正义感,或为了满足网民的窥私欲,大量曝光被举报人的隐私内容,如个人生活与成长经历、家庭住址、子女配偶信息等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引发网民发布网络通缉令对被举报人进行“人肉搜索”,侵入被举报人的私人生活领域,跟踪监视其社会活动,给被举报人及其家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这明显违反法律和突破了社会的道德底线。政府官员作为普通的社会公民,其与公共权力、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隐私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即便实施了贪腐行为,其合法隐私权同样需要得到保护”[6]“政府官员也有对私生活的合法预期,因为他们不仅是政府官员,同样也是人”[7]。网民不能打着反腐的旗号任意践踏其合法权利,对官员实施的“私刑”与我国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
(四)线上非理性的集体狂欢,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网络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场所,网络反腐的底层性和草根性很容易使网络成为网民线上肆意狂欢的舞台。爱弥尔·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提出了“集体欢腾”概念,他认为:“集体欢腾本身是建立在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之上的,而集体行动则是一种格外强烈的兴奋剂。一旦人们集中到一起,由于集合而形成的一股如电的激流就迅速使人们达到极度亢奋的状态,而到了这种亢奋的状态,个体也就不再意识到他自己,而是感到自己被某种力量所支配。”[8]在网络上,网民通过点赞、跟帖、转发、分享等互动对同一话题持共同倾向而形成一个集体,在网络反腐中,网民在自认为的“正义”“神圣”力量的支配下,人人都感觉自身是正义的使者,对腐败官员和腐败行为进行讨伐,在相互感染下发表各种情绪化的、偏激的、不理智的言论来表达对“神圣价值”的敬仰,在这种“群聚效应”的影响下,人们丧失了理性和判断力,即使有个别人发出理性而客观的声音,也会被集体群起而攻之,于是,个人屈从于集体的意志不再发声。在这种非理性的集体欢腾浪潮的影响下,民意被利用、被挟持、被绑架,处于盲从、躁动和无序的状态,在个别人的煽动下,网民很容易将对少数官员贪腐的口诛笔伐上升为对官员、对富人、对政府及对社会的仇恨,将虚拟网络上的声讨转移到现实生活中实施伤害,给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带来巨大的威胁。
三、网络反腐娱乐化的原因分析
网络反腐之所以开展得如火如荼并出现娱乐化倾向,有其深刻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原因。
(一)媒介对经济利益的追逐
根据传播学大师库尔特·卢因的把关人理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任何信息进入公众视野都要经过工作人员的过滤或筛选,而过滤或筛选的标准主要有新闻信息的客观属性、专业标准和市场标准(新闻价值和新闻要素)、媒介组织的立场和方针[9]。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形成了商业化的运营模式,媒介产品则是赚取利润的商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否迎合消费者的需求,是否能赚取利润,成为左右媒体把关人的重要考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量以爆炸式的方式增加,面对无限增长的信息,受众有限的注意力就成为稀缺资源,谁吸引了受众的注意力,谁就拥有了投资的价值,资本就会源源不断地注入。皮埃尔·布尔迪厄以崇高、深刻、神圣为核心趣味标准的“有限文化生产场”和以通俗、娱乐为核心趣味标准的“批量化文化生产场”之间为争夺文化资本展开了激烈争夺[10]。而轻松、通俗易懂、娱乐性强的通俗文化显然更受消费者的喜爱,“批量化文化生产场”更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马歇尔·麦克卢汉指出,传媒所获得的最大经济回报来自于“第二次售卖”——将凝聚在自己的版面或时段上的受众“出售”给广告商或一切对于这些受众的媒介关注感兴趣的政治宣传者、宗教宣传者等,这种“出售”行为出售的就是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也就是说,媒介所凝聚的注意力资源是传媒经济的真正价值所在[11]。当网络媒体创作出有吸引力的内容时,增加信息的点击量和影响力,自然就会吸引大量投资者的资本注入,因此,各大网络媒体为了争夺资本,想尽办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在视角选择、标题拟定、内容筛选、语言手法上,都以吸引受众的眼球为第一要务,各种带有娱乐元素的信息成为网络媒体吸引受众注意力的策略选择。网络反腐的低俗化和娱乐化的产生正是基于这样的市场环境。自媒体时代,网络平台众多,市场竞争激烈,如果网络反腐曝光的信息没有一点冲击力、震撼力,那么,很难吸引网民注意,也很容易淹没在浩瀚的反腐信息之中。目前,大量的反腐信息集中于官员的吃穿打扮、居住房产、情妇二奶等低俗化、娱乐化的话题上,这些话题正好迎合了受众的娱乐需求,自媒体平台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无节操、无底线地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片面追求所谓的看点和点击量,任由反腐这样的严肃话题被以娱乐的方式登场,借以吸引网民的注意力,这是导致网络反腐越来越偏离主题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原因。
(二)技术的发展及有力支持
互联网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资源的社会化和话语权力的全民化,以及“去中心—再中心”的自媒体传播特点所形成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为网络反腐的娱乐化提供了技术条件。从传播主体看,传播主体不再是传统的精英媒体人,而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大众,每个人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更可以作为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参与其中;在传播方式上,由传统的“点对面”的扇形传播转变为“点对点”的网状传播,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由信息源的中心不断向四周扩散,在扩散的过程中,又不断形成新的中心点;在传播效果上,自媒体平台可以进行“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在线和离线互动,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声音以及超文本链接技术的一次信息建构,就可以实现广泛传播而形成自己的舆论场。自媒体的这些技术优势在为网络反腐提供技术支持的同时,也为网络反腐的大众狂欢提供了可能。受自媒体平台的平民性影响,如果缺乏严谨精细的采编控制,那么,就会使大量素质参差不齐的网民活跃于网络之中,这就很容易使信息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大打折扣。反腐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随着信息互动人数的增多,附加在信息上的主观色彩就越多,为了能在众多的互动者中脱颖而出,有的网民常常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信息传递效果以赢得关注,在“人云亦云”下很容易形成娱乐化、低俗化的网络反腐舆论氛围。
(三)社会文化转型的催化刺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文化形态也在发生变化,由以公共理性著称的“精英文化”向以激进的、不理性的、极端主义的“民粹文化”以及向以平民的、通俗的、娱乐的“大众文化”演变,构成了网络反腐娱乐化产生的文化背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以社会精英主导的精英文化对崇高、理性的倡导,还是极端强调平民价值和理想的民粹文化对精神的追求,都带有很强的抽象性和严肃性,脱离了群众的现实生活,大众只能成为文化的被动接收者,无法激起内心的共鸣。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信息传播一改往日传统权威媒体的“一本正经”和“高高在上”,贴近群众、通俗实用的大众文化蓬勃兴起。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社会大众成为文化的创造者,人们的感性情感被重视,社会个体的自我价值得到充分的彰显。“我国公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机会、有时间、有能力关注自己的生存质量、追求生活的快乐和情感宣泄。”[12]在这种文化思潮下,大众传媒的娱乐化转向更加明显。在政治生活上,人们的参与意愿明显增强,参政议政不再是精英们的专利,也不再局限于“厅堂议事”,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虚拟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释放出来的利益和诉求越来越多,但现有的制度安排却无法将大多数利益表达纳入体制化的渠道,人们只好通过体制外的“网络”作为民情民怨的发泄工具。由于人们对腐败官员、腐败行为的深恶痛绝,更能激起人们在网络上的情感共鸣,在这种民间操刀、群起反腐所伴生的偶然迸发性、多重目的博弈、非理性化、非程式化倾向的作用下,就难免会出现根据是否“吸引眼球”的“好料”而进行的选择性爆料[13],很容易只关注房产、穿着、情妇这样的世俗信息,也容易不理性地将对个别官员的贪腐行为评价上升为对整个政府的攻击,从而偏离了反腐的根本宗旨,产生了“网络即是狂欢世界”的大众娱乐现象。
四、网络反腐娱乐化的治理对策
网络反腐中的娱乐化现象,消解着网络反腐的正能量,对国家政治文明和社会文化都有巨大的负效应。有学者指出,网络就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它诱使我们将人类本性中最邪恶、最不正常的一面暴露出来,让我们屈服于社会中最具毁灭性的恶习;它腐蚀和破坏整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和价值观”[14]。因此,为了推进网络反腐的健康有序发展,可从网络反腐立法、制度对接、行业管控、公民教育几个方面将其负效应控制在最低限度内。
(一)有序推进我国的网络反腐立法工作
网络反腐为普通公民提供了发声的机会、监督的渠道,是社会和时代进步的表现,但是,如果网络反腐超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沦落为网民消遣的手段、打击报复的工具,则无法成为治理腐败问题的有效武器。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我国公民的一切行为都应该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进行,与现实社会一样,开放而虚拟的网络社会同样需要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就目前来说,法律法规建设并没有跟上网络反腐实践的发展,虽然颁布了一些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但是,其针对的基本上都是互联网信息和互联网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还没有颁布专门针对网络反腐、网络监督等问题的法律法规,因此,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难以为网络反腐的规范运行提供法律保障。在现实的网络反腐过程中,公民监督权与官员个人隐私权、网络监督与造谣诽谤、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等之间的法律边界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如何对举报人实施有效保护和对恶意造谣者的严厉制裁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何保持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网络的有序运行之间的平衡还没有有效的法律举措。如果这些问题不在法律法规上加以明文规定,网络反腐将永远走不出娱乐化的窠臼。因此,必须加快推进网络反腐立法工作,明确网络反腐主客体的权利和义务,明确网络反腐的程序和网络反腐的奖惩条件,既要保证网民的言论自由、知情权、监督权得以行使,又要对恶意造谣生事者给予严惩,保障网络反腐工作的有序推进和规范运行,还网络一片洁净的空间。
(二)建立官民对接、开放参与的反腐机制
自媒体时代,在网络反腐过程中呈现的非理性、娱乐化等缺陷,不但反映出人们政治参与的无序及政治参与能力的低下,也暴露出我国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封闭。一般来说,政府运作的开放透明程度越高,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过程的参与能力就越强[15]。由于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需要全民的参与和担当,因此,应该为民众参与反腐提供制度化的渠道。网络反腐和体制反腐在运行方式和特点上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可以形成制度反腐为主、网络反腐为辅的基本格局。除了继续降低公检法反腐举报的门槛,保证信访、纪检监察系统反腐渠道的畅通外[16],还应尽快把网络举报与制度性反腐有机融合,实现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有序衔接、有效互动。例如,根据网络反腐的一般行动逻辑,建立网民、网络共同体、传统媒体、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鉴于政府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搭建政府舆情部门与网民的信息沟通平台,构建有效的网络舆情预警机制;针对部分网民对政府反腐公信力的质疑,建立快速的网络反腐信息反应处理机制,对网络反腐信息进行及时的反馈;针对网上讨论极易出现极端化、情绪化的网络舆情,建立有效的网络舆情监管机制,实时跟踪网络舆情发展的新动向[17]。
(三)加强网络综合管控,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网络媒体为人们参政议政、举报监督提供了平台和渠道,但是,如果对其缺乏引导和监管,网络媒体很容易受市场利益的影响而产生失范行为,并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为避免网络反腐出现娱乐化和低俗化倾向,应加强对网络媒体行业的综合管控。第一,加强网络媒体的道德自律与法律他律。在道德自律方面,网络媒体应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与使命,传播真实有效的信息、引导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树立和维护国家的良好形象、提升民众的生活情操、提供健康有益的网络休闲活动;在法律他律方面,国家应根据自媒体的特点,制定全覆盖、可延伸、适用范围广的法律法规,明确其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管理范围、管理机构职责等,以便对自媒体的法律监管做到有的放矢。第二,加强网络媒体行业社会组织建设。在自媒体时代,数以亿计的自媒体用户处于游离于社会组织之外的“碎片化”的个体状态,各大自媒体平台也没有成立相应的社会组织,缺乏专门组织的有效整合,难以规范其媒介行为,因此,应该成立专门的社会组织,对网络平台进行自我管理,通过社会组织的行业自律,明确行业操作规范、行为准则,提高网络媒体平台的媒介素养和道德操守。第三,加强政府对自媒体平台的间接管控。西奥多·罗斯扎克指出:“没有管理的互联网,所呈现出的也只能是一片丰富的荒凉、混乱的自由,是信息量大而尽是垃圾、新闻条多而没信度,是公民的隐私被侵犯、百姓的行为被误导。 ”[18]政府可通过立法、审核、监督、责任追究等几个重要环节对网络媒体进行管控,保障网络安全和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
(四)提升网民媒介素养,增强理性参与能力
要改变目前网络反腐的娱乐化、低俗化倾向,加强网民教育、提高网民的理性参与能力是客观要求。我们所处的网络时代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其中不乏含有大量娱乐元素的信息,一般来说,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能读懂娱乐的内涵,对待娱乐信息更加理性谨慎。自媒体时代,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信息、发布信息,甚至引导网络舆论,网民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网络空间的清朗程度。据《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显示,我国微博用户整体上呈现学历低、年龄低、收入低等特征[19]。这些网民年轻、有激情、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是,他们缺乏理性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容易沉迷于娱乐,容易被网上的言论所诱导和煽动,极易被别有用心的传播者利用和操纵,被披着“正义”外衣的非理性力量所挟持,将自己置身于积怨放大、情绪宣泄和娱乐化的狂欢之中,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必须加强网民媒介素养教育,增强网民对媒体信息的科学识别能力,避免落入他人定义的态度、认识、行为和情感的窠臼,使网民成为积极的媒介信息的使用者以及媒介话语权的表达者[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