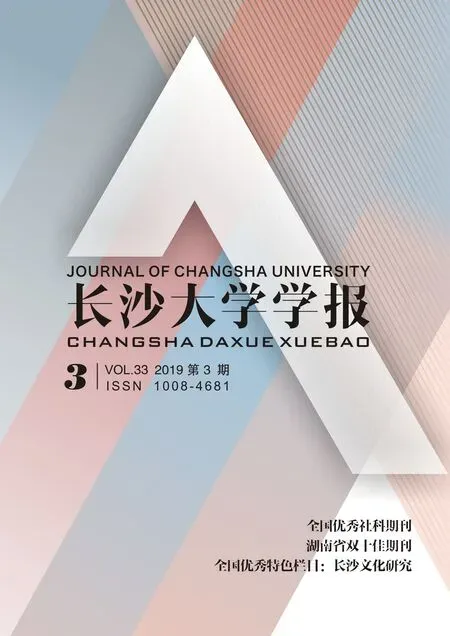罗尚贤校读“古之为道者……”辨析
柳 菁,邓谷泉
(长沙学院图书馆,湖南 长沙 410022)
《老子》通行本第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帛书甲本作“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帛书乙本作“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注帛书甲本、帛书乙本指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乙本。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汉简本作“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注汉简本指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学者虽校、读不一,但一致认定老子反对“明民”,主张“愚之”。本文针对罗尚贤校读“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的失误,作如下论证或认定:帛书甲本“故曰”误,当从“古之”;“非……将……”译作“不能……宁可……”有误,当从“不是……而是……”;“以”不可能是动词“认为”作谓语,只可能是介词作状语;“明民”“愚之”解读为“明于民”“愚于之”不可信,当从使(教)民明、使(教)之愚。
一 帛书甲本“故曰”误,当从“古之”
“古之为道者”的“古之”,帛书乙本、汉简本、通行本作“古之”,帛书甲本作“故曰”。罗尚贤说:
“故曰:所以说。此句表明下文‘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也……’皆是上文‘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违’注“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违”的“违”,诸本作“为”,罗尚贤读作“为(违)”,1996年版改成“为”。的引述。帛书甲本如此。帛书乙本及他本作‘古之’,将上下文割裂,纯属后人篡改。”[1]P265
若作“故曰”,必有上文,意味着第六十五章并非独立成章。帛书甲本有残缺不全的圆点分章标志,“故曰:为道者……”之前无圆点分章标志,上接第六十四章“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似存在“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为“故曰:为道者……”上文的可能性,但现有证据表明:第六十五章确是独立成章,帛书甲本“故曰”误,当从“古之”。
楚简甲本“其安也易持也……始于足下”对应通行本第六十四章前段“其安易持……始于足下”,对文上接第三十二章,下联第五十六章。楚简甲本“为之者败之……而弗能为”对应通行本第六十四章后段“为者败之……而不敢为”,对文上接第十五章,下联第三十七章。楚简丙本仅残存四组,各自独立,“为之者败之……而弗敢为”对应通行本第六十四章后段“为者败之……而不敢为”,独立成章。汉简本“其安易持也……始于足下”和“为者败之……而不敢为”各自独立成章。《韩非子·喻老》记有通行本第六十四章文字,第七段为“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谋也”之喻,第八、第九段为通行本五十二章“见小曰明”“守柔曰强”之喻,第十、第十一、第十三段则为“欲不欲……不敢为也”之喻。据楚简甲本、楚简丙本、汉简本和《韩非子·喻老》,理当认定第六十四章后段“为之者败之……而弗能为”独立成章。“为之者败之……而弗能为”的重要结论是“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为何“弗能为”?紧接着的“道恒无为也”作了回应。故“为之者败之……而弗能为”联结第三十七章“道恒无为也……”比联结第六十五章其内在联系更为紧密,更为合理,所以“为之者败之……而弗能为”和第六十五章不可能合为一章并构成上下文。
“古之”在一章之首,见于第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而“故曰”不可能作于一章之首。若作“故曰”,必有陈述其原因或理由的上文。第二章、第三章、第十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三章、第三十八章、第四十八章、第四十九章、第五十七章、第五十八章、第六十章、第六十三章、第六十四章、第七十五章、第七十九章、第八十章,有和第六十五章内容相联的文本,但其相关文本不是陈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的原因或理由,据其相关文本也不能逻辑推导出“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的结论,故其相关文本不可能和第六十五章合为一章成为“故曰:为道者……”的上文。若作“故曰”,则“为道者……”应为引用语的结论或作者自己的推论,而非原因或理由,但“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是“为道”的原因,“以其知也”是“民之难治”的原因,“故以知知国,国之贼也;以不知知国,国之德也”才是根据上文所作的推论。“故曰”之前无陈述原因或理由的上文,“故曰”之后却有原因和推论,反证原文不可能作“故曰”。故罗尚贤从帛书甲本“故曰”有误,当从“古之”。
二 “非……将……”译作“不能……宁可……”有误,当从“不是……而是……”
“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的“非……将……”,所见今译通常译作“不是(并非)……而是(而是要)……”,唯见罗尚贤译作“不能……宁可……”。他说:
“从此句本身意义说。非:否定之词,不能也。以:认为。此则字义,无可争论。”
“将:抑或。引申为宁可。”[1]P266
古汉语“非”“将”“以”有“不能”“宁可”“认为”之义,确无可争论,但古汉语“非……将……”“非以……将以……”习见,例如:
(1)“非不利也,将除害也。”(《左传·哀公十四年》)
(2)“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墨子·尚同》)
(3)“神农形悴……墨子无暖席,非以贪禄慕位,将欲事起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也。”(《文子·自然》)
(4)“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贪宝赂也,将以存亡平乱、为民除害也。”(《文子·上义》)
(5)“霸王之道,以谋虑之,以策图之,挟义而后动,非以图存也,将以存亡也。”(《文子·上义》)
(6)“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记·乐记》)
(7-8)“故昔善计者,非以求利,将以明数。”“昔善战者,非以求胜,将以明胜。”(《歇冠子·天权》)
(9-10)“撰良马者,非以逐狐狸,将以射糜鹿。”“砥利剑者,非以斩缟衣,将以断兕犀。”(《淮南子·说山训》)
上述十例复句明显不是取舍关系,关联词“非……将……”显然不能译作“不能……宁可……”,也未见有人译作“不能……宁可……”。《文言固定句式及熟语》说,“非……将……”由副词“非”和副词“将”组成,加强肯定和否定的判断,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不是……而是……”[2]P16。故从此句本身意义说,“非……将……”译作“不能……宁可……”有误,当从“不是……而是……”。
三 “以”不可能是动词“认为”作谓语,只可能是介词作状语
“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的“以”字,通常认定为介词,有不同今译,罗尚贤解读为动词“认为”。上举“非以”“将以”的“以”绝不可能是动词“认为”作谓语,只可能是介词作状语。例(3)“非以”的“以”是介词表原因;例(2)、例(4)“将以”的“以”是介词表目的或原因;例(5)至(10)“非以……将以……”的“以”是介词表目的或手段。“明民”“愚之”解读为使(教)民明、使(教)之愚,是认定形容词“明”“愚”作谓语,“民”“之”作宾语;解读为“明于民”“愚于之”则是认定形容词“明”“愚”作谓语,“民”“之”为介宾词组“于民”“于之”的省略,作补语。“明”“愚”作谓语,无可争论。问题在“明”“愚”既作谓语,“以”怎么可能是动词“认为”作谓语呢?“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不可能是独特语法。故从此句本身意义说,“以”不可能是动词“认为”作谓语,只可能是介词作状语。
四 “明民”“愚之”解读为“明于民”“愚于之”不可信,当从使(教)民明、使(教)之愚
“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的“明民”、“愚之”,通常解读为使(教)民明、使(教)之愚,罗尚贤解读为“明于民”“愚于之”,首要理由是:
“‘明民’与下段的‘上民’,‘先民’,句式相同,句意连贯:
明民:高明于人民。‘非以明民’,方能起总结群众经验的作用。
上民:高尚于人民。‘欲上民’,方能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
先明:先进于人民。‘欲先民’,方能在群众中起引导作用。
一般学者,既把‘先民’译作‘领导人民’,还有什么理由说,‘明民’不能译作‘高明于人民’呢?”[1]P267
“明民”“愚之”解读为“明于民”“愚于之”,其说新异,但不可信、不可从。
通行本第六十六章见于楚简本、帛书本、汉简本,校文如下:
“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能为百谷下,是以能为百谷王。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6章)[注]据楚简本、帛书本、汉简本、通行本校定,从通行本章次。
“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的“在民前”“在民上”,帛书本、通行本作“欲先民”“欲上民”。刘笑敢说:
“‘用欲’字则是条件句,没有‘欲’字则是描述和判断,文义有所不同……联系下段来看,竹简本始终是描述圣人的事实表现,逻辑上是一致的;帛书本和传世本则是这一段讲条件,下面则是对圣人表现的事实的歌颂,逻辑上稍嫌不一致。推敲起来,圣人既然称之为圣人,应该是已经在民之上、民之先,不应该再假定圣人希望(欲)在上、在先而应该如何。”[3]P643
有“欲”字,“上民”“先民”与“言下”“身后”表现为目的和手段的方案设计,是一种权术,而楚简本全章皆是知识陈述,并无方案设计。“欲先民”“欲上民”当为后人所改。用后人所改的“上民”“先民”作为“明民”“愚之”解读证据本身就隐含不合理性。“上民”“先民”虽是上于民、先于民省略了介词“于”,但“上”“先”本身不是形容词,而是名词,在文本中属于名词活用为动词,故“明民”与“上民”“先民”并非“句式相同”。“上民”,河上公注“在民上也”,楚简本正作“在民上”,并非“上民:高尚于人民”。“先民”,河上公注“在民之前也”,楚简本正作“在民前”,并非“先民:先进于人民”,故“明民”与“上民”,“先民”并非“句意连贯”。因此,“上民”“先民”并不能佐证“明民:高明于人民”。
“明民”“愚之”自罗尚贤解读为“明于民”“愚于之”以来,沈善增、赵又春提出了大同小异的解读。“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沈善增意译为“依道而行的君主,不是把自己放在比人民高明的位置上,而是要把自己放在比他们愚笨的位置上”[4]P172,赵又春今译为“都不以为自己比百姓高明,而是认为自己比百姓愚昧”[5]P349。杨进禄说:
“沈善增、赵又春推倒古今上述诸家之解,认为‘以’作动词‘认为’解,‘明民’为‘明于民’(比民高明),‘愚之’为‘愚于之’(比民愚),全句译作‘都不以为自己比百姓高明’。我以为这是以今解古。古代即使圣贤如老子、孔子,也不会把民众看得比自己高明,自己反倒愚不及普通民众。”[6]P431
《国语·鲁语》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黄帝能成命百物”,《礼记·祭法》引作“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历来注释大同小异,例如:
“‘以明民’者,谓垂衣裳,使贵贱分明,得其所也。‘共财’者,谓山泽不障,教民取百物以自赡也。”[7]P2373
“明民:使民不迷惑。共财:供给赋敛。共,同‘供’。”[8]P101
“明民共财:使百姓知道生财之道共同占有财富。”[9]P29
“以明民共财”的“明民”为形容词使动用法或形容词带使令宾语——使民明,不可能解读为“明于民”。“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的“之”指代“民”,“愚之”即“愚民”,“愚民”在古汉语及现代汉语中有三种用法,即愚之民、愚其民、使民愚,无“愚于民”的用法。故从此句本身意义说,“明民”“愚之”解读为“明于民”“愚于之”不可信,当从使(教)民明、使(教)之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