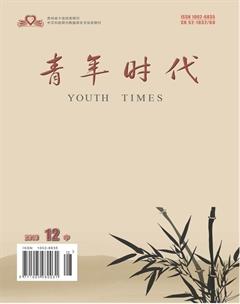温庭筠《菩萨蛮》组词主题内涵考辨
罗誉中
摘 要:温庭筠作为文学史上第一位大力作词的文人,被后人誉为“花间鼻祖”,对后世词作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菩萨蛮》组词为代表的温庭筠词,因其错金镂彩、浓艳香软的词风,展现出与前代诗文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因此,学界有关温庭筠词主题的考证一直以来都存有巨大争议,甚至在针对其有无寄托之上亦是考辨不断。故而,本文将以温庭筠《菩萨蛮》组词为中心,立足古今文人学者的考评考论,从晚唐诗词发展趋势、温庭筠人格诗格与词格、《菩萨蛮》组词情感内涵等多角度出发,对温庭筠《菩萨蛮》组词的主题内涵进行考辨。
关键词:温庭筠;《菩萨蛮》;发展趋势;人格与词格;情感内涵
在晚唐诗歌创作大多还未挣脱古典诗学传统的桎梏,秉承着诗言志的社会政治功用而抒发诗人主观内在情志之时,词史上乍现了一位“近世倚声填词之祖”:温庭筠。现今文学史认为,温庭筠作为“花间鼻祖”,其词作在由诗入词发展的过程中,上承唐代民间词之精神,下启北宋文人词之风韵,承前启后,影响深广。其收录于《花间集》中的十四首《菩萨蛮》组词,深切体现了温庭筠词的风格特点。然《旧唐书》曾载:“温庭筠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缟之徒,相与蒱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由是,自古以来众多文人学者皆以“侧词艳曲,词风香软”为其作评,口碑不佳。至清代张惠言赞曰“其言深美闳约”,方令学界正式重视对其艳词主题内涵的考证,并由此产生巨大争议。
温庭筠以《菩萨蛮》组词为代表的“侧艳之词”,学界对于其主题内涵主要持三种态度。其一,以《菩萨蛮》组词为代表的展现香艳绵密女性抒情特征之词作,皆存寄托之旨,暗抒志士之怀。其二,其对香闺美人细腻描摹、情思婉媚之风,皆无寄托之意,乃客观抒写而已。其三,“男子而作闺音”抒思妇惆怅之情,皆本无寄托之思,却潜意识暗合内在之情。以下,本文将从多角度入手,对此三种观点进行逐一考证,以求对温庭筠《菩萨蛮》组词的主题内涵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考辨。
一、存寄托之旨,暗抒志士之怀
《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篇》言:“诗以道志。”中国古典诗歌自古以来便承载着抒发诗人思想感情、抱负志向的责任。在长久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过程中,优秀而雅正的诗文不自觉地将社会政治功用性作为评判诗文优劣的主要标准之一。因此,诗人将诗歌作为一种正统文学进行对待,诗歌大多内蕴诗人的主观情感和志向,或抒发理想抱负,或感发志士不遇,或歌颂太平繁盛,或讽刺奸佞乱党,内蕴丰富、情志深厚。晚唐经过唐代诗歌发展巅峰之期,其古典诗学传统更是至臻至善。然而,作为一个动乱的时代,晚唐的政治异常纷乱,战乱连绵,经济萧条,百姓生活困苦。就如此前所有朝代更替之时所产生的情态一般,众多有志之士牵挂国之兴亡,或积极入世上表经国之略,或干谒将相心存济世之志,温庭筠亦然。故而,在入世之初,温庭筠怀抱经邦之志,遵循古典诗学传统,创作了大量干预时世、直抒抱负、讽刺政治之诗作。有直刺朝廷时弊,负傲骨凌霜之情的“丰沛曾为社稷臣,赐书名画墨犹新。几人同保山河誓,犹自栖栖九陌尘”(《题李相公敕赐锦屏风》);有寄托志向抱负,承满腔热忱之气的“河源怒浊风如,翦断朔云天更高。晚出榆关逐征北,惊沙飞迸冲貂袍”(《塞寒行》);有积极干谒将厚,秉入仕经国之愿的“羁齿候门,旅游淮上,投书自达,怀刺求知”(《上裴相公启》);有感负才不遇,叹理想现实相冲的“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过陈琳墓》)等。这些诗歌无不承载着古典诗学传统中忧国忧民、经国治世、讽谏规劝的言志忧患内涵。但也就是这样的时代氛围,造就了古典诗学传统的变革。
温庭筠积极入世,但屡遭贬谪与排挤。诚然,诗歌可刺世讽喻、可抒怀负志,却最终无法尽然展现诗人内心那些挥洒不去的苦闷与悲愤。于是,众多文人学者认为,温庭筠词是扩展了诗歌的功能,用另辟蹊径之法来抒发自己的主观感受。或采用赋比兴,或寄托香草美人之意象。故而,汤显祖评温庭筠《菩萨蛮》乃“意中之意,言外之言,无不巧隽而妙入”;张惠言则以“兴于微言”之原则分析其《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乃“感士不遇之作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陈廷焯同道“飞卿《菩萨蛮》十四章,全是变化《楚辞》,古今之极轨也。徒赏其芊丽,误矣”;吴梅亦云“唐至温飞卿,始专力于词。其词全祖风骚,不仅在瑰丽见长”。由此可知,汤显祖、张惠言、陈廷焯、吴梅等人,皆将温庭筠《菩萨蛮》组诗中所描绘的闺阁女子离愁别怨之情与屈原骚体中的香草美人意象相提并论。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上的“香草美人”之意象,与《菩萨蛮》中的女子相合,其离愁别怨暗合士之不遇,旨在通过思妇之情寄寓词人内心的感伤。这是古典诗学传统的解构方式,是以诗歌言志抒情的政治功用价值来衡量这倚声填词的新文体。
但是,如若跳出诗言志、文载道的樊笼,而独以美学艺术特性对其文体进行分析,其实可以发现,古典诗学传统发展到晚唐这个时代,开始亟需一种能走在文学边缘,不受制于政治功用,不承载政教负担的新文体来走出政治、描绘生活。政局纷乱,志向无处舒展,既然无法入世,那便萧然出世。于是,唐五代词,一种介于民间俗文学与诗歌雅正文学之间的过渡文学范式开始在温庭筠笔下展现生机。他继承乐府歌行与民间词的风格韵律,开拓其绮艳诗的主题内蕴,创造了一种不直接抒发主观感情而着重描绘客观事物人物的文人词。虽然,这些词尤其以《菩萨蛮》组词为代表的词作在温庭筠手中主要以描绘闺怨离愁为主旨,对女性的观照与描绘使得其词染上了“但觉错金镂彩,炫人眼目,而乏深情远韵”之感的侧艳之风,但正如成松柳所言:“温庭筠的词创作解构了中国古典诗学的传统。它解构了诗言志的传统,词人不再带着极为浓烈的主观感情去创作,只是为了配合宴席歌舞中的即兴演唱,于是,作者的主观情感隐退了,客观景物的装饰就成了烘托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最佳手段,装饰性也就成了温词的重要特点。”这决定了温庭筠词的整体内蕴,不载言志之功、不负经国之志,只单纯描写生活,描绘勾栏瓦舍、歌舞宴会,极具俗艳之风。这既是古典诗学传统经由巅峰而发展到晚唐时代必然产生的变革,又是溫庭筠叛逆人格的一面在文学上的反映。他出入亭台楼阁,好靡靡之音;他放荡不羁,知交游宴乐。加之最高统治者对可供玩赏于歌筵酒席的词作十分推崇,温庭筠在一定程度上将词当作一种流行歌体进行对待,这种词体不受限于古典诗学传统中各种寄托暗喻的功效,而仅仅作为一种歌舞酬唱和反映都市生活的文体。可以说,温庭筠的诗歌,是其人格的雅正之处,而其词作,则是文人士大夫纵情声色以稍解失意之态。故而,对于《菩萨蛮》组诗的主题内涵,不必要非得从各种寄托性着手,去赋予它类似于诗言志的内涵。作为文学史上第一位大力作词的文人,古典诗学传统发展到温庭筠手中,其实更多程度上,是文学和人格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作用的产物,而这些“侧艳之词”在创作之初,实际并无深意。后世众多对其所赋予的存寄托之旨,暗抒志士之怀的主题内涵,其实是对温庭筠“言词必奉以为宗”地位的唱和,以社会功用性来标榜其价值。这其实太过于绝对,考辨其《菩萨蛮》组词的主题内涵,还应更为全面的观照词本身的文学特色和美学价值。
二、无寄托之意,乃客观抒情而已
王国维曾于其《人间词话》中载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词之所以区别于诗者,便是能言诗歌所不能言之处,因而,诗词两者是相区别的。张惠言等人将《菩萨蛮》与诗言志、文载道之功相合,以风骚美人意象为之作寄托之解,有其一定的渊源,但准确而言,稍为牵强。为此,他特意提出:“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王国维认为,温庭筠《菩萨蛮》乃兴致所到而作之词,其主旨便是词作中所体现的那般以女性为描写对象,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亦只是单纯揣摩与描绘女性的思愁与哀怨,并不若张惠言等人所言那般富有深意。所谓的深意,皆是后人以文学解构的方法所强加赋予的意义罢了。
除此之外,李冰若、蔡嵩云、刘熙载等人亦持此类观念。李冰若于其《栩庄漫记》中直接反驳张惠言、陈廷焯等人之言论,道:“嗣见张陈评语,推许过当,直以上接灵均,千古独绝。殊不谓然也。飞卿为人,具详旧史,综观其诗词,亦不过一失意文人而已。宁有悲天悯人之怀抱?昔朱子谓《离骚》不都是怨君,尝叹为知言。以无行之飞卿,何足以仰企屈子。其词之艳丽处正是晚唐诗风,故但觉镂金错彩,炫人眼目,而乏深情远韵。然亦有绝佳而不为词藻所累,近于自然之词。”李冰若此番观点其实有失偏颇。诚然,温庭筠为人正如《旧唐书》所载“士行尘杂,不修边幅”,但其人格亦在上文我们所提及过的诗格中有所展现,在他沉沦秦楼馆阁之前,也曾壮志凌云、胸怀天下,“文多刺时,复傲毁朝士”,只不过生不逢时,志向无处施展。因此,温庭筠并不是没有悲天悯人之怀抱,并不是不足以仰企屈子,他的部分诗歌,亦有深刻内蕴。但是,温庭筠词并不是诗,他的词不直抒胸臆,他作词的意图便是描摹词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情感状态,这种描摹是客观的,人物的主观情感已经从客观描摹中隐退,因而尽显其词香软绮艳、镂金错彩。这是温庭筠对词的艺术风格、语言形式、表现内容的一种追求与探索,这种艺术风格,重色彩的浓艳婉媚,重言辞的繁杂缛丽,无特殊寄托,独艺术风格而已。
与此同时,刘熙载在其《艺概·词曲概》所言“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则显得更为中肯一些。他肯定了温庭筠词的艺术价值和审美趣向,认为其词精妙绝人,但是就其主题内蕴而言,则与王国维一样,认为其只单纯反映闺妇生活与恋情,并无深意。温庭筠《菩萨蛮》组词主题无寄托之意,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其应制酬和之功用。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假其新撰密进之。”由此可知,温庭筠的《菩萨蛮》组词是符合皇室口味的,并曾作为一种盛传之词传入宫中,宣之于众。这也就决定了,该组词更大程度上是具备着其在歌筵宴席中供于歌唱娱乐的价值,这种展示秦楼楚馆、描摹伶官女性的侧艳之词,无法在深寓寄托之旨、抒志士之怀的同时,亦在宫廷中酬唱盛行。因此,温庭筠《菩萨蛮》组词的主题内涵当无寄托之意,乃客观抒情而已。但其艺术风格、语言形式和表现内容,为后代文人词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其艺术价值不愧后世赞之“言词者必奉以为宗,洵万世不祧之俎豆哉。”
三、本无寄托之思,潜意识暗合内在之情
叶嘉莹在《唐宋诗词十七讲》中谈论温庭筠时曾言:“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词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本来不在中国过去的文以载道的教化的、伦理道德的、政治的衡量之内的。在中国的文学里边,词是一个跟中国过去的载道的传统脱离,而并不被它限制的一种文学形式。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它突破了伦理道德、政治观念的限制,完全是唯美的艺术的歌词。”也就是说,词是一种有别于诗文的一种特殊文体,相较于诗文而言,词更注重的是其艺术价值而不是其社会功用价值,温庭筠词亦然。故而,温庭筠作《菩萨蛮》之时,将词的艺术风格、语言形式作为重点考虑对象,注重客观事物的装饰以及人物动作的呈现。词中的人物具备的是该人物自身的心理活动,所有的渲染也是烘托其闺阁离愁别怨之情,体现的是词所内含的唯美艺术价值。这样的词,打破了古典诗文固有的写作方式,不言志、不载道、不直接抒情。
然而,若仅单方面从词兴起之初的特征便直接武断温庭筠词完全只是客观描写,而不具备人的主观意愿,因而无寄托,乃“侧艳之词”“乏深情远韵”,这亦是不对的。无论是诗文还是词,只要是人主观创作的,虽然可能在表面做到“客观冷静而无动于衷”,但是内在所隐性蕴含的依旧是文人的主观意志,只不过没有显性展现罢了。因此,叶嘉莹提出:“词当初只是在歌筵酒席之间写给歌女演唱的歌词,本无深意,在作者的显意识之中并无‘言志的用心。可是就在这些男女相恋的内容之中,作者却无意间把自己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流露了出来。”这段话是十分中肯的。就拿《菩萨蛮》组词中最有名的一首《小山重叠金明灭》作比,词中所提及的“小山”“画眉”,若追本溯源,其实在长时间诗歌语言符号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词语早就潜意识地具备了本词之外的潜在深意。温庭筠选用这些词语来填词,一方面是此类词语的本意如此可入词,另一方面则是其内心深处潜意识流露而选择的结果。因为时局纷乱,郁郁不得志而转向亭台楼阁、勾栏瓦舍的女性描写,腐朽的都市生活虽让其词作在一定程度上蒙上了“侧艳香软”之风,但是其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一直以一种潜意识状态伴随着作词的始终,其隐性词格在潜意识的状态下与其人格和诗格实现了统一。
综上所述,长久以来,学界对于温庭筠《菩萨蛮》组词主题内涵的考辨一直未曾停止。有以张惠言、陈廷焯为代表的认为其“存寄托之旨,暗抒志士之怀”,有以王国维、李冰若为代表的认为其“无寄托之意,乃客观抒情而已”,还有以叶嘉莹为代表的认为其“本无寄托之思,潜意识暗合内在之情”。基于前文的考辨,笔者认为,温庭筠詞有别于古典诗学传统言志载道之功,《菩萨蛮》组词的主题内涵本无寄托,或描摹男女相恋之情,或抒闺阁离愁别怨,但在潜意识的作用下,词人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情感被无意识激发,这种潜意识作用其实是其人格赋予在词格中的内在意义,这不仅是《菩萨蛮》的隐性价值,亦对后世词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曾益.温庭筠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张惠言.词选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4]孙克强.唐宋人词话[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
[5]张惠言.论词(词话丛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