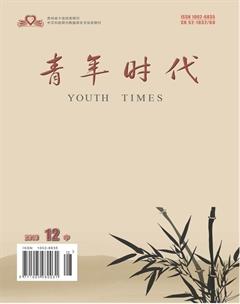论《史记》合理的文学性
廖文意
摘 要:《史记》是一部文史双栖之作。史官世家出身的司马迁继承父志撰写史书,秉承“实录”的原则,但由于撰写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主客观因素使《史记》包含了部分看似“虚构”的成分。史书不是单调地记录历史事件,司马迁在书中的合理推测和想象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合理文学性的体现,而这一部分内容也符合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史记》;史实性;文学性;以虚补真
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作为一部文学性强的史学著作,《史记》也遭到了质疑,不少人认为其中包含虚构的成分,如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逼真的历史场景刻画、人物独处时的“密谈”以及历代君王带有神话色彩的“感生”经历……然而,史书最根本的性质就是真实性,作为纪传体通史,它也不可避免的含有一定的文学色彩,那一部分文学性也必然要符合历史的真实。本文将从客观及主观两个方面分析《史记》作为史书的史实性及其合理的文学性。
一、客观上,难以避免的文学性
从客观层面来看,《史记》中的文学性部分是不可避免的。史书为人所撰写,而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浩瀚史料中缺失的一小部分只能通过对现存史料的合理推测进行补充,这基于史实的补充,是史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最为历代学者质疑的不外乎就是《史记》中细致的人物刻画和逼真的历史场景描写。
(一)细致的人物刻画
“鸿门宴”的历史真实性毋庸置疑,但真实的场景是否就与司马迁所记述的分毫不差?人物座次是否就是“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在暗示项羽可以行动诛杀刘邦以绝后患时有“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吗?樊哙进入宴席后真的有“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的神态吗?司马迁不可能在现场亲身经历这一切,他却能对宴席上人物的座次、神态作出如此细致的刻画和描写,这一部分叙述应该是司马迁在大量阅读典籍和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走访等途径得到口述历史及民间传闻的“史实”后,依照历史事实对不同性格的人物合理想象再加工的结果。这样的写法,不仅最大程度上还原了鸿门宴暗流涌动的局面,还表现出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而所谓虚构,是指凌空构作、凭空捏造,但《史记》中这一部分描写是基于事实的合理的推测,所以不能算作主观的虚构,笔者认为,这是历史真实与文学艺术性的统一,进行想象和推测是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二)历史人物的密谈与心理活动
然而更为人质疑的是《史记》中有关人物心理及人物独处时密谈的描写。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说:“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恒烛隐,何所据依软?”
以骊姬谮杀申生太子的记述为例——“献公始私谓骊姬,欲以其子而代太子,骊姬闻之伪泣,并扬言若此则自尽,而背后使人阴谮恶太子,欲立其子”。这一段记述属于骊姬与献公的“密谈”,身旁断不会有史官记录,而骊姬之泣是真是假只有她本人知道,她背后使人中伤太子的“密谋”除了她的心腹当然也无旁人知悉。而司马迁却对骊姬的心理活动及秘密行动了如指掌,这显然也与前文一般,是司马迁根据骊姬的个性及其想要谋夺王位的目的合理推测的结果。而这一部分想象也并非虚构,《左传》中也有相关描写——“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骊姬与大夫合谋夺取太子之位属于“密谈”,同样属于不可为外人知的内容,这一部分与前文鸿门宴中逼真的人物刻画同理。因此,这只能算是合理的想象,并不是扭曲历史真实的虚构。
至于历史场景的描写,《史记·项羽本纪》中对项羽“兵困垓下”的场景描写可谓极尽逼真。但同时也有人提出质疑,清人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可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类语,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笺补造化,代为传神。”
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们确实无从反驳,但这无从证实,也无从证伪,毕竟连这质疑本身也是基于历史情况的想象与推测。即便是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在记录事件时也不可能提供各个方面详实的材料,我们记录的历史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不含有文學性的成分。
“《史记》的虚构从形式上看是‘虚,实质是以理度真,以情揆真……《史记》毕竟以史实为主,虚构只是在史实基础上的一种‘以虚补真,司马迁潜心的遐想与揣摹,是为了修饰、补充史实。”①作为纪传体通史《史记》对于历史场景、人物心理等细节的合理想象与填充,使得人物形象生动情节丰富,确实具有一定的文学性,但此以大量历史材料为基础,并不是文学创作中的“虚构”,这样的文学性是合理合法的。这种基于史实的推测不会损害史书的真实性,更体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是史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
(三)感生神话的存在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五则感生神话集中在《本纪》。历代君王带有神话色彩的“感生”经历,在其他典籍上同样有记载。清梁玉绳曾云:“故于《殷纪》曰吞卵生契,于《周纪》曰践迹生弃,于《秦纪》又曰吞卵生大业,于《高纪》则曰梦神生季。”撰写史书“书法不隐”的原则要求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有中略无。感生神话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由于汉代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之说的盛行,第一代帝王的诞生是顺从天命的说法为大众所接受。今日看似虚构的感生神话被汉代民众认为是天神的授意,是天命真理,是他们的“史实”,《史记》记载感生神话的行为,正是其尊重历史的体现。
二、主观上,不可能存在的虚构成分
再者,从主观层面上看,《史记》不可能是司马迁随意添加主观虚构成分的作品。从司马迁的创作动机上看,他不会随意杜撰、虚构这部承载使命的著作。
(一)撰写《史记》是司马迁在父亲面前许下的承诺
司马迁是史官世家出身,他在父亲司马谈病重时允诺修史。重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司马迁写史书是继承父亲的夙愿,他不会不重视史书的编写。
(二)撰写史书是司马迁身为太史令的使命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②司马迁在与壶遂的对话中也曾明确表示自己只是在记录历史而非创作,这也表明了司马迁写作的目标是写一部史书,而不是一部举世瞩目的文学著作。
(三)撰写《史记》是司马迁的信念
《史记》是司马迁呕心沥血之作。因李陵事件遭遇宫刑后的司马迁身心遭遇毁灭性打击,对于司马迁而言,活着遭受的折磨比死去更痛苦,而他之所以还要艰苦地生存,不外乎就是为了《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志向。且司马迁早年曾跟随孔安国、董仲舒学习,有着深厚的文学和史学素养,并曾游历各地,见多识广,这一切都为他写史书打下了坚实基础。饱受史学熏陶的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撰写史书的原则是遵从历史的真实。由此观之,《史记》中看似虚构的成分并不是真正的虚构和捏造。
(四)为历代认可的真实性
《史记》从问世之日起,就其“实录”的原则受到极高的赞誉。班固曰:“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刘勰称其“实录无隐”、“秉笔直书”。鲁迅先生称其“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历代学者都对《史记》的史实性抱着坚信的态度,而对其文学性也有很高的评价,但归根结底,作为文史双栖之作的《史记》首先是一部史书,然后再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史实性是它最本质的特征,合理存在的文学性是它的附加价值。
三、结语
总之,《史记》的史实性毋庸置疑,但由于史官对历史事件的缺席、史料的欠缺以及记录时的主观性等主客观难以避免的因素,导致史家在修史时不可避免地在“史实”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阅读史料典籍的积累、民间口述传闻以及当时主流的思想文化对历史的细节进行合理的想象和推理补充,“即通过一定人为性的选择、融合和自解而来还原、构筑更加逼近历史的原图貌”③。这一行为始终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的面貌,是史实性与文学性的统一,此举是合理文学性的体现,符合历史的真实,并不是所谓的“虚构”。
注释:
①杨树增.《史记》的想象与虚构[J].贵州社会科学,1989(10):62-64.
②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③何颖敏.论《史记》中情节的虚构性[J].名作欣赏,2016(36):30-31.
参考文献:
[1]杨树增.《史记》的想象与虚构[J].贵州社会科学,1989(10):62-64.
[2]楚克侠.论《史记》的想象與虚构[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12(11):40-43.
[3]文丹.论《史记》的想象艺术[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4.
[4]何旭光.《史记》情节的虚构性和传奇性[J].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3):43-47.
[5]何颖敏.论《史记》中情节的虚构性[J].名作欣赏,2016(36):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