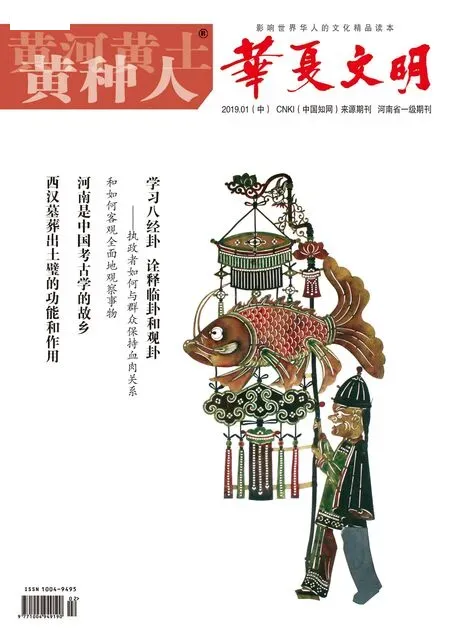濮阳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观察
□崔宗亮
河南省濮阳市位于豫、鲁、冀三省交界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濮阳地区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与周边其他地区相比,学界对濮阳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关注相对较少,这不能不说是华夏文明研究中的一件憾事。2014年10月,濮阳举办了规模宏大的“濮阳与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吸引了众多知名专家和学者。会议期间,大家各抒己见、相互讨论,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论述了濮阳地区在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对濮阳地区文明化进程问题的研究。笔者不才,曾对濮阳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有过一定的思考,现撰写成文,以求各位专家和学者斧正。
一、文明肇始期——仰韶时代早期
目前,濮阳地区发现最早的文化遗存可追溯到7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在戚城遗址发现有这一时期的小口壶、钵、罐等器物。但是,这一时期的遗址发现甚少,而且发掘面积较小,无法判断当时的聚落结构和社会形态。到了仰韶时代早期,濮阳地区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社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时,在濮阳地区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考古学文化,学界称之为仰韶文化“后岗类型”[1]或“后岗一期文化”[2],它与河套及山东半岛互为犄角,广布于整个黄河下游地区,而濮阳所在的豫北冀南地区正是该文化的核心区域。该文化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另有一些泥质灰陶、夹砂红陶和夹砂褐陶,一些遗址中也发现有较多的夹蚌褐陶。纹饰主要为素面,另有一些弦纹、附加堆纹等。彩陶数量较少,多为红黑彩的竖线、宽带、三角、网格等几何纹。器形有罐形鼎、盆形鼎、圜底釜、灶、弦纹罐、平底钵、圜底钵、盆、小口双耳壶、细颈瓶、鼓、支脚等,流行圜底器,不见圈足器。采用叠烧技术成器的红顶钵、盆等是该文化的一大特色,在该文化中也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白陶。后岗一期文化强盛时,曾对周边地区进行了剧烈的扩张和辐射,在周边的北辛文化、半坡文化、大河村文化以及岱海地区的一些文化遗存中都可见到该文化的因素。濮阳地区发现的后岗一期文化遗址共有8个,分别为西水坡[3]、铁丘[4]、戚城[4-5]、蒯聩台[6]、小海通[7]、咸城[6]、仓颉陵[8]、蚩尤冢等,其中西水坡、戚城、铁丘遗址经过科学发掘,为探讨这一时期的聚落结构和社会形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下面我们从单个聚落和聚落群两个层面分别论之。
先看单个聚落。西水坡遗址发掘面积较大,且出土遗物丰富,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我们便以西水坡遗址为例,探讨这一时期聚落内部的布局和结构,进而蠡测当时的社会形态。房址和墓葬最能反映聚落结构和社会形态,房址是人们生前活动的重要场所,而墓葬则是现实社会制度的写照或间接的反映[9],它像居址一样,也是一种“人群的居住方式”[10],因此二者可以相互印证,互为补充。西水坡遗址发现的房址较少,无法由此判断当时的社会结构,但从这些房址建造简单,主要为方形或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来看,当时社会应该还处于人人平等的阶段。西水坡遗址墓葬发现较多,明显地可以分为南北两个墓区,其中北墓区又可分为三个墓群,南墓区则有四个墓群(图1)。一个墓群实际上代表着一个社会基本单位。考虑到墓群内墓葬的数量有7~25座,平均每个墓群也就15座而已,而二次合葬墓内所葬死者的数量也在2~11人。显然,这些特征与家族的范畴比较吻合。因此,我们认为墓群所反映的社会基本单位就是家族。那么,由墓群构成的墓区就应为比家族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氏族,而由南北两个墓区形成的整个墓地则应为胞族一级的社会组织。这样,西水坡遗址墓群→墓区→墓地三个层次的布局正好反映了家族→氏族→胞族三级社会组织的存在。在这个社会组织结构中,氏族是最基本的组织单位,人们的许多宗教、祭祀活动都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的。家族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且从早到晚独立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但它的职能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生活方面,自始至终没有脱离氏族的束缚。在西水坡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不少二次合葬墓,所葬死者在2~11人,骨架的摆放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每个合葬墓代表一个家族单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这个家族是父系还是母系。这些合葬墓经过年龄和性别鉴定的有11座,从性别年龄组合来看,它们有多种形式,包括:成年男女合葬、成年男性合葬、成年女性合葬、小孩合葬、成年男性与小孩合葬、成年女性与小孩合葬。我们知道,合葬墓体现的应该是亲密关系,那么同性合葬、男女老幼合葬、小孩合葬便只能是血亲关系——兄弟、姊妹或另外的一些亲戚关系。在男女合葬墓中,男女比例不协调者(M86、M91、M108)以及虽然协调但并非一男一女者(M101),肯定也不是姻亲关系,而只能是兄妹关系。至于那些成年男女合葬墓中只有一男一女的,如M102和M169,我们无法完全排除他们是夫妻的可能性,但更多的应该还是血亲的兄妹关系。因此,西水坡遗址的合葬墓体现的是一种血亲关系,并不是姻亲关系,男女之间基本上呈现出平等的关系,当时社会属于母系氏族的可能性较大。

图1 西水坡遗址墓葬布局图
再看聚落群。在上述8个仰韶文化早期遗址中,西水坡、戚城、铁丘、蒯聩台相距不远,且集中分布,形成了聚落群,我们称之为“西水坡聚落群”(图2)。其中,西水坡遗址面积5万平方米,铁丘遗址面积3万平方米,蒯聩台面积2.8万平方米,戚城仰韶文化遗址面积不详,估计不会超过5万平方米。显然,西水坡聚落的面积要明显大于其他3个聚落,且发现有重要的蚌塑龙虎祭祀遗存。因此,它应该是这个聚落群的中心聚落,而戚城、蒯聩台、铁丘则为一般聚落。这样,西水坡聚落群就存在着两级聚落层次,而这两级聚落层次应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氏族→胞族两级社会组织的生动反映。但是,这两级聚落之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等级分化和城乡分野,居于较高层次的西水坡聚落不同于一般聚落的地方,仅在于其作为整个聚落群宗教祭祀中心而存在。那时的宗教祭祀事务还是一项社会全体人员普遍参与的公共活动,它为全体人员服务,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并没有出现特权阶层,而主持祭祀活动的巫觋也只是人们的公仆。
由上可见,当时的社会还处于人人平等的阶段。不管从单一聚落的布局结构还是从整个聚落群的聚落层级来看,当时的社会并没有出现分化和复杂化的迹象,依然处于人人平等的阶段。不过,在西水坡遗址发现了三组蚌砌龙虎图案,它们是当时祭祀活动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天文、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是华夏文明发轫阶段产生的第一批文明因子。正是这些文明因子燎起了华夏文明的熊熊大火,驱动了华夏文明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可以说,尽管仰韶时代早期的濮阳地区还处于平等的氏族社会阶段,但已经孕育出了当时华夏大地上的第一束文明,由此拉开了文明化进程的序幕。
二、文明发展期——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
经历了仰韶时代早期的辉煌后,濮阳地区进入了相对沉寂的阶段。到目前为止,在濮阳地区还没有发现仰韶时代中晚期的遗存。考虑到这一时期,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异军突起,黄河中游地区庙底沟文化空前扩张,处于两种文化相交地带的濮阳地区,不可能不留下一些重要的文化遗存,只是限于目前考古工作开展较少,还没有发现而已。相反,我们推测这一时期濮阳地区分布着众多的文化遗存。大凡一支发达的考古学文化莫不最早诞生于多支考古学文化的相交地带,而这也正是华夏文明能够最早诞生于中原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从地理中心的角度来看,中原的确处天地之中,实为四方辐辏之地;但从边缘效应理论的层面来看,中原却是周边地区的边缘和相交地带,因而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经常在这里碰撞、交融,进而更容易产生更加先进、更高层次的文化。由此来看,濮阳地区处在东西两大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最前沿,可以更加便捷、更加充分地吸收周边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和融合,因而可能较其他地区更早产生新的文明因素,进入文明化进程的更高阶段。因此,我们认为仰韶时代中晚期应为濮阳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图2 濮阳地区仰韶时代早期聚落及聚落群分布图
在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也即“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濮阳地区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文化遗存,如西水坡第五期遗存[11]、高城仰韶文化遗存[12]、戚城东城墙探沟底层遗存等。从发掘情况来看,它们与辉县孟庄龙山早期遗存[13]、新乡洛丝谭第二期文化遗存[14]等文化面貌相似,属于同一支考古学文化,有学者称之为“孟庄龙山早期文化”[15]。该文化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泥质黑陶和夹砂褐陶次之,有一定数量的夹蚌褐陶。纹饰以篮纹为主,绳纹、附加堆纹、弦纹和绳切纹也占一定比例,方格纹、楔点纹数量较少。器形主要有夹砂深腹罐、夹蚌厚胎深腹罐、盆、钵、高领瓮、碗、壶等,其中夹砂深腹罐唇部多压印花边,腹部多饰弦断篮纹,是该文化极具特色的代表性器类。该文化来源于大司空文化,同时也是后岗二期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该文化发掘的遗址较少,即使有所发掘,也没有见到完整的墓地、房址等,因此无法从聚落结构和聚落层级去考察当时的社会形态。但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该文化发现的几个重要遗址,在之后的后岗二期文化时期都有城址的发现,如孟庄、戚城、高城等。龙山城址出现这些遗址恐怕不是偶然的,与这里长期的文化积淀不无关系。也就是说,在龙山城址出现之前,这些遗址肯定也是当时所在地区的中心聚落。我们知道,史前城址至少是一个部落或者方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是社会分化、城乡分野、社会复杂化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在此之前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的层级分化就反映了社会分化和复杂化的初级阶段,而这正是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为文明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是濮阳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尽管这一时期濮阳地区发现的文化遗存较少,但是通过我们的推测和分析可以看出,在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这一阶段,濮阳地区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化和复杂化的迹象,文明化进程较之以前明显加快。
三、文明形成期——龙山时代晚期
经过两千余年的积累与发展,到龙山时代晚期,濮阳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步伐大大加快,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这一过程在考古学上有着清晰的反映。目前,我们在濮阳地区发现这一时期的遗址多达30余处,考虑到仍有很多遗址湮没在历次黄河泛滥的泥沙之下,那么,最初的遗址数量估计不会少于100处。通过对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分析可知,它们属于后岗二期文化的范畴。后岗二期文化广泛分布于太行山南麓和东麓的黄河、古济水两岸,西到焦作、济源一线,东至山东菏泽、聊城,北到安阳以北漳河一带,南达商丘、开封以南,接近《汤诰》中的四渎范围:“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该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泥质灰陶为最多,其次是磨光黑陶、磨光灰陶、泥质棕灰陶、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等,部分遗址有较多的夹蚌褐陶。纹饰夹砂陶以方格纹为主,篮纹、绳纹次之,泥质陶以篮纹为主,弦纹、刻画纹和指甲纹比较盛行。器形主要有罐、甗、斝、鼎、盆、刻槽盆、钵、圈足盘、豆、壶、觚、杯、鬶、子口瓮、碗和器盖等[16]。该文化在当时是一支先进、发达的考古学文化,曾对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濮阳地区作为后岗二期文化的核心区域,同时也是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汇聚了当时最先进的物质和精神因素。下面我们从单一聚落和聚落群两个层面对这一时期濮阳地区的文明化程度做重点阐述。
先看单一聚落。濮阳地区经过发掘,发现布局结构比较清楚的聚落仅有戚城遗址1处。戚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卫国畿内的一处重要城邑,因诸侯多次在此会盟而闻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内涵。目前,在地面上仍可看到当时的城址。经过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在东周城址下又发现一座龙山城址[17],大体与东周城址重合,略呈方形,东西长420米,南北宽400米,面积约16.8万平方米。其中,西城墙顶宽5.25米、底宽23.4米、残高4.8米,东城墙顶宽14.3米、底宽28.5米、残高3.05米。在城墙外发现有壕沟,其中北壕沟紧贴北城墙,宽30米,其余三面壕沟距城墙17~20米,东壕沟宽43米,西壕沟宽35米,南壕沟宽25米①以上为笔者参加“2014濮阳与华夏文明研讨会”时,听取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一丕副研究员的汇报记录。。在南城墙中部发现有可能属于城门的迹象。另外,在城址内部共钻探出6处夯土基址②参见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和戚城文物景区对戚城遗址的钻探资料。,但是否属于龙山时期目前仍不得而知,还有待于下一步的发掘研究。通过历年的考古发掘,在戚城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龙山文化遗物,尤其是2006年H1出土的红陶鬶[18],制作精细、形态优美、栩栩如生,肯定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用品,而应属于礼器的范畴,是贵族阶层祭祀、宴飨等使用的物件。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尽管戚城龙山城址的布局结构还不十分清晰,但是高大巍峨的城墙、宽阔深幽的城壕等体现出的浓郁的政治、军事色彩,无不说明当时社会已出现了严重的等级分化和阶级对立,而城乡分野也已成为当时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之一。另外,作为礼制物化形式的精致陶礼器,既是当时人们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区别贵族内部等级的标志物[19],它的出现和使用,正是礼制形成并且制度化、规范化的一个重要反映。由此观之,龙山时代晚期已是濮阳地区文明化程度高度发达的一个阶段。
再看聚落群。到目前为止,在濮阳地区发现这一时期的聚落共有33处(表1)。除仓颉陵、蚩尤冢、徐堌堆、玉皇岭和后玉皇庙等5处遗址位于濮阳地区北部和东部,比较分散,没有形成聚落群外,剩下的28处遗址集中分布于濮阳市辖区和濮阳县境内,形成一个庞大的龙山文化聚落群(图3)。按照聚落的规模,可将这个聚落群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高城遗址。遗址位于濮阳县五星乡高城村南,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在同时期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面积最大。另外,高城遗址还处于濮阳龙山文化聚落群的中心位置。显然,它是这个聚落群中的核心聚落,发挥着统驭整个聚落群的重要作用。
第二层次为围绕在高城遗址周围的面积较小的聚落。这类聚落的面积多为15万~50万平方米,它们是次一级的中心聚落,在高城周围共有3处。一处是位于北部的戚城遗址,在遗址内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的古城址,面积16.8万平方米,应是高城北部的重镇;一处是位于西南部的文寨遗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还有一处是位于东南部的咸城遗址,当地俗称“霸王台”,面积达21万平方米。在这3处次中心聚落周围都分布着一定数量的小型聚落,它们与次中心聚落一道构成了一个小型聚落群,而在这些小型聚落群中,次中心聚落又是中心聚落。

图3 濮阳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聚落及聚落群分布图
第三层次是围绕在次中心聚落周围以及其他一些零散的小型聚落,此类造地面积多小于10万平方米。这类聚落有24处,在戚城聚落周围分布有铁丘(3.1万平方米)、马庄(3万平方米)[20]、蒯聩台(2.8万平方米)、西门里(0.9万平方米)、金桥(30万平方米)[21]等遗址,文寨聚落周围分布有瑕丘(0.25万平方米)、三里店(1万平方米)、湾子(1.5万平方米)、西子岸(0.92万平方米)、齐劝(10万平方米)、高庄(2.5万平方米)等遗址,咸城聚落周围分布有李家庄(0.94万平方米)、程庄(1万平方米)[20]6、袁楼(6万平方米)、台上(1万平方米)、岗上(6万平方米)、后岗上(5万平方米)等遗址。另外,零散分布的一些聚落,如团堽(8万平方米)、小海通(9万平方米)、长亭(1.05万平方米)、青丘(1.2万平方米)、云峰寺(0.48万平方米)、后高庄(2万平方米)、丹朱堌堆(0.5万平方米)等遗址也属于这一层次的范畴。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濮阳龙山文化聚落群中聚落的数量从第一层次到第三层次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等差序列分布状态(图4),表明当时的社会结构十分稳固,这是社会严重分化、城乡分野、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濮阳龙山文化聚落群三个层级的存在表明当时濮阳地区已出现了一个“都、邑、聚”结构齐全的文明古国,濮阳地区也由此较其他地区率先进入了文明社会。其实,这一古国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濮阳境内,以濮阳为核心的河济地区都是它的分布范围。在河济地区,还分布有辉县孟庄[13]、安阳后岗[22]、博爱西金城①山东大学考古系2008年博爱西金城遗址发掘资料。、温县徐堡②郑州大学考古系2008年温县徐堡遗址发掘资料。以及山东阳谷景阳冈[23]等次一级的中心聚落。从整个河济区域来看,它们都围绕在高城遗址周围,显然高城遗址就是这一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图4 濮阳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聚落等级示意图
从对戚城遗址布局与结构以及濮阳龙山文化聚落群等级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龙山文化晚期,也即大约4000年之前,以濮阳为中心的河济地区率先步入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国家阶段,其优于周边各区的文化核心地位逐渐得以确立。历史文献记载及考古研究证明,当时河济地区已发展成为一个欣欣向荣、四方辐辏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16]。可以说,经过两千余年的积累与发展,濮阳地区在龙山时代晚期率先进入了文明社会,濮阳地区的文明化至此最终形成。
四、结语
濮阳处于中原华夏文化与东方夷族文化的相交地带,同时又是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相互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史前时期,来自东西南北的考古学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大放异彩,使其成为华夏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区域之一。可以说,正是因为濮阳地区地理位置的适中性,再加上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生业模式的多样性、文化传统的连续性等因素,其才在华夏大地上最先启动了文明化的按钮,率先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较早进入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国家阶段。当6400多年前的仰韶时代早期,整个华夏大地还普遍处于蒙昧状态时,濮阳地区的先民已率先举起了文明的火把。中华第一龙,蜚声海内外,华夏文明渊源有自,龙虎俱在铁证如山。因而,仰韶时代早期可称之为濮阳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肇始期。继之而来的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濮阳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相对沉寂,但沉寂正是一种积累和发展,在仰韶时代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这一发展过程开始明显加快,当时社会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和复杂化迹象。因而,这一时期可称之为濮阳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发展期。进入龙山时代晚期,濮阳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步伐大大加快,城址开始出现,城址的政治、军事等功能凸显;聚落层级有所增加,并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稳定结构;精致陶礼器开始出现,并形成了完备化的礼制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一时期社会分化已经十分严重,阶级或阶层对立已经十分尖锐,城乡分野已经十分稳固,社会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因此,这一时期可谓是濮阳地区文明化的最终形成期。
分析和研究濮阳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有助于深刻认识濮阳在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在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中,它可起到一定的完善和补充作用,并且可以观察华夏文明在不同地域所表现出来的独有特征以及了解其背后的深刻含义。不过,限于濮阳地区考古学材料的缺乏,我们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尤其是文明化进程的发展阶段,当时的聚落结构和社会形态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还有赖于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对其进行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