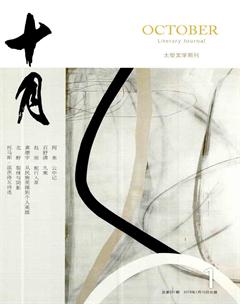追忆汪道涵同志二三事
陈鹏生
汪道涵同志是一位经国济世、业绩彪炳的政治家,是一位学养深厚、儒雅谦和的文化人。1993年4月间,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是汪老运用中华文化展示巨大亲和力的典范。这是一次破解40多年坚冰的会谈。当时汪老和辜老各自从一个边门同时走进会议室,走到长条会议桌两边,彼此相视而笑,同时举起右手紧紧地相握。于是出席会议采访的两百多位采访记者同声高喊:“再一次握手!”汪老环视一下记者们,微笑地向大家致意。这时真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两人都坐下来时,如何开始对话呢,汪老会前已对辜老的经历、性格和爱好作了详细的了解,知道辜老是一位曾拜孟小冬为师的余派老生名票,而自己也是对京剧情有独钟的梅派乾旦名票,于是一开始就从京剧谈起,谈到两岸文化同宗同源,然后自然地转向两岸关系的主题上来。汪老就是这样运用京剧情缘,使这种传统文化成为两岸联结的纽带,打开了会谈的话匣,促使会谈取得理想的结果。
时隔5年,在1998年10月,久违祖国50多年的辜老率团访问上海,与汪老再度会晤。汪老又专为辜老在兰心大戏院举办了一场京昆晚会。年过八旬的辜老激动得亲自上台亮嗓,唱了《洪洋洞》和《鱼肠剑》,当唱到“为国家那何曾半日闲度”和“一事无成两鬓斑,叹光阴一去不复返”时,辜老唱得特别深情,展示了老人满腔的家国情怀,引来台下长时间热烈掌声。辜老这次访沪,还参观了城隍庙的豫园,写下了“但知春意发,谁识岁寒心”的墨宝。其期盼祖国统一的殷殷之心,令人感佩。淡江大学一位资深的教授对我说,汪老运用京剧情缘真是绝妙好手。传统文化在他手里变成强大的政治推力,妙哉!伟哉!
还记得1994年秋,我随汪老及其夫人孙教授一起应日本经济界一批著名人士的联合邀请赴日访问,日本素闻汪老对儒家文化有研究,就由几位前任首相竹下登等人为首组织了一场欢迎会。专请汪老谈谈儒家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当时我国驻日大使馆事先知道参加大会的可能有些是台湾方面的人士,在两岸关系较为紧张的时候,可能会提出一些敏感的问题,要有所准备。汪老听了胸有成竹,泰然以对。果然,会中有些台湾媒体就两岸关系提问大陆准备如何应对。汪老听了,微笑地说,两岸本一家,两岸关系之道,唯和与合,我们只要目标一致,就可以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艺术地处理好两岸的关系。台湾媒体又进一步逼问,大陆有什么具体对策?汪老笑了一笑,说,今天会议的主题是谈中华文化,你们大概也是奔着对中华文化的共识而来的吧,我倒想听听你们对中华文化有何看法。台媒听了,一时语塞。我们站在边上的人,这时都感到汪老的应对,真是高超和淡定。
“大味若淡,大音稀声”是汪老的人生写照。他十分关注台湾民众的民心所向,讲和谐,重包容,时时以解开台湾人民的“历史心结”,纾解台湾人民的“历史悲剧”的胸襟去对待台湾同胞复杂的心态。有一次,一位学者写了一篇对台的文章,送请汪老审阅。汪老看后,只是将文章中的“战略”改为“方略”。他说,两岸同胞是兄弟,说话何必那么“大气”。我们要充分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这就要从细节处做起。明月不沉,哲人不朽,斯人已去,言犹在耳。我们都应把汪老的话,牢牢记在心间。
汪老是一位嗜书如命的人,他爱书,知书,又懂书。他的文化品格的形成,和他一生勤读书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每次见面,他总是先问,最近看了什么书,有什么心得。有时候,我把我们编写的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方面的书送去,他都是高兴地说,送书最好,送书最好,书交是神交,也是心灵之交。他公務缠身,但只要一有空,他就会亲自到附近的书店去选书、读书,以至附近书店的职工都认得他,还会把新书的信息送给他。即使是出国访问,他也是见缝插针,找机会到书店泡一泡。我们一起访日时,只要挑半天时间让大家自由活动,他就整个半天都泡在书店里,最后买回两大箱的书。汪老直到重病住院的时候,他还在病床上忍着病痛阅读由北京大学翻译的《古今数学思想》和《西方文化中的数学》,这一类的书是连专家看起来都有点费劲的专业呀。汪老一生爱书,藏书无数,其历年藏书多达十多万册。所以汪老说,将来应该把这些书捐献出去,成立个图书阅览室,供大家阅读。
汪老是把读书和做人联系在一起的。他知道我是从事中国法律史教学和研究的,就多次教导我,历史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宝库,治史很重要,但一定要有“自得之学”,既不要标新立异,也不要人云亦云,这是一种治史的器识和治史的胸襟。汪老的教导,也内在地反映其读书的高尚精神境界。
哲人其萎,风飒木萧。汪老关心国家社稷的情怀,视通万里的眼界,舒卷风云的器度,铸就了他作为一位睿智文化人的精神风范。“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经·小戎》),这种风范,值得我们一生追寻。
(作者为原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资深法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