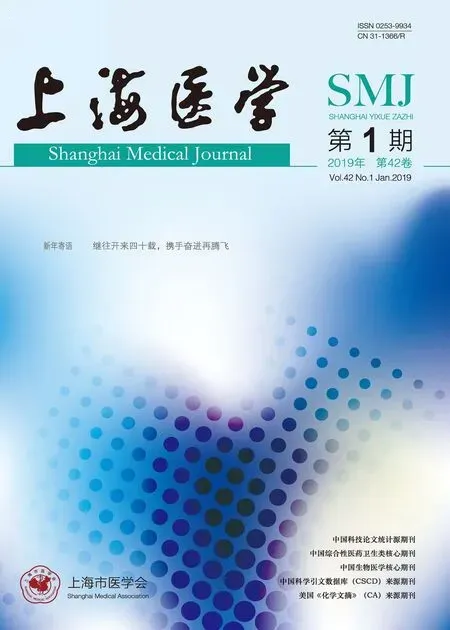肠道微生物与免疫的研究进展
周 瑛 王伟铭
大量微生物与人类和平共处,其数量约为人类体细胞和生殖细胞总数的10倍,其中超过70%聚集在肠道内。微生物作为病原体的屏障,发挥着重要的代谢作用,同时通过刺激免疫系统来调节炎性反应[1]。微生物群与人体之间的平衡如果被破坏就会引起多种疾病,常见的有炎症性肠病、乳糜泻、食物过敏、结肠癌等。人类免疫系统主要分为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现就从这两方面简单综述肠道微生物与人类免疫的关系。
1 肠道固有免疫
肠上皮细胞、微皱褶细胞(M细胞)、杯状细胞、肠腺嗜酸细胞、上皮内淋巴细胞(IEL)、巨噬细胞等在肠道固有免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肠上皮细胞通过模式识别受体(PRRs)识别微生物,M细胞是重要的抗原转运细胞,杯状细胞分泌黏液,巨噬细胞吞噬病原体和分泌抗炎细胞因子,IEL具有肠道异质性等[2]。
1.1 PRRs 常见的PRRs有 Toll样受体(TLRs)、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NLRs)、视黄酸诱导基因1样受体、C型凝聚素、黑色素瘤缺乏因子2样受体、OAS(2'-5'oligoadenylates synthesis)样受体等。TLRs和NLRs在肠道微生物免疫中起了重要作用;而视黄酸诱导基因1样受体等重点识别病毒,通过Ⅰ型IFN发挥作用。
1.1.1 TLR4 TLR4是TLRs与肠道免疫中最重要且被研究最透彻的,它由上皮和免疫细胞表达,并在肠黏膜防治革兰阴性细菌中发挥作用。在识别其同源配体时,TLR4二聚化并启动促炎反应的激活信号级联,此后诱导两种信号通路,即髓样分化因子88(MyD88)依赖性和My D88非依赖性途径,并产生促炎细胞因子和Ⅰ型IFN。目前已知参与这两个途径激活的衔接蛋白有4个:My D88、包含 Toll/IL-1 的接头蛋白(TIRAP)、IFN-βTLRS结构域衔接蛋白(TRIF)和TRIF相关衔接分子(TRAM)。My D88和TIRAP负责诱导促炎基因,而TRIF和TRAM诱导IFN。在MyD88依赖性信号转导中,MyD88识别配体后,被募集到TLRs的细胞质结构域并与之结合,通过磷酸化募集并激活IL-1受体相关激酶(IRAK)-4和IRAK-1,进一步激活TNF受体相关因子6(TRAF6)、转化生长因子激活激酶1(TAK1)。激活的TAK1磷酸化I-κB激酶(IKK-b)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6,使Ⅰ-κB降解,进而使NF-κB的核易位,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炎性反应发生。My D88依赖途径的激活同时激活了髓鞘碱性蛋白(MAP)激酶,如MAPK p38和c-Jun氨基末端激酶,进而导致转录因子AP-1的激活。而MyD88非依赖性途径则激活Ⅰ型IFN反应,促使IFN-α和IFN-β表达,发挥抗病毒效应[3]。
将感染后肠易激综合征(PI-IBS)患者与健康人群对比发现,PI-IBS患者的回肠和结肠中的IL-1α、IL-6和IL-8 m RNA水平,以及TLR-4蛋白质表达水平显著升高,而IL-10 mRNA水平降低;在用脂多糖(LPS)刺激后,干酪乳杆菌DG可显著降低促炎性细胞因子和TLR4的mRNA水平,同时提高IL-10的水平,提示干酪乳杆菌DG可改善黏膜的炎性免疫应答[4]。Alhasson等[5]发现,在海湾战争疾病中,化学暴露引起严重的肠道微生物失调,包括厚壁菌、软壁菌大量增加和拟杆菌大量减少,这些微生物的改变减少了闭锁蛋白,增加了紧密连接蛋白2,从而提高了肠道通透性,使内毒素入血,激活小肠和大脑的TLR4;而在TLR4敲除小鼠和无菌小鼠中,小肠和额叶皮层中酪氨酸硝基化、炎性介质IL-1β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则显著减少。提示,肠道菌群紊乱、通透性增加和内毒素入血引起的TLR4激活参与了海湾战争疾病中的神经炎性反应和胃肠失调。另外,在2型糖尿病肾病早期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中,TLR4表达水平高于正常人,且在体外经过LPS干预刺激24 h后,TLR4、NF-кBp65蛋白表达和IL-6分泌水平升高,趋化因子配体2和CD68在肾小管的过度表达,造成肾小管巨噬细胞浸润、组织损伤、糖尿病肾病进展[6]。
1.1.2 其他TLRs TLR2通过刺激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介导对细菌肽和肽聚糖的先天免疫应答,其主要位于巨噬细胞,参与介导IFN-β的产生。研究[7]发现,乳酸杆菌改善了5/6肾切除大鼠结肠中紧密连接蛋白和TLR2表达的下调,降低了肠道的渗透性,从而降低了血清吲哚酚硫酸盐、尿素氮水平和尿蛋白排泄量。另有实验[8]发现,用富含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的益生菌处理大鼠后,黏蛋白2、紧密连接蛋白-1、闭锁蛋白和TLR2的表达增加,而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3、环氧合酶2和β-链蛋白的表达降低,提示益生菌通过增强TLR2改善肠黏膜上皮屏障完整性和抑制凋亡与炎性反应。
TLR5可以识别鞭毛蛋白,鞭毛蛋白是目前发现的TLR5的唯一配体。克罗恩病相关性大肠杆菌可在鞭毛蛋白受体TLR5缺陷小鼠中诱发慢性结肠炎,并且在除去外源性细菌后不能自主恢复,提示微生物参与了先天免疫的调节并引发自身免疫性疾病,其机制可能与TLR5缺失导致依赖IL-1β的免疫途径异常有关[9]。
TLR9识别细菌DNA中未甲基化的胞嘧啶鸟嘌呤二核苷酸,并且足够水平的TLR9信号转导可维持肠道上皮中的稳态。另有研究[10]也发现,乳酸杆菌激活肠道固有淋巴细胞产生IL-22,增强肠道黏膜屏障功能并促进调节性树突状细胞向肝脏聚集,这些树突状细胞激活TLR9产生IL-10和转化生长因子-β,进而抑制急性肝损伤时肝脏的炎性反应应答,提示肠道微生物参与调节免疫耐受。
1.1.3 NLRs 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2(NOD2)是NLRs中常见的一种,在小肠的上皮细胞高度表达,被细菌胞壁成分肽聚糖激活后分泌细胞因子,介导自噬,细胞内囊交换,上皮再生,产生抗微生物的多肽,从而影响微生物的组成。NOD2可以识别脆弱杆菌,诱导产生高浓度的IL-6和IL-8、中浓度的IL-1β和TNF-α,以及少量的IL-10、IL-17、IL-23和IFN-γ。
De Bruyn等[11]在克罗恩病患者回肠活组织检查中发现厚壁菌和拟杆菌增加,考虑与NOD2突变直接参与了微生物生态失调有关。Ohlsson等[12]发现,在无菌环境下,与野生型和 Myd88-/-的小鼠相比,NOD1或NOD2缺乏的小鼠骨皮质厚度并未增加;骨组织上TNF-α和NF-кB配体的受体激活因子的表达量在无菌小鼠和野生型小鼠中显著降低,而在 NOD1-/-或 NOD2-/-小鼠中不下降,提示肠道微生物增加TNF-α、RANKL在骨组织上的表达和减少骨量的机制均同时依赖于NOD1和NOD2信号通路。
1.2 巨噬细胞 巨噬细胞作为固有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激活后产生包括 TNF-α、IL-6、IL-10、转化生长因子β在内的大量促炎细胞因子和各种活性氧,在肠道微生物与人类免疫系统之间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巨噬细胞激活包括经典活化型(M1型)和替代活化型(M2型)两种类型,M1型具有促炎作用,而 M2型相反。M1型巨噬细胞通过激活多种促炎性反应因子来根除细胞内的感染,是主要的“杀菌”成员。而不受管制的M1型巨噬细胞的活性反而诱导组织损伤,如在糖尿病肾病早期,在糖基化终末产物和TNF-α的作用下,可观察到促炎性的M1型巨噬细胞被激活[13]。此外,微生物反过来可影响巨噬细胞的功能。另一项研究[14]结果显示,大肠微生物发酵产物丁酸酯通过信号转导和转录活化因子(STAT)6/H3K9通路,促进体外和体内的 M2型巨噬细胞极化,同时可减轻右旋硫酸葡聚糖钠诱导的小鼠结肠炎模型中结肠的炎性反应。
1.3 IEL 分布于上皮细胞间的IEL是黏膜免疫系统的特征性细胞。小肠IEL具有很高的异质性[2],其中40%是γδT淋巴细胞。γδT淋巴细胞因其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的缺陷和独特的免疫调节功能,被认为是针对感染和肠道伤口愈合的第一道防线的关键细胞。胃肠道屏障不成熟使早产儿易患坏死性肠炎,而γδT淋巴细胞通过产生IL-17保持肠壁完整性并部分阻止细菌易位[15]。另一组重要的IEL是CD8+αβ+T淋巴细胞,其功能类似于常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Ⅰ类分子限制性细胞毒性淋巴细胞。在小鼠的肠道环境下,淋巴细胞活化因子家族受体4表达并与IEL上CD8+αβ+T淋巴细胞受体结合,通过信号转导控制细胞毒性CD8+αβ+IEL的扩增,调节固有层吞噬细胞的可逆耗竭和小肠中的炎性反应[16]。
2 适应性免疫
与机体其他部位的免疫系统相比,消化道的适应性免疫有其特点。首先,由二聚体免疫球蛋白(Ig)A介导的体液免疫是其主要形式;其次,辅助性T淋巴细胞(Th)17细胞在肠道免疫应答中十分活跃,诱导保护性免疫;再次,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维持了肠道对食物抗原和共生菌的免疫耐受。
2.1 Ig A 在肠道微生物和各种食物成分的刺激下,黏膜浆细胞产生的Ig A形成二聚体,与跨上皮细胞的Ig受体结合,控制相关基因的表达,调节免疫。Ig A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机制:经典途径是通过T淋巴细胞依赖性并由TGF-β调控;另一条途径与T淋巴细胞无关,而依赖上皮细胞、树突状细胞和先天性淋巴细胞。无论是哪条路径,都提示肠道微生物参与了Ig A浓度和多样性的调节。
肠腔内的Ig A可以抑制微生物黏附到上皮细胞,中和微生物产生的毒素或酶,增强M细胞对抗原的摄取和胞吞转运作用,调控微生物入侵的途径和调节对食物的耐受;也能与Ig A Fc受体(FcαRI)受体相互作用,招募并激活中性粒细胞,产生促炎或抗炎反应。感染诺如病毒的无菌小鼠的小肠和结肠中产生了大量Ig A,膳食纤维在微生物作用下产生的短链脂肪酸也可以刺激肠道Ig A 的分泌[17]。
微生物群促进了Ig A的产生,反之,其所产生的Ig A也会影响微生物的组合。在炎症性肠病高发的IL-10-/-小鼠中,使用丁酸钠治疗后,肠道菌群发生变化,如厚壁菌增多、普雷沃氏菌减少[18]。在刚出生的小鼠中,使用野生型母鼠喂养的小鼠的肠道内可以产生丰富的乳酸菌,而使用Ig A缺乏的牛奶喂养的小鼠的机会致病菌增加[19]。
2.2 Th17细胞 黏膜系统的Th17细胞主要分布于结肠和回肠的固有层,可能与这些部位有大量特定的微生物聚集有关,如梭菌相关性分段丝状菌易在该处形成群落,对于Th17细胞的分化有作用。Th17细胞表达的IL-17A和IL-17F不但能诱导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如IL-6、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进而调节嗜中性粒细胞的分化和活化,而且可以刺激上皮细胞产生抗菌肽和CCL20,诱导3型先天性淋巴细胞产生IL-22。此外,Th17细胞也可作用于B细胞,诱导全身B细胞分化和抗体产生。
IL-17和IL-22刺激肠道上皮细胞加速分泌黏液和β-防御素,具有保护黏膜免受微生物伤害的作用,如刺激IL-17的表达可预防柠檬酸杆菌的感染[20]。然而,Th17细胞的过度激活可能导致严重的疾病,如它可以在TGF-βl作用下诱导肾脏局部微环境中IL-17的产生,升高肾小球硬化指数,加重肾脏局部炎性反应[21]。
2.3 Treg细胞 普通器官中的Treg细胞含有对自身抗原特异的T淋巴细胞受体,而肠道中表达叉头样转录因子3的Treg细胞则不同,它含有一套独特的T淋巴细胞受体组,可产生IL-10,作用于髓系细胞,通过激活STAT3来抑制对膳食中无害抗原和共生微生物抗原的免疫应答。除髓系细胞外,Th17细胞也表达高水平的IL-10受体α(IL-10Rα),因此IL-10可同样抑制Th17的活性。如在小鼠中,多糖A产生的叉头翼状螺旋转录因子(Foxp)3+Treg抑制Th17活性,从而促进细菌肠道定植,被用于炎症性肠病的治疗[22]。另一方面,共生细菌及其代谢物也可促进并诱导黏膜耐受的Treg细胞产生。在经典的狼疮性肾炎模型小鼠 MRL/lpr中使用乳酸杆菌后,其肾功能改善,存活时间延长,可能机制是乳酸杆菌减少了肠道中的IL-6而增加了IL-10,降低了血循环中IgG2a的浓度并减少其在肾脏的沉积;同时在肾脏中,乳酸杆菌促进Treg表达的增加[23]。一些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和吲哚,也可作为信号分子,参与调节Treg细胞的功能。
3 小 结
近十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人体与肠道微生物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在大量的无菌和常规培养动物模型中发现,微生物在人类固有和适应性免疫的发展和调控中起了重要作用,并且与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关。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宿主和微生物的关系对预防和治疗与肠道微生物菌群失调有关的疾病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