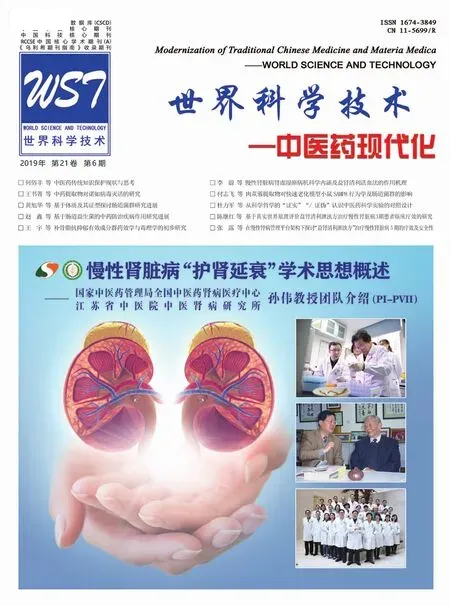中药调控肠道菌群防治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的研究进展*
戴永娜,付志飞
(1.天津中医药大学临床实训教学部 天津 301617;2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 天津 301617)
脂代谢紊乱是指各种遗传性或获得性因素引起血液及其他组织器官中脂类及其代谢产物异常的病理过程。血脂代谢是该过程的核心,当脂质来源、脂蛋白合成、代谢及转运等过程发生障碍时,均可导致血脂代谢紊乱。高脂蛋白血症及低脂蛋白血症是脂代谢紊乱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对机体的影响复杂而繁多。临床上以高脂蛋白血症为主,主要常见相关疾病包括动脉粥样硬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以及肥胖,血糖水平控制不良的糖尿病患者也常伴有Ⅳ型高脂蛋白血症[1]。另外,血脂异常对其他靶器官如大脑和肾脏等同样具有一定影响[2]。因此,探究脂代谢紊乱及其相关疾病发生发展的生物学机制,寻求有效调节脂代谢的治疗靶点和方法是防治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的重点研究方向。
肠道菌群是肠道微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体第二基因组”,其动态平衡对机体生理功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3,4]。近年来,系统生物学和多组学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肠道菌群的研究进程,诸多研究均阐释了其与代谢疾病之间的相关性[5,6]。肠道微生物群与宿主的免疫系统共同调节宿主代谢,肠道菌群失调对脂代谢异常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7,8],并且通过给予益生菌或通过粪菌移植等方法来改变肠道菌群组成,调节肠道菌群稳态亦能缓解并改善疾病状态[9,10]。故而,肠道菌群变化与疾病的关系以及通过调控肠道菌群来防治代谢性疾病的作用与机制亟待进一步研究。
中医学在利用肠道菌群治疗疾病方面早有记载[11]。中药及复方以水煎剂形式通过口服发挥药效,其多种有效成分进入消化系统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调节肠道菌群结构和代谢产物功能,有助于维持机体肠道菌群的稳态;另一方面,肠道菌群也对中药成分进行转化,产生出具有较强药理活性的次生代谢产物,从而作用于靶器官发挥药效[12]。中药在体内代谢及吸收入血成分呈现多途径和多靶点交互反应,从肠道菌群的角度阐明中药防治脂代谢异常疾病的作用机制,为进一步解释中医药多层次、多靶点的起效作用和精准治疗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综上,本文主要从肠道菌群与脂代谢紊乱的关系、中药通过调控肠道菌群防治高脂血症、肥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等相关疾病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 脂代谢紊乱与肠道菌群概述
高脂血症、肥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等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与肠道菌群之间关系的研究频见报道,目前仍以相关性研究为主,但随着研究技术的进步,因果性研究逐渐增多,机制研究逐步深入。脂代谢紊乱可影响肠道菌群稳态,对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大量动物实验研究表明,高脂饮食诱导的大鼠或小鼠脂代谢紊乱模型,其肠道菌群组成发生改变,或表现为肠道菌群多样性的降低;或表现为厚壁菌门、变形菌门及疣微菌门显著增加,而拟杆菌门显著减少[13];或表现为内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数目明显减少等[14]。基于217 名健康中国人的饮食干预结果发现,高脂饮食影响肠道菌群的平衡,具体表现为高脂饮食与Alistipes 属和拟杆菌属增加、粪便杆菌属减少相关,且血浆中促炎因子水平增加[15]。
肠道菌群也参与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肠道益生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是一种在肠黏液层稳定定殖的肠道共生菌,为目前研究较多的与代谢性疾病相关的细菌之一,多篇文献证实该菌对肥胖和糖尿病具有改善作用。研究证实肠道微生物群作为调节脂肪储存的环境因素,可控制禁食诱导脂肪细胞因子(fasting-induced adipocyte factor,Fiaf)的表达,通过提高肝脏脂肪生成和脂肪细胞中脂蛋白酶活性,降低磷酸化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的活性,以降低骨骼肌脂肪酸的氧化和能量消耗,导致脂代谢紊乱,增加脂肪组织合成进而脂肪积聚[16]。肠道内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菌属是人类肠道内的优势菌群,对降低血脂水平的作用尤为突出,可产生结合胆盐水解酶,水解结合胆盐转变为游离胆盐,与胆固醇共沉淀,并使经过肠道的重吸收减少而外排,同时肝脏利用循环中的胆固醇合成胆汁酸,完成胆固醇转化[17]。发酵乳酸菌Lactobacillus fermentum是一种含有乳酸菌水解酶的益生菌,体外研究发现增加该菌的的数量可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18]。随着肠道菌群分离纯化技术的提高,肠道菌群与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相互作用的关系逐渐被阐明。
2 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与肠道菌群之间的关系
2.1 高脂血症与肠道菌群相关性
高脂血症是引起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与高血压病、非酒精性脂肪肝、糖尿病等关系密切,受到广泛重视[19]。高脂血症时肠道环境受影响,明显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及比例,出现菌群失调[20]。肠道菌群可产生胆固醇氧化酶,加速胆固醇降解,平衡体内胆固醇水平[21];肠道菌群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要能源物质,其发酵主要产物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可通过抑制肝脏胆固醇合成或将胆固醇从血浆中重新分配到肝脏,调节胆固醇代谢[22];另外,一些益生菌能影响胆汁酸的肠肝循环,促使肝脏利用胆固醇合成胆汁酸增加,通过转化循环中的胆固醇而达到降低血脂的作用[23]。口服益生菌(如双歧杆菌和乳酸菌)可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群有效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与胆固醇代谢有直接关系[24]。
肠道菌群调节血脂平衡的机制大多分为两类:首先肠道菌群调节胆固醇代谢的相关基因,影响脂肪合成的转录因子以及酶。小肠上皮细胞表达的类尼曼-匹克C1 蛋白1(Niemann-Pick C1-Like 1,NPC1L1)是调节胆固醇吸收过程的关键蛋白,植物乳杆菌可下调NPC1L1 表达,加快清除胆汁中的游离胆固醇,进而降低胆固醇吸收[25];肠道菌群还可通过激活小肠中法尼醇X 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FXR)转录,促进成纤维生长因子分泌,抑制肝脏胆固醇7-羟化酶(cholesterol 7-alpha hydroxy-lase,CYP7A1)基因表达,是影响胆固醇代谢的重要途径[26,27]。其次,高脂血症等代谢性疾病的主要核心是机体慢性低水平炎症,而肠道菌群也会导致这种炎症的产生。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是参与该过程的重要物质,通过结合Toll 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 4,TLR4)诱导促炎因子如白介素-6(interleukin 6,IL-6)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MCP-1)分泌,加重代谢性疾病[28,29]。
2.2 肥胖与肠道菌群相关性
肠道菌群作为影响能量吸收和代谢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与肥胖的相关性研究始终是近年研究的热点。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的比值升高被认为与体重指数呈正相关[30,31],但也有文献指出其比值与体重指数无关[32,33],或呈负相关[34],至今尚无定论。2012年,赵立平教授首次证明阴沟肠杆菌是造成肥胖的直接元凶之一,它在人肠道里的过度生长是诱导肥胖的原因,这也是国际上首次证明肠道细菌与肥胖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35]。2017年,瑞金医院和华大基因的研究人员基于中国年轻汉族人群研究发现了抑制肥胖的肠道微生物——多形拟杆菌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并进行动物实验验证[36]。肠道菌群主要通过减少能量摄入、改善炎症反应等途径防治肥胖[37]。
肠道菌群与肥胖相关的具体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能量代谢:SCFAs 是机体一种重要的能量来源,其作用主要通过脂肪酸受体GPR41/43 通路介导[38,39],而该受体的能量调节作用依赖于肠道微生物群。GPR41/43 缺陷小鼠与传统饲养或肠道微生物定植小鼠相比,体重存在显著差异,而无菌条件下无明显差异[40,41]。肥胖小鼠肠道内的阴沟肠杆菌会导致Fiaf 活性降低[42],该基因可强效抑制脂蛋白酯酶(lipoprteinlipase,LPL)催化脂蛋白生成脂肪酸进一步合成甘油三酯,并且可以诱导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活化受体γ协同刺激因子1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γcoactivator-1α,PGC-1α)表达以激活脂肪酸氧化代谢,预防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43]。除此之外,碳水化合物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arbohydrate responsiv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ChREBP)和甾醇反应元件结合蛋白1c(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proteins-1c,SREBP-1c)介导肝细胞糖吸收和胰岛素水平,协同参与脂肪生成[44]。肠道微生物通过ChREBP 等转录因子活化增加介导的作用,刺激肝脏甘油三酯的生成[16]。腺苷酸激活蛋白激酶(Adenosine 5'-monophosphate(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是调节脂质代谢和胰岛素敏感性的另一个关键因素[45],与具有肠道微生物群的小鼠相比,无菌动物可通过增强AMPK 介导的外周组织脂肪酸氧化,从而预防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46];②代谢内毒素血症与慢性低度炎症:肥胖者呈现慢性低水平炎症的主要因素为LPS 循环浓度的增加,通过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TLR)-2/4-NFκB 相关通路介导炎症反应[47]。高脂饮食后双歧杆菌的降低与门脉血浆LPS 水平升高呈显著负相关[48],广谱抗生素可显著降低ob/ob 小鼠的代谢内毒素血症和盲肠LPS 含量,改善炎症并减轻体重[49];③肠道通透性:肠道菌群失调导致有害菌比例增加还会破坏肠黏膜屏障的通透性[50],主要由于内源性大麻素系统张力、紧密连接蛋白(Zonula occludens-1,ZO-1)、闭合蛋白和Claudin-1等表达增加所致[51],导致肠道通透性和代谢内毒素血症、炎症和代谢紊乱,而维护肠道黏膜屏障是防治肥胖的关键;④免疫系统:TLR-5是肠粘膜表达的先天免疫系统组成部分,在代谢综合征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52]。将TLR-5缺陷小鼠的肠道菌群移植到无菌小鼠(Germ-freeMice,GF)模型小鼠体内,观察到促炎因子水平升高,以及胰岛素抵抗、肥胖等代谢性疾病的特点[53]。先天免疫系统和肠道微生物群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代谢综合征的发生。
2.3 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与肠道菌群相关性
NAFLD是慢性肝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肝细胞内脂肪过度沉积为主要特征,是与胰岛素抵抗和遗传易感性密切相关的获得性代谢应激性肝损伤。随着肥胖及其相关代谢综合征患病率持续上升,NAFLD作为糖尿病、心脑血管等疾病的高危因素之一也越来越受到关注[54]。其主要致病因素包括遗传易感性、脂质过量积累和炎症反应。近来,肠道菌群在致病因素中的作用受到重视[55]。肠道菌群参与NAFLD 的主要机制包括肠源性内毒素血症、胆汁酸代谢、SCFAs等等[56]。
在西方国家NAFLD 发病率约为20-30%[57],而在病态肥胖人群中该发病率高达90%[58]。NAFLD的形成与能量代谢失衡相关。肥胖者的肠道菌群失调诱导了肝内乙酰辅酶A 羧化酶和脂肪酸合成酶的活性增高,进而肝脏脂肪合成也相应增加;另外,胆汁酸也可通过FXR 参与能量代谢中调节肠道菌群,进一步影响NAFLD[59]。
其次,肠道菌群与免疫系统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并且可以通过肠道菌群进行干预宿主的免疫功能。肠道菌群失调可能通过诱导免疫细胞活化,产生炎症反应,导致NAFLD 发生[60]。肝脏Kupffer 细胞的活化与NAFLD发生关系最为密切[61]。由T淋巴细胞和分泌型IgA(SIgA)组成的适应性免疫系统也是肠道抵抗致病原且调节共生菌的重要免疫系统屏障,通过效应T 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参与调节适应性免疫,而这些细胞因子的释放受某些肠道菌群的影响,比如毛螺旋菌科等;梭状芽胞杆菌还能够影响T细胞的分化,不仅会导致炎症发生,亦可破坏肠道黏膜屏障,导致NAFLD[62-63]。
在40%的NAFLD 患者中存在肠道通透性增加[64],胆汁酸代谢异常、紧密连接蛋白表达下调及分布异常和益生菌比例失调都会导致NAFLD 伴随的肠粘膜屏障功能障碍[65]。肠道菌群紊乱致使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可通过增加肠道通透性和促进LPS 或其他肠道细菌的吸收,肠内细胞间紧密连接受到破坏[66-67]。
2.4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与肠道菌群相关性
Wang Z 等在一项纳入1876 名受试者的大型临床队列中首次发现氧化三甲胺(Trimetlylamine oxide,TMAO)与心血管疾病相关[68],研究者开始关注肠道菌群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联系。随后在一项纳入4007名受试者的扩大样本的临床研究中,再次证明了血浆TMAO水平升高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存在联系[69]。TMAO 水平升高的患者罹患AS 等相关疾病的风险更高[70],TMAO 成为心血管疾病诊断的一种新的生物标志物,并独立于传统的危险因素。动物实验也验证了富含TMAO 饮食可促进AS易感小鼠发病[71]。因此,肠道微生物在三甲胺(Trimethylamine,TMA)代谢中起着重要作用:肠道菌群依赖性地代谢膳食卵磷脂胆碱生成TMA,并在肝黄素单加氧酶作用下生成TMAO[72]。
无论是TMA 前体物质胆碱还是与其结构相似的红肉和高脂肪乳制品等饮食中大量存在的L-肉碱作为底物,TMA 均是通过两种微生物酶系统产生的:胆碱TMA-裂解酶(cutC)及胆碱TMA-裂解酶激活酶(cutD)以胆碱为底物释放TMA[73];微生物加氧酶(CntA)及微生物还原酶(CntB)以L-肉碱为底物形成TMA[74]。TMA 通过门静脉循环进入肝脏被FXR 激活的肝黄素单加氧酶3(flavin-containing monooxygenase 3,FMO3)氧化成TMAO[75]。TMAO与AS相关性的具体机制尚未明确,但在该病的生理病理过程中TMAO 主要影响胆固醇代谢以及泡沫细胞的形成。首先,研究发现TMAO 可通过抑制胆固醇逆向转运,通过识别吞噬ox-LDL,促进巨噬细胞胆固醇积累和泡沫细胞形成,参与AS 进程[76];另外,TMAO 可下调胆汁酸合成酶和胆汁酸转运蛋白,如CYP7A1、CYP27A1,从而抑制胆汁酸合成而影响胆固醇代谢[77]。血浆TMAO水平升高还可激活NLRP3炎性小体[78]以及通过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和NF-κB 信号通路促进血管炎症等等[79]。SCFAs、LPS、胆汁酸等均会通过脂代谢紊乱等途径影响AS形成,机制与前面相关疾病相近,故不赘述。因此,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中相关影响因素的表达,如抑制TMA产生的关键的细菌酶等等,抑制TMAO的产生是治疗AS并减少心血管风险事件的潜在治疗策略。
3 中药调控肠道菌群以防治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的机制
3.1 中药调控肠道菌群防治高脂血症
含多酚、多糖等物质的中药及复方作为一种潜在的益生元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以达到防治代谢性疾病的作用[80,81]。黄连解毒汤具有降血糖、纠正脂质紊乱及改善胰岛素抵抗等作用,能增加高脂饮食诱导的高脂血症小鼠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和拟杆菌丰度,提示中医药清热解毒法具有通过调节肠道菌群以发挥改善脂代谢的潜在作用[82]。
黄连和吴茱萸联合使用可改善高脂模型动物血脂水平,其中小檗碱和吴茱萸碱是发挥药效的主要化学成分。小檗碱和吴茱萸碱等剂量配伍可改善高脂饮食诱导的大鼠血脂水平异常,机制与抑制肝脏胆固醇合成、促进胆固醇外排、抑制胆固醇的重吸收有关;同时可增加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提高益生菌表达、减少有害菌表达,主要集中在改善拟杆菌门、厚壁菌门、梭杆菌门以及疣微菌门菌群的表达[83]。
薏苡多酚提取物可改善高胆固醇饮食诱导的大鼠模型的血清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显著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可能与降低梭状芽胞杆菌和丹毒丝菌目有关,提示其可作为调节血清胆固醇水平以及肠道菌群失调的有效膳食补充剂[84]。
3.2 中药调控肠道菌群防治肥胖
中药不同化学成分如生物碱、多糖、酚类及中药复方均有通过改善肠道菌群而达到减肥目的的报道。如小檗碱能够纠正高脂饮食诱导的大鼠肠道菌群比例的失调,降低厚壁菌门与拟杆菌门的比例,保护肠道粘膜屏障,改善肠道通透性[85];能增加高脂饮食小鼠肠道内产SCFAs 菌的数量,降低致病菌,缓解炎症反应,改善胰岛素抵抗和肥胖[86]。中医的“扶正祛邪”对纠正肠道菌群功能紊乱具有一定的启示和临床意义,诸多研究证实,具有扶正气作用的补益类中药多富含多糖类成分,在调节肠道菌群紊乱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如灵芝菌丝体水提物能够降低高脂饮食肥胖小鼠体重、改善炎症,粪便移植实验表明其与调节肠道菌群相关,且高分子量多糖发挥关键作用[87]。麦冬多糖可以增加高脂饮食小鼠肠道益生菌,尤其是台湾乳酸菌和鼠乳酸菌的丰度,且呈剂量依赖性[88]。白藜芦醇因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而广为熟知,但其生物利用度极低,因此难以解释其体内药效物质基础,最近多项研究显示其药效作用的发挥与肠道菌群相关。研究表明,白藜芦醇能改善高脂饮食诱导的小鼠肠道菌群失调,提高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的比例,促进乳酸菌和双歧杆菌的生长,逆转脂代谢失衡,显著促进Fiaf 基因表达,降低血糖、血脂水平[89]。白藜芦醇和槲皮素联合使用可改变高脂肪蔗糖饮食诱导大鼠模型的肠道紧密连接蛋白和炎症因子相关基因的表达,进而达到改善胰岛素抵抗的目的[90,91]。肥胖受试者经熟地黄治疗后腰围均明显下降,放线菌门和双歧杆菌属增加,厚壁菌门也随之减少[92]。
除了单体中药、化合物外,亦有诸多中药复方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发挥药效的相关研究。大柴胡汤可减缓高脂饮食诱导的小鼠肥胖,并降低总体脂,改善脂代谢;调节脂肪组织中瘦素及脂联素基因的表达,同时可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93]。温阳益气活血方由四逆汤、真武汤、理中汤及四君子汤组成的复方,临床上用于治疗肥胖2 型糖尿病,临床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用药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均明显降低,且伴随着双歧杆菌、拟杆菌、乳杆菌数量的增加以及肠杆菌、肠球菌、酵母菌数量的减少[94]。益气健脾的四君子汤同样可以通过升高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数量,调节肠道菌群稳态以及降低肠道粘膜通透性,减少炎症介质产生,改善代谢紊乱[95]。
3.3 中药调控肠道菌群防治NAFLD
决明子、绞股蓝、大黄、葛根、马齿苋、银杏叶、三七、虫草、枸杞等均具有很好的降脂作用,其中以决明子应用较为广泛[96]。通过硫酸铁铵法筛选鼠李糖乳杆菌和植物乳杆菌等降脂菌株,和决明子总蒽醌协同作用于高脂饮食诱导大鼠NAFLD模型,可有效调节脂质代谢,并且改善高脂饮食导致的厚壁菌门比例升高,拟杆菌门比例降低,同时促进肠道紧密连接蛋白表达,维持肠道黏膜屏障完整性,减少肠源性LPS入血,缓解炎症反应,改善NAFLD[97]。
小檗碱[98]与栀子苷联合绿原酸[99]也具有相近功效,同样调节肠道菌群水平来改善肝脏脂肪变性、保护肠道屏障。中医学认为痰、湿、浊、瘀是NAFLD的主要病理因素,大黄泽泻汤健脾利湿、祛瘀泄浊,与该病病机特点相符,能有效减轻高脂饮食引起的NAFLD大鼠模型肝脏脂肪沉积、减轻体重、改善血脂水平,还可显著下调升高的厚壁菌门、脱硫弧菌属、埃希氏菌/志贺氏菌属等比例,上调拟杆菌门、颤杆菌克属等细菌比例;并且上调回肠、结肠组织中的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降低肠粘膜屏障通透性,减少致病菌及其代谢产物由肠道血流经门静脉入肝,以达到保护肝细胞、防治NAFLD的作用[100]。复方祛湿化瘀方,由茵陈、虎杖、栀子、片姜黄等组成,可显著降低高脂饮食诱导的NAFLD 大鼠体重,减轻其肝脏脂肪变性,同时降低肝脏中甘油三酯及游离脂肪酸水平;显著下降肠道中含条件致病菌的大肠杆菌/志贺氏菌属,并且短链脂肪酸产生菌属Collinsella丰度明显升高,提示该复方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结构以治疗NAFLD[101,102]。参苓白术散以补脾胃之药为主药,直接作用于肠道菌群改善脂质沉积,抑制肝脏炎症,改善机体代谢状态,亦可有效防治NAFLD[103]。
3.4 中药调控肠道菌群防治AS
关于天然药物防治AS的研究颇多,但着眼于肠道菌群的研究多以脂代谢、炎症等为基础进行阐述,包括小檗碱、葛根素、姜黄素、白藜芦醇、丹参素等。以多酚类药物研究居多,不仅能影响肠道菌群结构,并且修复肠道黏膜屏障,有利于改善炎症相关的代谢性疾病,已在其他疾病内容中详细总结。但值得关注的是,白藜芦醇是一种具有抗AS作用的天然植物化合物,能够通过调控肠道菌群抑制TMAO 生成,增加普通乳杆菌和双歧杆菌水平而改善肠道菌群结构,抑制肠肝FXR/FGF15轴,增加胆汁酸水解酶的活性,促进肝脏胆汁酸的合成,进而实现其抗AS的作用[104]。姜黄素可显著降低高脂饮食诱导的LDLR-/-小鼠血浆LPS水平,恢复肠道碱性磷酸酶活性和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在多水平上改善肠道屏障功能,显著减轻了AS发展趋势,提示姜黄素作为改善肠屏障功能、预防AS发展的潜在作用[105]。
4 结语
脂代谢作为机体的基础代谢在生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脂代谢紊乱与多种疾病及其并发症密切相关。随着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诸多科学研究支撑,对肠道菌群的认识取得了重大进展,也明确了脂代谢与肠道菌群具有密切关系。脂代谢紊乱发生时,肠道菌群结构及组成异常,而肠道菌群的失调亦会进一步加重脂代谢紊乱。故明确二者相关性对防治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高脂血症、肥胖、非酒精性脂肪肝、动脉粥样硬化等)的治疗具有指导意义。
中药活性化合物与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的研究具有重要前景,深入研究中药和肠道菌群的关系,又有利于丰富中医药理论。目前中药防治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肥胖方面,而关于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研究较少,可能与中药的生物利用度相关,并且与疾病的发病阶段和严重程度有关。且研究多为相关性研究,而对于因果性研究相对较少,中药中有近百种药食同源者,从中探寻具有调节肠道菌群的中药便是防治脂代谢紊乱相关疾病的新契机。对这些中药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进行证实和推广,补充研究之不足,将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