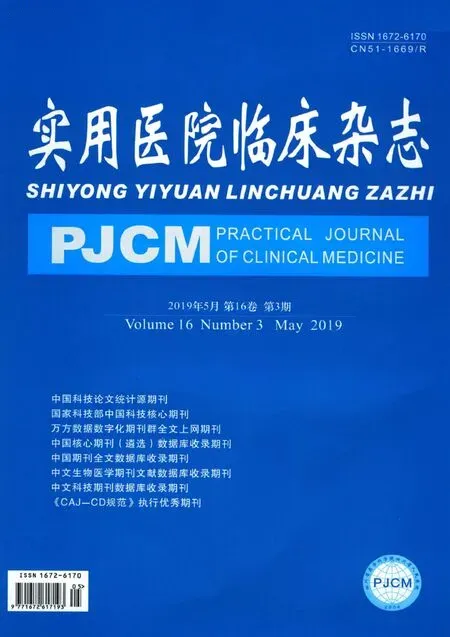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发病机制及早期诊断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刘劲燕,郭 璐△
(1.成都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2.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四川 成都 610072)
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和肺血栓栓塞症(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TE)。DVT是指血液在深静脉内异常凝结,导致静脉回流障碍的疾病。PTE是指来自静脉系统或右心的血栓阻塞肺动脉或其分支所致疾病,即通常所说的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研究显示,静脉血栓栓塞症年发生率为(100~200)/10万,已成为继心肌梗死和卒中后第三种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1]。本文就VTE相关的发病机制及实验室检测指标方面进行综述,以期有助于血栓的早期诊疗,减少血栓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
1 发病机制
1.1 遗传因素与VTEVTE是一种与后天和遗传多种危险因素相关的疾病。遗传因素与VTE风险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10年,已有超过88个基因与VTE相关,大约30%的特发性VTE是由于基因缺陷引起[2]。既往研究已在不同种族群体中观察到了VTE的遗传易感性,印证了基因缺陷在VTE发生中的重要作用。FV Leiden突变、凝血酶原G20210 A突变、抗凝血酶缺乏症和ABO血型等是西方人群的主要遗传危险因素,而对于亚洲人口则是罕见的;相反,PROC(c.565 C>T和c.574576 da/del)、PROS 1(c.586 A>G)和血栓调节蛋白基因(THBD)(c.151 G>T)等在亚洲人中很常见[3]。近年来,随着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s)等新技术的出现,不仅证实了VTE已确定的遗传危险因素,而且发现了更多新的遗传危险因素,如糖蛋白6(GP6)、人类免疫缺陷病毒Ⅰ型增强子结合蛋白1(HIVEP1)、KNG1和BAI3等[3]。
1.2 Virchow’s三要素与VTE1856年,德国医师Rudolf Virchow首次描述了导致静脉血栓形成的Virchow’s三要素,即血流淤滞、血管损伤和高凝状态[4]。静脉血栓的发生发展始于瓣膜或静脉窦[5]。虽然瓣膜有助于促进血液通过静脉循环,但它们也是静脉淤滞和缺氧的潜在位置。瓣膜窦血液淤滞与缺氧和血细胞比容增加形成高凝微环境可能导致抗血栓蛋白质,如血栓调节蛋白(thrombomodulin,TM)和内皮蛋白C受体(endothelial protein C receptor,EPCR)表达的下调,从而促血栓形成。低氧还会促进某些促凝剂,如内皮组织因子(tissue factor,TF)和P-选择素(P-selectin,sP-sel)的上调,进而导致白细胞或单核细胞衍生的含组织因子的白细胞微粒的募集[5]。虽然组织因子在这一过程中表达的确切位置仍存争议,但人们普遍认为,组织因子与P-选择素一起是血栓形成的基本成分[6]。血流量不足,纤维蛋白的沉积会局部激活凝血因子,与此同时,凝血抑制剂被消耗,而没有新抑制剂的流入[6]。抗凝血途径如蛋白C途径,它是由EPCR和与TM结合的凝血酶所触发,导致辅助因子Va和VIIIa的失活;组织因子引起的凝血被组织因子抑制剂所抑制;凝血酶则被抗凝血酶所阻断,反过来抗凝血酶又被类肝素蛋白多糖刺激[6]。随着凝血级联的展开,纤维蛋白、红细胞和血小板形成了所谓的静脉血栓并在血管内沉积。虽然静脉淤滞是静脉血栓形成的主要因素,但很少是造成血栓形成的唯一因素[6]。静脉淤滞和血管损伤或高凝状态的并存,大大增加了血栓形成的风险。
1.3 炎症、免疫与VTE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影响VTE形成的因素不仅仅局限于凝血系统,免疫系统与炎症也与血栓的形成和降解密切相关,三者的作用错综复杂,其间关系仍在探索中。
1.3.1炎症与VTE 炎症在VTE发生发展中的贡献需要从增强高凝状态和增加内皮损伤两方面来考虑。血栓形成的第一个事件可能是内皮细胞、血小板和白细胞激活,随后炎症发生和微粒形成,通过诱导TF(主要是由微粒携带的TF)触发凝血系统,这可能导致高凝状态[7]。血栓形成和溶解都与一系列炎症级联有关。有研究表明,在大约15%的肺血栓内膜切除标本中发现了中至重度炎症,并且,免疫/炎症基因占在VTE影响下表达显著改变的基因的近10%[8]。细菌性脓毒症是急性全身炎症反应后由内皮损伤和组织因子表达引起的炎症触发凝血的典型例子[9]。脓毒症导致凝血因子和血小板的激活和消耗,以及纤溶功能受损、内皮屏障破坏和血栓调节蛋白等生理抗血栓因子的丧失[10]。脓毒症中炎症与凝血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内皮的促凝特性尤为突出,如TF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vWF)的表达、激活与血小板的相互作用、促凝微粒的释放、组织因子途径抑制剂(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TFPI)和蛋白C/S抗凝系统的下调、纤溶抑制[9]。
1.3.2免疫与VTE 人体经历物理创伤、感染等各种“威胁”是不可避免的,而免疫系统则可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来识别这些危险或警报信号。凝血级联和抗炎反应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调节的关键因素,免疫系统如何识别外源性病原体的过程使得这两种机制之间的协同作用变得清晰,并由凝血机制将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以清除“威胁”。Engelmann和Massberg将这些相互作用称为“免疫血栓”,显示了它们之间微妙的平衡和协同作用[12]。多形核细胞、单核细胞和血小板是免疫血栓形成的主要细胞成分。这些细胞表达模式识别受体(PRRs)是止血和炎症反应密切调控的标志[11]。中性粒细胞可通过吞噬作用参与病原体的清除。从中性粒细胞产生的中性粒细胞外网状陷阱(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s)产生于对感染的反应,最初的特点是在宿主抵御微生物的过程中发挥着作用[13]。NETs还能通过激活内源性凝血级联、刺激血小板活化以及通过局部富集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和髓过氧化物酶以切割和氧化抗凝血剂(如TFPI和血栓调节蛋白)来支持免疫血栓的形成[13]。最后,NETs与血管内组织因子(ITF)结合,激活凝血的外源性途径[11]。单核细胞则可通过产生含ITF的微粒参与免疫血栓形成[11]。补体系统(特别是激活的补体成分C3a和C5a)通过触发血小板活化来支持免疫血栓形成[12]。免疫血栓形成的临界微妙平衡可被一系列炎症或外部机制改变,从而可导致病理性血栓如VTE形成。
2 VTE早期诊断标志物
2.2 凝血-纤溶相关指标
2.2.1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hrombin-antithrombin complex,TAT) 生理情况下,体内凝血酶原生成极少量的凝血酶,凝血酶生成后很快与抗凝血酶以1∶1结合成TAT而失去活性,以维持机体凝血/抗凝的平衡。TAT能够敏感地反映体内凝血酶的生成。TAT水平在血栓前状态可明显升高,所以临床上可以通过检测 TAT的水平来反映机体内血液高凝状态。Kansuke等的一项单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表明,近半数脓毒症患者初期出现严重的凝血病,在重症监护病房入院时单次测定TAT能够早期发现严重的凝血病[14]。另一项研究显示,下肢骨盆骨折患者术后第1、3、7天TAT水平在发生了VTE的患者中明显高于无VTE患者,经ROC曲线分析,术后第7天的TAT检测对预测术后VTE的准确率最高,且最佳截断TAT水平为3.0 ng/ml时,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93.3%和70.1%[15]。
2.2.2D-二聚体(D-dimer) D-二聚体在交联纤维蛋白形成和降解时产生,提供了凝血和纤溶系统激活的全局标志,并作为血栓性活动的间接标志。由于血管外纤维蛋白被局部纤溶酶降解为D-二聚体,后者分子量小,容易扩散到血流中。在其他条件下,如手术、创伤、感染、恶性肿瘤等,D-二聚体水平也升高[16]。以往观察表明,D-二聚体对排除VTE有较高的阴性预测价值,而对VTE的阳性预测值很低,因此D-二聚体测定仅作为排除性试验。此外,D-二聚体的诊断特异性随着年龄的升高而逐渐下降,以年龄调整临界值可以提高D-二聚体对老年患者的诊断特异性,并在排除可疑急性肺栓塞方面更安全有效。证据显示,随年龄调整的D-二聚体临界值[>50岁患者为年龄(岁)×10 μg/L]可使特异度增加到34%~46%,敏感度>97%[16]。
2.2.3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复合物(tissue 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plasminogen activated inhibitor complex,t-PAI-C) 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t-PA)和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1(plasminogen activator inhibitor type-1,PAI-1)是两种重要的纤溶活性调节因子。血管内皮细胞产生的t-PA,将在肝脏产生释放到血液中的纤溶酶原转化为纤溶酶,从而激活纤溶系统[17]。当内皮细胞损伤时,t-PA和PAI-1都释放,并迅速以1∶1结合形成t-PAI-C,因此可认为t-PAI-C也是血管内皮细胞损害指标的分子标志物。国内有学者通过对创伤骨折手术病人进行观察,发现血浆t-PAI-C浓度增高对术后静脉血栓形成有着良好的辅助诊断价值[18]。
2.2.4纤溶酶-α2纤溶酶抑制剂复合物(plasmin-α2plasmin inhibitor complex,PIC) 体内纤溶酶生成后很快被纤溶酶抑制剂(α2-plasmin inhibitor,α2-AP)以1∶1中和形成PIC,测定血浆PIC的浓度可反映与纤溶酶抑制剂结合的纤溶酶水平。机体内纤溶活性与抗纤溶活性的动态平衡产生了PIC水平变化,因此它是反映机体内纤溶与抗纤溶动态平衡的良好分子指标。在非溶栓治疗状态下,血栓形成前期以及纤溶亢进时PIC浓度明显升高,溶栓过程中α2-AP被消耗而致PIC值改变,亦可以提示溶栓治疗效果[19]。Ikeda等通过对183例接受妇科腹部手术的患者研究发现,PIC、年龄和肿瘤横向直径是VTE风险的重要独立决定因素[20]。另一项实验中则联合应用TAT、PIC,发现在接受恶性肿瘤化疗的住院日本患者中,TAT增高而PIC未增加可能是VTE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21]。
2.2.5血栓调节蛋白 血管内皮损伤是血栓的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TM系一种跨膜糖蛋白,存在于血管内皮细胞表面。当内皮细胞损伤时,TM则脱落入血使得血浆TM水平增加,因此,血浆TM的浓度增加能够可靠地反映血管内皮的损伤。此前学者们已证明TM水平与内皮细胞损伤程度成正相关。TM水平的检测已经作为反映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敏感且可靠的指标。与此同时,TM是使凝血酶由促凝转向抗凝的重要血管内凝血抑制因子[22]。既往研究已表明THBD突变与血栓形成密切相关[3]。
2.3 P-选择素P-选择素由活化血小板的α颗粒和内皮细胞的Weibel-Palade小体中释放,是细胞粘附分子家族中的一员。细胞表面P-选择素辅助白细胞黏附血栓,而血小板P-选择素则进一步束缚白细胞,促进静脉血栓形成。P-选择素还可触发促凝微颗粒的释放,增加单核细胞组织因子的表达。可溶性P-选择素(sP-sel)被认为是一种比D-二聚体具有更好诊断性能的生物标志物。Vandy等和Ramacciotti等发现与D-二聚体相比,当结合Wells评分≥2时,sP-sel>90 ng/ml的阳性预测值为100%[23,24],sP-sel<60 ng/ml和低概率Wells评分排除DVT的敏感性为99%,阴性预测值为96%[24]。在Antonopoulos等对sP-sel的Meta分析中显示,VTE患者或单纯DVT患者的sP-sel显著增加,在研究中异质性最小,且sP-sel的综合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0.57和0.73[25]。此外,随着血栓程度的增加,sP-sel水平增加的趋势也不明显[23]。由此可以看出,sP-sel能够反映血栓的存在,但并不能反映血栓的程度。
随着人们对血栓性疾病的逐渐重视,对VTE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但不难看出,VTE的发生发展机制是极其复杂的,涉及到的生物学标志物亦是多样且优劣性不一。如何能简便、快速、便宜且安全地尽早发现VTE,并及时预防或治疗是我们关注的热点,也值得我们未来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