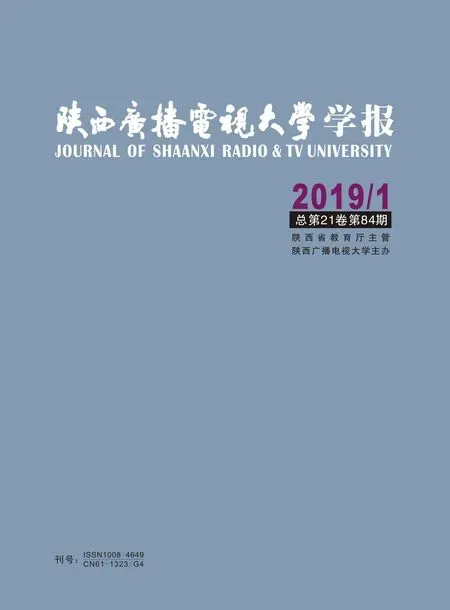战国魏楚秦变法比较研究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人事处,陕西 西安 710119)
一、魏国李悝变法
李悝,又作李克,公元前422年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魏国称雄于战国初期。主要内容有:
“尽地力”。“魏有李悝, 尽地力之教。”[1](2084)“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2](1124)即李悝向魏文侯游说“尽地力”之重要性,鼓励魏文侯制定重农益农法令。
“平籴法”。平抑粮价,由国家控制粮食购销价格。丰年以平价收购,防止商人压价伤农;灾年则平价出售储备之粮,防止商人抬价伤民。
编著《法经》。集诸国刑典,共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已失传。明代董说《七国考》引桓谭《新论》披露部分内容,重刑苛律,森然恐怖。
“夺淫民之禄”。“为国之道, 食有劳而禄有功, 使有能而赏必行, 罚必当”,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斥责“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者为“淫民”,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3](155)
“尽地力”“夺淫民之禄”简论:魏国疆域较小,地寡人众,“尽地力”旨在挖掘土地潜能,使地无旷土,尽其所用,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 农伤则国贫。”[4](1124)“平籴法”保障粮食价格平稳,无论丰年或灾年,保护农民实际收益,维护社会长久稳定。虽然史籍未见记载魏国推行了哪些“尽地力之教”法令措施,但其之所以成为战国早期强国,显然是以重农益农政策为支撑的。首先,充足粮食可凝聚人心,巩固经济基础,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其次,战争比拼的是一个国家的财力,战国时代攻伐频繁,需要强大持久的国力,农业乃重中之重。《史记》惜墨如金,但多处为“尽地力”用笔:“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5](1233)“魏有李悝, 尽地力之教。”[6](2084)“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7](3048)《汉书》亦言:“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行之魏国, 国以富强。”[8](1124)它们均未提及李悝变法有政治领域,也见出两位史学大家认为李悝变法主要在经济方面。但不得不说的是,李悝变法尚未触及经济制度的根本,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改革,而仅仅是对经济政策作了一些调整。
“夺淫民之禄”对于削弱贵族特权、改革用人体制、建立封建官僚制度有进步意义,但和彻底废除世爵世禄相距甚远,真正可“夺”世禄的“淫民”也不多,大多世卿子孙或在朝堂或在釆邑都是为官吏的,“夺淫民之禄”难得实效。再从魏国实际情况看,“夺淫民之禄”“使有能而赏”或许在魏文侯时代发挥了作用,但其后,用人政策阻滞而守旧,“食有劳而禄有功”未贯穿下去,能人干才先后离魏而去,如吴起、商鞅、孙膑,再其后张仪、范雎。
二、楚国吴起改革
吴起,曾佐李悝改革,魏武侯时遭猜忌,离魏入楚,为楚悼王倚重主持变法。主要内容有:
“明法审令”。禁止纵横家四处游说干扰新法实行,“破驰说之言从(纵)横者。”[9](1908)
“废公族疏远者”。“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10](1908)韩非则言:“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11](70)
降低俸禄,裁减职官。“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养练之士。”[12](70)
整顿吏治。“使私不得害公,谗不得蔽忠, 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13](2173)
“砺甲兵以时争于天下。”[14](122)
“废公族疏远者”蠡测:吴起变法因楚国贵族政治势力太过强大而变法夭折。楚国的疆域、人口、物产是其它他国无与项背的,但政治制度极端守旧落后。远在熊通自封为楚武王,楚国即创县制,分封“公”或“侯”以理县。许多攻伐或归降的小国大都成为楚国下辖之县。这些县制的权利名义上直属楚国朝堂,但实质上是贵族政治的领主分封制,公、侯保持独立的分治权和私家军队,与其他诸侯国卿大夫的采邑基本相同。由于众多的宗室贵族受封公侯,楚国领主贵族太众,势力强大。春秋时朝政一直由斗、成、屈、蒍四大公族把持,战国则屈、景、昭贵族领主家族左右朝政,直至楚国亡,是典型的贵族政治封建领主制社会。吴起奔楚,时值楚国由盛而衰,对外,连年战争敗于晋之三国,国势衰退;于内,贵族领主势力太强。吴起尝向楚悼王分析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若兵之道也。”[15](70)故此,针对内外现状,吴起变法的重心是政治方面。
“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司马迁与韩非之语,有所差别,相比之下,司马迁言似更可信。其一,屈、景、昭三大宗族势力正盛,不仅其祖辈于楚有功,子孙也在朝为官,有劳或有功,即使不继承父祖爵位,本人也必封爵。更况这些封建领主把持朝政,对外征战可与国君一致,于国内事务则多虑各自宗族根基。楚国的领主分封制决定了它根本没有废除所有封君之子孙三世爵禄的土壤条件。其二,未见其他史籍有与韩非所说一致的记载。故此,余以为根据楚国当时领主贵族强势之状,结合司马迁和韩非之言,应是废除了王室旁系家族封爵已历三代的爵禄,并非彻底废除世卿世禄制,两者相差甚远。“废公族疏远者”,只能削弱那些已经孱弱的领主贵族,而恰恰对于干涉朝政的强势宗族影响很小。故变法失败。
另外,吴起变法未能关注经济领域,几乎社会各阶层在变法中都没有获得实际利益;因而亦失去了任何一个阶层的支持。楚悼王卒, 变法立即遭到贵族领主疯狂反击,人死法亡。
三、秦国商鞅变法
前361年,秦孝公立。下令求贤,商鞅入秦,获孝公重任,前356年、前350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重编户籍,严刑峻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16](213)对任何作奸犯科,皆“重刑而连其罪。”([17](16)(下引《商君书》,均出自该版本,仅注明篇目)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毋论出身,“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18](213)官爵提升与斩敌首级数目相称。爵位分二十级,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所谓私斗,非一般斗殴,而指“邑斗”,即领主间为争夺土地、财产聚众争斗。不准私斗目的是严禁封建领主扩充势力。
奖励耕织,一是鼓励开荒,颁布《垦令》。二是解放农奴为庶民。“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19](213)即尽力从事男耕女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可升为庶民身份;弃本求末或游闲惰懒而贫困破产者没入官府为奴。三是多捐粮可获爵,“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靳令》)上述奖励农战。
“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去强》)“无以外权任爵与官(《恳令》)”,形成规范的选拔官吏机制。亦达整顿吏治目的,“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
废除世卿世禄制,变领主为地主。“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25](213)无军功的贵族领主,一概废除其爵位,变领主为地主,不再享受贵族特权。有军功者按军功大小重新核定爵序等级。
第二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除井田,允许土地买卖。《史记·商君列传》:“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汉书·食货志》记董仲舒云:“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21](57)从法律层面承认开垦土地的私有权,允许土地买卖,按个人所占土地面积划定赋税。
推行县制。“集小乡都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22](217)
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实现统一度量衡制。
四、商鞅变法的成功之处
分析评价历史上变法的成与败,不能以变法者本人的结局而言之,而应以变法改革带来什么功效以及是否持续后世为标准。相对于李悝、吴起,商鞅之法更全面、深刻、持久,执行力度更大。简论之:
1、以“壹赏、壹刑、壹教”为纲。纲举目张,奠定了秦国上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基础。“壹”,即统一、唯一。读《商君书》可见“壹”的述说甚众,“訾粟而税,上壹而民平。”(《垦令》)“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上作壹,故民不偷营,”(《农战》)“国务壹则民应用”(《壹言》)等等,不胜枚举。至《赏刑》篇,则明确为“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即统一奖赏,“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壹刑,即统一刑法,“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壹教,即统一教化,摈弃儒家等不利于农战的说教,“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请谒,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辟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以“壹”为纲,变法内容皆围绕于此铺陈,秦国上下方向尽明。另外,“壹刑”所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具有重要的政治启蒙意义。
2.完成了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变,形成强势的中央集权制。秦国比较落后,领主势力原本不强。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废除世卿世禄制,变领主为地主,是商鞅变法极重要一个举措,蕴含着历史的深刻性。范文澜先生说:“这是变法重最重要的一个措施,许多无军功的贵族领主因此失去了特权,变为民户中的富户。有军功的宗室。最高爵不过封侯。侯仅收食邑内租税,不直接管理民事,也失去了原有的特权。领主制度的秦国从此变为地主制度的秦国。”[23](233)这一点,是李悝“夺淫人之禄”和吴起废除王室旁系家族封爵已历三代的爵禄,难以企及的。只有商鞅之法彻底废除了封建领主贵族世卿世禄制,秦国一跃而为封建地主制国家。
战国时期各国国内皆存在者大小的领主,朝堂官吏也往往由大的或较大的领主卿大夫担任,他们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其领地和诸侯的封国一样可以置官署,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拥私兵,设刑戮,收族党,统治民众,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只有彻底消除领主制,废除领主贵族的地方政权、兵权、司法权,所有权力收归中央,方可建立起真正的中央集权制。商鞅变法使秦国做到了这一点。变法使秦国成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地主国家,变革贵族政治为官僚政治,而战国其他的任一国家均没有真正的实现强势的中央集权制。山东六国新兴地主“还不能完全压倒领主。”[24](239)
推行县制,此举与废除世卿世禄制相辅相成,废除领主地方政治管理权而收归中央各县令由中央任命,主管县政,彻底杜绝了领主在原釆邑插手政务的绝患,实现了中央“壹赏、壹刑、壹教”各项政令军令畅通无阻。与之相关的是统一度量衡,建立全国标准度量,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在经济上的影响,为经济交流活动提供便利条件,也为统一赋税制俸禄制产生积极作用。
3.激励耕战,形成了经济稳固、国强兵强、民众勇战的运势。商鞅深谙人性好利的本质,契合实际,以利诱之,以法驱之。其法内务耕稼,外劝死战,“武爵武任,粟爵粟任,”(《去强》)奖励农战的改革具有极大地普惠性、激励性,农奴和下等庶人藉此可以立功而获自由民身份,杀敌多可授爵位、得良田、安宅基,新法把为国家而战和为个人而战完全联系一起,形成了全民皆兵的盛况(《兵守》),秦国军队个个勇猛异常,如饿狼捕食所向披靡,砥砺出一支虎狼之师,锐不可挡。“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鋭士。”[25](147)
新法鼓励开垦,承认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买卖。藉此,从法律层面维护土地私有制,这亦是变法的一个关键所在,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世袭制度,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促进封建经济发展,为地主阶级的发展铺平道路,对确立新兴地主阶级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乃历史一大进步。藉此解放了大批农奴,普通农民可从中分享实惠,勤劳之民得以自给自足甚或初步富裕而上升为小地主。大小商贾购买土地则充盈了新兴地主阶层的力量。
4.持久恒定。商鞅变法,经十数年,国强兵强,威震诸侯,其人死,法固在,“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26](354)经四世,“六国毕,四海一”,秦终于完成统一大业。
荀子在商鞅变法约百年后曾入秦,从风俗、百吏、士大夫、朝廷四方面盛赞秦国现状,曰:“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27](260)韩非评价秦国变法功绩则云:“其国富而兵强。”[28](354)司马迁虽尝言商鞅“天资刻薄”,然评价变法之绩则曰:“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十足,民用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29](215)余言: 帝国制之核心者: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实行地主制,废除世袭制实行任命制。秦国已然也。
毋庸讳言,商鞅之法也有荒谬之处,“燔诗书而明法令”,虽然是为强推“壹教”、以驱使全民农战不得不用之,但对于历史文化的大破坏不容讳言。
五、结语
魏国改革在选人用人方面缺失根本性的制度保障而致才干流失,“夺淫民之禄”亦难有实效。重经济调整而无政治领域革新,使社会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力量。吴起变法没有经济领域变革,官吏百姓在变法中均未获得实际利益,则失去朝野上下支持;政治改革又不彻底,亦无土壤条件。唯秦之改革,政治经济并进,尤摧毁封建领主制的措施到位,建立起强势的中央集权封建地主制国家;奖励农战深得人心,富国强兵利民。新法既有益于国,又益于黎民百姓,而获成功。故改革之得与失,其要乃是为劳苦大众带来福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