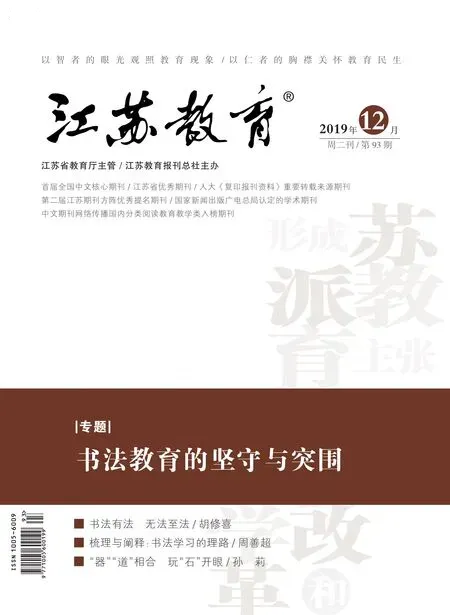“锥画沙”解析
赵 艺
书法艺术的核心技巧是用笔方法。谈到书法笔法,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锥画沙”,这一重要笔法最早出自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其文曰:
予传笔法,得之于老舅陆彦远,曰:吾昔日学书,虽功深,奈何迹不至于殊妙。后闻褚河南云:用笔当须知如印印泥。始而不悟,后于江岛见沙平地静,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锋画而书之,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自兹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当其用笔,尝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真草用笔,悉如画沙,点画净媚,则其道至矣。如此则其迹可久,自然齐于古人。
这里的张长史,是指颜真卿的书法老师、唐代草书大家张旭;张旭的书法老师、表舅陆彦远则是初唐书法四大家之一虞世南的外孙、书法大家陆柬之的儿子。张旭为颜真卿讲解笔法,转述陆彦远的学书心得,用“锥画沙”来形容用笔的方法,其权威性毋庸置疑,所以一直被奉为用笔妙诀。然因历经久远,其具体所指为何,则见解各异,莫衷一是。
现代书法大家沈尹默先生对“锥画沙”有一则具体且广为人知的论述,他在《二王书法管窥——关于学习王字的经验谈》中说道:“锥画沙是怎样一种行动,你想在平平的沙面上,用锥尖去画一下,如果是轻轻地画过去,恐怕最容易移动的沙子,当锥尖离开时,它就会滚回小而浅的槽里,把它填满,还有什么痕迹可以形成,当下锥时必然是要深入沙里一些,而且必须不断地微微动荡着画下去,使一画两旁线上的砂粒稳定下来,才有线条可以看出,这样的线条,两边是有进有出的,不平均的,所以包世臣说书家名迹,点画往往不光而毛,这就说明前人所以用‘如锥画沙’来形容行笔之妙,而大家都认为是恰当的。”即在沈先生看来,“锥画沙”是指行笔时毛笔要沿着笔道两边微微动荡行进,使线条毛涩曲折,呈现出“有进有出”“不平均”的独特形态。这样的解释值得推敲。
作为对相应的用笔方式作出的比喻式概括,首先,“锥画沙”的锥当然是对书写工具毛笔“利锋”的要求;它是由唐人提出的,所以要考察清楚唐笔的特性。唐笔短而锐,笔锋短小犀利如同鸡后爪,所以又被称作为“鸡距笔”(如图1),其笔肚圆润饱满,蓄墨量大,可以满足行笔时一定程度的提按,笔尖如锐利锋芒,白居易《鸡距笔赋》中写道:“圆而直,始造意於蒙恬;利而铦,终骋能于逸少。”可见唐笔的特殊造型决定了其特殊用法。利锋如锥需“立锋”,立锋则便于造成“藏锋”的效果,因为藏锋绝不仅仅是《九势》所谓“藏头护尾”的用笔起收处的藏锋,更是中锋行笔、确保笔画四面圆足,随倒随起、可以八面出锋,即蔡邕所谓“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用陆彦远的话来说就是“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宋黄庭坚《山谷论书》中说:“王氏书法以为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盖言藏锋笔中,意在笔前耳。”这是认定“锥画沙”为藏锋用笔。南宋姜夔《续书谱》中也云:“锥画沙者,欲其匀而藏锋。”这是强调藏锋且线条匀净。清王澍《论书媵语》:“如锥画沙,如印印泥,世以此语举似沉着,非也。此正中锋之谓也,解者以此悟中锋,则思过半矣。”将“锥画沙”解释为中锋用笔。中锋行笔使锋尖居于画中,力凝聚于笔芯,行笔时即如“锥画沙”,笔锋自然锐不可当。

(图1)
“锥画沙”的沙比喻的是书写载体。按照沈尹默先生的理解,“当锥尖离开时,它就会滚回小而浅的槽里,把它填满”,这里的“沙”是戈壁滩上干燥松散的细沙粒,在这样的细沙上“以利锋画而书之”,要想留得住笔,就不得不如沈先生所言将笔在其间动荡摇摆,以便制造毛涩感了。但是,陆彦远所经历的是“江岛见沙平地静”,众所周知,江岛岸边沙地不全是沙,而是沙中夹杂淤泥,江水涨落,江岸的沙地不具有流动性,且质地细密紧实,阻力也相对较大,在其上以锥书写,指掌腕肘所用的力度显然不同于在干燥松散的细沙地上书写。换言之,“锥画沙”原本特指的江岛沙地,已经暗示出画而书之的艰涩与紧执力行的用笔方式,根本不需要“不断地微微动荡着画”,笔道也会“不光而毛”。
由此可见,对“沙”的属性的不同理解,直接决定了对“画”的用笔方法的体认。中国纸张的质地在宋代才改良得精细,唐代的纸张还比较粗糙吃墨。在唐纸上写字如果行笔轻快画过,则线条虚浮无力;而用“不断地微微动荡”的方法书写以求笔道的毛涩感,固然笔道含蓄、质朴、凝重,但是不能称其为“媚好”,根本不符合自王羲之到智永、到虞世南、再到陆柬之这一脉相传的笔法追求。相反,如果采用在江岛岸边锥画沙的紧执涩行笔法,以增加行笔的阻力、增强笔毫与毛糙纸面的摩擦力,就会出现“画乃沉着”的效果。东汉蔡邕在《九势》中谓:“涩势,在于紧马夹战行之法。”韩方明《授笔要说》中说:“夫执笔在乎便稳,用笔在乎轻健,故轻则须沉,便则须涩,谓藏锋也。不涩,则险劲之状无由而生也;太流,则便成浮滑,浮滑则是为俗也。”轻须沉,则明媚利好。明丰坊《书诀》中说:“点必隐锋,波必三折,肘下生风,起止无迹,则如锥画沙,言劲利峻拔而不凝滞也。”胡小石先生也说过,书法线条“须如钟表中常运之发条,不可如汤锅中烂煮之面条。如此一点一画,始能破空杀纸”。笔毫虽软,聚力杀纸,有些笔画纤细如毫发却笔力万钧,起笔如刀扎进纸里,吃着纸走实,不能拖着笔迟缓绵软地行笔,更不能轻飘飘一滑或荡笔而过,不然则轻佻流俗,毫无筋骨。但是这种力度的产生也并非是将毛笔拼命按死的蛮力,而是手中的力量对毛笔的控制,捏笔紧,涩势行,正如宋人欧阳修所言:“行笔如逆水行舟,用尽气力,不离故处。”“涩行”使书家行笔时速度变缓,笔停留在纸上时间长,纸张充分吃墨,是向纵深处透入,入木三分。陆彦远所谓“当其用笔,尝欲使其透过纸背”,“锥画沙”所表现的力度,即是带有涩势和逆锋行笔的“穿透力”。
笔锋相对于纸面,力锐直透,径直地往纸里扎,仿佛透入纸背。但这是不是像沈尹默先生所言,“当下锥时必然是要深入沙里一些”呢?或者说书写者必须尽可能按笔铺毫呢?中锋用笔,点画藏锋,笔在线条中间走,保证笔画两侧形态饱满,这就要求对毛笔有很好的把控,笔不可往下按死,用笔肚、笔根在纸上蹭(这样不可称之为“锥画沙”,线条也会无力虚弱),而是提得起笔,利用好笔锋。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发笔处便要提得起笔,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语。盖用笔之难,难在遒劲;而遒劲,非是怒笔木强之谓。乃如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辄能起,此惟褚河南、虞永兴行书得之。须悟后,始肯余言也。”又言:“作书须提得笔起。自为起,自为结,不可信笔。后代人作书,皆信笔耳。信笔二字,最当玩味。吾所云须悬腕,须正锋者,皆为破信笔之病也。盖信笔则波画皆无力。提得起笔,则一转一束处皆有主宰,转、束二字,书家妙诀也。”提得起笔,是如何利用笔毫弹性和聚散的问题,若过分用力压笔,使前端笔毫散开或翘起离开纸面,这便不是万毫齐发了。“提得起笔”并非只提不按,否则笔毫不能完全铺开,线条单一怯弱;光按不提,笔毫失去弹性,笔画虽看似粗壮,却蓄墨四散,扁平无力,这就不符合“锥”利而锐的要求。
从实际书写看,“锥画沙”这种笔形更多地体现在篆、隶书的书写中,即所谓“篆籀笔法”,张旭、怀素等人的作品中亦不乏可见,甚至对后世王铎等人影响深远。不同于“屋漏痕”的所表现的弛缓的“渗透力”,“锥画沙”行笔并非一波三折地摆动,而是扎入纸中径直地往前拉。如颜真卿《祭侄稿》(如图2)、怀素《自叙帖》(如图3)表现的笔力美,多从“锥画沙”笔法中而来,浑厚沉稳,圆劲有力,畅而不滑,涩而不滞,纵横斜直无往不收,上下呼应一气贯之。“锥画沙”的笔法,锋虽藏而笔仍锐利,力虽沉而画仍明快,线虽圆而形仍劲险,这里提顿、轻重、快慢种种要领的把握之间都要极具分寸,与其他诸如“屋漏痕”“折钗股”“印印泥”等笔法,造就了书法线条丰富多变的用笔体系。

(图2)

(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