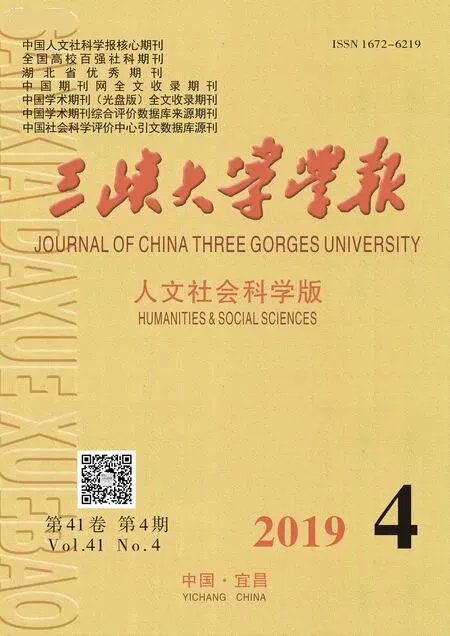明代中后期女性英烈风气研究
赵秀丽
(1.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2.三峡大学 期刊社, 湖北 宜昌 443002)
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官方正史和地方志中记载的数量庞大的烈女群体,分别从《列女传》的历史演变规律[1]、叙事策略[2]、书写与真实[3]、流传与实践[4]等方面对节妇烈女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不少学者认为明代女性在官方女教书籍和贞节观念的影响下,思想枷锁呈加重趋势,节妇烈女正是深受三纲五常观念毒化才沦为封建礼教制度的牺牲品[5]。田汝康认为寡妇自尽现象与该地区男性所受科考的压力与挫折有关[6];Susan Mann通过研究福建妇女的殉烈行为,认为地方治安的威胁、适婚妇女的人数短缺等因素,都是造成该省沿海府县寡妇自杀的原因[7];衣若兰也认为从“女性的焦虑来解释其自杀之因”更具有说服力[3]。笔者在研究明代女性思潮与女性行为时发现,中后期社会涌现出一股强劲的巾帼英烈之风,而朝廷命妇与青楼名妓在易代之际的忠君爱国实践,更是将这股风气推向高潮。
一、明代中后期女性英烈风潮的表征
中国古代女性,大多“婉耍闺房,以柔顺静专为德。其遇哀而悲,临事而惑,蹈死而惧”[8]。洪迈在《容斋续笔》中对妇人英烈的定义是“能以义断恩,以智决策,干旋大事,视死如归,则几于烈丈夫矣。”[8]素以温婉柔顺、缺乏主见形象出现的女性在明代中后期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知识女性群体出现,她们文韬武略,不让须眉。
明代中后期世家大族逐渐转变观念,高度重视“女才”,朝廷也大力倡导、推广女性教化,知识女性逐渐增多。这类女性伴随知识文化的增多,视野扩大,才干增加,往往在相夫教子、保家养身中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孝廉顾化雍,家境贫寒,邻居觊觎其家,联合乡中强人低价逼买,强行拆屋,据为己有。顾孝廉久受凌虐,忿恨不已,自缢而死。乡人皆畏赵势焰,无敢过问。王夫人出揭遍贴通衢,复刊揭五百余张,遣急足走丹阳,粘于街衢,复遍送诸生,且寓书曰:“愿诸君敦侯邑之谊,举鲍宣之幡助我,未亡人执兵随后,共报斯仇,则大义允堪千古。”诸生云集响应[9]。最终当道迫于民意,公正处理此事。尽管文中并未强调王夫人的才学,但她在夫死子幼、家产被占的情况下,以一己之力与恶势力作斗争,写揭揭露赵氏罪行,遍贴通衢,送至丹阳,并寓书请诸生伸张正义,善用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使官员不能官官相卫。这些举措生动说明她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宣传能力,最终成功为丈夫伸冤昭雪。
明代中后期的知识女性在家庭遭遇重大变故,特别是丈夫被捕入狱时,她们往往竭力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丈夫鸣冤、求情。例如明中叶林大辂谏武宗南巡被捕入狱,其妻黄氏吁天祈免,也被缇骑以咒诅被逮捕入狱,惨遭酷刑,黄拒不服罪,惟求速死,后夫妇二人一同出狱,黄氏被时人赞为“铁夫人”。尤侗在《铁夫人》中写道“妾家儿女本无知,焚香吁天诚有之。缇骑缚来坐咒诅,夫妇牵连入圜土。妾今有身不任刑,惟拚一死谢夫君。情辞慷慨相决绝,法吏满堂谁忍闻。一旦天恩并放归,都人夹道尽沾衣。”[10]214
再如沈炼以弹劾严嵩,被捕入狱十六年。其妻张氏陷入两难境地,“欲归奉舅,则夫之饘粥无资。欲留养夫,则舅又旦暮待尽。”她向法司陈词,情愿“代夫系狱,令夫得送父终年,仍还赴系。”张氏“此疏不忍读,读之血盈斗”。尤侗忍不住在《臣夫表》中感叹“呜呼!夫忠臣,妻烈妇,可与苏张三不朽。”[10]214可惜朝廷不肯法外开恩,又过了整整一年,十六年刑期已满方才释放。夏言妻苏氏、杨继盛妻张氏也曾相继上书,请求代夫入狱。
明代中后期社会涌现出一批有勇有谋、才智过人的知识女性,她们在万般绝望、无计可施的时候,宁可拚得一身死,在黄泉路上与夫做伴。丈夫为朝廷忠臣,妻子也是烈妇,夫妻双方都是道德典范,受到世人敬仰与推崇。
第二,知识女性擅长时艺,留心政治。
明代中后期才女学习文化知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女教书籍和诗歌文学作品。学有余力者或指导家中年轻一辈学习,或成为丈夫的良师益友,有些女性甚至对经学研究很深,造诣不凡。例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专门列出《妇人能时艺》,南京孙樾峰“少时师傅,惟其长嫂所授,即冢宰清简公嫡配,而俟居刑部之母夫人也。性严而慧,深于八比之业,决科第得失如影响,故樾峰受其教以取大魁。”汉阳萧象林“从兄大茹、大行,少时疏于制举业,屡试不第,后入赀为上舍。其内子阅其文辄涂乙之殆尽,戒其勿行,不听,而终不售。”至庚子岁始谓其可出,曰:“第可博榜尾缀列耳。”及榜出,果名籍将尽矣。日夜课之,及新春,谓“子功力尽矣,奈天资不超,技止此耳,然尚可望本房首卷。”举第八名。明代中后期文人大多科场受挫,抑郁不得志,萧象林从兄之妻对丈夫制业水平的点评竟然与场主相同,足见其水平之高。沈德符也忍不住惊呼:“良媛以笔札垂世者多矣,未闻娴习时艺,评骘精确乃尔,即拥皋比何忝耶?”[11]这些知识女性精通传统经典文化和八股文,教育子孙比男性名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她们受科举制度限制,不能将才华展示出来,真古人所云:“恨不使士大夫见之。”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将女性排斥在政治、军事诸领域,但明代有识女性仍关心时政,敢于点评朝廷利弊,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良策、作战方略。例如徐灿曾著《卧月集》,里面有许多关于经济、理学的文章,“率经生所不能为者”,足见其见识之高。徐灿与媳妇丁玉如都是性格豪爽之人,“慷慨好大略,常于酒间与灿论天下大事”。婆媳二人相处时,直言政务利弊与朝廷得失。丁玉如认为屯田法不行、三饷加派是朝廷内外危机的根源,她指出边屯与官屯的不足,提出新的解决之道,自己若有十二万金钱,“请淮南北闲田垦万亩,好义者出而助之,则粟贱而饷足,兵宿饱矣。”“然后仍举盐策,召商田塞下”[12]23。她认为商屯比边屯和官屯更有优势,更有效率,更为可靠。丁玉如继母张氏在李自成起义后,愤然作《讨逆闯李自成檄》,“词义激烈,读者如听易水歌声。”[12]23由此可见该檄慷慨激昂,令人肃然起敬。
明末清初涌现出来的女性知识群体对时艺的关注与擅长,对民生疾苦与朝廷大政方针的深切关怀,充分说明这些女性自我意识已经初步觉醒,她们希望在家庭之外,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与个人志向,并将个人命运与朝廷安危、国家兴亡密切结合起来,初步展示了女性的政治追求。
第三,女性崇尚英气,在社会掀起强劲的英烈之风。
明代中后期一大批女性将视野转向更为宽广的家外世界,关注中心从丈夫、父母扩大到国家、社会。女性诗歌主题不再停留于叹岁月流逝,思良人怀远人,而是一扫昔日脂粉、阴柔之气,关心时局,品评英豪,带有一些“英气”。例如大学士王锡爵孙女、徐本高妻王氏写下“金闺文作市,玉匣气成虹”的诗,充分展示了她的自信与豪迈[13]47807。
大清攻江阴时,明典史阎应元号令严明,“伤者亲为裹创,死则酹酒哭之”。陈明遇毁家殉义,善抚循,往往流涕相劳苦,士故乐为之死。李成栋破松江后,率所部十四万至江阴,驱降将至城下陈说利害。阎应元等人浴血奋战,英勇牺牲。当时王师有二十万,死城下者六万七千名。辛丑(二十二日)大清兵克。(江阴)攻守八十一日,竟无一人降者。大清兵之死者亦有七万五千有奇。闽中闻报,王泣曰“吾家子孙遇江阴人,虽三尺童子亦当加敬也!”城中尸骸枕藉街巷,池井皆满。江阴一女子题诗城墙曰“雪胔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忠未肯降。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14]422-423。柔弱女子孤身一人与攻城清军鏖战,力竭被杀,而明降臣刘良佐、李成栋以下无一死于江阴城下之人,十余万降军助纣为虐,二者形成鲜明对照,进一步展示了女性不畏死亡、忠贞不屈的英雄气慨。宫女宋蕙湘在被北兵掠去时,亦题诗驿壁,留下“风动江声揭鼓催,降旗飘扬凤城开。将军战死君王系,薄命红颜马上来。”[14]427由此可见,普通女性也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对明廷充分认同,其诗作凄然有去国离家之痛。
明末一些女性更是直接投身挽救明朝危亡的政治、军事实践中来。例如刘夫人是江西吉州刘讳铎女、王抚军次子谐妇,其父在魏忠贤危害社稷时不畏权势,坚持正道,被魏阉杀死,被人们尊称为“忠烈公”。甲申鼎湖之变时,刘夫人感叹说:“先忠烈与抚军两姓皆世禄,吾恨非男子,不能东见沧海君借椎报韩。然愿与一旅,从诸侯击楚之弑义帝者”,遂建义旗。滇帅欲与夫人合作,却“阴持两端,又醉后争长,语不逊。夫人怒,即于筵前按剑欲斩其首。”帅环柱走,一军皆擐甲。夫人掷剑笑曰:“杀一女子何怯也。”索纸笔从容赋诗一首,辞旨壮激。帅悔且惧,夫人曰:“妾不幸为国难以至于此。然妾妇人也,愿将军好为之。”遂跨马驰去[12]24。在明廷倾覆之际,刘夫人以一弱女子之身,毅然投身反清复明事业中,足见其忠贞爱国之情何等浓烈。她面对滇帅的无理挑衅,面对千万滇军的围攻,岿然不动,毫无惧色,一旦认清滇帅阴持两端,毅然与之决裂,潇洒离去,足见其聪慧、洒脱与刚烈。
这些弱女子见识高明,胸怀韬略,有的运筹帷幄,有的勇猛无敌,有的智勇双全,有的多才多艺,展示了巾帼女性胆艺俱绝、豪气冲天、有胆有谋、文武双全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为之振奋。
二、明代中后期女性英烈之风形成原因
明代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推崇,官方、民间女教书籍的广泛传播,文人及文学作品对英烈的赞赏,都对明代女性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明代女教书籍注重灌输贞烈与闺智观念。
明代女教大兴,其教育内容呈现出唯德独尊、尚节尚烈的倾向。《列女传》是广大女性最常见、最熟悉的读本之一,而贞节观念是女性知识谱系的重要内容。明代女性深受这种文化熏陶,“居安而有淑顺之称,临变而有贞特之操”。与前代女性相比,明代中后期涌现的才女可以阅读男性读本,在笔墨书香中细细品味儒家典籍所蕴含的伦理规范,因而她们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洗礼最为深厚,并对女性的责任、价值与义务等核心问题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明代影响最大的女教书——《闺范》的作者吕坤在其编纂的女性读本中,就用相当大的篇幅谈论闺智问题。例如《闺范》中曾记载乐羊子妻的事迹,“尝有盗入其家,欲犯之不得,乃劫其姑。妻仰天恸哭,举刀刎颈而死。盗大惭,舍其姑而去。”吕坤对此大加赞赏,认为乐羊子之妻贤哉,“遗金不受,临财之义也;乐守寂寥,爱夫之正也;甘心自杀,处变之权也。值此节孝难全之会,一死之外,无他图矣。史逸其名,惜哉!”[15]乐羊子妻在既不能不孝,又不能失贞的两难境界面前做出的抉择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以死保全名节。虽然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战国,但吕坤对她的赞赏和评价充分体现了明人所持的态度观念。
孝贞女姚全姑,美姿殊绝,端谨寡言,行止无苟,父母钟爱之。甲申,年及笄未字,有伪权将军见全姑美丽,欲纳之。全姑宁可断头,不愿辱身。贼执其父母及三弟妹,以此要挟。士忠曰:“若女受辱,我辈虽生犹死,不若共死为正”。众皆诺。全姑大哭,触柱求死,众抱持止之。全姑痛哭绝粒,示必死。贼见其志坚不可夺,乃数刑掠其父母。贼以事出,防少疏。全姑共其父母弟妹俱自缢。一弟绳断而窜。及暮,贼归。见全姑颜色不改,欲污之,尸忽转而动。贼惊以为鬼物将击已也,避去。而全姑以绳断,缢喉未绝,复生。贼喜溢望外,卑言求合。全姑佯应先殡父母弟妹,方可从。贼从之厚葬家人。全姑持刀骂贼,欲击之,因自刎。贼大怒,夺刀乱劈[16]。姚全姑因美貌引来寇贼觊觎,全姑不肯以身侍贼。贼以其父母并三弟妹威胁,全姑尚未作出决断,其父坚决制止,宁愿同死,不愿女儿受辱。家人达成共识,全姑愧疚不安,触柱求死,不成,又绝食求死,后与家人一同自缢。不料全姑以绳断复生,佯装答应寇贼条件,先厚葬父母弟妹,再持刀骂贼、击贼、自刎,最终被贼杀死。
明朝中后期大小叛乱不断,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安状态,女性很容易被流民、盗匪和官兵侵扰,不少女性在家人被抓后都面临艰难抉择,她们为了拯救家人,不惜与寇贼虚与委蛇,迷惑敌人,待家人平安后,或通过谩骂敌人激怒对方被杀身亡,或寻找良机主动自尽保全贞洁。这类烈妇烈女的死亡带有浓厚的悲壮色彩,既保全家人,又不违背自我意志,广为人们称赞、敬仰。
第二,明代中后期文学作品对女性智略、豪侠特质的倡导。
明代中后期文人对黑暗政治与社会现实十分失望,认为女性和孩童一样,没有受任何外在熏陶与污染,保持着赤子之心,灵魂和精神更加纯真,更能认清大道,因而纷纷转移注意力,将重心花在引导、教育女性身上,希望开发女性的潜能,践行儒家文化的道德追求。他们不约而同搜集古代杰出女性事迹,并赋予这些古代女性事迹全新的价值与意义,从而为明代女性新风尚提供依据,树立典范。例如明代文学家吴震元专门编纂了一部《奇女子传》,陈继儒在《奇女子传序》中点评古代经典《易传》、《诗经》、《春秋左传》、《列女传》等作品,对古代贤妻良母、贞女烈妇等事迹都有记载,唯独不曾关注奇女子。吴震元这部作品,将古代108位女性分为奇节、奇识、奇慧、奇谋、奇胆、奇力、奇文学、奇情、奇侠、奇癖十种类型,“小可以拊掌解颐,大可以夺心骇目。”陈继儒大声疾呼,希望众人“无以六经解嘲矣”[17]80。《奇女子传》所涉及的奇识、奇慧、奇谋、奇胆、奇力、奇侠六种类型,基本上都是古代女性传记较少关注的类型,充分体现了以吴震元为首的明代文人对女性智慧、胆识、能力、谋略、豪侠特质较为关注,褒奖女性品质的范围大大扩充。
明代中后期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专门列出“闺智部·贤哲”,记载闺中女性智慧、智谋之事,认同“智妇胜男”、“即不胜,亦无不及”的观点,认为女子的智谋包括“见大”“远犹”“通简”“游刃”“知微”“亿中”“识断”“委蛇”“谬数”“权奇”“灵变”“敏悟”等等,“所以经国祚家、相夫勖子,其效亦可睹已!”[18]276冯梦龙在“闺智部·雄略”中亦指出其遴选标准“士或巾帼,女或弁冕;行不逾阈,谟能致远”[18]285,由此可见,他将男性、女性一视同仁,对女性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加以褒奖,充分说明他对巾帼雄风持赞赏态度。冯梦龙在其另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情史类略》中专门列出“情侠卷”和“情烈卷”,继续表彰女性的智慧、豪侠、英烈之气。
张岱在《石匮书后集》第59卷《烈女列传》总论中批评明代列女传的书写“其间侠烈之事,愈出愈奇特”,他认为列女应该包括以贤孝见、以节义见、以侠烈见、以才慧见的各类女性,而不仅仅局限于节妇烈女[19]338。正是本着高扬忠孝节义精神的宗旨,张岱等文人在记载女性事迹时,将眼光面向社会各个阶层,义娼邵金宝、京师娼高三、歌者妇张氏等别具义行与贞操的娼伶也被收入卷中,凸显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最底层女性的侠烈事迹。
明代中后期社会各种诗集、戏剧、小说、弹词作品实际上为才女打开全新世界,这类文学作品不仅传播情欲观念,而且将创作者对儒家伦理和优秀品质的渴望、倡导亦传播开来。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也通过看戏、听曲、评书等方式获得大量信息。当明代思想家和文人对日益僵化、生硬、教条的儒家程朱理学表示不满,推崇阳明心学,言行举止日益僭越儒家礼法规范,从心所欲,率性而为时,女性反而以虔诚的态度学习、接受儒家文化。她们有一个自外向内逐步认识、接受、吸收的过程,服膺儒家伦理规范,认同“忠孝节义”、“仁义礼知信”等观念,深受贞烈之风熏染,并最终内化为自觉认识,转化为衡量自己行为的一个准则、尺度,从而使女性风气、言行较之前代,发生重大变化。
第三,社会尚奇、尚烈之风的盛行。
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发生巨大变化,奢靡之风、纵欲之风盛行。伴随市民文学的繁荣,特别是信息资讯的便捷传播,人们的阅读心理发生转变,尚奇、尚烈之风盛行。在女性节烈事迹的书写中,官员、文人往往不惜浓墨重彩、生动细致刻画、描绘女性固执己见、一心求死的过程。例如祝纯嘏在《孤忠后录》中用生动的笔墨记载了贡生黄毓祺妻周氏,其丈夫因反清复明被捕入狱并死于狱中。周氏闻讯,“自誓必死,复不食。第恐死于家,为里党累。不得已乃投老姑董氏家;人定后,径投宅后池中。漏二下,始觉而觅之,尸已浮水面。董氏多方救之,呕水数斗而活。天未明,捕卒驱迫,氏遽求死不得,闻人言,服金屑能杀人,喜曰:‘早知有此,何不悟哉!费我一夜熟筹!’乃扣质库,收董氏金钏归,屑三钱,服之,盘旋肠胃,痛不可忍,竟不死。抵暮,投故人杨廷玉家。廷玉闻之,甚悲。询氏求死不得状曰:‘金不赤,不得杀人,’乃脱内人指约双环,屑之以进,亦不验。然氏已阴置利刃于怀,以备万一之变矣。明早,太守坐堂皇,按册呼名,氏直立不应,举右袂障面,左手引刃自刎,刃入喉者二寸,流血冲涌而死。”[20]黄周氏在丈夫去世后,先后采取绝食、投井、吞金钏屑、吞金环屑、引刃自刎等方式,意欲结束自己的生命,不料七次自杀,均未成功。最后一次她在官府大堂,举右袂障面,左手引刃自刎。众人皆“以为精诚所感,好事者争醵金治木,将为发丧。”并持香烛祭拜烈妇,不料“夜半,喉中气转,复生”。太守为之脱罪释放。这段详尽、惨烈、奇幻的烈妇事迹被广泛传播,人们在惊叹烈妇事迹的灵异、奇异,满足人们的窥视欲望与猎奇心理之外,广大女性亦被普及了自杀的基础知识,并知晓女性贞烈实践可能创造神迹,甚至赢得官员与大众同情、尊重与拥护,美名传播,青史留名。这种自杀导致的神奇后果极可能影响其他女性,使之群起而效仿。
明代中后期社会出现一股强劲的巾帼英烈之风。不仅节妇烈女在面对人生重大变故和危机时“尚节”“尚烈”,宁死不屈,誓死维护自己和家族荣誉与尊严,而且社会各阶层女性都具有英雄情怀,在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重大危机面前,能够从容面对,竭力贡献自己的力量。明代中后期一些精英女性对英烈事迹大加推崇,对软弱男性嗤之以鼻,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与王朝死生存亡大业中来,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明清之际女性贞烈实践新特征
明代中后期一些女性十分注重自我德行的修炼,强调个体的内省,关注“自我”与“超我”,从而有利于心灵的内在升华和道德超越。她们对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儒家礼法制度与价值体系衷心拥护,并直接落实到日常行为实践中。正因为她们长期经受道德锤炼,磨砺了品质,因而在危急关头能做到泰然自若,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明清易代之际女性的贞烈实践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战乱动荡时期女性死烈行为以家族、宗族为单位,规模大。
战乱环境下,宗族对女性抉择的影响力更直接、更强大。例如慈溪沈氏宗族靠近大海,族众多骁黠善斗。当寇贼入犯时,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屡歼其魁,夺还虏掠。寇贼恨之入骨,结集大量兵力前来报仇,族长召集男性族人曰“无出妇女,无辇货财,共以死守,违者诛。”其妻章氏也集族中妇女誓曰“男子死斗,妇人死义,无为贼辱。”众竦息听命。“贼围合,群妇聚一楼以待。既而贼入,章先出投于河,周与冯从之。紫方为夫砺刃,即以刃斫贼,旋自刃。孟与孙为贼所得,夺贼刃自刺死。时宗妇死者三十余人”[21]5280沈氏一族在此战役中死节女性就高达三十余人,充分体现了群体决策对女性的巨大影响力。
明清易代之际,朝廷命官以身殉国,阖家死难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例如胡恒在张献忠攻陷成都时,与其子之骅战死。胡妻樊氏、妾成氏、冯氏,之骅妾周氏,仆京儿、弩来,婢女二从死,举家遇害[22]23。锦衣卫旗尉邬默、默长兄焘、次煦、弟勋兄弟四人、默妻赖氏率女及煦二女先死,煦妇刘氏、孙咸哥并孙女二人继之;勋妻霍氏缢死,勋亦死;焘与妻聂氏、孙健哥俱缢[23]29。
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军造反十余年,“妇女惨死者不可胜纪。其见闻详确,即易氏一族有足纪者,如易适尊妻王氏、易道一妻熊氏、易时升妻汪氏、易吉甫妻陈氏、易瞻明妻华氏、易道重妻周氏、易仰之女适何刚者、易文我女适夏继璜者、易道旦女适何际时者、易道位女适李尔常者、易道傅女适刘伯升者、易为继女适方尔闻者,凡十有二人,或死于水火,或死于刀绳。”[13]48443
这些阖门死亡的女性,往往因家中男性不辜负朝廷恩典,或杀敌死,或自尽死,家内女性往往自觉不自觉受其感染,纷纷选择自尽,不辱没家门。明末改朝换代之际,鉴于以家族为单位死亡的女性人数太多,方志编纂者往往以家族为单位,将同一宗族内死烈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来记载。《闺媛典》“闺烈部”副传中的女性绝大部分与正传女性有亲属关系或地缘关系,这一编写特点也充分说明了邻里宗族关系对女性抉择的影响力。
第二,世家、诗礼传家的女性深受“世受国恩”、“义不受辱”观念影响,更容易为维护家庭荣誉而死。
朝廷命妇身受国恩,对朝廷充满感激之情,世代效忠,因而对国亡的感触特别深刻,臣死忠,妻死夫,子死父,女死母的伦常道德观念在她们身上得到鲜明体现。例如曹文耀之妻在国难时“率子女哭家祠中曰:‘余家世受国恩,义不受辱,为先人羞。阖门矢死,庶无憾耳!’比城陷,张氏先缢,耀即自缢。时耀父妾姜氏、逊妻李氏、持毅妻邓氏、持顺及乳母孟氏、肃及持敏凡八人同缢。”[19]316新乐侯刘文炳家闻城陷,“母遽起登楼,文照及二女从之;文炳妻王氏亦登楼。悬孝纯皇太后像,母率众哭拜,各缢死。继祖妻左氏见大宅火,亟登楼自焚;妾董氏、李氏亦焚死。阖门死者四十二人。”[23]18宋文元妻刘氏在城陷后率子妇女孙十数人誓曰“吾家世受国恩,汝辈不可偷生苟免,致贻宋氏羞。”因尽驱入水[13]48508。沐天波妻焦氏贼变至金井庵,其姑遣人问计,答曰“吾家累世重臣,身为命妇,当死宗庙。”举火自焚,其姑闻之,笑亦自焚[13]48204。通过上述事迹,可以清楚看到社会上层女性的家族认同感和自我角色认同,体现了她们对“忠”“义”的追求。虽然这些传记都出自男性之手,女性临死前的誓言外人难以知晓,但男性文人对传主身份的强调正反映了他们对命妇角色、命妇行为的期待,借死难命妇之口表达了上层女性忠君爱国、不辱门第的观念,她们的铮铮誓言对幸存的贵戚大臣无疑起到了教化和激励作用。
出生诗礼之家的士人家眷大多受过儒家礼法熏陶,知晓忠义节烈之道,遇到危难宁死不屈。例如月娥“少聪慧,听诸兄诵说经史,辄通大义。城陷,月娥叹曰‘吾生诗礼家,可失节于贼邪!’抱幼女赴水死,诸妇女相从投水者九人。”[21]5257诸生王武珂妻熊氏被执,骂贼曰“我名家妇,肯辱身从汝?”贼怒杀之[22]20。万之益妻沈氏骂曰“我宦族清白吏子孙,岂受辱耶?”[13]48440程九万妻庐氏遇寇强之行,氏曰“吾诗礼世家,肯从贼乎!惟一死以随吾姑地下。”贼乱刺之死[13]48363。贾用售妻宁氏同群妇遇贼,贼逼去执炊,群妇皆随而氏独不从,曰“我读书人妻,岂肯与狗贼做饭?”踞地不起,骂贼而死[13]48360。傅之恕妻孙氏在贼围城急时召婢媵曰“吾家累世清白,义不偷生。”坠舍后井中死[13]48348。这些出生诗礼之家的女性,父兄夫子不一定中试为官,但家内儒风盛行,礼法治家,她们深受熏染,忠孝节义观念了然于心,深为认同,故有很强的家族认同感,断不肯苟且偷生,玷污家门。
第三,节妇、烈妇、义门之家女性深受家风熏陶,女性榜样示范作用显著。
家内女性的贞烈实践对族内其他女性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深处闺门之内的女性特别容易受本族节烈女性(尤其是母亲或婆婆)的影响,她们深为认同并以此自勉。在《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闺烈部”与“闺节部”中可以看到,女儿、媳妇总为母亲或婆婆的贞节自豪。当她们自己不幸丧夫时,往往将长辈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发扬光大,不愿改嫁辱没家门,令父母蒙羞。郭琛妻荆氏在夫病笃时说“我家世诗礼,母为节妇,岂容有再嫁女乎?君设不幸,当从死地下。”遂归与母诀,曰:“母十余年辛苦抚女成长,不得终事母,母善自爱。”其母非常高兴,“是真我女也。”[13]48400荆氏因出生诗礼世家,母亲又是节妇,家风使其认知非节即烈。对于女儿的殉夫念头,荆母并不反对,反而认为女儿此举正是继承自己优良美德的表现,十分赞同,荆氏之举带有明显的家风熏陶色彩。一门三代四节妇者相对较少,“双节”之家则较为常见。家内女性的贤德事迹是最生动、最感人至深的教育范例,对其他女性起着无形的教化与激励作用。尊崇孝道的年轻女性在困厄之际往往将家内典范作为参照标准、学习榜样,纷纷效仿,节妇烈女代代相承,节孝之家很容易成为“义门”。反过来,生活在义门之家的女性具有强烈的家族荣誉感和认同感,她们以生在义门为荣,面临困厄时,毫不犹豫选择死亡。女性这种浓厚的家族意识使她们一言一行都与家族名誉和利益结合起来,不辱没门楣。
明清易代之际,数以千计的烈妇、烈女用生命和鲜血彰显了女性精忠报国、忠义传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在在张扬、唱响巾帼雄风。这股巾帼英烈之风一直弥漫、影响整个清朝。生活在康熙年间、正逢盛世的才女倪瑞璇,“能发潜阐幽,诛奸斥佞”,令男性“每一披读,悚然起敬。”[10]653她曾写过一首诗《过凌城庙谒古戴二公忠义冢》“秋风鸣高空,乱峰下斜照。老树枝交天,苍黄覆古庙。入门扪残碑,太息拜遗貌。忆昔明运衰,群盗起聚啸。剿抚两失策,峰虿变虎豹。所过无坚城,苍生任凌暴。二公真人豪,忠贞出天造。金铁冶成心,冰霜厉寒操。贼峰一朝来,矢石躬亲冒。官小誓捐躯,力薄那自料。慷慨互争先,从容共谈笑。燃炮击贼人,天地为震悼。贼用魇魅法,蚁聚蜂屯到。众寡势不当,头断臂犹掉。成仁并取义,日月争光耀。碧血洒平芜,贼马不敢蹈。至今旷野中,白日常见烧。如何八十年,荐绅少凭吊?姓氏已稀传,父老犹相告。兰台事纂修,幽微须阐耀。谁为秉笔人,搜求不遗奥。”她专门写下题注,交代二公身份及自己写诗缘由“古讳达可,戴讳国柱,同以忠勇见知于可法史公。时史公总督漕运。巡抚淮扬。怀宗十四年,流寇袁时中寇睢,古时驻宿,邀戴往击,战于凌城庙,众寡不敌,俱死焉。史公随遣使致祭,命于所瘗地刻石立忠义冢。呜呼,二公真烈丈夫哉!丁酉秋,予同母氏往过拜其墓,深惜其事之未传于史也,因为诗以俟轩之采。”[10]倪瑞璇作为闺中女子对明清易代之事能有“剿抚两失策”的论断,并此诗补阙《明史》未曾记载的古、戴二公事迹,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对古、戴二位忠贞爱国行为的崇敬,对二人身后孤寂无名的痛心疾首,意为英烈立传,留名青史。
四、女性殉烈行为的评价
迪尔凯姆将“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24]《闺媛典》“闺烈部”女性虽是非正常死亡,但与司法刑事案件中的女性死亡不同,她们往往自主决定死亡的时间与方式,是一种主动的自杀行为。史崔汉博士将自杀区分为“理性或类理性的自杀”、“非理性或真实的自杀”两大类,而武士的切腹自杀被新渡户稻造称作“理性或类理性的自杀”的最好例子[25]104。新渡户稻造在论述武士道的精神时指出“勇气的精神层面必须以即使暴露在可怕的环境下,还能保持内心平静来证明。心平气和是勇气的休息状态,是英勇的静态表现,而大胆的行为则是勇气的爆发。一个真正勇敢的人都是很镇定的,他从来不会感到惊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扰乱他的情绪的平静。他在面对死亡危险和威胁时,依然保持自己原有的风格。他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因为他的心胸极为宽广,不慌乱、不焦躁、不困惑,总是充满余裕。”[25]27明清易代之际烈妇烈女无论是自杀,还是被“寇贼”杀死,她们都忠于自己的信念,从容不迫,坦然面对死亡,与坚守武士道自杀的武士非常相似。
常言道,“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26]“人惟贪生念重,故临事张惶”[27]。正是在这种觉悟下,她们坦然面对生死,从容不迫。马雄镇家族女性死烈的情形如下所示:“二烈女者,马文毅公女也,一小字二姐,一小字五姐。初文毅公陷贼时,二女相约同死,公妾顾氏亦愿从。公既遇害,女谓顾氏‘今日吾辈践约时也。’将为缳梁,从容语顾氏曰:‘夫人故诸母行位次,宜居中,虽颠沛,序不可失。’氏曰:‘某妾也,又无出,何敢与诸母齿让。’至再,竟先顾氏。五姐弱,力不能胜绠,久之,缳未就,呼曰‘姐助我’。二姐笑曰:‘妹怖死邪,吾助妹已。’乃以次就缳死。先是公子司寇公独脱身,闲道归京师,其夫人董氏、妾苗氏皆在贼中,董氏先二女自经,绠再绝,再仆地,伤额及足,三缢乃死。”苗氏与文毅公妾刘氏相继死在二女后。“文毅公夫人李氏视诸人含殓毕,曰:‘姑媳子女皆幸不辱身,吾无憾矣。’乃系帛奋身绝吭死。是日死者七人,二姐死时年十有八,五姐仅十五,顾氏年二十余,识字,工楷书。”[28]她们不仅未雨绸缪,率先做好自尽全节的思想准备,而且在赴死途中井然有序,不乱辈分,谈笑风生,互相帮助,视死如归,将维护名节、奋身蹈死视为本分,以集体自杀的方式面对未知的面运。虽是闺中弱女子,却在在显示巾帼女性的英雄本色。
“闺烈部”中的烈女虽然平时胆小怕事,一旦面对恶势力的威胁,涉及到贞节、道义,她们的理智就会战胜情感,变得勇敢坚决,视死如归。那些舍己救亲、救他人的女性,未被抓却闻国亡忠君殉国、以死激励家中男性尽忠全节、闻城破兵至自杀全节、为父兄报仇的女性,即使被抓仍英勇杀敌、智取贼命、怒骂求死、被贼杀害的女性,她们的死烈行为都属于一种主动选择。正如王自敏妻周氏所言“前后等死耳,他日恐其迟也!”[22]74女性在乱世必死无疑,早也是死,晚也是死,与其忍辱偷生,苟延残喘,过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屈辱生活,还不如英勇悲壮殉死,死得其所。因而在敌人未到,灾难未降临之前就做好准备工作,甚至随身携带器具,并向家人交代清楚遇难的后事问题,方便家人寻回尸首埋葬在家族墓地内,不幸被俘后故意激怒敌人被杀全节,毫不胆怯畏惧。她们的自杀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并非一时感情冲动的盲目行为,这种直面死亡的勇气和精神也使她们与武士一样,同为崇高道义的实践者,其死亡基本上也属于“理性或类理性的自杀”。明末在战乱中死烈的女性用生命捍卫、实践着儒家统治者倡导的美德:义不受辱之“贞”“烈”,舍己救亲救他人之“孝”“仁”,忠君爱国不降二主之“忠”“义”等。
女性的难能可贵还体现在她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坚持到底,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亦在所不惜。“虽然死而不足以成事者有矣,未有能成天下之事而其身不能死者也。故求死于事之可为者非难,求成于事之不可为者为难。死于事之必可为者非难,死于事之必不可为者尤难也。”[29]女性被寇贼俘虏后,明知敌我力量悬殊,一介弱女子根本不是凶横残暴的寇贼对手。她们并不屈服,与敌人斗志斗勇,在完全被动、劣势的形势下尽力争取殉死全节的机会。正如方孺人批评失节妇时所言,若真正存必死之心,也许短时间内未找到自杀机会,但绝对不会在敌营半个月仍无机会,即使无计可施,亦可以言词激怒敌人,借敌人之利刃结束自己的生命。总之,烈妇在王朝濒临灭亡、“寇贼”进逼侵犯时,或挥剑自刎,或以头触石,或投河自尽,或饮鸩服毒,或绝食绝水……他们最大限度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来结束生命,保全名节,她们的积极主动与男性的优柔寡断形成鲜明对照,弱女子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大丈夫明知其可为而不为,从道德到实践层面,弱女子与大丈夫之间的差距随着女性实践者人数的大幅增长而加大。
明末这些忠贞刚烈的女性以柔弱之躯,含笑面对死亡,表现出慷慨从容、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直面人生,舍生取义,在所不惜的壮烈举动,无不彰显着巾帼雄风和浩然正气,给人一种崇高、雄壮的感受。她们的“义”和“节”不仅仅表现在保持身体的贞操,更有为国家、民族、正义而付出生命,保存操守的忠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带有浓厚家族性、地域性、文化性特征的烈行赋予明末清初烈妇烈女全新的内涵,她们不再是可怜的、悲惨的贞节观念的牺牲品,而成为一个个彰显人类最高道德与情操,实践忠孝节义精神的英雄豪杰类人物,彰显生命的尊严与意义。这是女性第一次积极参与王朝社稷、地方社会的安危存亡,第一次强烈表达自己的存在感,凸显自己的意义。晚清中国陷入内忧外患,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已经在明清易代之际有过预演的女性们早已熟悉国家、社会、家庭与个人的关系,早已清楚女性超越自我追求道德升华能迸发出无穷力量,她们一改柔弱之姿,勇敢地为国家前途、民族安危、家族和个人命运而奋力拼搏,从而在清末民初再次掀起一股强劲的英烈之风,再现巾帼英雄本色,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