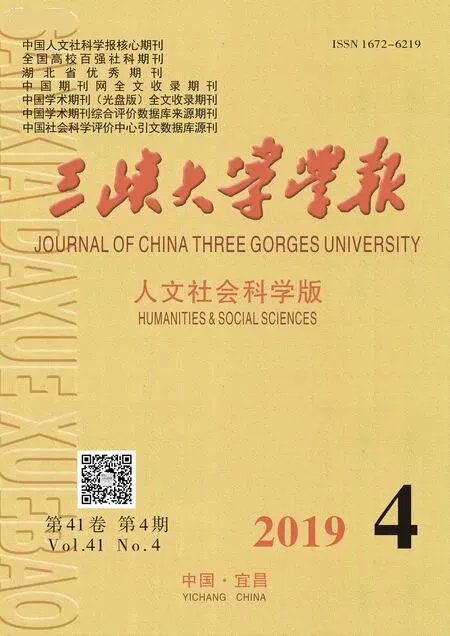放逐·解构·启蒙
——阎真小说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创作思想研究
周文慧
(湖北警官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34)
阎真将自己的写作状态基本定位为“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写知识分子”[1],其知识分子小说三部曲《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和《活着之上》展现了从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鲜活形象。《曾在天涯》反映80年代出国潮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在北美的生活状态,《沧浪之水》写出了90年代“后文革”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过程,《活着之上》展示“70后”知识分子在新世纪社会冲击下内心的挣扎与坚守。三部作品具有互文性,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嬗变过程,书写了不同阶段下知识分子面临的不同的精神困顿,呈现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整体的心灵发展史。
一、阎真笔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顿
《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以及《活着之上》中的聂致远,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三个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阎真通过他们展示了近四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危机、价值失范、心灵挣扎等精神困顿问题。
1.《曾在天涯》:异域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
阎真通过《曾在天涯》反映出8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对知识分子价值探寻的中止、精神的漂泊感和对人生的幻灭感。
小说写出了知识分子在80年代精神的漂泊感。作者通过异域环境的特殊化处理进一步强化了当时知识分子面对的精神危机。高力伟精神的漂泊感既体现在异国的生存环境中生命个体的身体漂泊感,也表现于文化环境转换后精神的流浪。小说中,高力伟跨越重洋、身在异国他乡,从外部切断了与祖国的关联,同时也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精神上的“无根”让他内心不断滋生漂泊感。在高力伟看来,“在国内好歹也是个人,现在呢,除了我自己把自己当个人就没人把我当个人,人整个地被阉了似的。”[2]142高力伟怀揣浪漫、感性和理想主义来到北美,而家庭夫妻身份的错位、社会身份的错位和文化价值的错位让他产生了“在这片土地上我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2]234的感受。高力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当他深切感受到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话语权威,认识到个人的存在价值在异国他乡的市场经济语境中难以实现时,自觉放弃了对知识分子个人价值的探寻,在形而下的生存层面寻求个人的存在感。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以释放生存的压力和挽回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人格尊严的失落感。生活环境的改变,让高力伟失去了中国知识分子生长的土壤,价值认知的差异让他不得不调整自我的价值体系,在异国土地上搁置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尊严、对社会的关注与思考,消解了知识分子价值和意义。
小说中,高力伟认识到时空的无限与个人的渺小、意义的崇高与生活的平庸,产生了人生幻灭感。高力伟面对墓地时跨越时空的精神探寻、对佛教精义的参悟无不透露出知识分子对人生的幻灭感。通过反复地对生命有限性的强调和时空无限性的诗意展示,作者进一步证明了知识分子追求个人价值的徒劳和追求人生意义的虚妄。高力伟在对人生意义的反复思考后,还是得出了“存在并没有终极意义”的富有幻灭感的结论。
2.《沧浪之水》:官场知识分子的价值失范
《沧浪之水》集中反映了90年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失范,具体体现在理想主义的幻灭,原有价值体系的迅速瓦解并无法用传统的知识分子价值观念认同社会的新变化,进而表现出对现实的无所适从。如果说《曾在天涯》从空间上设置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孤岛,让他们与外部社会发生第一次断裂,逐步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的身份,难以表现对社会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和社会参与意识缺失的话,那么《沧浪之水》则在时间上进一步强化了知识分子与外部的断裂,从社会体制和话语方式上让他们第二次与外部发生断裂,形成知识分子身份价值缺失的条件。
90年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追求精神理想与现实生活困窘的矛盾,正如有学者所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几经坎坷,到了世纪末,一个安定、宽松的时代来临时,新一代学人又面临着基础薄弱、世俗化挤压的无情现实。”[3]池大为曾经满怀激情,洋溢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精神,但经历了民主生活会事件、赤脚医生救助事件、儿子烫伤入院事件、舒少华策反失败事件、尤其个人命运的起伏逆转之后,他深刻地认识到“活着是硬道理,现实没有诗意的空间,只有真实到残忍的存在。把世俗世界甩到一边去的生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4]172他在社会生活中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价值选择,失守于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精神领地。
池大为一入职场,就感受到权力的力量遮盖了对人起码的尊重。他在工作中逐步发现,在卫生厅工作事实上是跟着大人物的意愿走,厅长的意愿影响事实的呈现形态,决定事情的走向。他意识到官场上的身份识别系统是“身份=权力+地位”,深刻地认识到“有些东西,一定要在那个位子上才会有,否则什么都没有,连尊严感都没有。尊严不能建筑在一种空洞的骄傲之上。”[4]135池大为原来持有的知识分子敢说真话、为民请命、关注天下千秋的价值体系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现实生活解构了知识分子崇高的价值追求,他在经历坚守与挣扎后最终放弃了知识分子价值选择,原有的价值体系土崩瓦解。
阎真还写出了当上厅长后的池大为面对现实的无所适从。他当上厅长后尝试进行民主改革,扫除卫生厅的政治痼疾,但是改革难以推进、民主改革难以取得实际效果,他发现现实中存在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即使自己有改革的想法也难以在下属中推行,个人的力量无法影响社会发展的世俗化潮流。
3.《活着之上》:象牙塔内知识分子的心灵挣扎
《活着之上》通过聂致远展示了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是坚守还是迷失的内心困惑,写出了知识分子在高扬欲望的旗帜还是传承知识分子精神之间心灵的挣扎。
中国8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随着与外部社会断裂的加剧,知识分子逐步退缩到大学象牙塔内。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在知识体制专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内部的断裂与瓦解。严格的学术规范、专业的成果评估、制度化的考核体系、企业化的管理模式使学院知识分子逐步放弃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立场。“这种学院化的专业趋势,形成了知识分子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断裂。”[5]正如闫真所言:“3年前我写《活着之上》的时候,我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这样一种世俗化还在进一步发展,一定程度上,它成为一种既定的文化格局”[6]。
《活着之上》被有些评论家称为集中反映了“儒林困境”,其实,它的背后反映出文化资本是如何影响和改变知识分子的身份认识与价值取向的。文化资本的直观表现形式是文凭和知识。在市场经济的巨型话语下展开,蒙天舒认为学习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与功利性,知识文化资本参与社会资本运行,知识文化成为功利主义的工具,因而他认为“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干什么都要知识做底子,不然省里那些大人物还跑来读博士干什么?”[7]112聂致远的博士室友郁明也深刻地认识到在知识经济时代,最要紧的是把知识变成生产力,读了博士可以提升在古玩字画钱币鉴定圈子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收入水平。蒙天舒从成绩平平的学生到教授、处干甚至校级领导候选人的转变深刻地反映出文化资本对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蒙天舒是那种有人罩着的人,那就是他的导师童校长。童校长全面安排他的前程,发表文章,申报项目,评各种奖项以至安排职位等等,都帮得上忙。童校长是副校长,活动能力超强,手里资源多。”[7]150蒙天舒也印证了“日丹诺夫规律”:“文化生产者在他的特定领域里越是没有作为,越是没有名气,他就越加需要外界的权力,也就越热衷于寻求外界的权力以抬高自己在本领域的身价”[8]。
布尔迪厄敏锐地注意到,在当今这个知识专业化的学院形态中,知识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已经被权力与金钱深入地控制了。文化资本成了知识专业化的学院形态中的硬通货。聂致远第一次考博士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徐教授招的博士竟是麓城大学副校长的老婆,其背后的原因是徐教授的女儿高考补录进了麓城大学,博士招生的结果其实在事先就已经确定了。在这里,博导招生权力与校长的行政权力进行了有效的交换。作者指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各个单位的重点学科,一般都在校长院长的那个专业,反映出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使得学院带有浓厚的“官本位”色彩,也促使权力对学术的影响生成,从而影响知识分子的价值观。
在小说中,作者重点塑造了在知识体制的专业化进程中既要遵循体制运行的规则,又希望在内心尽量保留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聂致远形象。聂致远是生活在大学校园的知识分子,他既面对世俗生活的繁琐,也要面对发表文章、评选优秀论文、申请课题、申请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知识体制专业化的事情。在聂致远身上,时常发生着精神的博弈。工作中,他既不得不面对行政领导的干预,在学生管理、个人职业发展中受潜在行政力量的左右,又想回避行政权力的影响,坚守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道德底线。生活中,他既不得不面对社会世俗化的影响,在解决妻子教师编制、自己找工作的过程中找关系、套近乎,又想坚持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人格底线,不做出违背良心与知识分子尊严的举动。精神追求上,他既想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怀有清风傲骨、不沾染世俗污迹,但又不得不经历世俗社会的考验、偶尔游离于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聂致远在象牙塔内经历着心灵的挣扎:对知识分子人格是坚守还是放弃、对知识分子价值是复活还是放逐,因而不断地产生身份的焦虑与价值选择的困惑。
二、阎真知识分子系列小说的创作思想嬗变
1.《曾在天涯》:现代主义意识下知识分子理想的放逐
在《曾在天涯》中,阎真从空间上设置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孤岛,让他们与外部社会发生第一次断裂,写出了高力伟的孤独感、虚无感和生活的荒谬感,放逐知识分子的理想,逐步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的身份,难以表现对社会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和社会参与意识缺失,并通过高力伟荒诞的加国之旅、悲凉的价值选择、执着而微弱的希望表现其鲜明的现代主义意识。
高力伟的孤独感一方面体现在生存空间的改变而引起的生存危机与追求心灵自由的矛盾中内心痛苦的无可言说,另一方面来源于在东西文化的冲撞中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与对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的排斥而引起的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高力伟个人价值的真空、人生意义的虚无带来了心灵秩序危机和人生的虚无感。他受困于生存的危机,在体验了生命存在的真实可感之外已无暇顾及更多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价值,认为最富有生命质感的真实就是卑微琐屑渺小平庸的现实问题,正如小说中所说,“世界也变得简单了,就剩了眼前自己抓得到的那点点东西,别玩虚的!”[2]142他生活艰难、内心孤寂,以至于在西方经历了生活的磨砺后,最终认识到追求人生的理想不过是人生的幻想,平庸是生活的本质,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平庸的生命,因此在异国以经济价值为导向的社会环境中放逐了知识分子崇高的精神理想与人生意义。
在《曾在天涯》中,作者通过荒诞的情节也写出了人生的荒谬感。高力伟本为夫妻团聚的目的到加拿大,但与妻子价值观念的巨大矛盾最终导致他们离婚;本来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到了加拿大只能靠出卖体力为生;本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高力伟去加拿大也追求拿到绿卡,但他最后毅然放弃即将到手的绿卡。高力伟一生总是在等待,他总想承担什么,却总也没有什么让他承担。在这荒诞的背后正反映出高力伟找不到精神归宿和终极价值的痛苦与挣扎。
对精神漂泊、个人价值迷失的书写让高力伟继承了“零余者”的精神血脉,充实了20世纪以来海外留学生的“零余者”形象群体,阎真也通过高力伟的形象反映出他对知识分子困境的认识:在80年代末,金钱成为影响知识分子价值选择的重要因素,如何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横行的市场经济秩序下构建心灵的家园,摆脱社会生活中的“边缘人”和社会身份的边缘化问题,是当时知识分子面对的特殊问题。可贵的是,作者留下了最后的一丝希望,通过知识分子选择对传统(祖国)文化的回归寄托知识分子渺茫的希望。
2.《沧浪之水》:后现代主义意识下知识分子价值的解构
《沧浪之水》进一步强化了知识分子与外部的断裂,从社会体制和话语方式上让他们第二次与外部发生断裂,阎真通过社会话语环境、话语方式的转变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彻底解构了知识分子的意义与价值,形成鲜明的后现代主义意识。
阎真关注到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的影响逐步从精神理想的放逐深入到价值体系的解构。市场经济通过市民社会的兴起挤压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通过强大的市民话语权压缩精英话语空间,通过形成的个人话语方式瓦解知识分子的社会中心地位,通过权力符号的强化解构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了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同时又是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9]。
在《沧浪之水》中,作者关注到伴随市场经济而生的市民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市民话语的崛起,从话语环境上进一步解构了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池大为的妻子董柳是一个中专学历的护士,她专注于过自己的日子,没有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因为帮厅长的孙女打针以解厅长燃眉之急而与马厅长夫人沈姨的关系逐步亲密,进而深刻影响了池大为的工作、身份和价值取向。和董柳一样,屈文琴、孟晓敏、尹玉娥、凌若云、宋娜、沈姨形成了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胜过一切精神追求,她们热衷于助力丈夫追求功名利禄以求夫贵妻荣,她们乐于享受权利带来的快乐而无视民生疾苦,她们也构成了与知识分子相对的庸俗的社会群体。池大为的妹夫任志强虽是一个专科生,但是他深谙市场经济的规律,从银行贷款“空手套白狼”做贸易,鼓动中间商收购股票做老鼠仓赚取暴利,处处显示出“牛皮客”的精明与老道。还有媚上欺下的丁小槐、见风使舵的小蔡,这些人物都是作者笔下的“猪人”和“狗人”,他们共同形成了市民社会,处处影响着池大为的价值判断,并逐步形成了占据主流的市民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使社会的风向标偏离了精英话语,并最终占领了社会的主流话语权。
话语方式的改变也成为池大为思想转变的重要条件。个人生存时代的到来虽然彰显了个人的独立性,但同时也使知识分子群体不再处于社会的中心,不可避免地居于边缘化的地位。在个人生存的时代,“现在是从个人看世界的时代,世界对自己有意义那才是真实的意义。起点变了,世界翻转过来了,从世界看个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4]408刚工作时,池大为本觉得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承担对社会批评的良知和责任,因而在民主生活会上对厅里铺张浪费买轿车、开宾馆起草文件、厅长独享特权等事情昭示天下,却招来了领导的扬长而去、同事的附和批评、自己事业的再次受挫。个人化时代的独语方式改变了池大为的思想与认知,也逐步削弱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
《沧浪之水》中解构知识分子认知体系的核心要素是权力。阎真通过对权力的影响力与支配力的深入挖掘明确其在知识分子价值解构中的作用。池大为认识到权力是身份的识别码,权力的大小决定着影响力和支配力的大小。在卫生厅,因为公共权力异化为马厅长个人的权柄和护身符,所以马厅长的权力至高无上,既可以随意支配人事权,又可以随意支配经济大权。在池大为儿子入院事件中,就连丁小槐作为一名处级领导的权力价值和意义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者也写出了权力的等级森严。例如,在抗洪一线,卫生厅神气的马厅长在牛省长面前也要表现唯唯诺诺,而牛省长在副总理面前都毕恭毕敬。
因此,当池大为身居高位、掌握大权后,他更充分运用权力。他运用权力调整人事关系,为因得罪马厅长而职称迟迟未解决的三十多人特事特办解决了职称问题,博得人心,扫清政治障碍。他安排重新审计厅里的财务情况,暴露前任领导执政期间的经济漏洞,扫除经济障碍。他统领全局工作,并把权力资本隐秘地转化为经济资本,通过运作安泰药业股票上市、重组,审批项目等方式赚取了丰厚的经济资本。权力成为一只无形的手,掌控池大为的行为与心理,调控他的价值取向与意义追求。
3.《活着之上》:带有启蒙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坚守
在阎真看来,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强烈的人格意识和责任意识,向内坚守自我的人格尊严,向外对社会负责,关注天下胜过计较个人得失。阎真关注到市场经济环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知识分子精神的自我放逐。但在《活着之上》中,作者通过聂致远的价值选择试图阐释他的思想的转变:不可能用精神价值的名义彻底否定物质化功利追求的合理性,同时,在物质化的社会环境中也需要珍视精神的力量,给知识分子精神价值一定的栖息空间。他试图以启蒙者的姿态建构一个与市场经济时代相适应的知识分子精神体系。
作为大学校园里的知识分子,聂致远坚守着知识分子的人格意识和责任意识,他不愿意以生存的理由放弃对知识分子理想的坚守,他认为“知识分子不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价值”[7]133。在行动中,面对求学、求职、职业发展中的失望与无奈时他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底线,试图找回知识分子的个体独立性。他坚守职业道德:对关系户学生范晓敏的成绩在领导的高压下最后给出了86分,不高不低,是不想给其他同学很大的伤害,也不丧失作为老师的道德底线;拒绝师兄张维以五万块钱做交易,帮助他完成科研项目,他认为学问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体现,如果拿学问做交易的话,辱没了学问,也辱没了自己的职业。他保留着理想主义情结:几次考博终获得成功,这让自己坚信只要努力,把志趣和职业糅合在一起的前景是有的;鼓励学生树立专业信念,试图说服学生保有精神追求和职业自尊,“在市场经济的巨型话语下,应该为精神价值保留一席之地,我们又是知识分子,不能把现世的自我绝对化”[7]140。他坚守人格尊严:在知识经济时代,不为金钱所动,拒绝为东北有“满洲制铁”历史的钢厂老板写传记;虽然阻力重重,但凭自己的科研实力得到了职称的晋升。他还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主动提出为贫困生捐款,全力帮助院图书管理员李灿云申请编制,理直气壮地帮助优秀学生贺小佳找工作,对学校采购固定资产吃回扣、浪费国家资源深恶痛绝等。聂致远虽然面对各种现实的问题与挑战,经常行走于坚持与放弃的边缘,尤其在他了解社会的潜规则时仍能坚守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没有触及知识分子道德的底线,坚守着启蒙的精神立场,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尊严,这也是作家给予当下知识分子的一个希望,有一抹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色彩,体现出市场经济的巨型话语下精神价值与物质现实之间的强大张力。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小说中带有启蒙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尽管存在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引导着的社会价值选择,但是也有拒绝与世俗社会妥协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形成新的精神圣地。小说中,曹雪芹、孔子、屈原、陶渊明等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标杆,他们坚持知识分子的理想,反功利、追求心灵自由。追寻曹雪芹生活遗迹的赵教授前后7次探寻门头村,目的就是为了让他鲜活起来,见证曹雪芹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他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探求者,也是理想主义的坚守者。辽宁大学的教授不唯利是图,没有为了孟老板的经济诱惑放弃知识分子的人格底线去美化东北有“满洲制铁”历史的钢厂老板的家族史。虽然学术圈存在知识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已经被权力与金钱深入地控制的现象,但是权威刊物的主编周一凡却对蒙天舒的文章赞赏有加,免收版面费就把文章发表了。虽然蒙天舒从成绩平平的学生到教授、处干甚至校级领导候选人的转变深刻地反映出文化资本对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但聂致远依然能够凭借自己扎实的科研成果取得职称的晋升,这也显示教授评审的相对公平性,教授也有坚持知识分子原则与底线的节操,反映出知识分子生存的“儒林困境”的相对纯洁。
阎真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持续关注贯穿80年代至今的近四十年光阴,反映出知识分子生存的社会语境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逐步缩小,从社会生存空间直至退缩至大学象牙塔。金钱、权力及文化资本是带来知识分子价值失落、人格退化的重要因素,是构成当前知识分子消解个人价值与意义的诱因。阎真在创作谈中提到“《沧浪之水》表现的是信念坚守的艰难和不可能性,表现现实对人的强制性同化和负面改造”,而《活着之上》“同样写信念坚守的艰难,但坚守是可能的”[10],他对知识分子的创作心态也经历了从放逐知识分子理想到解构知识分子价值,又回归到坚守知识分子身份的启蒙主义思想的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