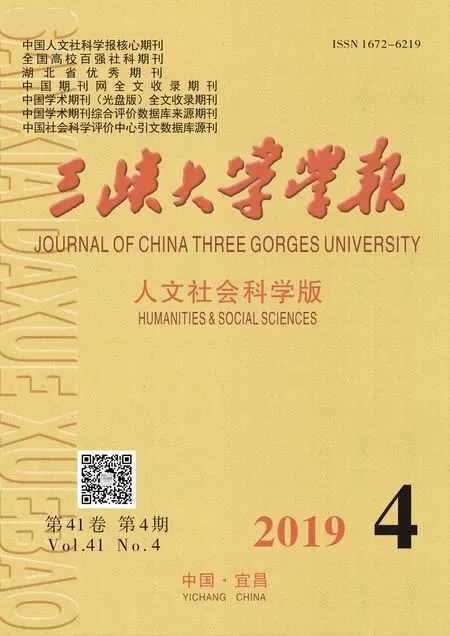电影《我不是贼》的叙事策略分析
郑丹丹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2014年由恩施导演吴钦拍摄的国产小成本电影《我不是贼》,是致敬2006年宁浩导演的电影《疯狂的石头》的诚意之作,影片借鉴了宁浩导演的叙事手法和诙谐幽默和荒诞的艺术风格,也在叙事结构、镜头语言和叙事伦理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独特追求。
一、叙事结构
电影叙事结构是“按照特定的规律而建构的,具有整体性质和转换与调节功能的事物的组织方式和表达方式”[1],是指电影讲述故事、思考故事的方式,简而言之,就是导演对作品素材整合的手法。《我不是贼》打破了时空对叙事的限制,采用非线性叙事结构,以多线索叙事、时空交错、大团圆结局等方式将影片中不同时空、各色人物和诸多事件进行有机组合,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1.多线索叙事
电影运用了多线索叙事方式,巧妙地设置了三组人物:金凤冠的仿造者——彭季恩、胡立军;金凤冠的偷窃者——欧文、鲁思思;路过彭家寨的农民工——牛西振、范刚。导演围绕一个价值连城的“金凤冠”,利用巧合和冲突将三组人物和事件串联起来,在这个三维空间中由三个利益团体延伸出多个故事线。
作为陈列在恩施博物馆的历史文物,金凤冠本来与这三组人物都不相干,但因为报道出金凤冠原本是一对,现还有一件文物埋藏在地下等待被发掘,于是另一件金凤冠的下落和出土成为关键。欧文是国际知名的盗贼,为了寻找金凤冠的下落,来到恩施彭家寨。工头牛西振代表打工者拿到工程款项,为了尽早发放工资让农民工们安心回家过年,取道彭家寨。彭家寨土家兄弟彭季恩、胡立军在家乡经营一家副食店,由于寨子外来者稀少,生意萧条,想到利用仿造金凤冠吸引众人关注,以此带动小卖铺经济。三组利益集团因为不同的缘由聚集到同一个地方,然后三组人物按照各自故事线平行推进剧情的发展,不同人物的跨时空拼贴,使每个利益团体在寻找(假)金凤冠的过程中完成各自的故事,也构成了整个电影的叙事内容。
2.平行交叉模式
众多人物故事平行推进,盗窃团伙寻找金凤冠、土家兄弟制作埋葬假金凤冠以及农民工寻找丢失的手提箱平行叙述,三个互不干扰的故事交叉进行,打乱各自的叙事线。
首先,影片设置了两个重要的物件将三组人物两两串联在一起,来结构人物关系。一个是仿造的金凤冠,它构成了整部作品的矛盾冲突。彭家寨兄弟两人偷偷仿造金凤冠并埋在祖坟中,让盗贼欧文以为此金凤冠便是雇主要寻找的宝物,而欧文探寻金凤冠的行为又让农民工以为他们要偷埋被盗走的结款工资。可以说整部影片中不同的三组人物因为一个假的金凤冠而交叉在一起。另一个是一模一样的手提箱,它是推动情节进展和增添喜剧色彩的关键。农民工携带工资的密码箱和盗窃团伙的作案工具提箱一模一样,一样的箱子让毫不相干的两伙人产生了交集,农民工误以为盗窃团伙偷去了他们的工资提箱,一路追随试图偷回提箱,欧文在发现工具箱被另一伙人偷走后自认为农民工和他们是同行要寻找金凤冠,瓜分胜利的果实,彼此之间的误会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其次,导演通过蒙太奇的剪辑方法制造巧合,将人物或两两交汇,或进行总交叉。影片两两交汇的场景较多,主要集中在盗贼与土家兄弟的相遇和盗贼与农民工的碰面,其中有一幕是欧文去小卖铺装定位系统时农民工在屋顶偷欧文的密码箱,两方人物的行动不时交叉进行,镜头在平行空间内的不同场景间转换跳跃,将同一时间段不同团体的行为戏剧性地呈现。至于三组人物总交叉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篝火晚会上,农民工偷走了盗贼的提箱,盗贼以为对方是同行,农民工以为对方把钱藏了起来,互相猜忌,互相斗狠,小卖铺两兄弟则是在一旁看两队人较真。另一次就是故事的结尾,盗贼和农民工同时在挖坟墓里的金凤冠,小卖铺兄弟前去阻止,众人打成一团,最终被警察一举抓获。
所有的主线故事都被导演巧妙地串联着,在紧密并行的节奏中推进影片的铺叙编排,乍看纷繁杂乱,实则逻辑线清晰,观众可从众多伏笔和冲突中把握故事的发展方向。
3.“大团圆”结局
“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结局模式,这一点特别符合中国人的美学原则和美学价值,体现了人们对美对善的追求,具有较浓厚的理想色彩。这部影片导演也专门设置了一个理想化的“大团圆”结局。当众人在土家兄弟的祖坟前纠缠在一起时,放牛的“傻子”偷偷叫来了警察,警察及时赶到,一群人被当场抓住,盗窃团伙被警察带走;农民工成为捕获盗贼的重要人物,结束之后农民工被土家族人热情地送到火车站,并附赠土家特产和玉碗,至于被骗的结算工资,导演也安排工程老板通过银行卡转账给工头,农民工可以拿到工资安心回老家过年了;彭家寨也因为赠送的玉碗被发现,成为文物出土地被大肆宣传,村寨乘机大力发展旅游业,土家兄弟的小卖铺生意也越做越兴隆。这些都符合了中国人所说的好人终是有好报的观念,“大团圆结局的出现是正文原则的体现和伦理信念的表达”[2],也符合观众的审美趣味。
这部电影的结局处理采用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团圆”模式,既为喜剧增添了圆满,又没有弱化影片的讽刺效果。一方面,导演设计了一心想通过仿造金凤冠获得关注度的土家兄弟,他们不知道放在家中最不起眼的破碗就是价值连城的宝物,荒诞地进行着他们自己的所谓“事业”,最终被警察一举抓获,“破碗”也当作赠礼送给农民工,影片的结局就是对这类人物最好的讽刺,他们并不是坏人,但缺乏对道德和法律的认识,他们本来是仿制文物的人,却巧合地成为抓捕盗贼的英雄,以此种荒诞的手法讽刺了那些追逐利益而做无用功的人们。另一方面,农民工终于找回自己的提箱却发现里面装的都是纸钱,这也意味着他们在外打工一年几乎白干了,最后导演戏剧化地设计农民工收到短信得知工资已打至银行卡来满足观众对这类人物的同情,也包含了导演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农民工辛苦地为城市的建设奉献血和汗,而无良的商人却狠心拖欠工程款,他们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喜剧结局的背后揭示的是人性的本质和悲伤的现实。
二、镜头语言
影片除了在叙事结构上极具特色外,在镜头的表现力、剪辑技术方面也深受宁浩导演的影响,特别是特写镜头的运用。吴钦导演在灵活运用镜头和色彩的基础上,还加入动漫元素,丰富了电影的表达方式。
1.多变的镜头
电影拍摄过程中远、近镜头的交叉使用能让镜头画面流畅多变,远景、中景、近景的场面调度,镜头的切换,使镜头对影片的故事讲述、情感表达都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3]。如影片中牛西振在吊脚楼上看到远处欧文手里提着和自己相同的提箱,镜头从远处的箱子移动到牛西振兴奋激动的面部特写,还有像牛西振趁着夜黑风高在屋顶用钩绳偷欧文的提箱时,镜头在箱子与其面部表情之间来回切换,让画面充斥了紧张和兴奋的氛围。特写镜头的运用,能刻画出人物内心的细腻情感变化,提供给观众更多的细节信息。除了运用镜头交替的方式之外,影片还利用画面的停顿和静止让观众将情绪带入到作品情景中来,使观众更好感受画面的内涵。盗贼欧文到小卖铺房顶安装定位装置后,在返回住处的路上被牛追赶遇上抱着手提箱的牛西振和范刚,在人物相遇之时,画面突然静止数秒,随后画面又恢复正常表达,欧文与两人错身经过,在镜头的捕捉上给人以较强的视觉冲突,并制造三人在夜晚巧合相遇的桥段来推进情节发展:农民工成功的偷走了欧文的工具箱偷偷摸摸地准备逃跑,却被从小卖铺返回的欧文遇见,但欧文并不知道他们手中的箱子就是自己的,这为接下来欧文发现箱子被盗,错认农民工是盗窃同行埋下伏笔。
另外,导演还从多个视点对故事情节进行讲述,在欧文与牛西振、范刚三人在夜晚相遇被牛追赶时,镜头开始以旁观者的角度看三人与牛的搏斗,随后切换到牛的视角,画面调亮并随着牛的运动抖动,让镜头由旁观者转向打斗的参与者,使影片带有疯狂的味道。而牛追赶夜晚做坏事的三人,这也暗示了故事结局——放牛的人发现盗窃团伙的不法行为,报警抓捕了盗贼们。
正所谓,电影由镜头和剪辑组成,导演的拍摄技术和蒙太奇技巧的运用,巧妙地、艺术地将复杂的人物关系组合在一起,增强视觉节奏,使整部作品结构顺畅,生动鲜明。
2.动漫的应用
电影中糅合动漫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电影新的维度,“动漫艺术夸张变形的表达形式、诙谐幽默和荒诞不经的艺术效果与喜剧电影的结合,连接了虚构与现实,也契合了电影的喜剧目的。”[4]电影《我不是贼》中既有动画又有漫画,运用到电影的构图之中,形成独特的视觉形象。电影片头就呈现出静态的漫画元素,将三组人物的特写镜头漫画化并放置在三个漫画框之中,随之用一段文字说明进行总结,有效区分了三个不同利益团体的身份及其聚集在彭家寨的目的。另外,影片中多次出现动画人物对真人行为的模仿,欧文和工头牛西振、范刚三人被牛追赶,导演采用动画方式模拟牛追赶他们并用牛角顶飞人的画面;影片最后众人打作一团,也采用了动画模拟真人的方式夸张地展示出人物纠缠打斗的动作行为。动画与漫画的融入,丰富了电影的表达,以动静结合的方式对画面的处理做到有的放矢,不仅突破了电影表现艺术的局限,更给观众带来十足的新鲜感,使电影画面以动漫式的夸张变形抓住观众的心。
3.光影与色彩的营造
光影和色彩的营造是电影重要的视觉语言,“在某些电影中,色彩/影调可以成为一部影片总体造型基调之一,也可以成为影片的意义结构的主要依托。”[5]电影《我不是贼》十分注重自然光的运用,尽量少使用人造光,自然光线使画面色彩更具有真实感和朴素美。影片利用大自然及人物生活环境中的各种光线,如晴朗时明媚的太阳光、阴雨天时灰蒙蒙的天空、夜晚的自然月色,日常生活中的电灯、灯笼、火把燃烧的亮光都是构成这部电影色彩的光源。色彩作为一种电影叙事语言,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也是情感上的。
“光的阴暗就带有象征性的意义”[6]。《我不是贼》的色彩艺术不仅给观众鲜明的视觉对比,也暗含了导演的思想和情感。作品以冷暖色调交叉进行拍摄,偷窃和仿造的戏份是冷色调的画面,无论白天或黑夜,人物在进行不法行为时,所呈现的画面往往是阴沉沉的,人物在冷色调的环境下的行动和脸部特写都清晰可见,昏暗的色彩则映射了人性的灰暗,冷色调让观众形成神秘和冷静的观影情绪。影片中彭家寨的魅力风光、淳朴村民的画面则以暖色调来处理,以红色为基调,红色的灯笼、暖黄的电灯以及篝火的红光,代表了热情和激情,衬托出了土家人的热情好客和人物内心的激情澎湃。
三、叙事伦理
喜剧电影的拍摄,固然是要带给观众欢笑,但只有融入思想内涵的影片才能称为成功的喜剧电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不是贼》在叙事方式上运用多种手法,使得结构、语言与叙事内容完美搭配,这种形象化、有意味的叙事形式也表达出了电影导演的叙事伦理,即采用反讽的方式,关注小人物的生存,描写土家风情,站在底层的立场上隐晦曲折地表达他的思考和价值观念。
1.小人物的真实写照
在传统的电影中,社会底层总是弱势,关注最多的是社会精英,带有浓厚的英雄色彩,《我不是贼》致敬《疯狂的石头》的重要方式就是将底层作为表现对象,通过荒诞的故事折射出底层小人物的物质匮乏和精神缺陷。电影《我不是贼》设置的小人物角色有农民个体户,有在外拼搏的农民工,有盗窃团伙,还有彭家寨乡民。影片中人物的“小”体现出强烈的真实感,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现实社会几乎一致,正因为对真实人物的展现,能够使观众产生共鸣,在观影中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这些小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对生活的映射,也是对普通人的认可和展现。导演以平民的视角讲述故事,代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发声,发掘小人物身上的笑点和泪点,关注他们真实的生活,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基础,也是社会和观众接受的前提。
2.以反讽艺术表达对人性与现实的思考
电影将反讽发挥到极致,用反讽的手段让观众在笑声中认识自我,看清我们生存的社会现实。一是在人物造型上进行反讽,导演在设计人物时进行了艺术加工,将国际盗贼欧文塑造成一个既傲娇又少女心的笨贼,他对自己的盗窃技术很自信,无论是探听消息还是安装窃听器都游刃有余,在密码箱被盗后自以为洞察了事情的缘由,认为农民工是盗窃同行,甚至在面对农民工晒在屋内的袜子,认为是高科技的防护,但同时他也是个喜欢海绵宝宝,害怕牛的傲娇男,笨贼的形象让人物性格和行为充满笑点。二是在情节安排上进行反讽,三组人物都有各自的反讽点,土家兄弟仿造金凤冠却不知自己看不上的玉碗是珍宝,农民工不是盗贼却被逼无奈做了偷窃的行为,而盗贼是贼却始终没有偷窃反而被抓,这种反常规的桥段设置,让人物在荒诞滑稽中进行人性的较量和考验。当然,由故事人物和情节传达出的导演对现实社会现象的反思,才是其反讽艺术的重要部分,电影对农村艰难的转型中农民法律知识的欠缺、农民工权益保障不到位的讽刺,对小人物优点和弱点的揭示,都触及当下社会的痛点,导演将它们拆解为影片的笑点,让观众在笑声中认识现实的复杂、残酷与无奈。
3.以本土元素张扬地方文化特色
吴钦导演是湖北恩施土家族人,电影将故事发生地选择在恩施宣恩县彭家寨,不可避免地在创作中涉及到本土特色,环境、民风民俗、语言以及服饰等方面都有机地融入到作品中。影片中大量使用地方方言,彭家寨乡民以及小卖铺兄弟交流对话使用方言,与盗窃团伙和农民工作为外来者形象在语言上形成鲜明对比,本土方言的使用不仅是导演追求细节真实的表现,也让观众有身份认同感,感觉到亲切、自然。电影中不同语言的交流使乡土气息更加浓郁,“一部影片如果在声音上有机地采用了方言,那么方言——这种乡土文化的无形载体,便能够有效地为作品追加、弥补、凸显镜头所无法企及的地域风情与生活质感。”[7]除了语言的本土化,空间领域也融入了民族特色,有土家吊脚楼,有土家风俗摔碗酒,有珍稀树种水杉,还有原生态歌舞龙船调、八宝铜铃舞、摆手舞以及篝火晚会,民风民俗尽可能地在影片的细节中展现,并配以文字说明向观众进行介绍。电影空间是表现现实空间最好的方式之一,将本土元素纳入影片中是追求艺术真实、渲染喜剧气氛以及张扬地方文化的有效途径。
电影《我不是贼》成功学习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一方面以轻松娱乐的氛围让观众对故事感到熟悉和亲切,使电影张弛有度,另一方面又以荒诞的手法反映现实,朴实而不失幽默,是一部能让观众在欢笑中思考现实的优秀电影。